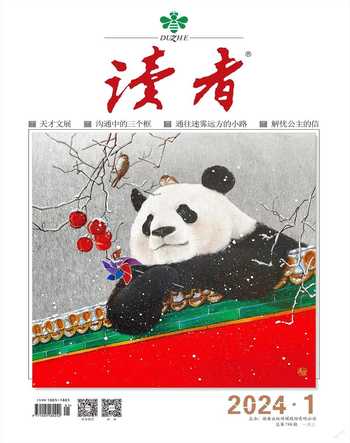宇宙的水手
七堇年

“流风回雪……”我轻声地自言自语,小伊没有听清。
“什么?”
“古人所说的‘流风回雪’,原来是这样的。”
这是4月的一个深夜,山路一片黑暗。我恍惚觉得自己已经被一头蓝鲸吞食了,正窒息地盘错爬行在它的肠道内,秉烛摸索出路。
车灯扫去,风挡玻璃前是一簇簇扑面而来的风雪,正在组成一种神秘的文字,汹涌地朝我倾诉着什么。我恍如身处一场永不天明的葬礼,冥纸铺天盖地;又宛如在深海潜水时,突然闯入了一团杰克鱼风暴——大量银色细小的鲹科鱼将你完全包裹,紧紧缠绕你的轮廓,如此切近,又变换迅捷,鱼和人仅有一寸之隔,但你休想触到任何一枚鳞片。
那情景令人想起华裔作家特德·姜的小说《你一生的故事》中,外星种族七肢桶使用的一种非线性语言。如果它们也有小说,那就不是一个字一个字或一行一行地写成的,也不是一个字一个字或一行一行读完的,而是一幅巨图,像一个层次丰富的汉堡包,一口咬下,每个横截面的味道都在其中了。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降临》,在一个七肢桶与人类对话的场景里,它们的语言,像一幅幅喷洒墨汁画出的画,或罗夏墨迹测验——那图景扩大亿万倍,就恰如我此刻眼前所见。
眼前大雪如涛,我感觉自己像置身暴风雨中的水手,徒劳地掌着舵,心里清楚,一切只能仰赖上天的仁慈了——在这样偏远的无依之地,深夜大雪,结冰后的路面一片银白,碾上去发出某种咬牙切齿般的声响,如同死神就静静地坐在我们旁边,不紧不慢地磨着刀。
路旁立着限速数值极低的警示牌,上面写着:“医院很远,生命很贵。”
小伊一直沉默着,整个人身体前倾,警觉地凝视着前方的虚空与黑暗,好像那深处藏着什么怪兽,一不留神就要从黑暗中猛然蹿出,扑向我们。
一种诡异的感觉笼罩了我。“你有没有发现……”我的声音颤抖起来,“一种错觉,我们是静止的……”
“……真的……还以为是我的幻觉,原来你也这么觉得……”她的声音比我的更轻。
我确信车正在缓慢行驶,同时又怀疑自己没有前进——雪花迎面扑来,抵消了我们的速度,创造出一种相对静止的运动状态,令人恍惚中觉得自己坐在一艘失去动力的飞船中,正迎着纷飞的星尘,悬停,静止,滑向真空的黑暗。
“现在,我们是宇宙的水手。”
那夜恰是小伊30岁生日的前夕。这场雪几乎就是为我们而上演的——不是“下雪”,而是“上演”。就在我们沉迷于眼前的危险与壮观之时,一辆大货车停在前面,似乎被堵住了。迫于不好的预感,我停车,打算下去询问出了什么事。
“前面有辆大卡车好像没绑防滑链,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停着,走不了了。”旁边一辆大货车的司机说。
“完了,”我回到车上,苦笑着告诉小伊,“我们可能要在车上过夜了。”
她伸了个懒腰,神情很放松。一路经历了太多不确定的事,我们的心态越发松弛,时常自我调侃:“习惯了被命运霸凌的人,暗暗计算着,第二只拖鞋什么时候砸下来。”
深夜12点,前方没有一丝挪动的迹象。
我打开车载音乐播放器,搜索以“生日快乐”为主题的歌,一首接一首地往下放。听到金玟岐的那首《生日快乐》中出现“烟花”一词,小伊说:“要是现在能放烟花就好了!”
“我真带了。”在小伊惊讶的表情中,我径直下了车,“走,放烟花。”
“砰”的一声,雪地被染成了红色。“砰”——金色,“砰”——绿色。我们的笑容绽开,笑声洒在雪地上,如同山影在水中轻轻颤抖。火光熄灭后,黑暗恢复浓郁,不知不觉间,雪已经停了。
想到30岁,诗人多多的那首《它们》就跳了出来。这首诗是多多用来纪念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写于1993年。后面的几句是:
是航行,让大海变为灰色
像伦敦,一把撑开的黑伞
在你的死亡里存留着
是雪花,盲文,一些数字
但不会是回忆
让孤独,转变为召唤
让最孤独的彻夜搬动桌椅
让他们用吸尘器
把你留在人间的气味
全部吸光,已满三十年了
1963年2月11日,31岁的西尔维娅·普拉斯在凌晨时分,走进厨房,关紧门窗,并且在门缝下面塞上湿毛巾——为了不殃及在卧室里沉睡的孩子。接着,她打开煤气自尽,就此变成天上的星星。
不知她站在厨房的最后一刻,看见的是什么?如果当时她的窗外有一场烟花,她会不会被那些光芒挽留?就像阿巴斯的名作《樱桃的滋味》里那个标本制作师,年轻时也曾想一了百了,把自己吊死在树上,结果却因此发现了树上甜美的樱桃。他尝了一个,又一个,好吃极了……直到太阳照常升起,世界变得明亮、翠绿。于是,他从树上下来,把地上的樱桃都捡起来,带回家和妻子儿女一起分享。
生活的低谷,也许酷似一场深夜大雪里的堵车。但再令人绝望的拥堵,也总有疏散的时刻。只是需要多一些耐心。
车龙彻底流动起来了。
在做好最悲观的准备之后,一切就再也不会比意料之中的更坏了。我有种被判流刑,又突然被赦免的庆幸。
(碧 鄣摘自新星出版社《横断浪途》一书,本刊节选,刘 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