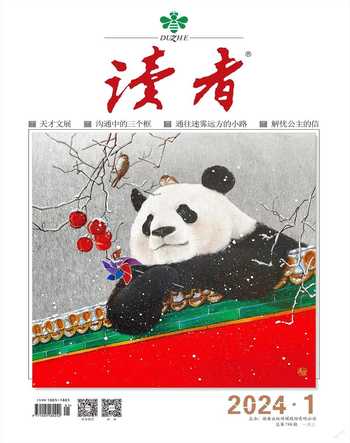二次捐献
金圣榆 丑故事

2012年4月,我在中南大学读大二。一天上午11点,我和同学背着书包,往食堂的方向走去。食堂门口停着一辆长沙血液中心的献血车。我就读的是医学院,献血车隔三岔五就会停在食堂门口。
我和同学说:“反正我们也没啥事,去献血吧。”上了献血车,我和同学各献了400毫升全血。
献完血,护士问我们,要不要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中华骨髓库)?
我正在考虑的时候,我的同学说:“没问题。”看到同学答应了,我也不好意思拒绝。
护士拿出两份表,让我们填写基本信息。她说,希望我们留在信息表上的电话号码能长期保留。
填完表,护士又各抽了我们10毫升血。
2013年春天,一天傍晚,我在寝室休息,手机响了。
打来电话的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她说:“你的入库血样HLA(人类白细胞抗原)数据和一名患者初配成功,你是否愿意捐献,挽救他人的生命?”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下意识地回了一句:“可以的。”
她说:“好的,如果后面有需要,我们会再联系你的。”
2014年,我读大四,正在湖南益阳的一家医院实习。有一天,我接到电话,工作人员说又有患者的HLA跟我的初配成功了,问我是否愿意捐献?
我回答:“愿意。”
接着,我多问了一句:“上一次我接到过这样的电话,可后来再没有消息了,这是怎么回事?”
工作人员告诉我,如果没有消息,说明患者“不需要”了。
电话挂了。过了几个月,依旧没消息。我猜想,也许对方没有等到移植的机会,病情恶化了。
对我来说,只是接了两个电话,但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很可能两条生命垂危了。没帮到他们,我感觉挺遗憾的。
2020年9月,我在杭州萧山一家医院的神经外科当住院医师。
回杭州以后,我一直保留着湖南的手机号码,想着有一天能再接到配型成功的电话。
2021年11月的一天,我接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有患者的HLA与您的初配成功,您是否愿意捐献?”
我的回答还是:“愿意。”
几天后,高分辨率配型通过。2021年12月10日,我在自己单位做体检。
杭州市萧山区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来了,陪着我。她叫小倪,是一个“90后”女生。
2021年的最后一天,小倪联系了我。她说,我的体检结果有一项指标比标准值低,出于对捐献者安全的考虑,要我再复查一次。如果指标还是过低,我就没法捐献了。
高分辨率配型都通过了,如果因为我身体的原因,最后没能捐献,那太可惜了。
为了能顺利捐献,我开始调整作息时间,加强锻炼。
2022年1月4日,我又做了一次复查。结果那项指标离标准值还是差了0.1。我不希望因为这0.1,让一个生命活下去的希望被浇灭。
我给小倪发消息:“我是医生,我的捐献意愿很强,哪怕前路未知,我也愿意试一试。希望你们能考虑我的想法。”
小倪说,她很感谢我,会帮我转达,但捐献者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在医学上,不会为了挽救一个人,去损害另一个人的健康。
6天之后,我在单位做了第三次复查。这一次,指标终于正常了。
萧山区红十字会通知我:可以捐献。捐献时间定在2022年1月24日,我将于1月20日入院。
2022年1月20日上午9点,我来到位于杭州市区的造血干细胞采集医院。
住进病房后,护士在我的胳膊上打了一针“动员剂”。
造血干细胞在外周血液中很少,需要通过注射动员剂,加速骨髓中造血干细胞的生成并释放到外周血中,才能进行采集。这种动员剂要连续打4天。
打完动员剂,我在房间里休息。房门开着,一位阿姨进来和我打招呼。
阿姨说,她的儿子住隔壁,患有白血病,需要加强营养。她想在中午和晚上借用一下我房间里的电炖锅,给孩子炖点儿排骨汤。
我说:“你随时可以来。”
上午11点,阿姨来做饭。我没什么事,就和她聊天。
阿姨说,她是单亲妈妈,好不容易供儿子上了大学,没想到孩子得了白血病。
说到这里,她有些哽咽。缓了缓,她继续说,她的儿子生病以后,心态挺消极的。病区里年轻人很少,我和她的儿子年龄差不多,她希望我能找他聊一聊。
下午,我见到了她的儿子。他叫小吴,脸黑黑的,有点儿浮肿,精神状态很不好。
我看到他的手机上播放的是游戏视频,就先和他聊游戏。他来劲了,和我讨论起打游戏的事,脸上的表情也放松了许多。
小吴说,他是学校乐队的成员,吉他弹得不错。
我鼓励他,要他弹一段。他回到病房,拿出吉他,弹了一首周杰伦的歌曲。
那几天,我每天都会去找小吴聊天,还加了彼此的微信。我和他约定,等他出院了,我再去看望他。
2022年1月24日上午8点,开始采集造血干细胞。
我平躺在床上,左右手臂上各扎着一根针。血液从一只手臂出来,经过血液分离机,提取出造血干细胞,剩下的血再从另一只手臂流回体内。
采集过程持续了4个小时,共采集了近270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
我成为浙江省第752例、萧山区第1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接下来,志愿者会把这袋“生命的种子”送到患者所在的医院。
捐献完,我感觉有些疲惫,回家休息了四五天,才恢复如初。
在这之后,我和小吴一直保持着联系。2022年4月初,我去看他。去他家之前,我买了一套乐高玩具。
见到小吴,我拿出给他买的礼物。他叹了一口气,说:“这辈子可能拼不完喽。”
我说:“你还年轻,别这么悲观,又不是没有希望了。我们医院有很多患者,情况比你的严重多了,他们都在积极治疗。你肯定会好起来的。”
他点了点头。
5月中旬,小吴跟我说,他很幸运,在中华骨髓库找到了合适配型的志愿者,马上要移植造血干细胞了。
2022年8月,小吴给我发了一条消息,说他恢复得不错,已经出院回家了。他还跟我说:“这种病都治好了,以后还有什么困难能阻碍我呢?”
他能这么想,我由衷地为他感到开心。
就在小吴出院后不久,我再次接到萧山区红十字会的电话,询问我是否愿意“二次捐献”。
这不是我希望听到的消息。出现这种情况,说明接收了我捐献的造血干细胞的那位患者,移植效果不太好。
不过,只要还有机会,我就愿意尝试。特别是小吴能回归正常生活,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相信远方的那个“他”,一定会好起来。
这次捐献的是淋巴细胞,不用提前打动员剂。我于2022年11月22日住院,准备第二天捐献。
11月23日上午,经过3个多小时的采集,我捐献了将近100毫升的淋巴细胞混悬液。
采集结束后,我除了有点疲惫,没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
医生和我说,愿意二次捐献的人很少,因为短期内身体会损失少量细胞,但不会有太大影响,一般一周左右便会恢复到正常水平。
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给了我一封患者写的感谢信。
我的捐献对象是一个孩子,信是他妈妈写的,字很漂亮。信上写道:
感谢给予我孩子二次生命的恩人。我是一位单亲妈妈,第一次移植那天,刚好是我孩子的生日。
现在,孩子的血型也变了,变得跟您一样,性格也比以前更成熟了。
孩子经常跟我聊生病后的感受,他说:“妈妈,等我病好了,我想见大哥哥,好好报答他。”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让我们碰到了。每次聊起这些,我和孩子都会流眼泪。
读完这封信,我非常感动。我意识到,当年入库的决定,不是简简单单填了一张表、抽了一管血,而是一份对生命的承诺。
我对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说:“如果有人需要帮助,即使需要第三次捐献,我也愿意。”
医生的使命,本来就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是一种方式,捐献造血干细胞是另一种方式。
但他们告诉我,每位志愿者只能给一位患者捐献,并且最多只能捐献两次。
我捐献完,休息了5天,就回医院上班了。
当我遇到小吴的母亲,看到她如此坚强地撑起家庭,照顾生病的孩子;看到捐献对象的母亲给我写的那封信,了解到她也是一个人照顾孩子时,我都会想起我的母亲。
妈妈不会放弃孩子,我们又怎能轻易放弃自己呢?
(海底飞花摘自微信公众号“丑故事”,本刊节选,沈 璐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