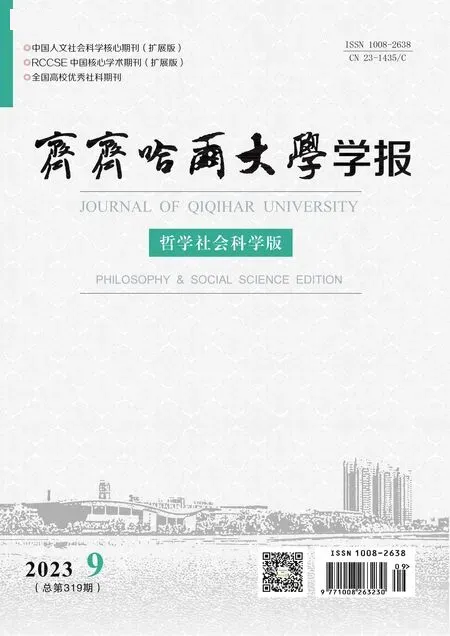1920年前后马克思主义在安徽的传播
刘 巍
(安徽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蚌埠 233041)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中共成立的思想基础。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策源地和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安徽是创建中共地方组织较早的省份之一。因此,对于中共安徽组织史的考察,不能忽略马克思主义在安徽的传播。目前所见,学术界已经对安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所关注。从成果形式上看,除了部分地方通史的相关章节以外,主要是省属高校的数篇硕士学位论文。但是,这些研究时间跨度较长,大多起于1917年的十月革命或1919年的五四运动,终于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结束。这些研究虽然从宏观上梳理了安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情况,但叙述较为笼统,将长时段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情况混为一谈,未能有效区分地方党组织建立前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差异性。实际上,在这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国内的政治格局和党派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造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巨大变化。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时段聚焦于1920年前后。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始于五四运动以后,终于中共安徽地方组织成立以前,以期为安徽地方党史研究的深入提供支持。
一、传播的主体:知识分子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一种外来的新思想不可能与本土文化传统完全契合,必然存在着若干抵触之处。若想在短期内获得大规模推广,不仅需要时局发生有利的变化,更需要积极主动的宣传和动员。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各种思潮在中国传播,仅仅是社会主义思想就有众多流派。这些思想在中国各有信众,彼此之间难分伯仲。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和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马克思主义在众多外来思潮中脱颖而出,开始受到瞩目。
知识分子是1920年前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以陈独秀(安徽怀宁人)为代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和《新青年》创办者,他以乡缘为纽带,聚集了一批思想进步的皖籍知识分子。以《新青年》第一卷为例,就包括高一涵(安徽六安人)、高语罕(安徽寿县人)、潘赞化(安徽桐城人)、刘文典(安徽合肥人)等,即使是外省人士谢无量(四川乐至人)和易白沙(湖南长沙人),也长期在安徽生活和工作。[1]同时,陈独秀作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也利用工作关系,带动和影响了一批有志青年。不过,新文化运动前期的陈独秀,虽然致力于旧文化的批判,但在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上还受到各种思想的干扰,没有设计出真正的方案。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被残酷的现实敲醒,最终抛弃了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真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在和陈独秀交往的皖籍知识分子中,许多人深受感召,后来积极回乡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他们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多以创办学校为切入点,通过师生之间的授课交往,形成并延伸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链条。以高语罕为例,1919年11月,他和刘希平(安徽六安人)在位于芜湖的徽州公学校址上创办第一商业夜校,招收各家商号的学徒入学。夜校国文课程使用的教材,就包括《新青年》等进步杂志上刊载的文章。同时,他自编上课讲义《白话书信》,向学生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为了争取更多青年入学,高语罕又先后创办了第二商业夜校和芜湖工读学校。在高语罕的引导下,许多学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不少人还在未来的革命事业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2]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者,也成为新的传播节点,继续影响他人。例如,薛卓汉就担任了职工学校的教员,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出了曹渊(安徽寿县人,黄埔一期毕业生,叶挺独立团第一营营长)等一批新的马克思主义者。[3]
在安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最为值得一提的就是恽代英(革命烈士,后被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作为武汉地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恽代英于1920年秋天来到安徽宣城,担任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执教期间,他严厉揭露和批判传统教育制度钳制思想的危害,大力推进教育改革,指导学生阅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等进步书刊,认真解答学生们遇到的疑难问题,许多学生受到他的影响,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李求实(“左联五烈士”之一)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授课之余,恽代英不仅努力撰写文章,还多次进行演讲,通过极富感染力的口头表达和肢体语言传播马克思主义,就连宣城四乡的农民也经常闻讯前来听他演说。1921年寒假,“芜湖学生联合会”和“安庆学生联合会”也邀请恽代英外出演讲。在这一过程中,恽代英还结交了许多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朋友,即便在他离开安徽以后,还和他们保持着密切联系。[4]
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思想的感召是潜移默化的。即使像刘文典这样早已不问政治的纯粹学者,也在有意无意之间庇护那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生,为他们的政治追求保驾护航。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之初,预科二年级学生王某某(江西瑞金人)被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发现系中共党员;在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刘文典立刻派人护送其离校,躲过了反动当局的拘捕。[5]随后,安庆共青团为了在安徽省立第一女中传播新思想,与反动军警发生冲突,从而酿成学潮。面对着蒋介石严惩学生领袖的命令,刘文典坚决予以抵制,以至于触怒蒋介石,被拘押和撤职。[6]
综合地看,在1920年前后,马克思主义在安徽的传播,离不开知识分子的积极推动,他们不仅是思想传播的发起者,也是执行者。以安徽人陈独秀为原点,带动了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安徽人,这些人又向更多的同乡进行宣传和动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尚未正式形成,因此有组织的思想传播路径尚未打通,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要依靠知识分子的信仰和热忱。换言之,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要体现了个人行为。他们利用学缘与地缘的资源进行宣传和动员,因而分布点极不均匀。安庆和芜湖作为交通要冲,风气相对开化,教育事业和商业经济比较发达,具有思想传播的便利性,上述优势使安庆成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活动场域,引领全省风气之先;但是,在广大农村地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就比较困难。所以,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安徽的接受者主要是在城市求学的青年学生。原因在于,他们不仅具有思想上的激进性;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与马克思主义者接触。另外,由于不存在稳定的组织经费,所以马克思主义者时常受到财力的限制,不得不分心于生计的考虑,以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时常中断。例如,恽代英从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辞职以后,本拟接受芜湖第五中学、第二女子师范和第二农业学校的授课邀请,但由于这些学校未能满足他的薪水要求,制约了他未来办学的计划,导致他不得不离开安徽前往上海。[7]
二、传播的载体:进步书刊
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以前,书籍报刊是思想传播的主要载体。与演讲和言说相比,书籍报刊的感染力虽然相对不足,但便于携带、传递和存世,对于思想的传播具有深远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思想,领会和接受并非易事,往往需要借助书刊进行反复地阅读和思考。在这种情况下,书籍和报刊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因此,考察1920年前后马克思主义在安徽的传播,必须重点关注进步书刊的传入与发行。
安庆和芜湖是1920年前后进步书刊的重要传播基地。五四运动以后,传入安庆的进步书刊包括《新青年》《新潮》《湘江评论》《每周评论》《新俄游记》《赤都新史》《唯物史观浅说》《共产党宣言》等。[8]在芜湖,由汪孟邹创办的科学图书社在进步书刊的经销方面功不可没。除了《新青年》以外,还经销《新潮》《每周评论》《新生活》《建设与改造》等刊物。科学图书社不仅经销与该店有联号关系的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新书,诸如泰东书局、中华书局、新青年出版社、北京晨报社、创造社、开明书店、生活书店等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译著也都有经销。包括《社会主义史》《各国社会主义思潮》《共产党宣言书》《共产党月刊》《近代经济思想史论》《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旅欧六周见闻记》在内的进步刊物能在芜湖流行,不能不归功于科学图书社的积极经销。当时,芜湖中学进步学生,几乎人手一本《新青年》。诸如蒋光慈、王稼祥、阿英、李克农、祖晨、薛卓汉、李慰农、陈原道、曹渊等进步青年,正是以此为起点,走上了革命道路。因此,当时流传出一句名谚:“要买新书,请到芜湖,要买新杂志,请到长街去。”胡适就比喻道,芜湖科学图书社给新文化“做了二十年的媒婆”。[9]
在安徽流传的诸多进步刊物中,《新青年》的传播尤为值得关注。原因在于,《新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发行量较大,不仅刊载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高水平文章,更是在1920年9月以后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因此,《新青年》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衡量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这一时期,凭借着汪孟邹、李辛白、蔡晓舟等进步皖人的积极努力,《新青年》安徽获得了广泛的传播,甚至连地处偏僻的霍山和金寨等县,都有《新青年》的传播痕迹。[10]
除了积极流传外省出版的进步刊物以外,一批安徽人也开始自办刊物,用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朱蕴山、蔡晓舟等人主办了《评议报》,蔡晓舟、王步文等主办了《黎明》《安庆学生》《洪水》《寸铁》和《安徽学生会周刊》,芜湖地区创办了《芜湖半月刊》《芜湖学生会周刊》,原芜湖《皖江口报》则开辟了《皖江新潮》副刊。同时,还有学生自办的油印小刊物,如五中的《实践》、二农的《海灯》等。1920年,黟县旅京学生舒耀宗、王同甲和欧阳道达三人还创办了以政治评论、科学知识及介绍当地民歌、民谣为内容的不定期刊物《古黟新语》。这一时期,滁县、全椒、凤阳、濉溪、萧县等地也先后诞生了许多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报刊,用以宣传科学、民主和新文化运动。[11]
在安徽人自办的诸多刊物中,高语罕编著的《白话书信》尤为值得关注。作为芜湖商业夜校的授课讲义,《白话书信》采用书信体的形式,论及了政治、经济、哲学、伦理、文教、社会与家庭等各个方面。该书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唯物史论、无产阶级专政)作了通俗浅显的介绍,还充分肯定和赞扬了俄国十月革命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及其苏维埃政权,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先河。《白话书信》也因此声名远播,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之后,深受读者喜爱,以至于多次再版,总共发行10万余册。[12]
在进步书刊的传入与发行方面,最为值得关注的人物是蔡晓舟(安徽合肥人)。在京期间,蔡晓舟任职于北京大学,深受陈独秀、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的感染。作为五四运动的亲历者,蔡晓舟深感“此次风潮鼓荡,实含转移社会、再造国家之势力,且于今后世界和平关系亦至钜,事体何等重大”。[13]因此,他和表弟杨亮功(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分工合作,花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五四》一书,并亲自经办出版事宜,成为记载五四运动最早的作品。1920年,蔡晓舟来到安庆第一模范小学执教,并开设了一家文化书店,作为进步书刊传播的基地。上文提到的《黎明周报》《安庆学生》《寸铁》《洪水》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就是由他创办。同时,在怀宁县学宫、安庆西门外和城郊地区,蔡晓舟通过创办工读夜校、工人政治夜校、文化补习班和业务小学等方式,将进步书刊予以推广,加强反帝爱国主义教育。[14]在此基础上,蔡晓舟于1921年4月在菱湖公园召开了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出席者有四五十人之多,其中就包括后来在中国革命史上名声卓著的王步文(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任书记)、舒传贤(皖西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和许继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等。会议期间,由于密探举报,20多名军警前来围捕。所幸事先得到报告,参会人员紧急疏散,成功地逃脱了反动军阀的捜捕。[15]值得一提的是,蔡晓舟的这一举动也奏响了中共安徽地方组织创建的序曲。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前期各种思想的涌入,1920年前后出版的进步书刊仍然未能完全摆脱其他思潮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杂糅和矛盾。以蔡晓舟于1920年底创办的《新安徽》为例,在创刊号上,《新安徽》虽然提出要励行“新俄国式的直接民治”,转载了《平民周报》倪鸿的译文《社会主义运动史概说》,发表了荫楠的作品《社会主义之星宿海》,使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在杂志上占了一定的比重。但是,《新安徽》又不愿意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理想,提出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口号,关于地方自治的主张和方法也都具有资产阶级改良色彩。这样的含混倾向在同一时期的其他刊物(如《新湖北》)上也有体现。[16]由此可见,这些进步书刊也带有一定的思想局限性,这也是1920年前后中国思想界的真实写照。
三、传播的影响:学生运动
学生运动是民国时期城市非暴力运动的重要形式,深受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科举废除之后,新式教育带来了新思想,让青年学生得以真正地“开眼看世界”,增加了对国家大事的关注度和责任心。五四前后,思想解放潮流进一步催动了青年学生的觉醒。中共早期很多重要人物的成长,都离不开学生运动的洗礼,他们或是学生运动的领袖,或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20世纪初期,徐锡麟刺杀恩铭和安庆马炮营起义给当时的安徽青年学生极大的触动和震撼。根据高一涵回忆,辛亥革命爆发以前,安徽青年学生受到了革命烈士英勇牺牲、革命志士宣传教育和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影响,这也为他们在后来接受进步思想埋下了伏笔。[17]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安庆青年学生群起响应,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决定于5月7日下午举行大会,邀集各校学生代表参加,共商大计。参会者共计50余人,会议决定成立安庆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临时联合会(一个月以后改为安徽全省学生联合总会,接受上海全国学联的领导),并以“安庆学联”的名义,分别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北京大学、北洋政府和上海媒体,表明坚定立场和严正态度。5月8日上午,各校学生3000余人齐集黄家操场,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宣传打倒列强、拒签合约等口号。在游行的进行过程中,还举行街头演讲、沿街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历时约3个小时,连同参加活动的群众约有七八千人之多。此外,安庆青年学生还组织国货检查所,抵制日货的传销;同年六月,又组织罢工、罢市、罢课活动,积极响应北京的“六三运动”,将五四运动推向深入。[18]与安庆同步,芜湖的学生运动也积极开展起来。当时,高语罕和刘希平正在芜湖五中授课,向学生传播了大量进步思想。5月7日上午,芜湖各校学生2000多人举行示威游行,并到镇守使署递交《请愿书》,要求北京方面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拒签合约。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各校学生还成立了芜湖学生联合会,成功地将之前交流很少的各校学生联系在一起。5月19日,为了响应北京学联的号召,芜湖学生举行了为期三天的罢课。随后,又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行动。[19]上述学生运动加强了各校之间的联络,锤炼了青年学生的意志力,安徽青年学生在五四运动期间获得了显著的成长,为他们日后开展更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增加了信心和经验。
此后,在知识分子的积极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在安徽传播开来,不仅为青年学生提供了思想引领,也强化了他们的斗争意识。1921年6月在安庆爆发的“六二学潮”,正是安徽青年学生自主发动的一场争取合法权益的革命运动。事件源于军阀对安徽教育的长期摧残和迫害。民国成立之后,安徽省长期处于反动军阀的统治之下,不仅是政治权力侵蚀教育界,还时常发生挪用教育经费的恶行。1921年,省政府编制财政预算时再度漠视了教育界要求增加经费的诉求,还拟将历年剩余之款用于省议员的贿选。在这种情况下,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和马克思主义熏陶的青年学生决定奋起反抗。6月2日下午,学生代表赴省议会请愿,却遭到反动军阀的殴打和杀戮,姜高琦身中7刀,不幸遇害,另有数十名学生受伤。惨案发生后,安徽省教育界将事件详情通电全国,各大报纸纷纷报道,社会各界进行了强烈谴责。面对着重重压力,反动当局被迫通过增加教育经费的提案,并对逝者进行抚恤。此后,安徽青年学生又相继开展了反对省议会贿选、驱逐反动省长李兆珍等斗争。在这一过程中,反动军阀的本相再一次暴露无遗,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被唤醒,学生运动的很多参与者,后来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20]
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在1920年前后的学生运动中,青年学生对于国家民族的热爱和对反动军阀的仇恨固然强烈,但对于中国未来的走向却很难有着清晰的把握。虽然不少学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但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和理解并不深入,因此,难以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之中。1922年3月,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王逸龙写信给团中央负责人施存统,明确告知,由于时间和人员的制约,无法派员参加4月份在上海举行的会议,只能授权现居上海的高语罕出席。[21]次月,皮言智等八人再一次致信施存统,表示安庆团组织无法派人参加5月份举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理由在于,“只因我们能力有限,又当安徽改造时期,事务繁重,我们几个人,整天的忙个不了,虽不见得完全有效,然总归是要花费工夫的,……又兼我们此时均在学校求学时期,不能完全不顾学业,所以对于社会运动,只能尽相当的责任。”[22]在这种情况下,安徽代表缺席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不能不说是安徽地方党史上的一件憾事。这一方面表明初创时期的安徽共青团组织还处于幼稚阶段,另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力度和深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总之,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重要阶段,发生在新文化运动末期的五四运动则使得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思想界崛起。1920年前后,依靠知识分子的宣传与动员和进步报刊的传入与发行,马克思主义开始在安徽传播开来,一批青年学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众。这一时期安徽省的学生运动正是以这一批青年学生为骨干,他们也成为日后中共安徽地方组织的核心力量,书写了安徽早期党史的序章。
但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要表现为先进分子的思想升华,还没有能够产生有规模的社会效应。因此,此时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者以青年学生为主,未能向社会其他阶层有效扩展,以至于限制了革命力量的组织和动员。上述局面在1921年以后(特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展以后)才有所改观,这样的史实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固然是中共创建和发展的思想基础,但中共的创建和发展也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