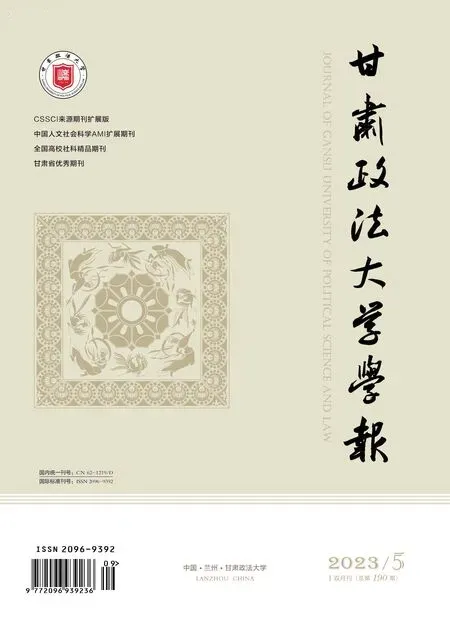寻衅滋事罪的性质及其构造
王广利
引 言
近年来,随着医患纠纷、非法上访、未成年暴力的高发,寻衅滋事罪的适用愈加频繁。黑恶势力行为,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行为,涉医违法犯罪行为,利用信息网络信访及编造、散布虚假信息的行为等均有可能被认定为寻衅滋事罪,这引起人们广泛热议。寻衅滋事罪的适用现状逐渐呈现出一幅怪诞的图景:人们始终觉得将大量的行为入罪并不合理,但又讲不清问题出在何处。即使被怀疑,寻衅滋事罪也没有停止扩张的脚步。(1)这一方面体现为该罪司法解释的不断扩张(自2000年来,几乎每年都有规制该罪的刑法规范出台),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大量行为在基层实践中被认定为寻衅滋事罪(据数据库统计,自2014年来寻衅滋事数量每年超过4万件,成为典型的高发犯罪)。此外,在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解释标准也极不统一,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该罪的负面意义。比如,在“王某军寻衅滋事案”中(2)王某军寻衅滋事案,浙江省龙游县人民法院(2020)浙0825刑初31号刑事判决书。,法官认为构成该罪需要发生在公共场所,进而扰乱公共秩序,但在“张某某寻衅滋事案”中(3)张某某寻衅滋事案,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法院(2020)黔0122刑初8号刑事判决书。,法官却放弃了这样的要求。这种认定上的混乱还发生在该罪内部协调以及与其他关联犯罪的协调上。(4)以故意伤害与寻衅滋事的关系为例,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故意伤害罪,但综合评价下来具有一定的危害性,司法实践很容易将这样的行为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也就是说,这种做法实质上将寻衅滋事罪等同于国外的暴行罪。如后所述,这样的理解存在一定的问题。司法实践对寻衅滋事罪的理解缺乏必要的共识,导致法官对寻衅滋事罪的认定过于依赖自己的直觉。如何在教义学上体系化地定位该罪成为破解该困境的关键。
根据《刑法》第293条规定,本罪有4种行为类型组成,即随意殴打他人的行为,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的行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行为,以及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严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描述上的过于模糊,导致该罪面临如下两个主要的理论问题。(5)出于某些历史原因或其他原因,本罪还面临是否要求“流氓动机”和“事出无因”等问题,但笔者认为这些问题不是刑法解释必须回答的问题,而是解释的结论。对“流氓动机”和“事出无因”等问题,参见陈兴良:《寻衅滋事罪的法教义学形象:以起哄闹事为中心展开》,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
第一,如何解释本罪的第4项与前3项的关系?尽管本罪被定位为侵犯公共秩序的犯罪,但除第4项外,前3项所列举的行为实际上跟“公共秩序”本身没有必然联系,因此如何解释本罪前3项与公共秩序的关系,以及第4项与前3项的关系成为一个问题。
第二,如何解释本罪与其他关联犯罪的关系?该问题又可分为两个子问题:一是本罪的罪状描述与其他关联犯罪(主要指故意伤害罪、侮辱罪、敲诈勒索罪、强制交易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高度重合,如何解释本罪与其他关联犯罪在构成要件上的关系便是一个问题;二是尽管与其他关联犯罪构成要件高度重合,但本罪的法定刑在同等条件下高于其他犯罪,如何解释本罪与其他关联犯罪在法定刑上的区别也成为一个问题。例如,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随意殴打他人致一人轻伤即构成本罪,而故意伤害致一人轻伤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寻衅滋事罪的法定刑要高于故意伤害罪。这不是个别现象,在同等条件下,寻衅滋事罪的法定刑高于与之相关联的其他犯罪。
在刑法教义学上,通说对该罪的解释采取了一种实质拆分的策略,即逐个地解释每一项罪状的成立条件及适用标准,同时还定位为其他关联犯罪的补充条款,但是,这种做法不仅未解决上述两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还实质上取消了寻衅滋事罪存在的独立性,因此是不可取的。有鉴于此,本文在区分政治共同体成员不同身份的基础上对该罪行为的性质进行了全新解读,以期为司法实践的认定提供思路。相较于通说,新的解读更能融贯地解决寻衅滋事罪的上述问题,而且还能建立更为清晰的教义学方案。
一、寻衅滋事罪的通说解读:批判与反思
(一)寻衅滋事罪第4项与前3项的关系
1.该罪第4项规定与前3项规定之间存在重要差别
根据《刑法》第293条的规定,寻衅滋事罪是侵犯社会法益(准确地说是公共秩序)的犯罪。但是,除了第4项的罪状描述明确规定要发生在公共场所外,其他3项均未作此规定,而前3项规定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侵犯“公共秩序”也不明显。因此,如何解释前3项规定所体现出的公共性,以及如何解决第4项和前3项的体系关系是一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通说对此的解释:本罪侵犯了双重法益,即既侵犯了个人法益,也侵犯了社会法益(6)参见陈兴良:《寻衅滋事罪的法教义学形象:以起哄闹事为中心展开》,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因此,若行为人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同时表现出对公共秩序的扰乱时,便成立本罪。例如,根据第1项,“随意殴打他人”的行为侵犯的是“与公共秩序相关联的个人的身体安全”,而随意殴打家庭成员的,尽管也侵犯了他人的身体安全,但由于没有扰乱公共秩序,所以不构成本罪。(7)参见张明楷:《寻衅滋事研究》(上篇),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1期。在这里,“殴打他人”表现了行为人对他人个人利益的损害,而“随意”则表达了该损害的公共性质。对于第2、3项,可作同样的解释。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随意殴打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还扰乱公共场所秩序,通说认为也构成寻衅滋事罪(因为公共场所秩序是公共秩序的下位概念),此时“公共场所”就是本罪前3项的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8)参见张明楷:《寻衅滋事研究》(上篇),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1期。
但是,当行为人随意殴打他人时,如何能同时做到扰乱公共秩序?或者,即便给“随意殴打他人”加上“公共场所”的限制,它的公共性的含义与第4项中公共性的含义一样吗?起哄闹事的行为是可以紧迫而现实地引起公共场所秩序混乱的,但无论在什么层面上,随意殴打他人都不能引起此种混乱。当行为人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时,如同放火和爆炸那般,很快就能被公众识别为一个公共危险,并能迅速地在人群中蔓延,从而造成公众恐慌而现实地使公共场所不加遏制地混乱。但是,当行为人(在公共场所)见人就打、见人就骂时,这并不能算作一个可被公众识别的公共危险,因为它有一个在人群中逐步传播的过程,很难像起哄闹事那般给公共场所中的不特定多数人带来紧迫且现实的恐慌感。由此可见,通说的观点并没有在如下两种情形之间进行仔细区分:一个是现实秩序的混乱,如“起哄闹事”行为,或者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放火、爆炸)等;另一个是行动预期的缩减,如“随意殴打他人”等。若说寻衅滋事的行为扰乱了某种“秩序”,那只能是在如下这个意义上:如果说之前人们可以自由地穿梭、通行于某场所的话,那么随着“随意殴打他人”“辱骂他人”等现象的出现,人们开始变得“看别人的脸色行事”,就此而言,寻衅滋事者的出现实际上缩减了人们对未来自由行动的预期。
这个概念的混淆所造成的实际后果是,谈论随意殴打他人引起公共秩序的混乱仅具有一种修辞的意义,而不能发挥对本罪的真正限制作用。例如,在唐某某寻衅滋事案中,被告人唐某某酒后未戴口罩到某卫生院探望其住院的父亲,因值班医生周某提醒其戴口罩,并制止其在正在使用的输氧病房内抽烟,唐某某心生不满,与周某发生口角,继而殴打周某头面部及颈部,并致周某衣物损坏;后唐某某又先后殴打前来劝阻的医生王某某、群众姚某某和唐某。(9)唐某某寻衅滋事案,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2020)苏0925刑初78号刑事判决书。在这里,唐某某打人的行为在何种意义上造成医院现实秩序的混乱在教义学上是完全不清楚的,毋宁说,其真正带来的危害是医生未来对从医行为和病人对未来就医行为的预期。
2.该罪第4项不能被视为前3项的“指导形象”
有学者看到了通说的这个缺陷,进而论证说,该条第4项和前3项并非并列关系,而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起哄闹事是寻衅滋事罪整体构成要件的“指导形象”,因此“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这一表述是前3项的上位条款,也是本罪的本质所在。通过借鉴交通领域的信赖原则,该论者又指出,寻衅滋事罪的行为本质不在于现实地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而在于行为人挑战了“信赖原则”。具体而言,在相应交往过程中,人们一般可以信赖对方会遵守交往的行为规范而不实施违法犯罪活动,除非有证据表明对方已经预见到自己的犯罪行为。若行为人违反了信赖原则,即可表明其是随意的行为。根据信赖原则,行为人随意殴打他人的行为将导致国民难以建立有效的事先预警机制,进而导致规范性预期的丧失。(10)参见李世阳:《寻衅滋事罪构成要件的分化》,载《法学评论》2021年第2期。
但是,这个论证依旧存在问题。一方面,将第4项作为整个寻衅滋事罪的指导形象直接导致第4项在《刑法》第293条的存在变得多余,这不符合通行的解释规则——立法不赘言的要求。(11)参见英格博格·普珀:《法学思维小学堂》,蔡圣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1-62页。根据第4项的体系位置,显而易见的是,该项是与前3项并列存在的,而非前3项的共同要素。那么,可否像第225条(非法经营罪)第4项所起到的作用那样,将本罪的第4项看作前3项的兜底条款,从而对前3项起到实质性的指导作用?这种做法也不合适。非法经营罪的第4项是真正的兜底条款,它最终起到的是扩张行为类型的效果,但将“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的行为视作前3项的指导形象的做法实则取消了该项的存在。总之,基于条文结构对刑法教义学的极端重要性,上述理解并不可取。
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使“随意”这个要素丧失了寻衅滋事罪与其他犯罪的界分功能。如果“随意”指违反了信赖原则,那么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在交通肇事罪中违反信赖原则从而导致被害人死亡的行为也是随意性的行为。如此一来,随着信赖原则的推广,“随意”概念便被泛化:其不但是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素,也是交通肇事罪等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业务过失犯罪的构成要素,甚至类似于危险驾驶罪这样的抽象危险犯也是一种随意性的行为,因为该罪也破坏了“社会交往中的信任感与安全感”(12)李世阳:《寻衅滋事罪构成要件的分化》,载《法学评论》2021年第2期。。
就其根本而言,随意性在寻衅滋事罪中是行为的属性,用来表征行为本身,而不是用来表征结果,更不是用来表征某种思想特征的。例如,在危险驾驶罪等抽象危险犯中,行为人“醉驾”行为的选择和执行并不是随意的,而最多表明醉驾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是开放的;在交通肇事罪等业务过失犯罪中,行为人的行为也谈不上随意地实施,而是处在无意识的状态,或只是在持有一种很弱的无所谓态度下实施的,但在这种状态或态度下的“举动”甚至称不上一种行为(13)Vgl.Urs Konrad Kinderhäuser,Intentionale Handlung,Sprach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zum Verständnis von Hangdlung im Strafrecht,Duncker &Humblot/Berlin,1980,S.153ff.,而这与寻衅滋事行为中的随意性是不同的——该罪行为人至少有明确的意识。由此可见,该观点其实混淆了行为随意性、结果开放性及态度的无所谓性之间的差别,未能抓住“随意”在寻衅滋事罪中的真正含义。
(二)该罪与其他关联犯罪的关系
由于本罪的罪状描述与其他关联犯罪如故意伤害罪、侮辱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罪状有很大重合,所以如何解释本罪与与之相关联的其他犯罪的关系是另一难题。通说认为,本罪可被视为其他关联犯罪的补充性质的条款,即成立寻衅滋事罪不以成立其他犯罪为前提,且如果某行为成立其他犯罪,根据该罪的补充性质,便不再成立寻衅滋事罪。例如,某个行为不构成故意伤害罪(即没有致人轻伤),但如果该行为反复且严重,且能够整体评价可罚的话,便可以以寻衅滋事罪论处。(14)参见张明楷:《寻衅滋事研究》(上篇),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1期。
通说并未回答“补充性质”何以会成为解释本罪的理由。学者们普遍认为,由于寻衅滋事罪是一个易被滥用的兜底条款,为了限制寻衅滋事罪的泛滥,所以应当尽量限缩该罪的范围。(15)参见陈兴良:《寻衅滋事罪的法教义学形象:以起哄闹事为中心展开》,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陈小炜:《论寻衅滋事罪“口袋”属性的限制和消减》,载《政法论丛》2018年第3期。但是,此处的补充性质并不是兜底条款的含义。原因在于,根据教义学理论,成立兜底条款至少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新补充的行为需要和明确列举出的行为具有可类比性;第二,新补充的行为需要和明确列举的行为具有相同的规范目的。显然,随意殴打行为和伤害行为不但难以算作同种性质的行为,而且它们意图保护的法益也不相同。更重要的是,如果该条的补充性质是对的,那么如下两种情形就是无法区分严重程度:其一,行为人故意伤害致一人轻伤;其二,行为人随意殴打他人致两人轻微伤。前者构成故意伤害罪,后者构成寻衅滋事罪,但是,有什么理由认为,后者的行为比前者更严重呢?这显然与刑法规定不相符——在同等条件下,寻衅滋事罪的法定刑均重于其他关联犯罪。
“补充性质”算得上学者们为该罪开出的一个特设性论据,但它在教义学上存在疑问。如果条文的补充性是一个真正理由的话,那么它要么应当引申自其他教义学原理,要么能够在其他地方得到印证,但除了在寻衅滋事罪等极个别犯罪中,根本不清楚补充性质为何可算作一种解释理由。而为寻衅滋事罪独创一个解释理由是一种过于独断的做法。
除此之外,补充性质的理解会导致一些不可接受的理论后果。它导致寻衅滋事罪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犯罪,而是多种犯罪类型的复合体,即,它由多样的行为类型构成,也不存在单一的法益。例如,对于第1项,它是故意伤害罪的补充条款,因此,若行为不构成故意伤害罪但殴打行为“在整体上可罚”时,可以被认定为寻衅滋事罪;第2项是非法拘禁罪、侮辱罪、敲诈勒索等罪的补充条款;第3项是强制交易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罪的补充条款;第4项是其他扰乱公共秩序犯罪的补充条款。这种实质性拆分寻衅滋事罪的做法更容易导致寻衅滋事罪的滥用,因为其不过将本罪中模糊的语词(如随意、任意、起哄闹事等)换成了另外一些模糊的语词(如整体上可罚),而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等同于其他关联犯罪则彻底失去了统一的标准(16)司法实践对寻衅滋事罪的扩张与刑法学界对该罪提出的含混标准不无关系。通说对该罪的矛盾态度体现在,一方面既不主张废除,另一方面又没有区分本罪与他罪的清晰标准,这种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该罪在基层司法实践的大量扩张。,而且这种做法实质上取消了寻衅滋事罪的独立性。既然寻衅滋事罪在地位上依赖于其他犯罪,那么立法者显然没有必要另外再规定一个寻衅滋事罪。
(三)安宁权不是一个有效的替代方案
鉴于通说解释力的不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寻衅滋事罪是行为人对其他不特定社会成员安宁权的侵犯。具体而言,每个社会成员对日常生活都具有一种稳定性期待,只有这样,社会成员才能合理安排自身的生活,进而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人格。同时,每个社会成员都需要保持精神的平和与宁静,这是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寻衅滋事罪的四种行为本质就是一类滋扰行为(17)在文献中,还有学者从“软暴力”的角度理解这里的“滋扰行为”,即寻衅滋事行为是一种非强制性的滋扰。但这个主张并没有通过非强制性滋扰来定义寻衅滋事行为,而是用寻衅滋事行为的存在来论证滋扰行为在刑法中的存在。因此这种方案不能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参见陈毅坚:《软暴力刑法性质的教义学展开》,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0年第4期。,其侵害了社会中不特定社会成员的安宁权,使社会中的不特定社会成员安稳宁静的精神生活状态被破坏,影响不特定社会成员自由地发展其人格,并损害了不特定社会成员的人格尊严。(18)参见江海洋:《寻衅滋事罪法益新解》,载《法治社会》2021年第1期。然而,这些说法具有潜在的误导性,也无助于我们解决上述提出的问题。
第一,这也依旧无法掩盖第4项和前3项的差异。换言之,即便本罪保护安宁权,“安宁”这个概念在第4项和前3项里也不是同一个意思: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的行为侵犯的是不特定社会成员的现实的安宁,而在前3项中,行为人侵犯的只能是某个特定社会成员的安宁利益,从而导致其他社会成员未来预期的受损。所以,安宁权无法成为这4项罪状的共同上位法益。这也同时表明,德、日的“暴行罪”与寻衅滋事罪存在根本差别:暴行罪侵犯的是被害人个人的安宁(个人法益)(19)《德国刑法典》第223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身体上乱待他人或者损害他人健康的,处五年以下的自由刑或者金钱刑。”参见《德国刑法典》,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页。《日本刑法典》第208条规定:“实施暴行而没有伤害他人的,处二年以下惩役、三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拘留或者科料。”参见《日本刑法典》(第2版),张明楷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页。,而寻衅滋事罪侵害的公共秩序(社会法益),忽视这个差别,简单地将暴行罪的法理移用到该罪,就会蹩脚地掩盖寻衅滋事罪的独特性。
第二,如果把该罪的安宁理解为社会成员对未来行动的规范性预期,那么这种做法就彻底抹消了寻衅滋事罪与其他犯罪的差别。因为在论述“刑法的任务是什么”问题时,刑法理论上那些坚定的规范论者认为,刑法的任务就是稳定规范性预期,因此,若此处的稳定规范性预期是正确的话,那么不仅寻衅滋事罪,而且刑法中的所有犯罪都侵犯了这种预期。可见,“规范性预期”的说法并没有指出寻衅滋事罪和其他犯罪的关键差别,当然也无法具体指导该罪的适用。
二、寻衅滋事罪的性质:基于政治共同体的框架
不难发现,通说对寻衅滋事行为的分析过于强调本罪所列举的动词,如“殴打”“毁损”“占用”等这样的语词,而忽视了对本罪中“随意”“任意”等副词的分析。行为类型当然是罪状分析的重点,但从以上通说的失败来看,本罪的关键可能不在于具有何种行为类型,而是在于行为类型的属性。正如有论者指出,该条列举的4项条款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行为随意性的一面,而这一点与其他犯罪存在重大差别。(20)参见李世阳:《寻衅滋事罪构成要件的分化》,载《法学评论》2021年第2期。有鉴于此,本部分将搭建一个用来理解行为随意性的“脚手架”,并且给出“随意性行为”的定义,然后在下一部分探讨该定义对寻衅滋事罪的解释力。该部分指出,寻衅滋事行为的规范形象体现在行为人对抗政治共同体的态度中,共同体的概念为判断行为的随意性提供了一个标准。
(一)政治共同体内的参与者和异议者
毋庸置疑,共同体表征了一种集体生活关系。一般而言,其至少具有如下三个特点:第一,共同体的存在取决于其成员有共同目标和共同生活的愿望。共同体不是一个松散的集合体,而是成员之间彼此享有紧密的情感联系和情感承诺。第二,为了实现这种共同理想,共同体成员制定了构成性规则或制度(21)See John Rawls,Two Concept of Rules,64 Philosophical Review 3,21-23(1995);John Searle,Constitutive Rules,4 Argumenta 51,51-54(2008).,并对彼此负有特殊义务。共同体的成员因为共同制定并践行的制度而具有一种不与其他共同体的成员所分享的忠诚。谁若想参与该共同体,就意味着其将自己置于该共同体的规则之下,并负有忠诚该规则的义务。第三,共同体内部成员可以相互援引规则对其他成员的行为进行评价。谁若与规则的指引相符谁就是在遵守规则,并确证着自己的成员身份,而谁若违反了规则,参与该共同体的其他人就可以援引该规则对其进行谴责,所以成员行为受规则的指引。最终,共同体成员共同决定、共同行事、共同取得成果并宣称为之负责,成为集体行动的产物。(22)See Andrew Mason,Community,Solidarity and Belonging:Levels of Community and Their Normative Significa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20-23.
以学术共同体为例。一个学术共同体内部成员分享着共同的目标和承诺——追求真理,这些目标和承诺使他们彼此连接在一起。学术共同体乃是一种小型联合体,为了维持彼此之间的关系,实现追求真理的事业,他们深感对对方负有某些义务,并在相互之间确立了共同体运行的规则,如“不得抄袭他人的学术成果”的规则等。这些规则构成了学术共同体的实践。谁若想加入这个学术共同体,就必须负有忠诚于该共同体内规则的义务,而通过负有这些义务,一个人确立了其在共同体内的成员资格,并能够在违反这些义务时接受共同体内其他成员的谴责。(23)参见安东尼·达夫:《刑罚·沟通与社群》,王志远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9-74页。最终,学术共同体成为一种轮廓分明的集体事业。
同样的道理适用于政治共同体。(24)有人可能质疑这个类比的效力,因为政治共同体毕竟与学术共同体在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比如,谈论一个人对政治共同体的“进入”或“退出”是不真诚的),但是作为一个共同体,它们的性质和功能是一致的。本文仅强调在这个共同点上的比较。在政治共同体中,交往的场域不再是小范围的学者之间,而是发生在一个更大的场域,即国家内部的成员之间。国家是一个具有伦理含义的联合体,尽管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25)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导论”。这不是说国家是虚假的产物,而是说它的存在依赖于一种集体想象活动。政治共同体致力于追求一些共享的目的(法益):生命、健康、行动自由、财产、隐私等。为了实现这些目的,共同体成员制定了法律规则及相应的制度。(26)See S. E. Marshall,R. A. Duff,Criminalization and Sharing Wrongs,11 Canadian Journal of Law and Jurisprudence 7,8-9(1998).这些规则和制度构成了该共同体的基本形态。通过服从、内化这些规范,共同体中的成员表达了其对该政治共同体的忠诚,而谁若违反了共同体规范,就应当接受其他共同体成员的谴责(惩罚)。(27)参见罗纳德·德沃金:《法律帝国》,许杨勇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51-152页;安东尼·达夫:《刑罚·沟通与社群》,王志远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4-77页。
在社会中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处于一个乃至多个共同体之中,这些共同体之间不必然是排斥关系。一个人既可能处于学术共同体、家庭共同体,同时是政治共同体的一员。共同体不是按照物理空间来区隔的,而是按照规范性视角来划分的。但不管怎样,无论处于哪个共同体,人们都必然要遵守这个共同体的规则,并自觉受该规则的指引。共同体、构成这个共同体的规则和受规则指引下的行为有着如下紧密关系:选择加入一个共同体,进而成为共同体的成员,就是选择自愿地受其内部规则的支配,同样地,自愿地忠诚于那些规则,也就代表他已经成为共同体的成员。就此而言,规则界定了成员的身份。(28)在本文中,“规则”和“规范”两个概念不作区分。特此说明。
鉴别一个人是否处于某个共同体之中,只要看看其行为是否与规则的指引相符。比如,一个法官不属于法学学术共同体,因为他不会遵守该学术共同体内的规范。又如,一个公民属于政治共同体,因为他认同该共同体内的规则,而一个局外人就不属于这个共同体,因为他可能不持有共同体内部成员的共享价值观。在这里,对于那些自愿忠诚于共同体内的规则,将自己归属为该共同体内一员的那些人,我们称作该政治共同体的参与者,而对于那些不认同政治共同体的规则,不愿意参加政治共同体的人,我们称作该政治共同体的异议者。(29)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个社会中并不是所有人、也不是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愿意忠诚于政治共同体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但鉴别一个人是否已经处于政治共同体之中有一些难度,因为政治共同体有一些特殊性,即每个人从一出生就已经处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并且似乎人们没有其他选择(参见莱斯利·格林:《国家的权威》,毛兴贵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8页。)不过,尽管从行为外观上不容易区分,但是从对共同体的态度上,我们还是可以作出区分。也就是说,对于在心理上自愿地忠诚于政治共同体的人,属于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反之则不属于。本文在最后一部分将探讨这个区分标准的经验界限。此外,德国刑法学者雅科布斯提出了“市民刑法”和“敌人刑法”的区分,以此将敌人从市民社会中区别出来。(参见京特·雅科布斯:《敌人刑法学说》,汤沛丰译,载《量刑研究》2019年第1辑。)尚不清楚本文的“参与者”和“异议者”的区分与“市民刑法”和“敌人刑法”的区分有何种联系,读者可自行判断。
有人可能质疑,区分共同体的参与者和异议者有根据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善意地视所有社会成员为该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成员,并像要求“我们”(参与者)自己那样要求“他们”(异议者)?只能说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情况,其中每个人总是视彼此为同道,在共同理想的激励下一起参与一个实践、改进一个实践,但现实世界并非总是如此,有的人在某些时候并不认同这个共同体,甚至怨恨这个共同体。此时如果我们用适用于参与者的法律去要求他们就必定错失焦点,因为惩罚一个人就已经预设了其是共同体的成员。
除此之外,在政治哲学上,参与者和异议者对共同体负有的义务也是不一样的。(30)对“公民是否有服从法律的义务”这个议题的讨论,See John Rawls,Legal Obligation and the Duty of Fair Play,Collected Papers of John Rawls,ed. Samuel Freema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17-129;Robert Paul Wolf,In Defense of Anarchis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p.69-82;Joseph Raz,Authority and Consent,67 Virginia Law Review 103,103-130(1981);John Simmons,Moral Principles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 p.191-210.对参与者而言,由于其是共同体成员,所以他们负有忠诚法律规则的义务,并在违反法律时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后者,政治共同体并不能强制其加入并要求其服从,所以他们并没有忠诚法律规则的义务。但异议者并非不负有任何义务,否则,若其能够任意地违反法律,那么隶属于该政治共同体内的法律规则便丧失了基本作用。异议者至少负有一种尊重义务,即便他们不认同该共同体规则,其行为也应当保持对共同体的必要尊重。
需要提起注意的是,参与者与异议者的区分不蕴涵更多的规范意义。这个区分是语言上的区分,意在强调,即便对于同样一个行为,那些意图参与这个政治共同体的人(参与者)和那些不想参与政治共同体的人(异议者)行为性质是不一样的。因为只有对参与者而言,才谈得上对规则的认可与否定,而对异议者来说,这些语词都不适合评价他们的行为。除此之外,这个区分没有任何其他规范含义,比如,不能认为参与者的地位比异议者更“高级”,或者异议者是我们社会的“敌人”(31)如果敌人刑法理论的确蕴涵这样的含义,那么,至少在这一点上,它与本文关于参与者/异议者的划分是不同的。等,即使不认同这个政治共同体,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如宗教或其他团体)也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成员。政治共同体,包括这个共同体内部成员制定出的法律,仅仅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而非最终目的。(32)See Joseph Raz,Authority and Consent,67 Virginia Law Review 103,106(1981).
(二)参与者行为和异议者行为表现的差别
既然参与者和异议者有着不同的实践旨趣,那么当他们的行为偏离了规则的指引时,会有哪些细微的差别呢?
在学术共同体中,当一个参与者自愿遵守规则时,他便视自己为该共同体的一员,反过来,当一个参与者违反规则——如通过抄袭他人的学术成果而为自己攫取名誉,他并不否认自己是该共同体的成员,而他之所以这样做,乃是因为他想暂时通过违背规则获取好处。换句话说,对参与者而言,无论是遵守还是违反规则,他都不否认规则对于学术事业的重要性,或者就此宣称退出学术共同体。因此,当共同体内其他成员援引与规则有关的事实对其施加谴责时,他知道自己的行为不是光明正大的,也知道这样的做法为人所不齿。但是,对于一个“民间科学家”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由于他们并不在乎学术共同体成员的看法,所以对他们的行为就不能用诸如“遵守规则”或者“违背规则”的语言来谴责他。同样地,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当一个共同体内的成员违反了“不得伤害他人”的规则,进而侵犯了他人的利益时,其侵害行为仅仅想“搭便车”(33)See John Rawls,Legal Obligation and the Duty of Fair Play,Collected Papers of John Rawls,ed. Samuel Freema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17,123.,而不会就此宣称“不得伤害他人”的规则从此对他无效,或者将彻底退出该共同体。尽管其自己做了一件错事,但他依然认同该共同体内的规范的构成性作用,并视自己为该共同体内的成员。但是,对异议者而言,由于其并不分享共同体内部成员的价值观,也不认同共同体内部的法律规则,所以其主要目的显然不是否定规则的效力,而是从根本上否定那些共享规则对该共同体的重要性。
由上可见,参与者的行为和异议者的行为有一个重要差别,即参与者犯罪和异议者犯罪发生在不同层面:参与者意在否定规则对他当下行为的效力,而异议者犯罪意在否定规则对维持共同体的重要性。因此,当参与者的行为与规则相符时,就是在服从规则,与规则相悖时,就是违背规则。但是,与规则相符或相悖这样的语词却不适合用来评价异议者的行为,因为当异议者犯罪时,其在整体上是对抗该规则的。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的“异议者对抗规则”,没有必要从一种综合的意义上进行理解,相反,从一种分离的意义上理解更合理。也就是说,异议者不一定是对抗该共同体内的所有规则,而仅仅是不满意其中的某些规则。比如,异议者对“不得伤害他人的规则”有所不满,但对“不得杀人”没有任何异见,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同样地,异议者对抗规则也没有必要理解成异议者在任何时候都会有对抗情绪,而是说当行为人偏离规则的要求时,如果具有“否定规则对维持共同体的重要性”的特点,那么他是异议者。
由于参与者和异议者表面上都处于现实政治共同体中,所以他们的行为外观非常相似,那么该如何区分他们的行为呢?根据上述描述的行为特点,不难发现,虽然参与者和异议者看似都在遵循或违反规则,但他们遵循或违反规则的理由是有差异的,因此,通过考察他们行为背后的理由,便可以区别他们的行为。具体而言,由于为行为提供理由的活动就是为自己的行为作辩护(或狡辩),所以行为人必须诉诸共同体成员能理解并认同的话语,否则就会陷入践言矛盾(performance contradiction)。比如,当参与者伤害他人时,就需要为其行为提供理由,如果行为的理由是“为了报复”,那么这样的理由就是可理解的,尽管不能获得辩护,而如果行为理由是“为了自我防卫”,那么这样的理由是可理解且可辩护的。无论如何,由于参与者是为了获得共同体内部成员的理解,所以这些理由一定早就存在于共同体中。然而,当异议者伤害他人时,他是不可能提出能被共同体成员理解的行为理由的,因为其从根本上就不认同共同体的某些价值观,相反,如果他能提出这样的理由,那么就表明他不是异议者。在此需要注意的是,人是否有理由做某事不取决于其主观意愿,而是取决于共同体内共同的价值观,因此是客观的。
笔者主张,所谓随意性行为,便是无理由的行为。准确地讲,如果行为人做了某事,但又无法指出之所以这样做的且能够被共同体成员理解的理由,就是一种随意性的行为。笔者将在下一部分展示这个定义的教义学前景,接下来将先指出,如果这个定义是成立的,那么在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中,可否找到针对这种随意性行为的根据?
(三)我国刑法中的参与者规范和异议者规范
第一,毋庸置疑,我国刑法中的大多数犯罪是针对认同政治共同体的参与者而言的。对这些参与者而言,通过忠诚于法律规范,他们确证了自己的成员身份。他们负有服从法律权威的义务,并且在违背这些法律规范时接受共同体其他成员的谴责(惩罚)。
第二,刑法中的少部分犯罪是针对不认同政治共同体的异议者而言的。根据对共同体犯罪的严重程度,大致可分为三个层级。第一类是最严重的异议者,其要么是一些极端主义者,单纯地否定政治共同体规范,要么是一些恐怖主义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如宗教目的或其他反人类目的)选择性地漠视共同体价值。这类犯罪分布在《刑法》第120条(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第120条之一(帮助恐怖活动罪)、第120条之二(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第120条之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罪)、第120条之四(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实施罪)、第120条之五(强制穿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罪)、第120条之六(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第121条(劫持航空器罪)。第二类是较严重的异议者,其为了自己的私人目的(称霸一方、为非作恶等),不认同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政治共同体。这主要是黑恶势力犯罪,分布在《刑法》第294条(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第三类是较轻的异议者,他们为了自己的私人目的(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漠视共同体规范,这主要是第293条(寻衅滋事罪)。
这个分类是否穷尽了所有的异议者规范?这里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归纳,因为这不但取决于个罪的具体分析,也取决于分类的旨趣。无论如何,能够确定的是,参与者和异议者犯罪应当适用不同的刑法法规,因为他们的行为性质有显著差别。举例而言,对同一个杀人行为,一个极力否定共同体规范的恐怖主义者和一个认同共同体规范的参与者的犯罪是不同的。对前者而言,其极力地反对该政治共同体的某些规范,如上所述,这种反对是坚决而彻底的,因此他的杀人行为意在破坏共同体规范的存续,而非有意针对某些或某个人。对后者而言,其并不否定其成员资格,其杀人行为是想从某些或某个具体的规则违反中获得特定的“好处”。对同样一个伤害行为,一个为了自己难以为共同体共享的目的而对抗共同体规范的寻衅滋事者和一个认同共同体规范的参与者的行为性质也是不同的。前者的行为具有随意性,后者的行为是有具体指向的。
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恐怖主义杀人罪”“恐怖主义伤害罪”,或者“黑社会性质抢劫罪”“黑社会性质敲诈勒索罪”类似的犯罪。对于恐怖分子和黑社会组织成员犯罪的,我国刑法规定转用本应适用于参与者的“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敲诈勒索罪”等罪。但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因为制定专门针对恐怖主义犯罪分子的刑法规范也是可能的。立法者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出于立法经济的考虑,因为恐怖主义犯罪的法定刑之重导致其与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之间没有实质差别。与之不同的是,对于轻罪,我国刑法规定了针对异议者的特殊条款,即寻衅滋事罪。因此,对于异议者犯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罪、非法拘禁罪、侮辱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罪的,不能适用本应适用于参与者的条款,而应当直接适用寻衅滋事罪。
三、寻衅滋事罪的构造:比较与建构
如上所述,寻衅滋事罪中的行为人是一类特殊的身份犯。其是一个身份犯,是因为行为人否认共同体内的某些规则,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并不视自己为共同体内部的一员;其是特殊的,是因为这个身份不是在共同体内进行划分的,而是在共同体内和共同体外进行划分的。寻衅滋事者是处于共同体之外的,因为寻衅滋事者不分享共同体内部成员共同的价值观,当寻衅滋事者对共同体进行犯罪时,其行为是随意性的,即行为人不能指出他如此行事的理由。因此,行为人是无理由地行为的。
(一)身份犯定位比通说更能融贯地解释寻衅滋事罪的特点
1.对于异议者,为什么适用由参与者制定的法律?
首先需要回应一个可能的质疑:既然寻衅滋事者不认同政治共同体的法律,而刑法又是共同体内部成员意志的体现,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用共同体内部的法律去谴责异议者的行为?这对异议者公平吗?
政治共同体有一些特殊性,即不存在一个居于共同体内和共同体外之上的中立机构,可以客观地评价寻衅滋事者的行为。在法律实践中,如果双方有不同的实践旨趣,那么只能寄希望于互相尊重:政治共同体内部成员需要尊重异议者的私人观念,而异议者也需要尊重政治共同体的价值观;如果发生了严重分歧(比如,涉及触犯刑法的问题便是严重的分歧,因为刑法关系到政治共同体根本的价值和目的),那么双方就只能以理解自身的方式去评价对方,尽管这种评价是基于最大善意的。
以参与者制定出的法律去评价异议者不一定不合理,关键取决于这种评价能否得到辩护。共同体的参与者通过这种方式来理解异议者:如果政治共同体内的法律是其成员通过真正多数表决的方式制定出来的,那么就可以合理地假定政治共同体中的法律是正义的,或者是接近正义的。(34)参见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9页以下、第344页以下。所以,参与者有理由认为自己制定的法律(至少是刑法)是正义的。在寻衅滋事罪中,参与者必须对异议者适用参与者自己的法律,是因为在遇到真正分歧的时候,参与者很难设想,是否真的存在一种可能的法律:它既容许伤害和侮辱他人的现象存在,还能被称为是正义的?因此,参与者只能通过适用其自身的刑法来传达其共享理念,尽管这些理念不一定能得到异议者的认同,但是参与者已经最大限度地限缩了对异议者行为的评价范围,例如,把异议者对共同体的侵犯限制在一些几乎不会引起争议的自然犯上。参与者也通过这种做法已经真诚地将异议者视作这个正义共同体内的一员(35)对这个论点的详细说明,参见安东尼·达夫:《刑罚·沟通与社群》,王志远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6-180页 。,并希望他们能够加入这个共同体。
2.本罪的第4项和前3项均体现了异议者身份的公共性
如前所述,通说对于本罪第4项和前3项关系的处理面临一些严重的困难。相反,本文设计的方案不存在这种困难。异议者与参与者仅仅存在身份上的差别,以及与身份有关的行为表现上的差别。因此,与参与者一样,异议者不仅会侵害他人的具体利益,也会侵害公共场所的秩序。如果异议者侵犯个人法益的,那么适用寻衅滋事罪前3项的有关规定,如果异议者侵犯社会法益(尤其指危险驾驶罪等轻罪)的,那么适用寻衅滋事罪第4项的规定。也就是说,寻衅滋事罪一条文浓缩了所有针对异议者的相关犯罪(轻罪)。如果异议者对参与者进行重罪侵犯的,那么不应当适用寻衅滋事罪,而应当适用其他针对异议者的犯罪条款:恐怖主义犯罪相关条款和黑社会组织犯罪条款,即或者直接适用有关条文(例如《刑法》第121条),或者转化适用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罪等罪。
该如何理解本罪体现出的公共性呢?据通说的看法,公共性尤其指的是公共场所的公共性,而公共场所指的是供不特定人出入的场所。(36)根据2013年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的规定,所谓公共场所,指车站、码头、机场、医院、商场、公园等场所。如前所述,将这样的理解适用到寻衅滋事罪中缺乏合理性。不难发现,通说是在物理意义上理解公共性的,但如前所述,这种理解方式面临困难。除了在物理意义上理解公共性,我们还可以在心理意义上进行理解,即身份的公开性。比如,在共同体内部,公务员是一个公共职位,而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对该共同体内的所有成员而言都是公开的,这种身份的公开性意味着公共性。同样,异议者由于不共享共同体内部的价值观,所以这种身份对于共同体内部所有成员来说也是公开的。换句话说,一旦将异议者定位为真正的身份犯,那么这一点对共同体成员来说是个公开的知识——当异议者否定规则对共同体的重要性时,其扰乱了共同体成员的公共确信。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本罪的第4项“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行为的公共性也体现在异议者所具身份的公开性上,而寻衅滋事者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特指的是寻衅滋事者实施了本应由参与者实施的未遂的放火、未遂的爆炸、危险驾驶罪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因此这里的“公共场所”也特指这些罪所发生的公共场所。
对刑法教义学理论来说,这种对公共性的理解是否是一个过于严重的代价?因为如果寻衅滋事罪的公共性体现在心理意义上,但《刑法》第六章第一节存在其他犯罪但不能同步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是否会违背体系性解释的原理?笔者认为,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原因在于,本文并没有对公共性这个概念作出一个有别于日常理解的界定,而是强调公共秩序的不同属性——公共性是有诸多面向的,没有理由认为,《刑法》第六章第一节的犯罪侵犯的都是物理意义上的公共秩序。
3.本罪与其他关联犯罪是排斥关系
(1)本罪是其他关联犯罪的补充条款吗?
通说认为,本罪是其他关联犯罪的补充条款。也就是说,如果行为不符合故意伤害罪、侮辱罪、财产犯罪的构成要件,但考虑到行为的反复性和严重性,如果能从整体上评价为可罚的话就可以成立寻衅滋事罪。就此而言,《刑法》第293条具有明显的补充性质,且补充的不是一个罪,而是相关的多个罪。但如前所述,这种理解存在缺陷。
本文认为,本罪与其他关联犯罪并非补充关系,而是排斥关系。也就是说,对于异议者犯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罪、非法拘禁罪、侮辱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罪的,不能适用本应适用于参与者的条款,而应直接适用寻衅滋事罪。通说的看法没有注意到参与者和异议者犯罪之间的关键差别:异议者不认同参与者所属共同体的规范,所以对他们适用参与者的条款是不准确的。
那么,异议者犯罪是否需要达到其他关联犯罪的入罪要求呢?第一,在入罪行为方面,寻衅滋事罪和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罪、非法拘禁罪、侮辱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罪没有任何差别。比如,如果寻衅滋事罪中的行为人构成“随意殴打他人”,那么这种“殴打”行为的属性跟“伤害”应当完全相同,或者说,殴打行为至少要达到跟伤害行为同等强度的危险。第二,在入罪结果方面,即寻衅滋事者殴打他人的,是否需要满足故意伤害罪的入罪门槛(1人轻伤)?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根据2017年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第8条第1款的规定,随意殴打他人致1人轻伤或2人轻微伤的可构成寻衅滋事罪。可见,该规定认为1人轻伤在结果上可以等价于2人轻微伤。(37)需要指出的是,司法机关经常作出这样的等价规定,例如,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1项在死亡1人和重伤3人之间的替换。由于缺乏明确的比较标准,这种替换有时会引起法条之间的不协调。但是,这样的规定不能作为比较两罪的基准,因为这种等价显然取决于一个可以在人际间比较的标准,即1人轻伤在造成损害的量上等同于2人轻微伤,但在寻衅滋事罪和故意伤害罪间不存在这样的标准。因此,笔者认为,出于公平相待的考虑,一个保守策略是合理的,即对于异议者犯罪的,共同体不能提出在结果要求上比参与者犯同样的罪更低的入罪门槛。以第1项为例,寻衅者必须致至少1人轻伤,才能在同等情况下进而构成寻衅滋事罪。对于第2、3、4项,应作同样的理解,也就是说必须存在一个共指称的其他犯罪,且行为人构成该犯罪,然后在满足其他条件的情况下构成唯有由寻衅滋事者才能构成的寻衅滋事罪。
(2)为什么异议者对政治共同体的侵犯更严重?
前文所述,在同等条件下,寻衅滋事罪的法定刑要高于与之相关联的故意伤害罪、侮辱罪、敲诈勒索罪、强制交易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那么寻衅滋事行为究竟严重在何处呢?不妨拿故意伤害罪和寻衅滋事罪进行对比。寻衅滋事行为在两方面比故意伤害行为更严重。在故意伤害罪中,行为人否定了“不得伤害他人”规范的效力,从而动摇了其他社会成员未来对该规范的预期,与之不同的是,在寻衅滋事罪中,行为人并非意在否定该规范的效力,而是通过否定该规范对该共同体的重要性,试图对抗该共同体。其间的差别在于:其一,在目的上,寻衅滋事者具有对抗共同体规则的目的,而共同体内部成员的犯罪仅有“搭便车”的目的,因此,寻衅滋事者对共同体的伤害是更大的;其二,在后果上,故意伤害者动摇了其他社会成员未来对该规范(即不得伤害他人)的反事实的预期(38)参见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刑法总论教科书》,蔡桂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寻衅滋事者不但动摇了共同体成员未来对该规范(即不得伤害他人)的反事实预期,而且现实地减损了共同体成员未来的行动预期,就此而言,寻衅滋事者比故意伤害者造成的结果更严重(对该两点的说明可参见下文)。(39)本文以规范论的话语体系作为论述背景,是因为规范论的主张与本文提出的某些主张容易产生混淆,而无意于在法益论和规范论之间作取舍。相反,本文的主张从法益论的角度来理解是更为方便的,即故意伤害罪仅侵犯了被害人的健康,但寻衅滋事罪除此之外还现实地侵犯了被害人未来可选择的行动空间。总之,这里的论证中立于刑法学中的法益论和规范论之争。
(二)寻衅滋事罪的教义学构造
根据如上论述,当且仅当满足如下条件时,行为人便可以构成寻衅滋事罪:第一,寻衅滋事罪的实行行为和其他关联犯罪相同;第二,行为人无理由地行为;第三,行为人现实地减损了被害人的行动预期;第四,行为人主观上有对抗共同体的目的。(40)这四个要件经过适当调整也同时能适用到恐怖主义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异议者犯罪。
1.寻衅滋事罪实行行为和其他关联犯罪应作相同认定
可以说,寻衅滋事罪是适用于异议者的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罪、非法拘禁罪、侮辱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罪。因此,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随意殴打他人”等行为,实则是判断行为人的行为危险是否等同于刑法上的伤害(第234条)、拘禁(第238条)、侮辱(第246条)等。有争议的是,“随意殴打他人”造成的结果是否需要完全和故意伤害罪中的结果一样?《补充规定》认为不需要完全一样,但本文认为应当采纳更加保守的策略,即“随意殴打他人的”必须与伤害结果一样(即至少1人轻伤)。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构成其他任何犯罪都有希望成立寻衅滋事罪。成立犯罪仅以本罪所勾勒出的犯罪轮廓为限。例如,在杨某等故意伤害案中,寻衅者杨某随意殴打他人致他人重伤、死亡的,无论如何不能构成寻衅滋事罪。(41)杨某等故意伤害案,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8)粤1973刑初367号刑事判决书。如上文所述,这种类型的随意性应当以黑恶势力相关犯罪论处(在满足其他条件的情况下),由于我国并没有对这类异议者规定特定的法条,因此应当直接转用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罪和故意杀人罪。
2.行为人无理由地行为
参与者和异议者行为的区别关键在于后者对他人的侵犯是没有理由的。所谓无理由,是指行为人的行为背后的理由不能被共同体内部成员所理解。它不但指行为达致目的的手段让人无法理解,而且行为人指不出它侵犯此被害人、而非彼被害人的理由。(42)根据2013年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构成本罪需要行为人“无事生非”或“借故生非”,但这样的规定过于模糊,无法为司法实践提供有效的指引。本文主张,这里的无事生非,是指行为人无理由地行为。
第一,行为人的手段让人无法理解。例如,在唐某某寻衅滋事案中,被告人酒后未戴口罩至江苏省某镇卫生院探望其住院父亲时,因值班医生周某提醒其未戴口罩,并制止其在正在使用的输氧病房内抽烟,唐某某心生不满进而殴打周某;后唐某某又先后殴打前来劝阻的医生王某某、群众姚某某和唐某。(43)唐某某寻衅滋事案,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2020)苏0925刑初78号刑事判决书。因被提醒戴口罩而殴打他人,这样的行为对于被害人是难以理解的。又如,被告人陈某某为发泄嫉妒、仇富和内心不平衡的情绪,用自制铁锥戳破停在路边或停车场汽车的轮胎,所损毁汽车轮胎价值计人民币7488元。(44)参见《陈宏礼为发泄仇富情绪随意损毁汽车轮胎构成寻衅滋事罪案》,载江苏高院编:《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报》2014年第2辑。在这个案件中,被告人出于仇富心态而任意损毁公共财物的行为同样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那么,究竟怎样的理由是不能被共同体内部成员所理解的呢?这里,我们可以借鉴正当防卫中的需要性要件。在正当防卫中,只有防卫行为在规范上是合适的,防卫才是需要的。需要性要件是对正当防卫成立条件的限制,因此,如果对方只是轻微的攻击,那么行为人就没有必要使用过于严厉的防卫手段。例如,在节日期间,游客大声放歌影响了附近居民的夜间休息,那么行为人就不能采纳伤害游客的手段进行防卫。(45)参见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刑法总论教科书》,蔡桂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1页。同样地,如果被害人只是引起了行为人轻微的不适,或者只是轻微的攻击,那么行为人就不能使用过于严厉的反击手段,否则就是无理由的。在上述案例中,因被提醒戴口罩而伤害他人在手段上是难以让人理解的,也就表明行为人持有对抗共同体内“不得伤害他人”这条规范的态度。
第二,行为人选取被侵害对象的无差别性。这是无理由行为的必然推论。因为如果行为人对共同体内规范持有对抗的态度,那么属于该共同体内的任何一个对象受损对行为人而言都是没有差别的,相反,如果行为人能指出他之所以侵害被害人A,而不是B,C……,那么就说明行为人是在求诸共同体内成员的理解,而这表明他并不对抗该共同体。
那么,究竟怎样判断行为人选取被侵害对象时是否进行了差别对待呢?这里,我们可以适用可替换性原则。如果将受侵害的被害人在同等条件下替换成其他人,行为人还是会实施同样的侵害行为,那么就表明行为人是无差别对待共同体成员的,因此就是无理由的行为。在上述唐某某寻衅滋事案中,值班医生是谁对行为人而言是没有差别的,因为将周某换成任何一个提醒其戴口罩的人,行为人都会实施殴打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无差别性并不是通说所指的“不特定性”。通说在论述“随意殴打他人”时,为了满足公共性的要求,要求这里的“他人”必须是不特定的行为对象,如前所述,这种理解是错误的。而这里的“无差别性”不等于“不特定性”,因为即便行为人针对的是特定的行为对象,只要这个对象是行为人无差别选择的结果,那么就有可能满足“随意殴打他人”的要求。
3.行为人现实地减损了被害人的行动预期
与参与者不同,异议者犯罪减损了被害人对自身未来行动的预期。理解该要件不妨将适用于参与者的故意伤害罪和适用于异议者的寻衅滋事罪作一对比。在故意伤害情形中,行为人违背了“不得伤害他人”的规范,侵害了被害人的具体利益。在规范论的语境中,我们会说,行为人通过伤害他人从而损坏了其他人对该规范的预期,那么寻衅滋事罪所指的行动预期与规范论中所说的对规范的预期有何差别呢?
规范论中的预期是一种反事实的预期:当其他人处在和行为人同样的情形中,他是如此推理的——“如果我处在行为人所处的情形中,我会如何行为”,如果其他人得出了跟行为人相反的答案,就说明其他人对“不得伤害他人”这条规范的反事实的预期被动摇了。与之不同的是,这里所说的预期是一种现实的预期,不是反事实的预期。以“随意殴打他人”为例,行为人不仅损坏了被害人对健康的反事实预期(这一点与故意伤害罪一样),而且也现实地损害了被害人对未来健康的现实预期。以“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为例,危险驾驶罪仅造成当时公共场所现实的混乱,而该罪还损害其他人对公共场所秩序的预期。在行为人寻衅滋事之前,被害人享有广泛的行动空间,而在行为人寻衅滋事之后,被害人需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被害人的行动空间的范围被现实地缩减了。
例如,在张某义寻衅滋事案中,被告人张某义之妻庞某在江苏省某县医院接受剖宫产手术时,张某义因怀疑该院妇产科男医生刘某某故意看庞某私密处而心生不满在住院部四楼医生办公室对其实施殴打。(46)张某义、庞某伟、胡某恒寻衅滋事案,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2015年6月24日,https://www.spp.gov.cn/ztk/2015/sy/dxal/201506/t20150624_100012.shtml。在该案中,医生的健康不但现实地被危害,而且由于被告人一些捕风捉影的猜忌,未来该医生在对女性进行同样的私密检查时其行为必然受限。这样的限制并非假想出来的,而是现实存在的:该医生为了不被再次殴打,其医疗行为的发挥将是不完整的。又如,在官某某寻衅滋事案中,被告人官某某伙同蔡某某等人在县实验中学门口无故用锤子敲打下晚自习回家的实验中学学生林某某,造成其头部受伤。此外,被告人官某某还伙同蔡某某等人在清流县儿童公园路段、九龙桥头、红绿灯路口、校园门口多次无故殴打在校未成年学生,先后导致五名学生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47)官某某寻衅滋事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官网2015年9月18日,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15568.html,2023年7月25日访问。在该案中,学生本应有完整的行动自由权,即可以任意地选择自己的出行路线而不受其他人的干扰,但是由于被告人的无端扰乱,被害人现在的出行不仅受到了干扰,而且其未来出行的预期也受到不合理的改变。
4.行为人主观上有对抗共同体规范的目的
从根本上讲,恐怖主义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寻衅滋事罪等罪中的行为人是极端怀疑主义者或极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相信现实的政治共同体揭示了这个世界的规范真理,也不分享共同体内的价值观。当寻衅滋事者逾越了尊重的界限时,他会质疑政治共同体的某些规则。因此,所谓的“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48)根据2013年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行为人构成寻衅滋事罪需要具有“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的主观动机,也就是“流氓动机”,但该条的规定过于模糊,难以为实践提供清晰的指引。本文主张,这里的流氓动机,是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对抗共同体规范的目的。,指的便是这种对抗共同体规范的态度。这并不是说寻衅滋事者具有某种先天的犯罪人格,从而不可能重新回归守法的轨道,而是说,当寻衅滋事者在犯罪时,由于具备直接针对共同体规范的特点,所以其不同于参与者犯罪。
那么,在现实中该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否持有对抗共同体规范的态度呢?这里不存在先验的标准,而只能依赖于行为人犯罪时那些经验性证据。(49)参见车浩:《寻衅滋事罪是用来打流氓而非耍流氓的》,https://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FullText.aspx?ArticleId=119611,2021年11月20日访问。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属共同体对异议者的宽容程度,以及不宽容能否得到实质规范性的证成。但是,我们可以排除一些明显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不能认为行为人的犯罪是针对共同体的。例如,这里所说的“共同体内的目的”指的是共同体内部成员共同的价值观,而不是某些个别行为人或利益集团的私人价值观,因此,如果行为人不认同这些私人价值观,不代表他就是对抗共同体的。又如,显然不能认为,只要行为人给公权力机关带来了麻烦就表明行为人是对抗共同体规范的,但如果行为人反复对公权力机关实施同一犯罪行为(如辱骂、威胁等),在满足其他条件的情况下,便可推定行为人是对抗共同体的。
例如,在黄某寻衅滋事案中,江苏省某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闫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该案经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后维持原判。闫某之母黄某不服一、二审判决,多次申诉信访。徐州中院、扬州中院和江苏省高院对该案进行复查,均驳回黄某申诉;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查后决定对该案不提起再审。后黄某因不满闫某案的复查结果,单独或者带其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媳先后数十次到徐州中院门前,通过采取身披状衣、使用高音喇叭播放录音等方式干扰法院办公,并不断辱骂该案承办法官。(50)黄某寻衅滋事案,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4)泉刑初字第283号刑事判决书。在该案中,寻衅者没有让人理解的诉求,只是为了单纯地宣泄其对共同体规范的不满,从根本上讲是敌视共同体的怀疑主义者。并非现实的政治共同体是不容置疑的,但对政治共同体的不服从不能逾越尊重的界限,尤其是不能违反刑法。
又如,在李某寻衅滋事案中,李某曾是某幼儿园工作人员,2007年该幼儿园因机构改革及债务纠纷而停办。总公司与李某签订协议书,就其分流一事达成协议:李某同意以货币补偿的形式分流,公司按照李某的工龄一次性为其进行了经济补偿,双方就此终止劳动关系。下岗后李某没有找到工作单位交养老保险,渐渐无力承担保险费用。自2016年起,李某先后多次到信访局、省信访局、国家信访局上访,要求支付所谓的欠付工资,并解决剩余三年保险费用,但都没有得到解决。2018年两会期间,李某再次前往北京上访,并威胁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称“不给钱绝对不回文登”,最终李某索要人民币9万元。(51)李某寻衅滋事案,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 (2018)鲁1003刑初164号刑事判决书。与上个案件不同的是,在这个案件中,难以认为行为人持有对抗共同体规范的态度。
结 语
对寻衅滋事罪而言,如何说明其内部各项之间的差异,解释它的公共属性,以及协调它与其他关联犯罪在构成要件上的重合关系是一大困难问题,对此传统理论的解释方案被证明是不成功的。通过政治共同体的概念框架,本文论证了寻衅滋事罪实际上是一类特殊的身份犯,即异议者犯罪。当异议者犯罪时,它的公共属性指身份公开性,而它与其他关联犯罪的差别主要体现为寻衅滋事罪是刑法专门针对异议者所设置的犯罪(轻罪)类型。在实践中,有理据地限缩寻衅滋事罪的任意扩张,就是要正视该罪的身份犯属性,以及由此导致其在行为表现、危害结果以及主观态度上与一般犯罪的差异。当然,不容否认的是,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明确性原则,该罪规定存在立法上的疑问,因为缺乏一个清晰的行为类型必然丧失对公民行为的有效指引,本文的解释方案也将成为一种有力的立法论层面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