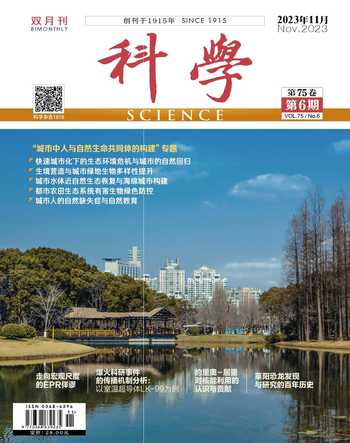快速城市化下的生态环境危机与城市的自然回归
达良俊 宋坤

在地球人口步入80億的当下,城市化的加快导致的生态环境危机,不仅让地球万物付出沉重代价,也让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面临严重威胁。我们的城市将何去何从?如何迎接挑战,为化解危机开出根植于中华传统自然智慧、顺应生态文明发展方向的中国城市建设方案?
人类活动正在越来越以城市为中心。人们在城市中的生产和生活曾经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土地和自然的束缚,然而城市正面临日益严重的人口和建筑物密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
地球生态系统面临巨大考验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1月15日世界人口达80亿[1]。纵观世界人口变迁过程,人口数量在19世纪前增长速度比较缓慢,进入19世纪后增长速度加快,从20世纪中叶开始急速增加;特别是从1960年的30亿增长到2022年的80亿,每增加10亿平均用时仅为12.4年,而近两次的增长速度更是缩短为11.0年/10亿。据估测,全球城市化率将从2021年的56%上升至2050年的68%,其中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将达到86%,而我国将达到71.2% [2]。

在工业革命开始后200年,人类取得以快速工业化、城市化为表征的现代化的巨大成就。然而,快速增加的世界人口规模不仅给地球的生物圈带来生态环境危机,也让人类社会面临从区域到全球的生态环境问题,地球和人类均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为表征的生态环境问题已使地球上100万种动植物面临灭绝风险,地球可能遭遇人类引发的第六次大灭绝,最终必将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3]。不仅如此,在不断增长的地球人口中,大部分涌向不足地球陆地面积5%的城市,由此引发的快速城市化进程给业已成为人们生产、生活和经营活动主要场所的城市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同时给城市人群的身心健康带来不利影响。
亟需遏制生态环境危机加速趋势
据分析,上述生态环境危机与人类社会生存模式的变迁密切相关。人类社会在原始文明阶段的生存模式包括三个基本环节:①索取:通过生产从自然界获取生存资源;②消费:将生存资源用于自身消费;③弃置:将改造和使用过的自然物和废弃物归还给自然界,使其重新参与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过程。随着向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推进,加工和分配环节加入进来,人类社会的生存模式发生改变,并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两大问题。这在自然界引发了生物多样性的衰退和丧失,以及生态系统的受损和退化。环境污染业已成为城市病和城市亚健康的主要成因,而生态破坏则以城市自然生态空间丧失、本土生物多样性衰退为主要标志,这又有可能造成城市中人们生理和心理的疾患,以及行为上的失常。

面向当前的生态环境危机,近年来由联合国确立的有关生态环境的世界性、国际性主题日,如每年4月22日的“世界地球日”、5月22日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6月5日的“世界环境日”,均将主要关注和重要关切聚焦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生态系统恢复方面。由我国发起且联合国决定的每年10月31日的“世界城市日”,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理念为总主题。近几年的“世界城市日”则以本地化为指导原则,提出“应对气候变化,建设韧性城市”“汇聚资源,共建可持续的城市未来”等目标。
我国政府一直结合各个主题日活动,提出多项行动倡议和战略决策。2016年底,为有效治理城市病,住房城乡建设部全面部署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的城市“双修”工作。2020年4月27日,《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即《“双重”规划》)强调推进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从自然生态系统演替规律和内在机理出发,着力提高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促进自然生态系统质量的整体改善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全面增强。202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了2030年完成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我国在2022年强调,在促进全社会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投身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丽中国的同时,进一步体现中国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作用,讲好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故事,贡献中国传统自然智慧,并提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当代中国方案。
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经济体系的发展方式及其对生态环境和人类自身的影响,减少生态环境危机给地球和人类社会造成的损失,最终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双体”目标。
我国在改革开放初始的1978年,城市化率仅为18.9%,甚至低于北宋时期的20.1%和南宋时期的22.4%。我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始于1980年代,此后以每年1%以上的速度增长,到2022年达65.22%。在此期间,城市建设目标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从最基本的“洁居”(卫生城市)、“美居”(园林城市),经过“适居”(环境友好型、紧凑型城市)和“易居”(智慧城市)阶段,向“宜居”(森林、湿地城市)和“安居”(平安、健康和韧性城市)转变。按照生物群落演替规律,并依据当前的趋势推测,我们的城市正朝着我们心中向往的理想城市“生态宜居城市”或“新田园都市”发展[5]。
然而,在当今城市发展过程中,不乏冠以“生态”之名的技术路径和工程措施的“伪自然—假生态”做法,成为“生态形式主义”的典型[7]。“伪自然—假生态”表现形式多样:未遵循生态学规律去建绿造林,形成种类单一、结构简单的绿林地;未经生物安全评估就从国内外大量引进植物,跨地带种植,等等。这些做法并不能真正形成健康、安全的生态空间,也无法向城市中的人们提供高效的生态系统服务和优质的生态产品。
正是由于城市原生自然生态的丧失造成本地生物多样性的严重衰退,以及“伪自然—假生态”城市空间的叠加效应,近年来在城市人群(特别是青少年)中,出现了自然缺失症现象。尽管目前尚不能确定它是一种疾病,但却可以导致孩子行为与心理上出现问题。

日本学者沼田真认为,人类是唯一的“自我驯化型动物”:人们根据生存需要,创造并不断加工城市生态环境,还不断从生理、心理、精神、观念和行为等方面进行自我调节,以适应自己所创造和加工的新的生态环境。从环境生态学属性来看,城市人群既是调节者,又是被调节者。有学者据此推测,较少接触“真自然”是自然缺失症形成的主要原因,而接受自然教育则为主要解决方式。
鉴上,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不应是简单的城市化妆运动,也不仅仅限于污染的强化治理和环境要素的重点修复,洁化与美化并不等同于生态化。但是,城市生态环境建设该如何体现、实现“近自然—真生态”?在这一点上,对“生态”寓意的深层次理解,以及如何认知城市和拥有正确的城市自然观,都至关重要。同时,在生态文明建设全民参与的当下,科普教育应该重点关注以面向自然缺失症为主要目标的自然教育。
城市科学研究者和城市建设者应该剖析目前城市生态保护、恢复与重构中存在的“伪自然—假生态”现象与瓶颈问题,以当前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在保护现有良好生态空间的同时,针对受损和退化的生态系统部分,以近自然生态恢复与重构为抓手,通过构建以乡土植物、乡土动物和自生微生物为主体的“地标性生物群落”,推动城市“近自然—真生态”演替的进程。同时,有关部门可通过野外课堂、自然研学等形式的自然教育活动,缓解城市人群的自然缺失症。此外,还应该考虑从中华传统自然智慧中寻求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方案。
中华传统自然智慧与当代生态文明理念
中华传统自然智慧的具体体现与表征是《易经》的“天人合一”思想。这种思想不仅强调要整体、系统地认识和把握世界,更把人与自然视为互相感应的有机整体。《老子》《孟子》《荀子》《齐民要术》等著作蕴含了尊重自然、順应自然、欣赏自然、善待自然和善待生物的生态伦理观念。当前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则被认为是这些质朴睿智的中华传统自然观的当代传承,而城市将成为实践这一理念的主要阵地。

“生态”与“天人合一”思想的自然观
中华传统智慧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人合一”思想的自然观,被学者认为由当今的“生态”这个舶来词所承接。“生态学”的单词“ecology”最早由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E. Haeckel)于1866年提出,被定义为一门“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1895年,日本东京大学的植物学教授三好学将这个西文概念译成汉文,即我们现在说的“生态学”,后经武汉大学张挺教授介绍到我国。三好学所说的“生态”具有“生之态”的寓意,强调“生”的形态、状态或态势。尽管在《辞源》《辞海》中未见收录“生态”一词,但我们可在中国传统经典中寻到它的踪迹。对于“生”字,《易经》有“天地之大德,生也”,《道德经》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儒家的“生生”思想表征的“生生不息,繁衍不已”的寓意,或许更符合“生”的发展态势。对于“态”字,其繁体字为“態”,《说文解字》认为它“意态也,从心从能”,其将外在特征和内心本质完美地统一在一个汉字中,表达了“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因此,“生态”既是“生”之存在“状态”、“生”之发展“态势”,更是“生”之人生“态度”[8]。
笔者根据对“生态”的理解,结合对城市生态系统基本属性的认知,提出生命观、动态观、系统观“生态三观”的准则,倡引城市生态环境建设进入演替“近自然—真生态”的新阶段。
恢复城市的本土生物多样性
正如越来越被大众接受的“地球是人类与其他生命(即万物)共同家园”的认知,人类保护万物也将惠及自身。人与万物本不对立,从生态伦理角度应追求生物种类间的平等共处。尽管在当前农业生产等具体实践中,为保证粮食产量和保障粮食安全,不得不针对农田生态系统中的有害生物实施直接杀灭的措施,但面向未来应进一步探索驱离等间接的非杀灭性措施,体现中性思维[9]。这种倡行善待万物的生物友善理念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要义。
本土生物多样性由在某个区域(如城市)及其周边相同气候带自然分布的生物种类组成,是区域生命组合的自然表征,具有地标性特征和属性。基于本土生物组成的地标性生物群落由乡土植物、乡土动物和自生微生物三大类群组成,是经长期物种演化和群落演替过程所自然形成,并与区域自然环境相匹配,且物种间适配度极高的组合,可被认为是物种层面上的生命共同体。因此,城市生态更新应拒绝“伪自然—假生态”,从规划设计到建设,再到管理和运营,应以尊重自然生态规律、倡行生物友善理念为指引,以珍视本土生物多样性的生态价值、恢复本土生物多样性为路径,以构建近自然的地标性生物群落为目标,全面建设城市的“近自然—真生态”。
从人工建筑地标走向自然生命地标

当前的城市建设往往通过打造由知名大楼、大桥等地标性建筑和构造物所组成的非生命的人工建筑地标来彰显城市人文环境的内涵与特质,然而城市文化不应只体现在人文环境上,也应体现在自然生态上。重视打造具地标性的城市绿色基础设施——表征本土生物多样性特质的城市自然生命地标,正是解决“千城一面”的本土文化良方[8]。虽然城市普遍存在自然生态空间禀赋不足、残存的自然生态空间不大,以及半自然/半人工生态系统拓展空间有限的现实问题,但具有生态功能的城市绿地、林地和湿地,以及郊区乡村的耕地、园地等类型的半自然/半人工生态系统,可被认为是生态功能空间,能开展近自然型地标性生物群落的构建[10,11]。这种群落的构建需以区域自然植被为参照,应用模拟自然、接近自然的方法和技术,充分考虑动植物的生存空间,通过人工修复与自然恢复的完美结合,在传统的“适地适树”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推行“适地适群落”原则,采用乡土植物营造近自然植物群落;为乡土动物提供栖息地,让它们“用脚投票”“用翅膀投票”,请它们“回家”;通过林下地被层的保护和枯枝落叶层的保留,促进自生微生物的“协同演替”,形成具有区域特色、可自循环、自维持、自更新的健康、稳定的城市自然生命地标。

上述“生态三观”准则在帮助实现城市生态功能空间增值提效的同时,也为城市人群提供可亲近、可享用,以及接近和认知本土生物的“近自然—真生态”空间,用以满足人们回归自然的愿望。同时,通过社会一体、面向全民的自然教育体系,为缓解、疗愈自然缺失症提供支撑[12],进一步丰富城市人文关怀精神的内涵,实现草木苍翠、虫鸣鸟啼、人水至和的和谐景象,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生物友善型和人文关怀型兼具的“三型”美好城市,最终构建城市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根植于传统中华自然智慧的当代中国城市建设方案。

[1]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Summary of results. New York: United Nation, 2022.
[2]UN HABITAT. Envisaging the Future of Cities, World Cities Report. Nairobi: UN HABITAT, 2022.
[3]IPBES.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of the global assessment report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n Díaz S, Settele J, Brondízio E S, et al. (eds.). Bonn: IPBES secretariat, 2019.
[4]盛连喜. 环境生态学导论(第三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5]达良俊. 基于本土生物多样性恢复的近自然城市生命地标构建理念及其在上海的实践. 中国园林, 2021, 37(5): 20-24.
[6]达良俊. 生态型宜居城市离我们有多远. 新华文摘, 2013(9), 5: 114-116.
[7]张桂林, 柯高阳. 过度求新求美,实则生态损毁: 城市绿化须防“生态形式主义”. 半月谈, 2023, (9): 74-76.
[8]达良俊, 郭雪艳. 生态宜居与城市近自然森林: 基于生态哲学思想的城市生命地标建构.中国城市林业, 2017, 15(4): 1-5.
[9]田志慧, 沈国辉. 都市农田生态系统有害生物绿色防控. 科学, 2023, 75 (6): 15-18.
[10]胡远东, 宋坤.生境营造与城市绿地生物多样性提升. 科学, 2023, 75 (6): 6-10.
[11]商侃侃, 赵坤. 城市水体近自然生态恢复与海绵城市构建. 科学, 2023, 75 (6): 11-14.
[12]杜伊, 唐继荣, 达良俊. 城市人的自然缺失症与自然教育. 科学, 2023, 75 (6): 19-23.
关键词:城市病 自然缺失症 近自然生态恢复 城市自然生命地标“三型”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