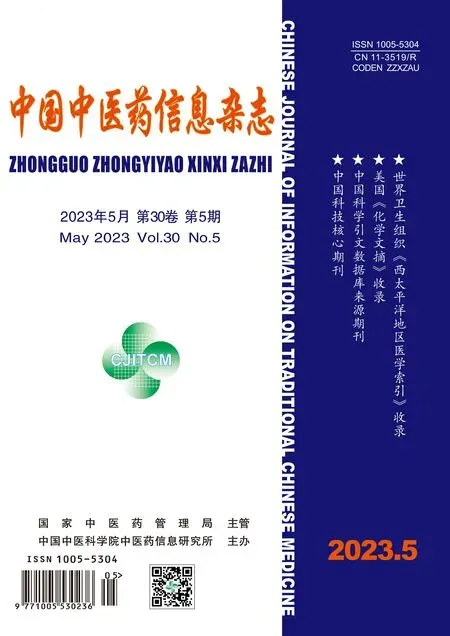从心、肝、肾论治子宫内膜异位症伴焦虑、抑郁
何甜甜 ,霍超越 ,林陶秀 ,张文娟 ,张悦健 ,马小娜
1.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 2.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北京 100029
子宫内膜异位症(endometriosis,EMs)是指子宫内膜组织出现在宫腔被覆内膜及子宫外的部位而引起的疾病[1]。10%~15%的育龄期女性可能发生EMs[2]。目前EMs发病机制尚未明确,其具有转移、复发、恶变等不良预后,是育龄期女性常见疑难疾病。EMs除带来躯体上的不适外,患者还要承受治疗疾病的经济和心理压力,患者常因疼痛、不孕、术后疾病复发及长期的治疗而产生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研究表明,EMs患者焦虑、抑郁发生率分别高出非EMs患者1.4、1.5倍[3],焦虑、抑郁与EMs相互作用、互为影响。焦虑、抑郁不仅增加EMs的发生、发展风险,而且严重影响EMs的治疗效果及预后。本文通过阐述中医心、肝、肾功能异常对EMs及焦虑、抑郁的影响,进而从心、肝、肾论治EMs伴焦虑、抑郁,为临床提供思路和方法。
1 焦虑、抑郁与子宫内膜异位症
焦虑、抑郁可能增加EMs发生、发展的风险。一方面,焦虑、抑郁可通过下调血清维生素D和钙水平,增加子宫平滑肌的痉挛和收缩,引起经血逆流频率增加[4-5];另一方面,焦虑、抑郁可通过调节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促进EMs发生发展。患有EMs的女性唾液皮质醇浓度显著低于对照组[6],而皮质醇是HPA轴功能障碍的生物标志物,与不同精神疾病有关。HPA轴可在焦虑、抑郁等异常心理状态下被激活[7-8],使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增加,下调免疫应答,机体清除异位病灶的能力下降[9];焦虑、抑郁可促进神经递质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分泌,进而促进子宫收缩,增加宫腔内压力,提高经血逆流的发生率[10]。此外,焦虑、抑郁情绪可引起HPA轴、交感-肾上腺-髓质轴的过度活跃,导致糖皮质激素和儿茶酚胺释放增加,激活肾上腺素受体β2和环磷腺苷效应元件结合蛋白信号通路,促进血管生成并加速EMs病灶发展[11-12]。
焦虑、抑郁还可影响EMs的治疗效果。研究显示,EMs导致的长期慢性疼痛可使患者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使患者在情感和认知上增加对疼痛的主观感知,从而导致对疼痛的耐受性降低[13];焦虑、抑郁情绪还可通过炎症反应诱发中枢敏化,产生病理性疼痛,影响临床治疗效果[14]。且当患者处于消极情绪时,可能出现交感神经兴奋、内分泌失调、胃肠功能紊乱等异常,影响药效的充分发挥,使临床治疗效果欠佳。
2 中医病机
根据EMs临床表现,可将其归属于中医学“痛经”“不孕”“癥瘕”等范畴。目前普遍认为,EMs因脏腑功能失常、气血运行失调,致血不归经,“离经之血”留结于下腹而发病。EMs病位主要在胞宫、胞脉,其发病与五脏功能失调相关,而EMs伴焦虑、抑郁主要与心、肝、肾异常有关。
2.1 心与子宫内膜异位症伴焦虑、抑郁
痛经、慢性盆腔痛是EMs最主要的症状,与心存在密切关系[15]。心主神,EMs疼痛的感受由心神调控。《素问·评热病论篇》认为心可借助胞脉与胞宫相连,“胞脉者,属心而络于胞中”,《素问·至真要大论篇》又提出“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可见胞宫疾病导致的疼痛与心密切相关。唐代王冰对“心与疼痛的关系”有具体论述:“心寂则痛微,心躁则痛甚……痛痒疮疡生于心也。”由此可知,心神失调,情志不舒,可加重EMs疼痛程度。心主血脉,脉为血府,血行脉中,血液充盈,则血行不息,营养全身。《灵枢·五音五味》云:“妇人之生,有余于气,不足于血,以其数脱血也。”若女子长期心血不足,血液不能濡养胞宫胞脉,胞宫血流减少,不荣则痛。现代医学认为子宫血流量下降可导致子宫内膜处于缺氧环境。缺氧状态下可上调缺氧诱导因子-1,促进环氧合酶2及前列腺素E2的生成[16],增加子宫腔张力并促进子宫收缩,引起疼痛。缺氧还可通过调节雌激素生成、诱导EMs的上皮-间质转化及促进血管生成,进而影响EMs发生、发展[17]。
心主神志,心之功能异常可影响人体的精神活动,包括思想及情志活动[18-19]。《内经》对心调节精神活动的论述可归纳为两点:其一,“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灵枢·邪客》),心主宰五脏六腑,而五脏精气为精神情志活动的基础,说明情志活动虽与五脏功能皆有联系,然主要受心神调控。《医门法律》较详细地描述了心与五情的关系,“忧动于心则肺应……此所以五志唯心所使也”。其二,“心藏脉,脉舍神”(《灵枢·本神》),血液充盈,精神情志活动才能得以正常施展。心血虚可导致精神恍惚、情绪低落等,《金匮要略》亦有“血气少者属于心,心气虚者……而精神离散”。《景岳全书》归纳道:“情志之郁,则总由乎心,此因郁而病也。”焦虑、抑郁统归于情志病,由心主神明的功能所统摄,故焦虑、抑郁与心藏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2.2 肝与子宫内膜异位症伴焦虑、抑郁
女子以肝为先天,EMs发生发展与肝关系尤为密切。肝郁致瘀,血瘀是EMs的基本病机。肝主疏泄,促进周身气血运行,肝疏泄功能失常,肝郁气结,引起血液流变学改变、血小板聚集增多等[20],导致血瘀形成,影响胞宫血液运行,进而促使EMs的发生。其次,肝主疏泄可影响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免疫调控功能以肝主疏泄为核心[21],肝失疏泄可致自然杀伤细胞、T淋巴细胞等免疫细胞功能紊乱。虽然EMs发病机制尚不清楚,但免疫系统异常是EMs发生、发展的关键因素。机体免疫调节失常,导致炎症发生,促进子宫内膜细胞异位种植、生长[22]。肝郁还可干扰机体性激素分泌[23-24],使雌激素水平升高,加重EMs症状。另外,肝经循股阴入毛中,过阴器,抵小腹,EMs疼痛主要在小腹,严重者可向腰骶、会阴、股内侧等处放射,此与肝经循行路线相一致。冲脉任脉同起于胞中,出会阴;且任主胞胎,冲为血海,与女性生殖器官密切相连,冲任气血失调则影响胞宫生理功能。《医学真传》云:“盖冲任之血,肝所主也。”肝血充足,则下注冲脉血海,冲脉血海充盈,胞宫方能藏泄有时。因此,肝在EMs发病中起重要作用。
肝主疏泄,可疏通和调畅全身气机,气机不畅可导致情志异常[25]。《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提出“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的肝主疏泄理论。中医学认为,肝主疏泄主要表现为肝调节全身气机,协调平衡全身脏腑经络气的升降出入。《周慎斋遗书》将郁证的病机概括为气机失调:“郁证,乃地气不升,天气不降,致浊气上行而清阳反下陷也。”脏腑气机失调,清阳不升,浊阴不降,气结于内,郁证乃生。调畅情志当以肝的调畅气机为前提,肝失疏泄则气血运行失常,气不顺则郁。女性心思敏感,易于忧思郁怒,女子以肝为先天,肝调畅情志的功能对女子尤为重要。
2.3 肾与子宫内膜异位症伴焦虑、抑郁
肾为先天之本,又为胞脉所系,谓冲任之根,与EMs导致的痛经、结节、不孕等有重要联系。国医大师肖承悰教授认为EMs的病机主要为肾阳不足、寒凝血瘀[26]。EMs导致的痛经及结节与肾之阴阳盛衰变化有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云:“阳化气,阴成形。”EMs患者体内结节为有形之瘀积久而成,有形之瘀为阴邪,当肾阳不足,气化无力,血流不畅,致体内瘀浊等阴邪成形太过,积聚胞宫,不通则痛,久病则出现癥瘕积聚。《妇人大全良方》对“癥瘕”形成的病机亦有“夫妇人疝瘕之病者……脏腑虚弱,受于风冷,冷入腹内,与血相结所生”。《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有“诸寒收引,皆属于肾”,肾阳亏虚,不能御邪于外,寒邪入侵胞宫,使胞宫收缩、拘挛而致疼痛,寒邪与离经之血搏结,积而成癥。临床上,EMs患者常合并不孕,此多为肾阳衰惫之故。《圣济总录》有“妇人所以无子者,冲任不足,肾气虚寒也”。若肾阳亏虚,阴寒内盛,下不暖煦胞宫,则胞宫虚寒,阻碍摄精,遂难成孕。王秋香等[27]从肾虚血瘀论治EMs,发现患者基础体温的黄体期缩短而体温升幅不高,B超检查提示患者卵泡多发育不成熟,可作为中医肾虚辨证的科学依据。
肾藏精,精舍志,人的精神情志活动和肾的功能密不可分。《灵枢·本神》有“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指出“精”是神志活动的根本。肾藏精,包括先后天之精。“先天之精”来源于父母,决定着人的体质,禀赋不足则易产生情志疾病,即张景岳所言“禀赋不同,情志亦异”。肾主骨生髓充脑,肾精亏虚、髓海不充,神机失用,出现喜怒无常、悲忧无度、郁郁寡欢等情志异常表现。阳主动,阳气鼓舞人体生命活动。《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论述了阳气对精神活动的影响,“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阳气受损可导致精神活动紊乱[28]。肾主一身阴阳,肾阳为脏腑阳气之本,《景岳全书》载:“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肾阳亏虚,不能温补心阳,心神失养,从而引发情志疾患;肝肾同源,肝阳根于肾阳,肾阳不足,肝阳无以温煦,推动无力,则肝气郁结,情志不舒。
3 从心、肝、肾论治
《素问·举痛论篇》有对疼痛病机的描述,“寒气入经而稽迟……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脉泣则血虚,血虚则痛”,后世医家将此总结为“不通则痛”“不荣则痛”。血瘀是EMs的病理基础,贯穿EMs发生发展整个过程[29]。瘀血留滞下腹,气血运行不畅,引发疼痛、结节等,以活血化瘀为基本治法。焦虑、抑郁多因气机不畅,郁结不通而发病,治疗EMs伴焦虑、抑郁应坚持气血同调、标本共治。临证当根据具体情况调整治疗方法,用药也需灵活加减。
3.1 疏肝行气,气行则血行
肝郁则气滞,气滞则血凝;而瘀血内停又阻碍气机运行,气滞与血瘀相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妇人大全良方》有“若经候顿然不行,脐腹疞痛……气郁抑而不舒,则乘于血,血随气行,滞则血结”。焦虑、抑郁状态下,EMs治疗重在疏肝行气、活血化瘀。可选用柴胡、延胡索、香附、川楝子等,通过调肝理气达到活血化瘀目的,体现了以血载气、以气行血的逐瘀理论。肝郁日久,易化火灼血伤络,迫血妄行,离经之血瘀积胞络而致疼痛,可加栀子、牡丹皮、赤芍、夏枯草、蒲公英等以利肝气、降肝火。若痛经剧烈,多为子宫痉挛性收缩所致,可少佐全蝎、蜈蚣、地龙等虫类药物解痉。中医强调“有是证用是药”,但临证常需变通,于化瘀药中配伍疏肝行气药,可更好地发挥化瘀止痛作用[30],故疏肝行气活血法在EMs 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柴华等[31]使用行气活血方剂膈下逐瘀汤治疗EMs患者,治疗后痛经症状评分低于单纯使用活血中药益母草颗粒的对照组,且治疗组治疗后血浆黏度、红细胞沉降率及血清糖类抗原125均低于对照组。现代研究表明,行气活血中药可调节免疫机制,抑制病灶周围组织所产生的炎性反应,减轻盆腔粘连,改善盆腔微循环,缓解疼痛;还能抑制异位内膜细胞的黏附、侵袭、血管生成,减缓异位病灶的生长[32-34]。
3.2 补肾温阳,阳盛则阴消
EMs病程较长,久病损伤肾阳。阳化气,阴成形,阴长则痰瘀凝聚,阳长则化痰行瘀。肾阳不足,推动乏力,温煦失司,机体代谢失常,内生“瘀”“痰”等病理产物。瘀血停滞下腹,旧血不去,新血难生,积久成癥;痰浊阻滞中焦,气机升降失调,气滞则郁。痰、瘀皆为阴邪,王冰注《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故治疗EMs伴焦虑、抑郁,可加肉桂、仙茅、淫羊藿、乌药、桂枝等温肾助阳药。温阳之品大多辛燥,用量不宜过大,临床上常配伍少量女贞子、墨旱莲、鳖甲、龟甲等以滋肝肾之阴,使温而不燥。夏桂成教授认为,经间期阴阳消长转化不利或经前期阳长不及是痛经的根本原因[35]。经间期重阴转阳,前期则为阳长阴消,以阳气转化或增长为主,故可于经间经前温补肾阳,有利于消散子宫之外的瘀浊,使气血流畅、经脉通利,通则不痛。陈景伟等[36]研究发现,补肾温阳化瘀法能降低EMs患者血清内皮生长因子、糖类抗原125水平,抑制EMs血管生成、缩小病灶。
3.3 养心安神,心寂则痛微
“诸痛痒疮,皆属于心”。疼痛的感受由心神主控,如果心神失调,则人体对疼痛刺激的敏感性和承受力也随之改变[37],疼痛尤其是焦虑、抑郁状态下的疼痛程度颇受心境左右。国医大师夏桂成教授治疗痛经非常注重心神的作用,强调“从心论治”[38]。因此,对于EMs伴疼痛患者,加养心安神之品如首乌藤、合欢皮、远志、莲子心等,可加强镇痛作用。郑纯教授认为,妇科相关痛症与情志因素、心主血、心主神志等有关,主张宁心安神、滋阴养肾:经前期阴消阳长而易心气郁化火,需加清心安神之品;行经期冲任气血变化,易致经行不畅、心气下降,宜宁心降气,调经止痛,通畅胞脉;经后期阴血亏虚,滋肾阴同时加宁心安神之品[39]。
此外,心理干预对于焦虑、抑郁的改善至关重要。临床上可通过认知行为干预的方式让患者了解病因、纠正不良的认知行为、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改善不良情绪,提高生活质量。应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提高EMs患者的认知水平和依从性。同时,引导患者宣泄情绪,鼓励患者倾诉内心感受,或者通过深呼吸、阅读、运动等方式来缓解心理压力和负面情绪,使患者心态平和,有利于提高患者自身免疫力和临床治疗效果。
4 结语
EMs伴焦虑、抑郁临床常见,并相互作用、影响。EMs伴焦虑、抑郁主要与心、肝、肾功能失调密切相关,肝失疏泄、肾阳不足、心失所养均能导致气血运行失常,形成气滞血瘀,而气滞血瘀是EMs伴焦虑、抑郁的主要病机。故在EMs伴焦虑、抑郁的临床治疗中,合理评估患者的焦虑、抑郁情况,从心、肝、肾角度进行辨证论治,结合心理干预,可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增强临床治疗EMs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