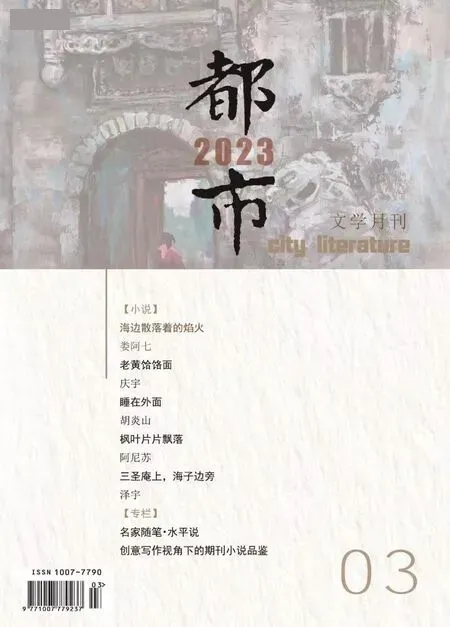那几乎是标本
——读陈河《蜘蛛巢》
○钟小骏
钟小骏,1978 年生,祖籍浙江,长居山西。文创二级。小说、人物传记曾获奖,参与创作影视剧多部,有随笔、杂文等散见于国内各媒体。晋中信息学院创意写作兼职教师。
《收获》2022 年第6 期上发表了陈河的《蜘蛛巢》,全篇一万字出头,描绘了一件事情,“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百万公里安全驾驶员”公交车司机卢桂民忽然有几天不上班了,这在他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从未发生过,原因是他的女儿离家出走多日不归,女婿上门后他不得不开始在整座城市中寻找女儿。
小说吸引我的第一个“点”是“细节”:“他是一九五八年培训出来的客车驾驶员,这批人后来被称为‘五八师傅’。那时会开车的人少,能开客车的简直和现在的民航飞行员一样光荣。”“胖女人指了指油腻的墙上,上面刻着一些记号。卢桂民突然想起来,三十年前他也经常赊账,那个三豹老司也是用记号刻在那面墙上的。”“小南门饮食店。他在这里吃东西的时候,这个店的招牌上还写着‘公私合营’几个字,‘文革’期间,店名改成过‘红星饮食店’,后来又改了回来。”作为现实主义小说,对细节的观察和准确再现是再怎样突出也不为过的要求——它是让读者“相信”的基础。而相信,是共情的前提。当然,表现细节的手段很多,甚至“细节”本身的意涵也非常丰富,动作、表情、语气、神态、特殊的名词、准确的外号、心理活动,或者一抹独特的风景都可以构成那个关键的“信息”节点,进而成功地说服读者进入故事,但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最关键的当然是要先有这个概念。
在接下来的故事行进当中,已经是一个姥爷的卢桂民,迈着中年后期的步伐,追寻着一些只鳞片爪的信息,一边还原着自己的曾经,一边重新勾勒着他那看起来有些陌生的女儿的形象。女儿晓燕小时候是多么的“乖”啊,“扎着两条朝天辫子,脸色红红的像个苹果……在学校里也很乖,虽然读书也不是那么好……悠然过来给他提亲……志敏爸爸是个好人,听说志敏也是个好驾驶员。他征求女儿意见,她没反对……孙子现在都五岁了……”可是自从她认识了那个“长得像外国人的阿琼”之后,晓燕变了,她在“小南门饭店”里和一群人吃喝,还赊账,经常外出,回家很晚,之前每次丈夫跑完长途回家都有的热饭热菜消失不见。她在“东门桥头舞厅”频繁出没,也曾深夜出现在“八字桥头大排档”吃饭,然后和另外一男一女共同离开……从结构上看,这是多么典型的小说推进:一个固定的目标呈现在前,主人公在行进的过程中不断地受到考验——寻找——失败——新线索出现——再次上路——再次失败——逼近目标——结局。假如在这个模式当中,在故事叙述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地融入其他背景,使得故事呈现得不那么单一,有了更多的维度,那么小说的完成度就会更高,甚至经典化。
打动我的第二个“点”,就在于不同的维度了。美之为美,斯恶已,从审美或者哲学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善恶无绝对,是一个相对概念。但太多的读者甚至包括写作者都有着迫切的宣扬“真理”的冲动,而“除我之外不可有别的神”,于是“真理”有了排他性,体现在作品中就是几乎“无所不在”的“标准”:它包括善恶、包括动机、包括评价,当然也就包括了“立场”。可“小时候有一回他带女儿到中山公园去玩,女儿正和其他孩子玩得高兴,可他没有时间了,硬是抱着她回家了。她平时都很温顺听话,就那一次她哭闹挣扎拳打脚踢强烈地反抗。她以后再也没有这样反抗过。”“有一天晓燕回娘家时告诉卢师傅,说她今天售出的车票有北京开往昆明的3982 次特快列车。那些地方她都没去过,但她听说过西双版纳的名字,现在看到去西双版纳的车票就在她的手里,心里很激动。售票窗口很小,看不到外面的人,只能看见买票人的手。她觉得买去云南车票的那些手都不一样,指甲皮肤都很特别……”于是,一个已经结婚了的、有着稳定的工作的、有孩子依赖的、家庭风评很好的女子忽然放弃一切,选择和社会上的“走卒,赖沦客,无赖骨,没职业的”男人以及天天不回家“半夜三更在外面一定是干坏事……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到卫生间里洗澡,洗很久”的女人厮混时,我们脑海当中第一个浮上来的评价“堕落”就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当晓燕被卢桂民带回家,当她吃下了母亲做的海鲜面,当儿子投入她的怀抱之后,她还是选择“从窗外的瓦背上跑走”的结局呈现时,我们似乎有些理解了。
从我的个人创作经验来看,对“答案”的追求在结构故事时非常重要,某种程度上让我失去了更多的可能性。当整部小说完结时,除了隐约的感受,我不能提供一个在故事中切实呈现的“动机”,于是我询问自己,这个故事让我来处理,会是什么样子。但关键信息的缺失让我找不到答案。好在陈河有一篇《一篇写了三十年的短篇》创作谈。
三十多年前那天下午,小说中的劳模驾驶员急匆匆跑到我办公室,要我帮助找他女儿,说我仓库里的阿琼是肇事者。我为此还去了阿琼家寻访,听她婆婆怒气冲冲述说了一番。几天后,劳模驾驶员又来找我,说自己找回了女儿,为此打了一次群架,最后女儿还是跑了……
我最初倾心的是想把晓燕出走和出走后做了些什么写出来,下过很大的力气写她和阿七和阿琼在外面鬼混浪荡的日子,想按照加缪的《局外人》那样写。但写了一段之后就写不下去,因为我不知道晓燕究竟是什么原因出走。我甚至想写晓燕在出走前,在汽车站票房里盗用了大量的公款供给阿七挥霍,结果是越写越糟,迷失方向,只得再次放下……
我终于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不应该用自己作为叙述中心,而是改成一个父亲寻找女儿的故事。我把看过上百遍的索尔·贝娄的《寻找格林先生》又看了一次,心里就亮堂堂了。
这一回,我用卢师傅的角度来写,感觉是那么轻盈鲜活,温州老城的气息都弥漫开来。我很奇怪为何自己不早点换成卢师傅的角度,但写小说就是这样,你就在迷宫中,有时候运气好,一下子就找对了门路,有时候你得在迷宫中兜圈子几十年。当你最终找到了你心目中要写的小说样子时,所有的冤枉路都变得有价值了。
所以你看啊,这就是让我激动的第三个“点”:它清晰地告诉我们,小说,即使是现实主义小说也有着无数多的可能性,也许,你转换一下“视角”,你曾经心动的很多“素材”,就终于可以摆脱“难以处理”“小说逻辑与现实逻辑相悖”“关键信息缺失”“人物行动不合理”的困境,变得“亮堂堂”起来。
说句题外话,我现在想着,莫尔索杀掉那个阿拉伯人的动机我一直没找到,最大的原因也许就是加缪从来不像我这样考虑问题吧!我的一个作家朋友说,那天的天气真好,于是他开了枪,也许这真的是答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