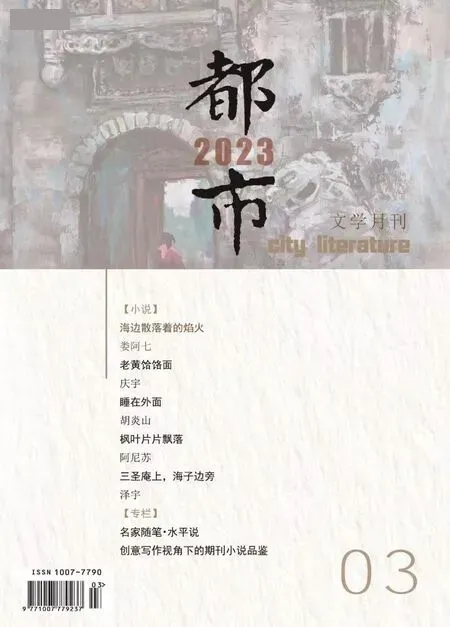如果你足够真诚
——读魏思孝《诗人》
○张 敦
张敦,原名张东旭,80 后。曾出版短篇小说集《兽性大发的兔子》。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晋中信息学院创意写作教师。
魏思孝的短篇《诗人》发表于《雨花》2022 年第1 期。这篇小说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感伤的情绪。读完之后,我心里有点难过。等冷静下来,我思考起自己为什么会受到感染?答案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真诚。
不客气地说,文学期刊中有太多虚头巴脑、虚张声势、扭捏作态的小说,不可否认有些作品故事还不错,人物形象也挺鲜明,但却不能打动我,简单说原因,就是因为“虚”——我看不到小说与作者之间有什么情感联系。或者说,我不知道作者为什么要写这篇小说,他要解决自身的何种问题。
作者本人的生命体验,应该是严肃小说创作的基础。作家要从个人经验出发,向世界提出问题——这挺难的,现实的无情,再加上内心的虚妄,会让你不由自主采取回避的态度,用所谓的技巧粉饰太平。
《诗人》的好,在于魏思孝的质朴与坦然,他叙述了自己与诗人劲辉的交往经历,不止写了诗人的所作所为,还写了自己的生活困境,尤其是后者,可谓整篇作品的情感基础,是下面分析的重点。也就是说,魏思孝的这篇小说,把“自己”放了进去,很“实”,这种“实”不是指故事的真实性,而是情感的真实性,当然前者是后者所产生的原因。
这里不得不提到《诗人》的主人公劲辉,其人物原型是已故诗人小招。在百度百科中,能查到小招的相关信息,他已于2011 年离世,愿他在天堂安息。据我所知,魏思孝与小招(作品中的劲辉)曾在青岛相熟,结为好友。后来小招在家乡自杀,这件事在圈子里传播甚广,我听闻后心有戚戚,作为其朋友的魏思孝,更是大受震动。可以想象,一年又一年,这件事一直萦绕在作家的心头,成为他不得不去面对的写作素材。
问题在于怎么写呢?如何将这位已然离世的朋友写到作品中?恐怕所有写作者都要面对这样的问题,那些离开我们的亲人和朋友,总会让我们难以释怀,胸中充盈着复杂的情感,表达欲油然而生。可是,又有几个因素左右着我们的表达。首先是伦理的问题,逝者为大,不忍还原其真实面目;其次是事过境迁,恩怨情仇早已放下,龌龊之事该统统回避;再者就是写到自己时往往过度美化,将自己塑造成超然入世的完人形象。这些问题,应该同样摆在魏思孝面前。他的选择是直接面对,用坦诚的态度面对已故老友,真实地表露自己内心所想,一五一十地呈现当年那些困顿的生活。
魏思孝的技巧就是“没有技巧”,好像在他那里,从没有“不知道选择哪个人当叙事者”的苦恼。他的叙事者总是他自己,一个来自山东农村的男作家。叙事者决定了叙事视角和叙事腔调,魏思孝的视角是“我”的所见所感,腔调也是“我”的口吻。这样的“我”的优势是更容易取得读者的信任。
小说开头,直接写“我”与劲辉的相识,没有一句废话,更没有矫情的“追忆式”的倒叙。看一眼魏思孝对劲辉的外貌描述,再看一眼小招流传于网上的照片,会发现他没有虚构,而后面对劲辉“传奇经历”的叙述,更是与百度百科相贴合。不得不说,小招是个不用作家费心虚构的人物,因为他的行为足够戏剧化,他好像就站在一个灯光昏暗的舞台上向平庸大众表演艺术家的生活状态。对于这样的人物,作家如果能做到记录下他的一言一行,让读者自己体悟他的行为逻辑,窥得一个丰富而独特的内心世界,就算完成任务了。
塑造人物形象,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给读者展示人物的过去。在魏思孝笔下,劲辉的过去是什么样的?有过数次类似于行为艺术的疯狂举动,在困顿的生活中坚持写作,还尝试画画。其中还有一句看似闲笔的叙述,“和劲辉同住的画家刘秀,几年如一日画一组杜尚与少女下围棋的油画。”写主人公周围的人,也能从侧面展示出主人公的形象。
读了前几段,我发现魏思孝并没有因为小招的离世而对其进行美化,他依然保持着足够的冷静和客观,写出了劲辉身上最大的特点,那就是虚妄。这是个沉溺于理想世界不能自拔,同时毫不顾忌他人感受的诗人,是天才,还是疯子?好像离后者更近些。
接下来,魏思孝写到了自己,下笔更狠。“我”是个小说家,生活和创作都面临困境,可以说看不到什么出路。有一笔写道,“那阵子,我热衷于好莱坞的血浆片,简单粗暴,不用动脑子。”这样意味深长的细节中有股子冷幽默,作家很难凭空想出来,只能来自真实的经验。
从这里开始,魏思孝“把自己放了进去”。我们试想一下,不写他自己的事,行不行?如果那样的话,笔墨集中到诗人劲辉身上,故事几乎没有变化,但味儿变了,似乎有什么东西会因此而消失不见。那是一种很重要的东西,决定着这篇小说的价值。这种东西是真实可信的情感。所以,这个“我”很重要。
小说后面叙述的是“我”和劲辉的交往过程。依然按照时间顺序来写,我看到的是魏思孝一以贯之的对笔墨的节省,每一件事虽是寥寥数笔,却总能写出最关键的部分,就像是球场上精准的点射。如果少了这些“点射”的部分,叙述就会滑向流水账。比如,劲辉曾经痛苦的恋情,劲辉房间的肮脏和凌乱,劲辉和我在屋顶上抽烟的样子。重点是其中两段,写到“我”与劲辉的通信,那是两人的分歧,让朋友关系变得复杂了,多么真实,若要瞎编,真编不出来。
在这部分中,重点写的是“我”当时的心境,绝望,还有些悲观,仿佛跌入了幽暗的谷底。当然,这是包括劲辉在内的大部分年轻人都会面临的困惑,值得反复书写。劲辉走后,魏思孝用了一种类似于电影中“平行剪辑”的方式,将“我”的生活与劲辉的生活放在一起。“他在中途下车,把鞋子、钱包、身份证等随身物品扔了,在街头流落两天后被治安大队送进收容所时,我在一百多公里外的老家,和父母一道为婚礼的细节熬灯……”我非常喜欢这一段,我甚至认为,如果没有这一段,整篇小说会失色不少。
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这篇为逝去的故友而写的小说,一直刻意地压抑着抒情的冲动,最多只是喊出一句,“一个小地方出来的人,想要做点事,究竟有多困难。”这仍是一句非常务实的话,保持着与全篇语言风格的高度统一。
最后,我想说的是,对于小说而言,情感的价值大于技巧。如果你足够真诚,直面困顿、龌龊、阴暗的现实生活,每一句话都来自真实的生命体验,那么你的作品自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