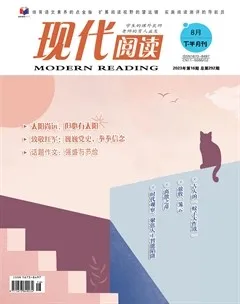成由勤俭败由奢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历史舞台过客缤纷,决定成败兴亡的,固然非止一端,但勤俭与否确实是影响个人成长、家业兴旺、国家兴盛的重要因素。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俭之为德,由来已久。上古尧舜之时,节俭的作用就被高度肯定。相传,虞舜曾称赞夏禹:“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大禹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吃粗米饭,喝野菜汤,穿短打布衣,住茅草屋,为后人所称道。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在生活观念上却几乎一致“尚俭”。老子曾言:“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孔子讲究礼仪,但强调以节俭为本:“礼,与其奢也,宁俭。”墨家更进一步地提出为人为政都要节用:“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
正所谓“俭生廉,廉生威”,节俭往往会催生廉洁,而廉洁亦会提高威望。为官者把俭朴和廉洁的关系理清楚了,节欲戒奢,戒奢从俭,以俭养廉,也就掌握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法宝。因此,古时官吏的升迁考核,常将能否“节俭”作为一项基本内容。
历史上众多有识之士都秉承俭朴家风。《颜氏家训》强调:“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宋代学者倪思告诫后人:“俭则足用,俭则寡求。俭则可以成家,俭则可以立身,俭则可以传子孙。”这些都体现出对子孙后代注重节俭、勤俭持家的要求和期望。
北宋名臣范仲淹不仅政绩卓著,而且“以清苦俭约著于世”,言传身教,范家子孙都严格遵守节俭的家风。《曲洧旧闻》中记载,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官居宰相,一次,他请朋友吃饭,饭局过后,朋友感慨这次居然吃到了两片肉,以前到范丞相家吃饭只有面条米饭上盖着豆豉佐餐。可见范家之清苦自守。
南宋理学家朱熹历事四朝,一生淡泊名利,安守清贫。一次,他去看望女儿女婿,未料女婿不在家,女儿留他吃午饭。因家中贫困,女儿只端出几碗大麦饭和一碗葱汤,对父亲很是愧疚。朱熹却不以为意,开开心心地吃了。吃完饭后,他还题了一首诗:“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道儒家风味薄,隔邻犹有未炊时。”女婿回来看到后大为感动,便将此诗作为家训,于书房悬挂。后人亦以“朱子固穷”赞扬朱熹。
“成由俭,败由奢”,在古人看来,节俭不仅是个人生活中的美德,更应该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去看待。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失了勤俭,沉溺于奢靡享受,自然会衰退了务实、开拓、变革的精神。
春秋战国时期,秦穆公奉行“以俭得之,以奢失之”的为政理念,勤俭治国,为秦的强大乃至后来的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基础;而秦始皇兴建豪华奢靡的阿房宫,终为“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汉初文帝执政23年,躬行节俭,以上率下,使社会形成尚俭崇廉风尚,产生“文景之治”。然而此后“崇奢”之风愈演愈烈,为亡国埋下祸根。
隋朝统一国家后,文帝力除侈靡之风,“务从节俭,不得劳人”,“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乘舆御物,故弊者随宜补用;自非享宴,所食不过一肉;后宫皆服浣濯之衣”,国安民乐;而隋炀帝却穷奢极欲,致使亡国。
公元960年,陈桥兵变,宋太祖赵匡胤从一员武将登上了皇位。多年流落江湖和长期从军的经历使赵匡胤养成了俭朴的作风,史载:“帝性孝友节俭,质任自然,不事矫饰……宫中苇帘,缘用青布;常服之衣,浣濯至再。”皇帝的专车叫玉辂,赵匡胤用的是前朝皇帝用过的“二手车”。皇后问他为何不用黄金装饰一下轿子,赵匡胤笑道:“别说用黄金装饰轿子,就是宫殿全都用黄金装饰,亦非难事。但是我当皇帝,是为天下的百姓保管钱财,岂能胡乱使用!”
然而,北宋的第八位皇帝宋徽宗即位后,前几年还励精图治,可渐渐就奢靡了起来。他宠信重用的将相大臣,也几乎个个是挥金如土的高手。重臣蔡京生性好客贪吃,经常大摆宴席,一次请僚属吃饭,光蟹黄馒头一项就花掉一千三百余贯钱。他家仅厨师就数十上百人,内部分工极细,有人专做包子,有人专门切葱丝。最终,金人南下,北宋灭亡。
沉于奢,必将百姓置于与自己完全对立的地位,当百姓再也无法忍受之时,就是统治者的覆亡之日。
历史需要常常回看。奢靡之风给每个时代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有的国破,有的家亡,有的殒身,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不良社会风气,贻害深远。无数事例也证明,反对浪费,推崇节俭,必定会提升人民的精神状态,促进吏治清明、社会向上与国家兴盛。正所谓“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侈则肆,肆则百恶俱纵”,俭与奢的影响,在“百善俱兴”和“百恶俱纵”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节选自《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