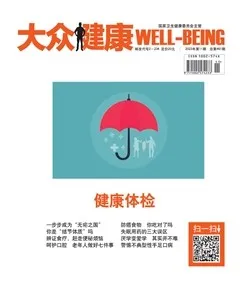人类的分娩过程为什么会有危险
一提到分娩,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危险”。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统计,全世界每天都有大约800名女性死于分娩过程,这是个令人震惊的数字。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孕妇极少在家里分娩,而是必须去医院,在产科医生、护士的帮助下才能顺利完成分娩。与此相对应的是,刚出生的婴儿也极其脆弱,目前全世界新生儿(出生一周之内)的死亡人数占5 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的一半。这也是个令人震惊的数字。
除此之外,人类在其生命的前5 年里,生活几乎完全不能自理,需要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儿童甚至连学走路都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相比之下,除人类之外的几乎所有雌性哺乳动物,都不需要任何帮助就能自行完成生产过程,而且大部分陆生哺乳动物的幼崽出生几小时之后,就可以自己走路了。
科学家们早就注意到了这一差别。美国人类学家舍伍德·沃什伯恩于1960 年首次提出了分娩困境(又名产科困境)这个说法,用来描述人类的这一独特的生理现象。他认为人类之所以有这个困境,主要原因就是直立行走和越来越大的脑容量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具体来说,沃什伯恩认为直立行走要求人类的骨盆不能长得太宽,否则会大大降低行走的效率,这就对女性产道的大小产生了反向的进化压力。与此同时,人类又进化出了独一无二的大脑袋,这就给女性的产道带来了正向的进化压力。两种相反的进化压力必须同时得到满足,所以人类只能选择牺牲另外一样东西,就是婴儿在子宫内的停留时间。婴儿必须在尚未做好准备的情况下提前出生,这就是为什么婴儿会如此脆弱。与此同时,女性的产道在两种压力下进化成了和婴儿的大脑袋刚好匹配的程度,容错能力相当低,只要稍微差那么一点儿,分娩的过程就会变得异常艰难。这就是人类独有的分娩困境。
这个说法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于是便迅速在媒体的帮助下扩散开来,成为人类分娩之所以如此危险的官方解释。但是,一直有不少人类学家不同意这个解释,他们通过严格的实验,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新证据,对分娩困境假说提出了挑战。
2023 年8 月1 日出版的《进化人类学》杂志刊登了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的人类学系教授安娜·沃伦娜撰写的一篇综述,梳理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沃伦娜在论文中列举了很多分娩困境理论的漏洞,大部分都不难理解。比如有人对比了灵长类动物的体重和妊娠期时长,发现两者呈明显的正相关,即体重越大,妊娠期就越长。比如黑猩猩的妊娠期约为32 周,而体型更大的大猩猩的妊娠期约为37 周。人类的体重介于黑猩猩和大猩猩之间,但人类的妊娠期约为38 周,反而比大猩猩更长。如果换算成同等体重,那么人类的妊娠期要比其他灵长类动物长出37 天,不存在为了顺产而提前出生的情况。
再比如,有人研究了人类孕妇的死亡原因,发现失血过多或者细菌感染才是主因,因难产而死的情况并不常见。
而沃伦娜本人在哈佛大学读博期间曾经测量过不同骨盆宽度的人在行走时的能量代谢率,没有发现骨盆宽度对能量代谢率的影响,直立行走导致骨盆无法变宽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有人曾经根据这一实验结果提出一个新的假说,认为人类女性的骨盆不能太宽的真正原因不是为了方便直立行走,而是为了增加骨盆盆底的稳定性,因为直立行走对骨盆产生的压力太大了。另外,人类女性的骨盆之所以要比男性的更宽,原因也不全是为了扩张产道,而更有可能是为了给子宫和卵巢的发育留出地方。
婴儿的脆弱性也存在不同的解释。有研究显示,婴儿之所以无法在母亲子宫内多待,原因并不是为了生产顺利,而是受到了能量的限制。母亲和胎儿之间的能量传递是通过胎盘来进行的,这种能量传递方式存在上限,通常不能超过母亲基础代谢的2.1 倍。根据计算,在母亲怀孕9 个月时,胎儿的能量需求已经超出了上述上限,所以母亲只能把胎儿生下来,改用母乳喂养,这是一种更高效的营养转移机制。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乔纳森·韦尔斯所做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分娩困境。他发现史前人类的生育过程要比现代人容易得多,分娩难的问题是在农业出现之后才变得越来越显著的。于是他得出结论:农业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饮食结构,使得农民们摄入了更多的碳水化合物,所以胎儿变得越来越重。与此同时,农民们的蛋白质摄入量反而比史前人类下降了,导致女性的身高越来越矮。胎儿变重与女性变矮之间的矛盾才是分娩困境的真正原因。
如果这个假说是正确的,那就说明分娩困境的真正原因是农业导致的食物能量过剩和质量下降。通常情况下,如果某一动物群体的能量过剩,肯定会导致出生率暴涨,人类自然也不例外。而人类的生育率之所以没有上涨得更快,原因很可能与分娩困境有关。人类母亲花在照顾新生儿上的时间太长了,付出的健康代价也太大了,导致她们无法持续地生育,也无法保证每一个婴儿都能长大成人。
换句话说,分娩困境其实就是大自然控制人口过度增长的方法之一,否则人类早就把地球资源耗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