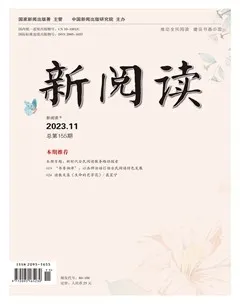打开传统帝学与宋代政治研究的新视野
宋代开国之初确立了文治的政治导向,而文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经筵制度的定型。经筵讲学,不仅为士大夫以儒家经旨义理影响帝王及其政治实践提供组织机构等方面的保障,还为帝王学习经史提供了专门的师资队伍与平台,于是“帝学”应运而生,成为宋代儒学的新动向。
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王琦教授长期从事儒家哲学、艺术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其新近出版的《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以宋代经筵讲学以及“帝学”之代表人物、著名理学家朱熹为研究对象,为学界奉献了一部朱子学、“四书”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及与宋代以帝王之学为中心的政治思想研究力作。
宋代经筵讲义的兴起
宋代的士大夫面对唐宋思想转型,纷纷致力于经典的重新诠释与思想撰述,力图以学术影响政治,致君尧舜,道济天下,从而建构起不同于汉唐传统士大夫之学的新帝王之学。以崇尚义理为特征的新经学体例——经筵讲义逐渐兴起,到了南宋初年则蔚为大观。王琦教授通过对经筵讲义文献的收集与整理,结合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学术等多方面原因分析,系统呈现出经筵讲义在宋代的发展、流传与定型过程,极具创新性。
《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一书重点回顾了宋代士大夫与经筵讲义的关系。宋代的帝王为了重建社会秩序,巩固中央集权,采用了右文抑武的策略,通过幸学、鼓励读书、科举取士等方式,将一大批有着崇高理想与社会责任感的读书人吸纳到各级政府机关之中,极大地提高了他们参政议政的热情,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士大夫阶层的崛起。随着士大夫队伍的不断壮大,国家政权对士大夫的开放度也不断增大。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一种适应帝王读书与求治需求而产生的经筵制度呼之欲出,这种经筵制度也为士大夫切入政治,根据时代与政治需要,对经典进行重新诠释,通过经筵讲学来影响帝王及其政治实践,提供了制度性平台,为宋代学术摆脱传统章句训诂的束缚,转向义理(性理)之学提供了契机,新学、蜀学、洛学、朔学、关学等众多学术流派的产生,道学的兴起与发展,就是这种时代潮流的产物。
该书系统梳理了经筵讲义在宋代的发展流传及其特点。经筵讲义能够发挥经旨义理,感格君心;联系帝王实际,语含劝诫;讲说形式自由,语言通俗;建言朝廷时政,经世致用等,从而与传统的章句训诂之学相区别。经筵讲义的产生、发展与传播,既是宋代经筵制度定型与义理之学发展的产物,又是士大夫以学术影响政治、致君尧舜的帝学形成与道学发展的重要环节,体现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交融与互动。正是在帝王与士大夫的双向互动中形成的帝学,成为宋代儒学发展的新动向。
“四书”经筵讲义与新帝学
《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研究了经筵讲义与新帝学的关系,这正是学界需要系统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宋代以文治国方略的确定,让士大夫有了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机会,极大地激发了他们参政议政、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主体意识。经筵制度的定型,则又为士大夫利用经典诠释的优先权,以学术影响帝王及政治,提供了平台与契机,一种与宋代之前重在驾驱臣民、富国强兵等帝王之“术”不同的儒家新“帝学”应运而生。在“学”以求“治”目标之下,宋代帝王部分地接受了士大夫以儒家正学来造就君德、规范政治的价值追求;士大夫们通过儒家经义的重新诠释,引导帝王学习的重心由“术”向“德”转变,将帝王外王事功的开拓建立在内圣基础之上,既满足帝王求治的需求,又确保国家的治理出于王道而非霸道,从而建构其理想的帝王之学。
所谓新帝学,是旨在与前代重治术、权术不同的帝学。自从范祖禹率先提出“帝王之学”谓之“大学”之后,关于什么是帝王之学的问题,引发了士大夫持久而热烈的讨论。如吕公著、范祖禹、程颐、胡安国、张栻、张九成、朱熹等都试图对帝学进行界定,将帝王之学与书生之学及其他学统区别开来。本书最终得出结论:新帝学是宋代兴起并由宋儒从士大夫的立场出发建构的,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以君德成就为根本,以尧舜圣王为榜样,指导帝王为学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与理论体系,是宋代经筵制度定型与义理之学发展的产物。
任何一种思潮的兴起,都是对其时代与社会问题的回应,作者进一步谈到了宋代新帝学兴起的原因。首先,新帝学的兴起是对汉唐儒法杂糅治国理念的反思。宋代面对晚唐及五代十国之乱所造成的社会失序与人心沦丧的严峻现实,如何重构政治社会秩序,成了帝王与士大夫关注的重大时代课题。宋代新帝学,正是建立在对汉唐帝学反思的基础之上,力图通过对传统经典思想内涵的重新挖掘与诠释,为社会秩序重构与个体安身立命提供理论依据与解决方案。其次,宋代经筵制度的定型,为新帝学的兴起提供了平台。宋代士大夫利用经筵平台建构思想体系,争取学术主导权,寄寓其成就君德帝业的政治理想。最后,儒家新帝学的兴起也是基于对王安石变法的反思。王安石以学术辅人主,与神宗君遇合,将儒家的理想从“坐而言”的理论推进到了“起而行”的实践,让士大夫认识到经筵正是以学术影响政治、致君尧舜,实现三代之治最根本、最有效的方法,从而激发他们通过经典诠释,建构理想的帝学热情。但由于王安石倡导的道德性命之学既不排斥释老,又对刑名法术兼收并蓄,而导致了“学术不正,遂误天下”。所以北宋中期以后,士大夫特别关注当以何种学问为“正学”,引导帝王于“正道”的讨论。以道学建构帝学、以道统规范治统,从而造就圣王明君,这种观念在南宋初年的学术与政治之中则更为普遍。
《大学》经筵讲义与朱熹帝学
作者以“经筵讲义”为视角,对朱熹帝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为了深入研究朱熹帝学与《经筵讲义》的关系,本书还原了朱熹帝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书中指出,朱熹从《王午应诏封事》以《大学》为“不可不熟讲”的帝王之学,至《癸未垂拱奏劄》言大学之道要旨,为其帝学思想的萌芽阶段;后又在《庚子应诏封事》与《辛丑延和奏劄》中,朱熹将帝王修德立政的关键归之于正君心以立纪纲,视为君臣各正其位、共治天下的根本原则,此为其帝学思想的发展期;最终在《戊申延和奏劄》《戊申封事》《己酉拟上封事》中,朱熹重新对其正心诚意之学进行反思,以正君心为天下之大本,而配之以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方面的施政纲领,从讲学明理、正心修身以至齐家、治国、平天下,设计了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具体措施,则标志着其帝学思想的正式成形。在32年间,朱熹通过多年的学术研究与政治实践,构建了一种新的帝王之学。朱熹帝学思想经历了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三阶段,三阶段内在有机联系,贯穿其中的主旨就是讲明《大学》之道以正君心,通过规范帝王的德行来成就帝业,达成社会秩序的重构与王道理想的实现,为圣王理想的确立及实现提供了理论依据与逻辑论证,从而第一次完成了以道学建构帝学的理论任务,将帝学推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促进了道学的进一步发展与传播。
面对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和异彩纷呈的学术流派,朱熹为何会将《大学》视为架构帝王之学的首要经典与理论框架?这是由《大学》自身的思想内涵、结构特点所决定的。首先,《大学》浓缩了《六经》的经旨脉络,承载了尧舜等圣王授受的心法之要。儒家的精神价值与理想追求主要承载在《六经》之中,而《六经》的经旨脉络则详细而明白地体现在《大学》之中。掌握了《大学》的纲目,帝王之学便有了一个框架与方向。帝王苟惟不学,学则必“主乎此”。其次,《大学》提供了内圣与外王的双向通道。它不仅阐发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修身治人的规模,而且指明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为学路径,体现“圣人做天下的根本”。因此《大学》为帝王和士大夫提供了一条由内圣而及于外王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目标与实践途径,儒家的君臣之伦、治国之道无不体现在其中,系统地展示了儒术纲目与儒家功夫序列。此外,经朱熹重新厘定后的《大学》经传,从逻辑结构上看,不仅提纲挈领,而且易于推寻,能够快捷明了地掌握大学主旨及进德修业的秩序,学习易见成效。作为帝王而言,如果掌握了《大学》的纲领要义,就能“取是舍非,赏善罚恶”,成为圣帝明君,成就王道政治。可以说,朱熹确立以《大学》为首而及“四书”与“六经”的为学次第与规模,无非想以《大学》作为帝王之学的理论框架与入学门径,由此融会贯通其他儒家经典,为帝王提供一种学做圣人、成为圣王的新范式。
为进一步厘清朱熹对经筵讲义的贡献,作者还从朱熹对《大学》的创造性阐释出发,指出其真正目的就是以儒家的价值理念引君于道,从而影响帝王的心性修养与政治实践,实现尧舜之治。朱熹通过多年的学术思索与政治实践,认识到通过讲学以正君心立纲纪,不仅是解决南宋王朝整体性危机的关键之所在,也是实现儒家仁政德治为核心的王道理想的根本之所在。建构帝学,首先必须确立帝王学习的经典体系,朱熹通过对什么不是帝王之学的辨析与反思,确立了以儒家正学来引导帝王的思路,其实质就是以道学建构帝学。其次,朱熹倡明儒家正学,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意义,就是以程朱“道学”为正学。朱熹所倡导的儒家正学,其实质就是宋代兴起的道学。只有以道学作为指导帝王正心修身、治国理政的“正学”,才有可能引导帝王步上符合儒家价值观念的“正道”,并进而规范“政统”,成君德立帝业。格物致知以明理是正君心之前提,诚意正心以修身是正君心之关键,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术的实施,则是君心正而后纲纪立的自然延伸,体现了朱熹以道学原则规范帝王及政治的理想追求,其实质是以道统规范治统,限君权而出治道。
该书还通过对朱熹的《大学章句》与其《经筵讲义》的比较,指出其为后世树立了一种训诂与义理兼备、汉学与宋学兼采的经典诠释范例,既避免了“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的汉学之弊,又避免了后世不问章句训诂,脱离经文原意而导致的空疏浅薄的宋学之弊。这揭示帝王之学是促进宋代经学从传统章句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转型的关键因素。这一发现,进一步揭示了经筵讲义与帝学、道学的内在联系。
“四书”经筵讲义与道学及政治
该书的另一突出贡献在于,全面梳理“四书”体系通过经筵进讲向帝王传播的过程,明确了经筵与道学、政治之间的具体关联。随着“四书”在经筵的进讲,经过宋代道学家重新诠释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思想价值不断向最高层传播与渗透,不仅推动了宋代思想学术的转型,而且逐渐获得了帝王的认可与支持,从而使得“四书”逐渐超越“五经”,成为宋明理学的新经典体系。与此同时,成为“帝王师”的经筵讲官大多为“天下第一流”人物,他们在经筵讲学的所讲所感,不仅是其一生学术思想与政治理念的精髓浓缩,而且凝聚了士林的群体意识。各学派领袖人物入侍经筵,不仅使其所进读的经典与撰写的讲义成为社会关注与学习的对象,而且促进了学派学术宗旨、思想观点与价值理念的传播,扩大了学派的社会影响力与吸引力;而士大夫之间的交流切磋,则又加速了学派之间的学术交融与思想碰撞,共同推动了宋代学术的蓬勃发展与思想争鸣。因而研究宋代道学及其学派的发展,通过“四书”经筵讲义向帝王进行传播的过程,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新视域。
作者还谈到了经筵讲义与学术、政治的关系。经筵,原本是为帝王经史教育而设置,为何会逐渐成为一个政治活动的空间?本书通过对真德秀和徐元杰等人经筵讲读记录的梳理,敏锐地意识到作为经筵讲学重心从“析章句,考异同,专记诵,备应对”到“裨圣德,究治体”,于君德与圣治成就处用力的转变。当士大夫有机会得君行道“尧舜其君”之时,他们便积极参政议政,力图实现道济天下的理想;在此过程中讲官对经典的诠释虽然有绝对的主导权,但帝王也可以通过有问有答的互动,彼此交换意见,拓展信息收集的渠道,为政策决策提供了参考,为士大夫以学术切入政治,以儒家之道教化帝王并影响其政治实践提供了可能,从而更好地奠定了“君臣共治天下”的思想基础。因而研究宋代君臣共治的政治格局,经筵也是不可忽视与回避的重要环节。
结语
在《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中,作者以“四书”经筵讲义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以及经筵进讲过程的全面梳理,探寻士大夫如何以经筵为平台,通过经典的创造性诠释,用儒家的思想观念与价值理念影响帝王及其政治,以道统规范治统、成就君德圣治,寄寓政治理想,重建政治社会秩序。并在学术思想、社会政治之间的互动中,促进以“四书”为核心经典的宋明理学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从而展现经筵讲义、宋明理学、帝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演变轨迹。该书不仅清晰呈现朱熹以道学建构帝学的全过程,填补了学术界关于朱熹与帝学思想研究的空白,给朱子学的研究提供了另一视角,而且打开了传统帝王之学与宋代政治研究的新视野,从而为当代儒学复兴与现代转化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