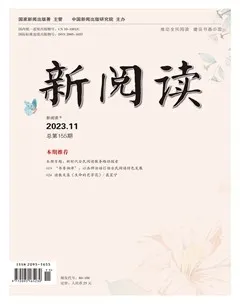从文本到图像的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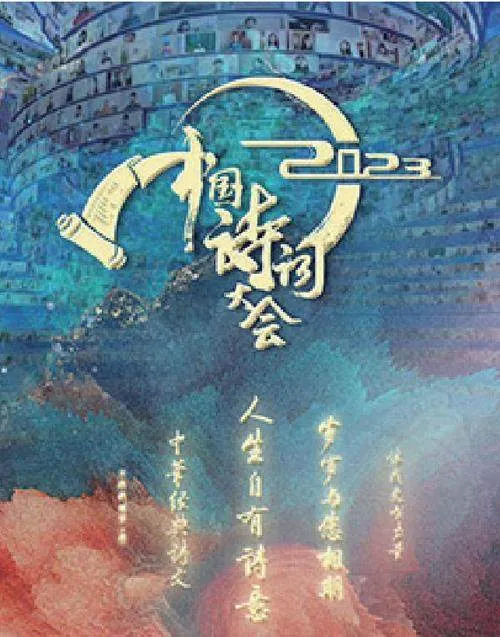
艾媒咨询旗下移动互联网产品数据分析系统发布的《2022年度中国App市场月活数据排行榜》显示,短视频平台抖音的月活超7.59亿。如此规模的用户量与传播力在传统媒体时代难以想象。如果能够利用好短视频这一传播载体,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传播,那将一定会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传统文化涉及内容广泛,风土民俗、衣食住行、历史古迹、博物艺术等均可纳入其中,而这些内容本身就具有游观性质,将其转化为影像化的大众传播,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实现无缝链接。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内容集中在中华经典文本中,如何将其从文本转化为图像,特别是进入短视频这类对青少年影响极大的社交平台,是一项重要课题。
经典文本视觉转化的可能性
经典文本的视听传播历史为其转化为短视频传播提供经验。从听说到读写,是人类从运用本能到运用理性的过程。但从接受的角度来看,本能地接受要远远易于理性地接受。传统经典文本的传播从口耳相传开始,到文字记载的阅读,从口头传播到印刷传播的历程,说明经典的文字文本形式并不是它唯一的传播途径。相反,视听传播有着更悠久的历史。在《诗经》《楚辞》配乐吟唱的阶段,还没有文本形式的广泛传播。经秦火焚毁的经典,在汉代初期都是靠老师宿儒的默诵重新整理而成。
虽然经典的文字文本传播途径窄,但是干扰少,阅读专注度高,因而传播效果显著。在大众媒介传播初期,经典传播仍然以文本方式为主,借助于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依旧保持着良好的传播效果。然而,后现代文化纷繁的视觉经验、多元的世界观、对传统和权威的挑战以及碎片化的日常生活,加之互联网带来的传播媒介巨变,经典的意义不断被消解,文字文本(包括纯语言)的形式在日常生活中的传播面临众多干扰,需要克服重重困难才能进行文化传播。
在这种情况下,经典从文本再次进入视听阶段就成为必然,短视频只是其中的一种。不过,它不是简单地探寻出路,而是新环境下解决自身传播困境的主动融入,力争以全新姿态实现自身传播的最佳效果。
经典文本的视觉化是媒介融合时代的必然
经典文本在向视觉表达和传播方面始终不懈地努力着。从电影、电视到互联网,一直都有传统文化的影子。《百家讲坛》《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诗词大会》等节目都是传统文化在视觉传播中发挥影响力的例证。文字文本的传播力衰退是显见的事实,即便在其传播能力最强的时期,印刷物的影响范围也远远不能和数字时代的媒介相比。杂志或报纸数十万册(份)以及畅销书百万册的销量都曾是令人惊奇的成绩,而这样的数量级在网络传播中往往只是起步阶段。在时间和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的当下,传统的内容再以传统的方式传播无异于墨守成规。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指出:“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非常需要乘短视频之东风实现自身的再发展、再传播。
经典文本的短视频转换
经典文本以短视频的方式传播需注意两点:一是能不能转换,即庄重严肃的经典文本能不能进入短视频这个极富娱乐色彩的领域;二是怎样转换,文字文本与图像之间的距离不只是视觉的差异,更是认知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怎样转换才能使经典文体的呈现方式符合短视频传播的特点。
一方面,高雅与低俗不是传播方式决定的,而是传播内容决定的。在经典文本内容价值毋庸置疑的前提下,转化为短视频形式非但不会折损它的价值,反而会促进其传播。只是按照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低俗内容的传播力远远强于高雅内容。经典的理论研究者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反对的一方,被视为视觉文化传播重要人物之一的西奥多·阿多诺对高雅艺术作了坚定的辩护,同时也对文化工业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认为“文化工业强行将已分离数千年的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两个半球合并起来”,不仅摧毁了两者各自的“严肃性”,而且“将利益动机赤裸裸地置入文化形态”。钱锺书先生也曾说过:“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高雅与低俗在权威文化学者那里的定义,让经典从文本走向图像的脚步不免有些坎坷。
但是,经典从文本到图像,形式上的改变会带来陌生化的艺术效果以及更大的冲击力。戴建业教授讲古诗红遍网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古典诗词赏析从来不缺乏听众,但也从未想过短视频会让经典文本的听众数量变得如此之大。这应该也是权威文化学者始料不及的事情。
另一方面,影像有自身的语法与节奏。传统文化在以短视频方式传播的过程中,其传播效果究竟是依赖原始作品的吸引力,还是依赖视听化表现形式发挥的作用,其实并不重要,甚至可以说二者原本就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赋予短视频传播艺术价值和意义,那么康德所说的“艺术的无意义形式”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理论支撑,因为体验美涉及我们对生活世界的适应性。如果仅仅是因为传播媒介特殊性,而把短视频的经典文本视觉化,看作现代技术分离了艺术的核心真理和审美经验,那传统文化走过的每一步都面临过这种困境。所以,只要视觉叙事者用新颖而特殊的工具进行叙述结构的再造,经典文本在视觉媒体中能够实现最大限度的保真,能够将传播目标、受众接受特点和视频的叙事方式结合起来,最终形成观众愿意关注的事物,就实现了经典文本阅读的意义和价值。
经典的意义和价值不是必须依附于文本形式才具有的,那么将其转移到短视频平台也不会降低或减少它的意义和价值。
谁来缩短经典从文本到图像的距离?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爱德华兹在《素养概念重塑》中指出“用图像传递含义比文字更易为人们所接受,这让视觉素养成了一种有力的教学工具,利用视觉和数字媒体的教学方法能够更好地让学生为瞬息万变的未来做好准备”。而早在1922年,摄像机的发明者爱迪生就说过:“我认为动态影像必然会变革我们的教育体系,在几年之后就会大规模甚至完全替代教科书。”现代读者必须能够彻底适应并改造自己“阅读”和“书写”世界的方式。
经典从文字文本到视觉图像,需要制作者具有良好的传统文化和视觉素养。观看如同阅读一样,“在其深层上或许是一个难题”,而且“视觉素养无法在文本模式中完全言明”。将图像认作图像不能构成素养,那么在图像的基础上,导向图像的内容、意义与功能理解和阐释就很重要了。在传统文化的短视频传播中,必须要明确,短视频制作者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图像的建构者,而是受图像意义暗示的建构者,其本身要具备一定的传统文化素养,并有赋予短视频图像力量及“观者技巧”的能力。
互联网使得教育进入泛在教育时代,只有培养出更多合格的影像制作者,优秀传统文化才能通过短视频传播,在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互动中形成良性循环。既然数字阅读和短视频阅读已经成为潮流,既不可能视而不见也无法逃脱回避,那么理应将最优秀的文化文本送上短视频这一新平台,让人们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