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物的生活世界中重识媒介
□王敏芝
【导 读】 生活世界发生着从“物”走向“非物”的范式变化, 这是韩炳哲对现代信息社会的特征判定; 生活中基于物的实在性已经被信息所祛除, 由此导致了碎片化、无根基、丧失客体关系等诸多病候。 在非物世界的生成过程中, 数字媒介发挥了决定性的技术建构作用, 数字技术为自身选择和创造了“数码物”这一非物性的物质载体, 成为信息世界主导的装置系统并最终实现了世界的“非物化”。 理解非物的生活与文化, 重点是要从技术应用与社会实践的视角重新理解数字媒介及其创设的社会情境。
从物到非物, 人类的生活世界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 韩炳哲在他的新著《非物》 中集中论述了这一观点。 韩炳哲认为, 物具有构成秩序、安定生活的功能, 从来都是支撑人们生活世界的根本构成, 是生成人们思想观念的认识论基础,但这种既有秩序和生活世界被数字化打破了: “非物全方位地涌入我们的周遭世界, 他们正驱除着物。 人们称这些非物为信息。”[1]3-4于是,人们生活在信息的海啸中而迅速丧失了物作为生活栖息地的牢靠感,“我们不再迷恋物, 而是迷恋信息和数据”[1]5, 甚至形成了崇拜信息和数据的拜物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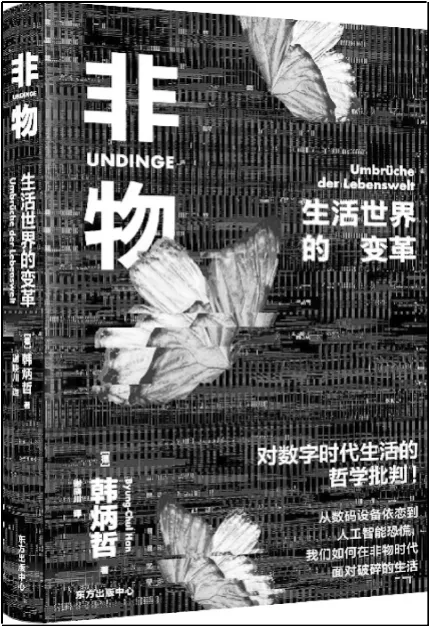
非物的信息世界从数字化开始,数字技术把世界转化成了通用数据,数字媒介广泛迅疾地收集、传播和使用着这些数据。 数字技术一方面改变了媒介的物质载体, 一方面又通过数字媒介改变着世界形态与人的感知。 数字技术/数字媒介制造的数字化转向, 真正结束了生活世界的“物的范式”, 使人们被信息包裹、生活在数据云端, 其直接的技术后果是深度媒介化的数字社会,是彻底被数字媒介文化席卷的行动与心灵。 那么, 在非物化的过程中,我们该如何理解置身其中的新世界,如何理解作为最广泛社会情境的媒介本身? 在非物的生活世界里, 我们还能不能、还要不要再次去找寻物的意义?
一、走向非物: 信息穿透了物
韩炳哲在 《非物》 中认为, 非物世界的核心表征是人们的生活世界开始由非物质性的信息或数码构成甚至主导, 这从根本上区别于基于物而存在的前数字化世界; 同时,在认识论层面, 非物质性的信息使原本可以通过物来感知的世界变得不可感, 因为信息是流动的、去形式化的, 于是, 世界便变得不可捉摸、虚无缥缈。 信息世界中的物变得越来越不被重视和关注, 或者说物的世界被全面取代。 韩炳哲认为,物的世界被取代被抛弃, 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因为即便是在工业革命之后, 机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在客观上制造了人与自然、人与手工劳作的隔离, 但人们仍然生活在物的世界, 仍然能在日常生活中被物包围, 感受到存在的坚实与可靠。 而信息时代的数字化则让人们彻底抛弃了物的范式: “它让物臣服于信息。 硬件是恭顺于软件的基础。 对信息来说, 它们是次要的。硬件的微型化让它们变得越来越小。物的互联网让硬件变成了信息的终端设备。 3D 打印机让作为存在的物贬值。 物被降格为信息的物质衍生品。”[1]6当前人们就处于这种“信息穿透了物”的现实中。
生活世界里信息的主控地位以及信息对物的全面取代, 导致的社会后果巨大而深远, 《非物》 重点讨论了信息世界的如下特征: 去历史性; 监视性/控制性; 后真相; 体验性; 信息资本主义。
第一, 信息没有历史, 也没有回忆。 历史和回忆需要跨越长时间段的叙事, 需要叙事的连续性, 但信息这种数值化的加成与积累天然地排斥铺陈与叙事, 因而, 信息世界排斥这种借由连续叙事的意义与关联而导致生活秩序的去历史性与碎片化。 第二, 信息领域具有明显的双面性, 一方面带来自由, 另一方面形成控制。 因为信息的数据特征, 信息世界充满严重的监视与控制这一事实日常可感, 譬如, 即使是在睡眠中, 我们也遭遇着智能手环或智能家居的监视, 它正在将我们的呼吸、体温、心率、睡姿等通通记录在案并转换成数据/信息。 数字技术越发达, 监视就越便捷, 它能轻而易举地渗透至衣食住行、身体心理等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 第三, 信息会让生活世界更明亮和更确定吗? 并不! 海量信息只会带来认识上的混沌, 会让人们陷入无比巨大的信息洪流而对现实无从辨识,真与假仅从信息层面而言变得没有区别, 因为假信息也是信息, 也同步在信息空间中传播流转并且和其他信息具备同样的影响力。 社会对信息传播效应的追求彻底取代了对真相的追求, 这便是“后真相时代”的秘密。 因此, 信息世界是不追求真相的世界, 是缺乏确切性与实在性的世界。 第四, 信息世界中, 体验世界的主导路径是对信息的消费,消费信息就意味着感知世界。 人们每天在智能手机上浏览, 一目万千,手指划过屏幕的时候便是人们在体验世界。 数字技术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更炫酷更多样也更稀缺的生命体验, 人们可以拥有数字分身, 可以体会第二人生, 可以进行自由人设,还可以控制关系……不得不承认,信息世界中人们的生命体验极大地丰富了。 正是因为信息消费即人生体验, 对信息的接入便强过对物的占有, 人们开始对物、对占有不感兴趣, 也开始不情愿遵从以劳动和财产为基础的“物之道德”, “他更愿意游戏而非劳动, 更愿意体验与享用而非占有”。[1]24第五, 信息世界中, 生活本身具有商品的形式,体现了商品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非物质性的事物, 比如, 人全部的社会关系都可以商品化, 因为这些都可以变成数据。 比如, 当我们观察社交媒体时会发现, 人的关系以及关系间的交流已经成为平台获利的工具, 朋友变成了朋友圈的数字,喜爱变成了点赞, 社会关系被视为商机, 甚至人们习以为常的网络“社区”以及“群组”, 根本就是共同体的商品形式。 可以说, “信息资本主义展现了资本主义的一种锐化形式”[1]28。
在韩炳哲看来, 信息世界形成的过程中, 媒介具有基础的生成性作用。 世界在智能手机那里, 体现为“完全可控的数字化表象”, 人们在智能手机上的点击与滑动, 正在影响人与世界的关系: 我不感兴趣的信息会很快被划走, 我所喜爱的东西会被放大和停驻, 我完全掌控着世界, 或者说, “世界是以我为尺度建立起来的”。 智能手机--也是数字媒介的代表--构建出的世界是数字化的、可观看的、可消费的,它祛除了物的实在性, 也祛除了世界的神秘感。 智能手机首先是图像与信息的媒介, 它把世界对象化为图像, 定性为可获取的信息和可消费的图像, 这个信息与图像的世界体现出“超现实的现实性”, 物的实在性消失了(或者说被彻底无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总是会掏出手机, “让这个装置来代理我们的感知”。 换句话说, 人们通过屏幕而不是通过身体或者物理环境来感知现实, 越过身体和物性的感知具有超现实性, 与世界发生的关联是非物质性的, 因此韩炳哲才感慨“智能手机祛除了世界的现实性”。
智能手机等数字媒介成为人们感知世界的代理, 成为人们与现实发生关联的主要界面, 跨越这个界面所进入的, 正是信息/数码的世界即非物的世界。 但非物的世界并非仅体现在生活本身的数字化过程中,更体现在媒介本身“去物质性”的特性中, 或者说, 在数字媒介祛除世界的现实物性的同时, 数字媒介本身也在迅速隐退自身的物性。
近几年学界集中关注讨论媒介的物质性, 重点在于讨论媒介作为一种存在物, 如何将其确定的物质质料、技术形式与特定目的结合起来并发挥作用的问题。 媒介物质性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 “在媒介理论的视野中, 媒介并非只是指向内容、机构以及形塑这些的社会力量, 而是作为一种基础设施和中介物, 在技术条件上提供了跨越时空的联结性, 开启了人类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感知意识, 建构了人的主体性意识,并成为形塑日常生活场景与文化实践形式的物质性动力源”[2]。 从狭义的角度理解, 媒介的物质性必然且必须与物质相关。 海德格尔也在哲学意义上讨论 “物”的多重含义,其中最基础的便是作为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 是有形的。[3]
因此, 讨论媒介的物质性, 必然要同时考虑物质、技术形式与目的, 以及这三者如何统一地体现在一种中介载体即媒介物之上。 物质和形式关注物本身以及物所承载的技术形式, 目的则强调媒介的社会效力与关系建构, 重点考察媒介物所能实现的某些意志或可发挥的某种效能。 数字媒介之所以与传统媒介存在革命性区别, 就在于数字媒介在其物质载体、技术形式与社会目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改变, 因为其技术形式的突破, 导致媒介物在物的层面上不断隐退, 或者说, 数字媒介使得非物成为物。
从数字媒介的技术特征分析,数字媒介与传统媒介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形态差异: 数字媒介是通过“数字化表征”运作的, 而其他传统媒介则不是。 数字媒介的技术规定性在于, 媒介的运行通过数字(二进制) 符号的生产和处理得以实现,这一技术规定性形成了数字媒介诸多关键特性: 首先, 数字媒介使信息更加可操控可编辑; 其次, 数字媒介通过协议, 可以成为各种用户彼此交互的界面, 从而实现重构社会社交网络的目的, 如卡斯特所说的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联结; 再次, 数字符码使文化形态的表征极易复制且以前所未有的便捷程度被传播; 最后, 数字媒介在处理信息与数据时体现出密集化特征,即通过对大量数字信息压缩的技术而将其存储于一个很小的物理空间,比如, 过去一个巨型图书馆的所有藏书都可以被数字化后装进一个小小磁盘, 甚至根本不需要磁盘, 而是一个远程据点或者是云。
因此, 数字媒介更突显其技术形式, 并更强势地用其技术逻辑改造现实世界。 媒介自身也从石板、泥块、木条、纸张等可触摸、可视见的载体形式, 变成不可触摸的界面、不能视见的信号, 许煜称其为“数码物”。 另一方面, 媒介本身越来越以技术的方式与人结合, 成为一种隐匿的存在, 它无从可感却又无处不在。 媒介作为技术手段与物质载体结合而成的技术物, 其存在可以是触目可见的, 也可以是隐匿不见的, 海德格尔用 “上手”和“在手”来表达二者的区别。 对于可触摸可见的媒介装置, 人们更容易察觉并进行研究, 但对于隐匿了的媒介装置, 则需要更强大的洞察力去发现其存在特性。 这种不易察觉的隐匿性被伊德定义为具身关系[4],即技术与人的结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斯蒂格勒为其弟子许煜的著作《论数码物的存在》 所作的序言中直接指出: “数码物本质为技术。”[5]
二、数字装置: 非物世界的生成基础
非物世界的生成有其特定的装置系统, 即基于数字技术的数字媒介。 数字媒介作为这个时代的信息载体与传播渠道, 也作为这个时代思想的物流形式, 决定了当下生活世界的非物性形态。 媒介学者彼得斯主张对媒介进行一种“基础设施主义”的理解[6], 强调媒介尤其是数字媒介对当下生活的技术建构作用, 更强调了数字媒介在总体的经济与社会数字化转型中的关键支撑功能。 数字基础设施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核心内容, 涵盖了5G、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成果, 共同推进信息世界的生成与创新。 可以说, 非物世界的生成前提, 是数字媒介作为基础设施, 正是数字媒介这种信息装置与思想的物流形式的突破创新, 才制造了生活世界前所未有的形态变革。
任何一种媒介都是由物质载体和技术手段结合构成的信息传播装置, 且二者缺一不可。 从最古老的人际传播到最普遍的大众传播再到当下深度媒介化社会的网络传播,信息传播与社会互动中所使用的媒介多种多样, 但任何一种媒介都同时具备两个基本的构件, 即其物质载体与技术手段。 最原始本能的媒介是人的身体, 这是人际交流得以实现的基础与前提: 身体就是信息的物质载体, 声音、知觉、动作等躯体功能作为技术手段, 二者结合才共同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与社会交往。 正如丹麦学者克劳斯·布鲁恩·延森(Klaus Bruhn Jensen) 所揭示的, 人的身体具有交流与传播的功能, 是最初始也是最关键的媒介, 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发挥着关键作用。[7]作为媒介的身体,具有生产性, 也具有接收性, 正是身体对信息的中介属性, 赋予了每个人交流与传播的能力。 这种具身化的传播显然造就了人类天然的媒介禀赋。
从身体发展到身体的延伸, 是媒介演进的一大步, 意味着媒介的物质载体与技术手段在其构成方式层面获得了巨大的突破, 同时带来社会发展与文明演进的重大契机。羊皮与书写的结合, 纸张与印刷术的结合, 直接催生了印刷物这种新型媒介, 它是人体的延伸, 是人的眼睛、耳朵、手臂与脚力的延伸。人们因为报纸和书籍看得更远、听得更多, 因为印刷物这一比转瞬即逝的声音更能够长久保存的物质载体而可以与历史对话。 人因为这类新媒介的诞生获得更加巨大的力量,也在与客观世界的交互中更进一步地彰显着自己的主体性, 甚至社会结构的方式也受到印刷媒介这种物质载体与技术手段特定构成方式的影响。 哈罗德·伊尼斯在讨论传播与社会形态时就举了羊皮纸卷的例子,他的结论非常笃定而直接: “罗马帝国的官僚体制, 是依赖羊皮纸卷的必然结果。 但是, 帝国的稳定有一个前提: 官僚体制要和宗教组织融合, 而宗教组织又依赖羊皮纸。 国家的官僚体制倚重空间, 忽略时间。相反, 宗教却倚重时间, 忽略空间,西方羊皮纸的主导地位, 使时间的重要性增加了。 建立在羊皮纸上的知识垄断诱发新媒介, 比如, 纸的竞争。”[8]可见, 羊皮纸卷作为媒介, 由于其物质载体较之以前的石头或木板等具有轻便易于携带等优势, 也较少地占用信息储存、传播与接收的空间, 因此, 可以帮助人们获得空间层面的扩张; 同时, 附着于羊皮纸卷之上的文字符号与书写等技术手段, 又为信息生产与接收制造了较高的技术门槛, 必然导致信息垄断从而形成权力的集中。正是关于媒介物质载体/技术手段与人类文明形态之间因果关联的洞见,使伊尼斯的媒介思想获得广泛认可。
观察数千年媒介演化史会发现,当媒介的物质载体或技术形态发生变化时, 媒介的社会与文化建构功能就会发生改变, 但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强调技术形态层面的变化:新技术会为自身寻找合适的物质载体, 比如, 书写找到了羊皮, 印刷找到了纸张, 而某一特定物质便也随着自身实现了的技术可供性而在性质上由物变为媒介。 这样的逻辑可以推演至媒介演化史上的若干次革命之中。 不同的物质载体, 比如,石头、泥板、纸张、电波等, 凭借自身的某种可供性转化为媒介。 从物质到媒介的过程, 包含着人类的创造力, 更是技术选择与技术规定的结果。 石头或者是树枝, 并非天然地作为媒介被人们使用, 而是在其向媒介的转换中体现出人技术性的、创造性的使用。 因此, 从物质到媒介的过程, 是发掘传播物质条件的过程, 也决定了媒介的物质性基础。
不同历史时期的主导媒介形式取决于不同物质载体与技术手段的结合方式, 根本上取决于技术的技术规定与物质的技术可供性, 这当然会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尤其是生产力水平, 但这一主导媒介形式一旦形成, 则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实践形成规制。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 不同时代主导性媒介的物质载体与技术手段的结合形式, 还决定着一个时代思想观念的物质化形态, 即媒介学家雷吉斯·德布雷所言的“思想的物流形式”, 用以解释人们的观念如何通过媒介化转化成为一种物质力量。[9]德布雷用“逻各斯域”“书写域”“图像域”概括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文字、印刷、视听的主导媒介形态, 认为历史演进的过程契合着上述三种思想观念的物流形式,并以此建构起他视野宏阔的媒介学理论框架。
但德布雷只是分析到了“图像域”, 伴随着互联网数字新媒介的诞生, 媒介的物质载体与技术手段又一次发生了革命性变革, 信息的承载方式、传播的技术特性以及观念的物流形式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数字媒介的诞生并非媒介演化中改进性的变化, 而是全新技术与全新载体结合之后的革命性突破。 比如,我们可以认为, 口语词、书面词、印刷书、报纸、杂志、图书馆等,这些媒介形态都属于一个 “媒介链”。[10]78因为尽管其物质载体发生了变化, 但其内在的技术手段是一致的, 都是基于语言文字符号; 同时我们也发现, 印刷书、广播、胶片摄影与互联网, 彼此间却属于媒介形态的突破式更新, 因为其物质载体与技术手段及其结构方式, 不是某一“媒介链”的延长, 而是完全另辟新径。 这种创新的媒介链,是对物质可供性新的发现, 意味着在新技术条件下, 一种新的物质转换成媒介。
显然, 互联网时代的数字技术,为自己找到了新的, 并且具有非物质性特征的物质载体--数码物。如同延森的发现: “不同的物质载体(material media) 使得我们能够接触并体验多种多样的现实世界、可能世界, 甚至纯粹想象的世界。”[10]65媒介物质载体与技术手段之间不同的建构方式, 会导致人们感受到的“世界”在认识论层面上的迥异, 这一点在口头媒介向印刷媒介、印刷媒介向电子媒介、电子媒介向数字媒介的演化过程中都得到了历史性验证。 数字媒介的出现, 颠覆了既往媒介生成的物质条件与技术基础,首次实现了现实世界与数字(虚拟)世界的整合, 实现了文本、图像、声音等几乎所有信息格式的统一,实现了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和网络传播的融合。 数字媒介以“数码物”为载体, 以数字化技术为核心技术手段, 成为当下传播中的 “元技术”。 正因为数码物的特殊性, 使信息正在成为物质, 使物质正在成为信息, 非物的世界以此才有生成的技术条件与 (非物质性的) 物质基础。
三、重识媒介:面向技术与实践的理解
如前所述, 数字媒介是媒介演化史上最重要也是最新近的革命,得益于数字通信技术与互联网技术,媒介的技术手段发生了推陈出新式的创新。 数字技术为自己找到和发明了一种新的、去物质化的物质--数码物--作为数字媒介的载体, 从而创设了一个新的、数字化的信息世界。 伴随着数字媒介的使用, 现代社会进入到一个“深度媒介化”的社会, 数字媒介为社会行动者铺就了新型基础设施, 创设了一个逐渐深度融合于物质世界的数字世界,这个世界模糊了物质与非物质的界限, 也消弭了现实与虚拟的区隔。
韩炳哲《非物》 的重点在于对当下数字化的、非物质性的生活世界进行文化批判, 直接地表达他对物的文化的眷恋。 在他看来, 物的“实在性”对人存在的意义类似于本雅明的“灵韵”之于艺术, 祛除了物的生活世界将不再能够使人安居,也难以容纳有生命力的情感, 人的存在变得“无所依托”。 但很显然,这种想法过于悲观和保守 (固执)了, 而且, 他可能也不得不承认,让生活世界重回“物的范式”并不现实。 如同“灵韵消失”并没有真的使艺术葬送而是让人们开拓了理解艺术的新视角一样, 面对数字媒介所创造的新世界与新秩序, 或许更需要的, 也是理解媒介的新思路。
数字时代的媒介, 强烈地体现出物质形式的隐退与技术形式的凸显, 甚至可以被直接理解为技术本身。 无论是麦克卢汉在《古登堡星汉》 和《理解媒介》 中对活字印刷机的分析, 还是洛根对新媒介的理解, 都表达了一个一致的观点: 媒介、技术和工具都是近义词。[10]9比如, 制造活字印刷机的机械是技术,印刷机本身是工具, 但印刷机的社会功能则是媒介。 因此, 在洛根看来,媒介本质上就是技术及其社会应用,这也体现在他对新媒体的分析上。“技术是最广义的意思, 不仅包括硬件(机器), 而且也包括一切形式的传播和信息处理, 包括言语、文字、数学、计算和互联网‘语言’”[10]9。数字技术具有强烈的“去物质性”,这一点直接影响到信息技术主宰下的生活世界的基本形态, 也形成了数字时代人们对媒介的重新理解,即把媒介理解为技术及其社会应用。
在面对技术与人的关系这一技术时代的根本问题时, 斯蒂格勒强调技术的构成性意义, 其核心观点是认为技术创造人, 人不仅是自然存在者, 更是技术存在者。 尽管技术是人的发明, 但同时人也是技术的产儿, 在技术和工具的使用中人才成为人。[11]因此, 理解技术与人的关系, 核心在于理解技术对人的构成性意义。 如果用这个观点理解数字媒介, 我们便可了然, 为什么数字媒介对人的存在状态具有如此强大的决定性, 为什么只有数字技术才会创生出一个非物的生活世界。
正是技术的这种构成性意义凸显了文化的巨大功能。 斯蒂格勒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技术问题[12], 认为人类的生命记忆与文化传承可以分为生物性和非生物性的, 生物性的记忆是基因遗传式的, 比如, 人和其他动物一样, 其生命过程都会受到纯粹生物学因素的影响, 现代人的DNA 中也包含和记载着远古祖先漫长进化的记忆, 斯蒂格勒将其称为“遗传记忆”。 另外一种记忆则只发生在人身上, 属于文化记忆。很显然, 数字媒介正在改变人们文化记忆的内容与方式,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韩炳哲眷恋 “物的范式”的文化回归表示存疑的原因, 因为数字文化正在以“非物的记忆”的方式被继承和保留。
历史地看, 15 世纪末之前的人类的生活是孤独的, “世界”被自然地理分割为不同的独立领地, 各自区隔有界且独立生活, 并没有出现大范围的有效接触。[13]在这之后,“世界”的形成有赖于经济、政治与军事等相关因素, 也得益于贸易与运输。 “然而, 将这一世界作为‘既定事实’ 置入日常事务的却是媒介”[14], 正是因为媒介, 世界才得以促成, 并成为我们可以感知的日常事务与生活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是现代生活世界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 它和社会实践紧密相关。
数字时代的生活样式所发生的巨大改变, 与媒介使用密不可分,当我们把关注点置于媒介使用以及媒介使用过程中所建立的新的需求、规范、语境与习惯之时, 我们就是将媒介视为实践。 这种理解媒介的实践范式需要一个广义的、宽泛的媒介定义, 它包括所有用于传播符号内容的结构、格式、形式和界面,而且是制度化、固定化的社会操作;同时也需要一个聚焦的问题指向,即指向媒介的社会实践: “不是把媒介当作物件、文本、感知工具或生产过程, 而是在行为的语境里参照人正在用媒介做什么。”因此, 当我们把媒介视为实践的时候, 我们是在承认, 数字时代的媒介是作为普遍的社会情境与行动依据存在的。
基特勒所说的“媒介决定我们的情境”, 提醒我们从社会情境生成的角度理解媒介。 比如, 手机, 它时时刻刻与我们在一起, 为我们提供包裹日常生命体验的信息洪流,为我们提供行动的渠道、方式和具体操作, 更作用于学习、工作、娱乐、消费等几乎所有的社会情境领域。 可以说, 手机 (媒介) 就是我们的生存环境, 就是我们的行动方式, 就是我们何以实践的关键。 数字媒介的实践性, 并不在于它前所未有的数据存储和提取能力, 而在于它使日常生活世界数字化的能力。生活内容成为原生性的数字文本或数字档案, 社会行动都成为可以“归档”的信息内容, “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使用数字档案的社会中,而是生活在一个信息社会, 其本身就是数字档案”[15]。
数字媒介作为一种实践方式,成为总揽社会空间的条件和基础,成为勾连社会关系的动力和枢纽。但在其无比重要的情形下, 媒介反而将自身隐退, 用非显在的方式将自身的逻辑嵌入社会生活与日常行动之中。 “媒介一词本身就表明媒介之藏匿不见的特性, 媒介通过自身的隐退, 使某些事物得以呈现。 唯有出现混乱和断裂时, 使用者才会意识到媒介的物质性。 这种把中介变得看上去毫无中介的能力, 本雅明称之为中介的‘非中介性’”[16]。数字时代的媒介, 无声无息又无处不在, 它隐退为一种看不见的、非物质化的存在, 内敛为一种实践的规定性, 成为现代生活的底层逻辑。
可以总结一下, 数字化的非物世界里, 媒介是技术的同义语, 是实践的潜台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