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20 世纪60 年代:电路时代的声音回路
□赵 希
【导 读】 《回路聆听: 全球1960 年代的中国流行音乐》 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安德鲁·琼斯教授的新著, 与其之前出版的《像一把刀子》 (Like a Knife)、《黄色音乐》 (Yellow Music) 共同组成了中国流行音乐研究三部曲, 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化与流行音乐研究中重要且富有影响力的成果。 本书聚焦于20 世纪60 年代, 既是从音乐的角度对“全球60 年代”非殖民化运动崛起、电子媒介技术发展等一系列历史变革之影响的聆听, 同时也是以中国音乐为例, 将边缘、乡村和更广阔的第三世界的声景汇入这一全球性话题, 并检视地缘政治、全球分工的差异如何交织于音乐的全球流通之中。
“我们如何以别样的方式聆听1960 年代--从农村边缘, 而非大都会中心? 我们怎样才能听得出一种全新的理解, 对于这个非殖民化和冷战时代的音乐与媒介史?”[1]1在《回路聆听: 全球1960 年代的中国流行音乐》 (以下简称 “《回路聆听》”) 开头, 琼斯抛出的这两个问题为本书所辐射的图景设置了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视角。 从时间角度看,《回路聆听》 是一本关于 “全球60年代”的音乐史, 它延续的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Fredric Jameson) 在“60 年代断代”中所做的历史分期及其潜能。 詹姆逊对全球60 年代的宏观描绘呈现了一组清晰的辩证关系: 当第三世界非殖民化运动崛起,并核爆为全世界土著人的解放之时,新殖民主义也在通过 “绿色革命”扩张, 工业化与资本逻辑深度渗透与摧毁了村庄, 失去土地的新无产阶级从农村流向城市。[2]13-14流行音乐如何记录并讲述了这一充满紧张感和断裂性的历史时刻? 是什么让一首60 年代的歌谣符合或背离了它的时代风格? 又是什么影响并形塑了我们对“时代风格”本身的感知?从空间角度看, 《回路聆听》 聚焦于中国流行音乐, 试图找到一条从边缘和乡村重述60 年代音乐史的途径, 汇入和扰动现有研究中那些独唱着巴黎、纽约或旧金山的单一声部。 时间与空间的双重视角让这部“声音的断代史”具有同一与差异的张力, 正如琼斯追问的那样: “在多大程度上, 跨越冷战地缘政治的分裂和非殖民化的斗争, 谈论一个共同的60 年代的声音是有意义的?”[1]4
与之相关, 标题中的 “Circuit”也包含双关之意: 既是“电路”, 又是“回路”。 电路, 关乎同时代性,具体来说, 是晶体管的应用。 作者认为, “正是晶体管将1960 年代与所有更早的音乐和媒介时代区分开来”[1]5。 在这本书中, 晶体管担任了测绘60 年代声音地貌的核心线索, 它为詹姆逊所说的“形式的断裂和其 发 展 之 间”的 “同 构 关系”[2]3提供了物质和技术条件--晶体管使得我们聆听60 年代断裂之间的关联成为可能。 回路, 则是空间问题, 是音乐类型与唱片的跨国、跨区域流动, 是音乐家与听众的城乡移民与巡回观演, 也是他们所携带的语言、文化、身份意识的碰撞。随着电路的延伸, 本书聆听的“中国流行音乐”穿越了一系列区域:中国、日本、东南亚、美国、欧洲,以及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等更广阔的第三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 琼斯听到的不只是通路, 还有“不通”: 是什么抑制甚至阻断了某种声音的流通? 技术媒介的差异化境遇揭开了60 年代的另一面, 那是冷战的隔绝和全球分工、城乡经济、地缘政治、语言身份的不平等。 聆听这种不均质性, 也实践了一种聆听历史分期的方式: 不是整齐划一的单声部合奏, 而是包含着噪音和沉默的交响。
一、晶体管: 上天入地的微型革命
在本书 “序言”中, 琼斯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并置了两首在20 世纪60 年代极具影响力的歌曲: 《东方红》 和披头士(The Beatles) 的“All You Need Is Love”。 前者是一首改编自陕北民歌的革命颂歌, 后者是采用了多轨人声和混合节拍的流行歌曲, 听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历史和美学关联。 但琼斯发现了两首歌曲的重要交点--它们都通过晶体管支持的传播网络而变得无处不在。 20世纪60 年代, 当《东方红》 通过有线广播系统传遍中国村村落落时,“All You Need Is Love”通过第一个全球卫星直播电视节目OurWorld播放给了24 个国家约4 亿观众。 几年后, 中国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 让《东方红》 的旋律巡游太空, 响彻宇宙。 在作者看来, 晶体管化的电子技术组成了影响力空前的通信网络, 让这些声音轻松地传遍世界, 甚至上天入地,这正是60 年代声音景观的时代特征: “拆开1950 年代末开始遍布中国城市街道和乡村广场的千万个公共喇叭, 你会发现廉价的晶体管。刮开一颗卫星的表面, 无论是‘东方红1 号’ 还是将披头士播送到全世界的国际通信卫星组织站点, 你都会发现一系列晶体管电路, 将太阳辐射转化为可用的能量, 又将超短波信号传回地球。”[1]6

晶体管
晶体管, 是一种类似于电流“阀门”的半导体器件, 可以对穿过其中的电流起到放大、开关、引导、调节等作用。 这个在1947 年发明于美国贝尔实验室的微小装置, 却在随后半个多世纪里掀起了一场“微型革命”。 在《微型革命: 半导体电子学的历史和影响》 中, 两位作者强调, 半导体电子技术发明和应用所造成的影响是超乎想象且与日俱增的: 计算机、自动化、通信卫星、太空探索、晶体管收音机、便携录音机、电子计算器……新的产业、职业、生产和组织方式也随之诞生。[3]到了20 世纪60 年代, 晶体管得以普遍化应用并带动电子工业爆炸性增长, 也引燃了音乐生产、流通与消费的变革。 《回路聆听》 每个章节都追踪着晶体管在60 年代中国不同区域和角落的声音轨迹。 第一章中, 晶体管组成的媒介网络让香港女明星葛兰唱着来自古巴的舞曲亮相于美国电视。 第二章聚焦大陆农村的有线广播, 晶体管扩音器搭建起一个辐射全国的社会主义传播网络。 第三、四、五章转向冷战背景下声景混杂的台湾, 琼斯不仅听到了晶体管收音机播放的英美歌曲、台语歌曲、翻唱歌曲和现代化“民歌”, 还照亮了一个重要史实:在20 世纪60-70 年代, 日本和中国台湾相继成为晶体管收音机及电子产品全球重要出口地。 因此, 以东亚的耳朵来聆听这场 “微型革命”的必要性也不言自明。 第六章将麦克风递给邓丽君--这位开启了一个新时代音乐美学的歌唱家, 她的音色、唱法、录音和收听方式, 与彼时便携式收音机和家用录音机的消费相互达成。
值得关注的是, 尽管极力强调技术的基础性影响, 琼斯对于技术和媒介的态度却并非如“技术决定论”这个短语听上去归结得那样简单。 受启发于布莱恩·拉金 (Brain Larkin) 对尼日利亚媒介与基础设施的研究, 琼斯提醒道: “从技术进步畅通无阻的抽象模型中提取出的媒介理论, 存在着将理想误认为现实的风险。”[1]18因此, 技术的贫乏、干扰甚至崩溃, 当地的地理、资源与经济条件的限制, 以及普通实践者自身的能动性与灵活性, 同样需要被听到。 《回路聆听》 第二章对农村有线广播网的研究, 是充分呈现这种技术、地缘与人为之间调适与协商的绝佳案例。
有线广播网络对于20 世纪50-70 年代社会主义生产、组织和宣传的作用似乎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1955 年10 月,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发展农村广播网”, 开启了全国性的有线广播建设热潮。[4]农村有线广播, 根据一本1966 年出版的技术手册, “就是在县市级城镇或公社成立一个有线广播站, 安装上有线广播设备, 在生产大队、生产队办公室或者农民住房里安装广播喇叭, 并通过广播线路把广播站和用户喇叭连接起来”[5]1。相较于无线广播, 有线广播具有成本低、保密性强、覆盖范围广等优点: “不管是住在广阔的平原地区,还是住在浓密的森林里或崎岖的山区里, 凡是有广播喇叭的地方, 都可以收听到广播站播送出来的各种节目。”[5]1然而, 该手册也指出, 线路和喇叭的维护会带来很大的工作量, 情况又复杂, 要克服这些困难,“只有充分发动群众, 把技术教给群众, 并取得群众的积极支持”[5]1。
这些地方群众自行调适技术的“土办法”, 在琼斯看来, 对技术进步论的线性叙述提出了有力的疑问:60 年代, 当麦克卢汉宣称一个依赖着电力技术紧密相连的 “地球村”来临之时, 中国绝大多数村庄还没有电力供应。[1]63-65也正因如此, 能在资源匮乏的广大农村地区建立有线广播网络, “土办法”呈现了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复杂样态, 并非旧技术被新技术淘汰那样简单。 在第二章中, 作者分析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 辽宁人民广播电台研制的TY5727 型有线广播设备, 依靠一头驴来发电, 利用牲畜拉磨的方式牵引着滑轮和发电机, 供给一台25瓦的扩音机。[1]65为了应对牲畜的生理因素给发电带来的不可控风险,该电台结合农业经验提供了详尽的操作指南, 包括“给牲畜戴上‘矇眼’”“选用善于拉磨的驴或骡”“当广播前做准备工作的同时应使牲畜便尿一次”, 等等。[6]琼斯指出,这样一头驴子, “理论上能够为不少于250 个扬声器提供动力, 轻松地为整个村庄及其耕地提供广播节目”[1]65-67。 在尚未解决电源的广大乡村, 类似这样因地制宜的“土办法”, 搭建起无数个小型广播站, 使得社会主义媒介网络能够延伸向旱地和山区。
正是在这种电力匮乏的背景下,晶体管以其廉价、轻便、效率高的优势, 惠及了60 年代的中国城市和偏远乡村。 琼斯追溯了自50 年代末晶体管在中国的早期发展史: 1957年中国已经开始生产晶体管音响设备, 1958 年北京无线电器材厂推出“牡丹牌”晶体管收音机, 几年之后, 便携的晶体管收音机、麦克风、扬声器不仅广泛可得, 并且延伸到农村地区。[1]68随着城市青年的上山下乡, 晶体管收音机方便他们将音乐随身携带, 如作者所说, “晶体管电子技术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催生了新的交通方式, 并在60 年代末加快了农村声景的转变”[1]69。 这场电路上的微型革命, 用声音信号将中国各地无论是田间还是街道的人们连接在一起, 就连在太空也能听到熟悉的旋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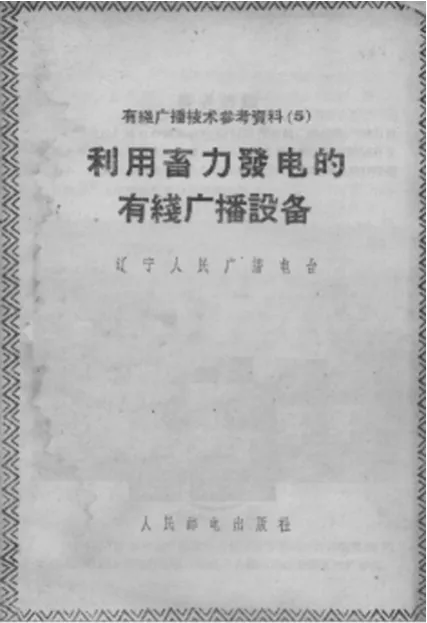
二、音乐类型: 全球流通的白话调制
晶体管电路不仅沟通了城市与农村, 也允许来自地球上某处的声音跨越大洲和海洋, 流通向世界各地, 以别样的方式在另一个时空产生回响。 在电路时代的声音巡游中,音乐类型(music genre), 即对具有特定属性音乐作品的分类, 意味着什么? 对此, 琼斯发出了一系列极具洞察力和启发性的追问:
音乐类型是如何进入全球流通的? “类型”是否本身是一种“旅行皮箱”(portmanteau) 或集装箱, 让音乐变得全球便携? 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类型既不是本质, 也不是特定的剧目, 而是全球流通形式的白话调制(vernacular modulations), 在迁徙和大众媒介的回路中回响? 我们如何聆听和追踪这种回路的结构?在一个录音和声音日益便携的时代,它们会诉说何种关于音乐形式的流动性的信息? 某些类型的日益全球化的播散, 以及因此它们作为大众媒介商品的可替换性, 是不是20 世纪60 年代音乐的一个重要预兆?[1]30
“白 话”(vernacular), 也 译 作俗语, 是琼斯在讨论音乐类型时反复提及的一个概念。 著名电影学者米莲姆·汉森 (Miriam Hansen) 的“白话现代主义”(vernacular modernism) 为洞悉这里的“白话”用法打开了一扇窗口。 汉森指出, 美国好莱坞的经典电影之所以成为一种全球可译的“白话”, 实现跨国家、跨语言、跨文化的流通, 不仅是因为其提供了普适的叙事模式和美学效果, 同时也经过了各地本土语境的调制。[7]延续汉森的讨论是这里的意旨之一, 而作者还有一个重要的对话对象是美国文化史学家迈克尔·丹宁 ( Michael Denning) 的著作《噪音起义》。 《噪音起义》 播放了一段特殊的历史: 从1925 年电子录音引入到20 世纪30 年代大萧条短短几年内, 一场 “噪音革命”爆发,并构成了整个20 世纪的音乐革命的核心。 商业录音公司用留声机录下了哈瓦那、开罗、雅加达、火鲁奴奴殖民地音乐家的 “白话音乐”(vernacular music), 制作了成千上万张虫胶唱片, 这些音乐类型后来以新的名字在全球范围内回响: 颂乐(son)、伦巴(rumba)、桑巴(samba)、探戈 (tango)、爵士 (jazz)、卡里普索(calypso)、法多(fado)、弗拉明戈 (flamenco), 等等。[8]2丹宁从白话音乐中听出了反殖民斗争中饱含张力的节拍: 它们来自殖民地港口群岛数以万计的移民工人,每一种音乐类型都像白话语言一样有自身独特的语法和词汇--节奏、乐器、舞蹈。 当这些白话音乐通过唱片在殖民帝国世界里回荡, 一场耳朵与身体、音乐与文化的挑战奏响了非殖民化的序曲。[8]6-10
琼斯将“噪音起义”推进到20世纪60 年代, 并分析其在经济、交通、技术等基础设施的变化之中呈现出新的样态: “绿色革命”引发农村人口向工业城市移民, 晶体管收音机、录音机在发展中世界渗透,喷气式客机对民航业的拓展, 多式联运集装箱航运确立了全球标准,推动了世界市场的紧密连接。[1]23许多新的音乐类型, 正是诞生于大范围的城乡移民和全球流通之中, 比如, 源于60 年代牙买加、后来风靡世界的雷鬼音乐(reggae), 其独特的节奏律动里内含着美国、非洲、加勒比地区的跨洋线路。[1]10-11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 “回路聆听”成为最忠实于时代的聆听方式, 如琼斯所说, “所有的本土音乐(local music) --尤其是在现代商业录音时代--都是由它们所嵌入的特定媒介和移民回路构成, 并需要在其中被历史化”。 而回路聆听“可以帮助我们避开那些模糊地归因于单向度的、看似受到不可避免的影响的音乐诠释, 同时让我们的耳朵打开,听到任何全球文化的本土调解之中所包含的代理性、不可化约的动态性和复杂性”[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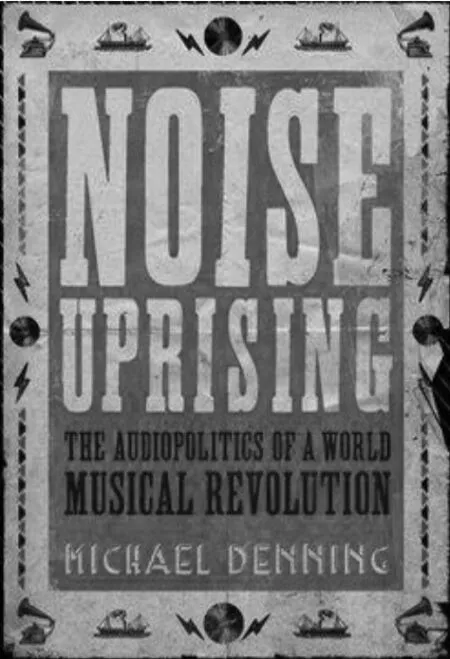
第一章中的女明星葛兰和她标志性的曼波 (mambo) 舞曲, 就充分展现了这种音乐类型全球流通的复杂性。 葛兰(Grace Chang) 是20世纪50-60 年代活跃在华语歌舞片中的著名演员, 以能歌善舞的活力表演著称, 其代表作《我要你的爱》历经徐小凤、梅艳芳、叶倩文等众多歌手翻唱, 至今仍在广为流行。对当时的中国观众来说, 葛兰的角色具象化了战后香港对国际文化的拥抱和现代性的追求, 而这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她所唱的那些直接指涉外域类型的歌曲, 如 《曼波女郎》、《我爱恰恰》 (cha-cha)、《我爱卡力苏》 (calypso)。 流利的英语、熟练的美声演唱技巧和热情自由的舞蹈, 也让她被视为一个深受西方流行文化影响的新女性形象。 与此同时, 当她受邀登上美国电视表演并得到百代公司旗下国会唱片(Capitol Records) 录制的机会时,又被冠以“东方夜莺”“香港的葛兰”的标签。 无论是西方文化影响东方还是东方声音输出西方, 这些单维的理解都很难穷尽葛兰这一文化现象的多元性, “回路聆听”则有效地避开了这些二元对立的陷阱。琼斯认为, 葛兰并不能被视为单一之地的产物, 而是深嵌于多重回路:“从殖民时期的上海延伸到香港, 再到东南亚和台湾的离散华人聚居地,横跨太平洋至好莱坞和叮砰巷, 从纽约市到古巴、特立尼达和牙买加等加勒比岛屿--她的音乐素材大多来自这些地方。”[1]35
曼波和普通话一起, 为葛兰的跨洋流通颁发了重要的通行证。 作者进一步追溯了曼波作为一种“全球白话”(global vernacular) 的旅行轨迹: 由非洲-加勒比地区音乐融合而来, 在流动过程中消除了那些不易翻译的部分, 保留具有高度辨识性的特色, 经过一定的简化和空心化, 成为方便各地复制的音乐白话。 于是不仅有《香港曼波》 《意大利曼波》, 还有《宝岛曼波》 《山东曼波》。[1]41-42也许这些本土化的曼波在音乐特点上与加勒比地区的原始曼波已经相去甚远, 然而“回路聆听”的方法启发我们: 与其将曼波、卡里普索这样的音乐类型理解为诞生于一地、影响了另一地的文化输出, 不如将其视为全球流通这个过程本身的产物。 曼波不属于任何一个本土, 但同时, 每一个本土都可以变奏自己的曼波。 音乐白话的跨国性和在地性由此构成交织而和谐的对位法。

尽管如此, 琼斯提醒我们同样不要忽视那些 “被关闭的回路”(closed circuits)。 地形、语言、基础设施的限制, 深嵌于全球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和分工的不平等之中。对它们而言, 时代许诺的自由流通是一种触不可及的神话, 正如作者在书中两次强调: “并非所有电路都是平等的, 它们不能获得相同的电源。”[1]37第一章中另一位曼波歌手洪一峰, 由于缺乏资本公司的支持和普通话的通行证, 无法像曼波女郎葛兰那样畅通无阻。 第三章中的台语歌手文夏, 他的音乐和电影如他所塑造的农村移民一样, 在不断追逐城市路途上的流浪。 这些被阻断的声音, 也折射出詹姆逊描绘的60 年代的“月之暗面”: 绿色革命、城乡移民, 与新型生产方式和技术条件下的社会不平等。
第五章中台湾民歌手陈达的故事更加耐人寻味, 它显示了电路时代民歌--或者说本土音乐的难题。1967 年, 台湾音乐家史惟亮和许常惠在“民歌采集运动”中, “发现”了恒春乡下的民歌手陈达, 弹着月琴、演唱着恒春民谣《思想起》。 在70 年代“唱自己的歌”的民歌运动中, 陈达又被邀请到台北餐厅、大学里表演, 被视作民歌与本土文化的标志性人物。 陈达作为文化符号的回响不绝如缕, 缅怀陈达的歌曲《月琴》 中的一句 “再唱一段思想起”也成为2015 年“民歌40”纪念活动征引的主题句。 也许正因如此,既有研究通常以追溯的视角, 聚焦于陈达与民歌运动之间的关联, 讲述70 年代校园民歌如何继承和接续陈达的民歌精神。 然而, 思想层面的叙事并非总是与音乐层面同频。琼斯正是在声音中听到了二者的参差, 并敏锐地提问: 为什么以反殖民主义为初衷的民歌运动, 在音乐上却采用了英美流行的木吉他与和声结构, 而陈达民歌中的那些本土特色, 并没有真正被保留和延续?[1]137答案有些出乎意料: 它或许是个格式问题。 作者分析, 陈达民歌表演的独特之处, 包括即兴的创作和修改、灵活多变的声学效果, 尤其是经常跨越两首歌曲边界自由扩展时长的演唱方式, 使它们超过了黑胶唱片(Long-Playing Record) 所能承载的最大时间容量, 更不适合广播、电视等时间流更快速及格式更标准的媒介。[1]155-156而校园民谣的青年歌手们, 深受鲍勃·迪伦(Bob Dylan)等60 年代风靡全球的英美民谣影响, 弹着大规模生产的木吉他, 唱着时长、曲式、节奏均标准的流行化“民歌”, 与黑胶唱片、晶体管收音机和商业电台的技术与审美偏好完美适应。[1]162最终, 陈达的民歌成为只见其名、难闻其声的奇观, 而校园民歌则汇入了全球民谣复兴的余波--那是另一种60 年代全球流通的音乐白话。
三、音色: 美学、技术与网络踪迹
在聆听了60 年代各种声景后,本书的最后一章将耳朵转向了邓丽君--一位被公认为开启了声音美学新时代的坐标式歌手。 不过, 琼斯所着重聆听的并非作为历史人物的邓丽君, 而是邓丽君作为“一种特殊的音响效果, 一种情感可供性(affective affordance), 甚至是作为一种家用电器”[1]173。 换言之, 作者将邓丽君的歌声置于技术、人声效果与听众接受方式的多元互动中, 来聆听她所嵌入并牵动的那个转折性历史时刻。 为此, 琼斯别出心裁地选用了“音色”(timbre) 这个概念作为追踪邓丽君的线索。 作者首先综述了“音色”的理解和阐释的历史: 在18 世纪, 音色原本用来形容乐器的声音特质, 后来也被用于人声。 相较于响度和音高, 音色由于超出了声学符号的描述范围, 而成为一个有些难以捕捉也更加灵活的概念, 与特定历史时间中的人、乐器、地点都有关联。[1]173紧接着, 作者提醒我们, 在多轨录音室时代,尤其是在数字化声音工程之后, 音色不能再被仅仅理解为一种真实的物质性印记, 因为录音师们会使用足够多的技术来精心制作音色, 如回声、混响、延迟效果等, 还可以利用软件自动调谐。[1]174由此, 琼斯提出, 音色就像一种 “网络踪迹”(network trace), 记录着其所在时代的技术环境、听觉实践和审美关注形式。 在此意义上, “网络也是一种‘乐器’”[1]174。
邓丽君的音色, 或许正铭刻着那个划时代的网络踪迹。 琼斯没有亲自去解读邓丽君的歌声, 而是聆听了当时的人、邓丽君的听众们如何聆听邓丽君。 他听到, 无论是喜爱她的歌迷, 还是厌恶她的反对者,二者对邓丽君音色的识别与感知是相通的: “一种从呼吸中产生的肉身感, 在一个音符前几乎难以察觉的吸气声, 一种声母的咝咝声, 增强和延长一个音节的颤音, 或一个乐句趋向沉默时的轻微鼻音叹息。”[1]187这种极具身体感和亲密性的音色,被一些人形容为浪漫的、柔和的、亲切的, 而对另一些人来说, 则是堕落色情的“黄色歌曲”。 十分有趣的是, 在《怎样鉴别黄色歌曲》 这本名噪一时的音乐论文集中, 许多严肃愤怒的批评家对邓丽君音色、发声技巧和听觉效果的分析非常精准和详细, 展现了较强的音乐学和语言学的综合分析技术与文本细读能力。 琼斯特别关注了其中周荫昌的文章, 这位专业的音乐家以义正词严的语调却十分敏锐地捕捉了邓丽君独特音色的发声技巧, 包括“大量地采用轻声、口白式的唱法”“以气裹声”“吐字的扁处理”“大量地使用前、后、上、下滑音, 及短时值内装饰性的颤音”, 以及“演唱中使歌腔延迟出现和重音倒置”。[9]24更重要的是, 周荫昌还听出了邓丽君歌声的技术环境: 多轨录音室的使用, 使得人声与多种乐器形成了清晰分明的层次, “结合成一个融浑的整体”[9]23。 在琼斯看来,周荫昌对邓丽君的聆听实践准确地描述了其演唱风格相关的技术条件,既包括麦克风的使用带来的身体性的亲密感, 也涉及双声道家庭立体声系统, 将家庭空间内的听众预设为声音网络的一部分。[1]191
在这个意义上, 琼斯将邓丽君解读为一种“家用电器”, 不仅是一个比喻, 也连接着邓丽君所处时代的媒介消费与经济背景。 他指出,邓丽君在台湾的第一次飞跃是在1968 年, 此时台湾成为电器和电子产品的制造商和重要出口商, 邓丽君担任岛上第一个彩色电视综艺节目《每日一星》 的主持人, 又为电视连续剧演唱热门主题曲。[1]1781981年, 邓丽君成为日本雅马哈公司跨国广告的代言人, 她骑着机车“跑速乐”的形象在亚洲各地的电视上播放。[1]181而当她的歌声飞过海峡,又被大陆的听众以晶体管收音机接收, 成为人们在私密空间里偷偷享用的信号。 在许多的论述中, 邓丽君的歌声唤起的私密性往往与个体性的追求、个人情感的释放相连接,并被解读为对过去时代集体性聆听方式的反拨。 但新颖的是, 琼斯的分析并没有滑向这个可预测的方向,而是指出了这种分析思路的潜在问题: 制造了截然的二元对立--集体与个人主义, 落后与现代化, 压迫和自由。[1]186取而代之, 作者以一种别开生面的方式并置了20 世纪50-60 年代的声景与邓丽君的新声,对比了两种不同的声音美学里如何铭刻着当时媒介网络的痕迹。 他分析, 以 “高、快、硬、响”为主的革命歌曲被有线广播网络的技术条件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音域较小的旋律特点不仅是为了便于集体演唱,还因为反射式号角喇叭的频率范围极其有限, 几乎没有低音响应。 因此, 这时的公共音域是向中高音及以上倾斜的。 同时, 单声道使得在合唱中很难分离出个体的声音, 而缺乏近距离的录音技术又会使声音呈现颗粒感、低保真度和失真的效果。[1]187换言之, “高、快、硬、响”不应仅仅被理解为一种政治或美学选择, 同时也包含当时技术条件下一定的必然性。 而在邓丽君唱片制作的新技术条件下, 饱满的低音、切近的人声、宽广的频率、多层次的立体声都成为可能, 封闭而安静的室内环境也便于听众专注地品味邓丽君音色中携带的微妙情绪。[1]193
琼斯对这两种音色的聆听, 重审了技术、人声与美学--或者说更广义的“文化”的关系: 不只是技术记录和保存了人声及其所承载的时代美学和文化, 同样地, 技术也在人声的表达空间与听众对声音的感知方式中留下印痕, 进而影响甚至塑造了一个时代的审美, 并沉淀成我们称之为“文化”的一部分。音乐家与声音研究学者米莉亚玛·扬(Miriama Young) 提出, 从留声机的发明起, 到磁带、唱片、MP3 和现在的电脑, 技术一直在以或直观或隐微的方式改变着人们对嗓音和“身体”这个概念本身的感受、理解与想象, 它可以保存身体、驱逐身体, 可以使人们崇拜无身体的声音,也会在数字时代重新召回声音的身体。[10]
关于邓丽君的“身体”, 琼斯引用的两个小故事值得回味: 一个是邓丽君在试图偷渡日本时在机场被粉丝认出, 而没有成行; 另一个是她去世之前都没能亲自现身在祖国大陆。[1]194然而, 肉身的阻隔并没有影响邓丽君的声音回响在全世界的媒介网络中, 让电影《甜蜜蜜》 中的两位主人公重逢在纽约街头, 相视一笑。 2022 年与2023 年, “虚拟邓丽君”两度登上大陆地方卫视的跨年晚会, 将继续吸引我们思考VR时代的声音、技术与身体问题。
四、结语: 作为方法的“回路聆听”
我们能从《回路聆听》 所呈现的聆听方式中, 听到哪些关于音乐、声音以及文化研究方法的启迪? 首先, 如琼斯多次强调, 对于一种声音回路的全球追溯, 有助于避免“东方”与“西方”二元对立和单向决定论的陷阱, 同时让我们听到来自世界各地更多元的声音, 比如,在现代音乐的发展中演奏着重要声部的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以及更广阔的“全球南方”。 一个富有意味的细节是, 作者在引言中的一个小小注释中谈及他对华语语系研究 (Sinophone studies) 的反思。他认为, 将 “Sinophone”这个后来的概念应用到语言、身份、文化认同复杂的当地历史中会导致时代错置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 “回路聆听”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与其他许多世界各地近邻和远邻的联系,这不是仅仅关注“华语语系”就可以完全涵盖的。[1]208在这个意义上,跨国家、跨地域、跨语际的全球史视野, 或许才是我们更值得寻求的方法。
另外, 追索网络、交通、巡回带来的声音流动性, 需要关注支撑或阻碍其流动的基础设施与媒介环境, 不仅包括交通工具、空间线路、通信设备等具体的物质技术, 还应注意移民、语言等文化的层面。 这些基础设施变革和人员流动给艺术带来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想象得更早、更深刻。 约书亚·戈尔茨坦(Joshua Goldstein) 对晚清京剧的研究表明,铁路、火车和汽船的出现将全国大小城市连接为一个交通网络, 方便北京的戏班子巡回演出, 刺激了更多的商业资本流向剧院, 在晚清京剧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11]饶 韵 华 (Nancy Yunhwa Rao) 对跨洋粤剧的追踪显示, 早在20 世纪20 年代, 移民群体就把粤剧传播到了北美, 开设了一个个华人戏院。[12]马彦君(Jean Ma) 则展示了“歌女”的银幕形象与歌声如何从战前上海延续到战后香港, 跨越了战争、地缘与时间。[13]
最后, 让我们再次回到詹姆逊,完成本文的一个回路。 在21 世纪的今天再去聆听60 年代一种边缘的声音, 有何种意义? 60 年代, 如詹姆逊所说, 当第三世界非殖民化运动爆发, 点燃一系列关于解放的可能性之时, 晚期资本主义也开始渗透乡村, 由此60 年代成为全球范围内体制重构的过渡阶段。[2]50而当前社会, 在他看来, 跨国资本主义网络与消费文化蔓延全球, 城市的建筑形成一种抹去时间感和距离感的“超级空间”(hyperspace), 人们迷失于这种后现代的景观之中, 难以再以感官系统组织周围的一切, 也无法认知自身在外界中的位置和方向。[14]后现代的身体被暴露于直接的感官冲击之下, “无论是漫步在后现代的酒店里, 还是被耳机封锁在摇滚乐中”[15]351。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陷入一种感知的悖论: 越是忠实于一人、一地的实际感知,反而离真实的世界越遥远, 被同质化、扁平化的幻景所捕获。 我们拥有前所未有发达的通信设备和高解析度的耳机, 却鲜少听到第三世界和乡村、边缘的声音。 詹姆逊提出“认知测绘”(cognitive mapping),鼓励我们穿透空间的迷雾, 在全球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中寻找定位,将局部与全球相连。[15]353回路聆听正是一种认知测绘, 而某种意义上,认知测绘也是一种“回路聆听”。 无穷的远方, 无数的人们, 都和我们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