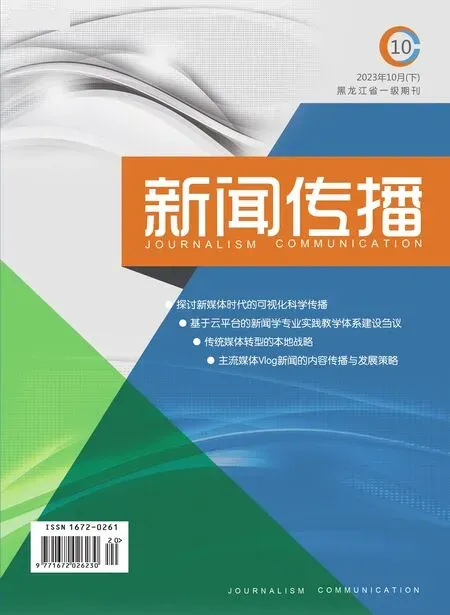数字霸权语境下个人信息传播向度的研究
王唯先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英文名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309 Regent Street,London W1B 2HW]
过去几十年间,全球化进程推动着世界各地的经贸发展,也催化数据、电子、信息产业的科技创新,层层迭代下数字革命已然形成势不可挡的浪潮。在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者看来,数字革命将会给人类带来空前团结,在协同发展中迈向真正的平等繁荣。而持批判态度的学者则尖锐指出:对数字技术的掌控力及对数据产业的参与度成为人类社会的比例尺,穷人越来越穷,有钱人的资产却像滚雪球一样增长,信息技术垄断与数据媒介霸权恰恰是这一切的元凶。与此同时,科技的负能量也辐射到大众身上;普通人类生活不断与大数据、算法等“新技术”相融合,人们几乎是被动地与之产生依存关系毫无抗性,却连自己最基本的信息安全都没法保障。活在当下,我们已经很难将“大数据”从日常生活中剥离,越来越多人也由此提出诸多质疑:在享受大数据提供便捷服务的同时,人们又在以什么身份与其构成互动关系?
一、大数据革命:我们的生活逐渐“透明”
大数据(Big Data),一个诞生于数字革命浪潮中却无法被具象化定义的时代新词。作为国际性新闻商业周刊《经济学人》的长期供稿人,美国资深信息学者肯尼思·库克耶(Kenneth Cukier)在其文章中使用“大数据(Big Data)”一词来形容信息以数据形式广泛流通的时代,在总览技术的发展脉络过后对这项技术的发展趋势持积极的“技术拥抱者”态度,认为原本没有价值的数字信息即数据能通过这项新工具的发明实现有效挖掘[1]。汤姆·布鲁尔(Tom Breur)则将大数据解释为一种不适应于传统分析治理方式的数据集成,但偏偏又因其蕴含的巨大潜力使得人们针对它的开发需求持续激增[2]。纵观人类今日生活也确实如此:数据的采集、传输、储存、分析等技术在不断地优化更新,互联网已经能自动生成一个人的数据痕迹,交流讨论、视频点播、网上购物等行为已不再仅作为隐私而存在,整个世界正在逐渐成为一大堆可以被测量和优化数据的集合。而对于以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及持续发展,西方学界也秉承了一贯的批判态度。其中,法兰克福学派哲学与社会理论家马尔库塞的思想较具指向性,其提出的技术理性霸权是指技术在受政治深度影响下产生的极权主义形态,而在经历技术迅猛进步、生产力极大提升、资本持续介入后,技术的异化将使支配具备合理性,成为消解个人主体性的统治工具[3]。蒂兹纳·特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则批判大数据语境下互联网自由劳动的虚伪,并揭示互联网公司运用大数据进行用户遴选,打着自由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的旗号实行营销工作的事实[4]。从有关于技术的讨论开始,到如今互联网时代被巨头控制的威胁,人类发展技术进步的同时反思和批判也从未停止。
倘若文章至此所展现的内容稍显欠缺吸引力和趣味性,不如让我们来讨论几个生动直白的例子。希伯来大学历史系教授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在他的畅销书《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里引用过一个值得深思的案例来探讨大数据:2012 年,生活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位男士怒气冲冲地闯进了他家附近的一家TARGET 店铺进行抗议,他气愤地指责TARGET 居然给他尚在读高中的女儿寄了孕婴产品优惠券。此事在店内引起了轰动并且终由经理出面致歉了结,但在几天后的电话回访中这位父亲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她女儿的确怀孕了,并曾经在TARGET 购买过母婴用品,TARGET 比这位父亲得知女儿怀孕的时间足足提早了一个月[5]。另一个案例则发生在COVID-19 疫情期间,视频软件使用率激增,人们因社交传播范围缩短不得不竭尽所能地将科技融入生活;办公、学习、娱乐,甚至婚礼和葬礼都可以在网络上如期进行。但2020年4月15日,美国科技媒体Bleeping Computer披露了视频会议软件Zoom 存在重大安全漏洞:约有超53 万个Zoom 账号密码在暗网被黑客以极低价格出售,但其实在当年3 月就已经有认为该软件的视频和语音通信方式存在暴露用户登录凭证风险的消息传出,更有人发现云端上储存的海量视频被上传到其他媒体平台[6]。对Zoom 公司而言这可能只是一个强时效性的“舆论风波”,但它也恰好警示着个人信息安全与数字技术发展的对立;从工作到生活,所有举动都能被信息工具记录,越来越“透明”;仿佛置身于“全景敞式监狱”,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注视之中。
二、深入心灵的监视:如同置身于“全景监狱”
全景敞式监狱(Panopticon)来源于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设计构想:空间以环形建筑构建并在其中心竖立一座360°覆盖环形窗的瞭望塔,外围的监狱部分则被分割为若干小囚室,每个囚室的两扇窗分别置于对向瞭望塔的“里侧”与对向外部空间的“外侧”。如此设计,当光线从外侧照进时囚犯们将如同艺术展中的剪影般一览无余,然而他们却看不见位于中心瞭望塔内的监视者,对其一无所知。上世纪70 年代,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发展了全景敞式理论,他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指出:全景敞式监狱从建筑学角度出发是一个对人的肉身进行监督改造的地方,但以哲学角度探究更是一个能生产新知识的场所;瞭望塔中的监督者可以观察置身于“全景”中的囚犯,从他们的行为和状态中总结出一系列犯罪学和监狱管理等专业的知识理论,从而制定出更科学的监狱行为规范。这就象征了人们对于权利运作的认知与行驶意愿由表层的外界强势干预向深度的无差别自我规训而转变,而且福柯还认为全景敞视监狱的终极目标是在被囚禁者、被监视者身上形塑一种有意识且持续性的自我规训状态,以此来保障权利机制的运作且兼顾可持续的有效性,而且这将会变成现代人类社会的特征之一[7]。
不幸的是,福柯一语成谶:在新媒介生态环境下,当代社会的信息传播方式确实更多元也更发散,但“全景敞式监狱”的模型也从越来越多的维度映射进人类的传播过程当中。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更指出:随着电子化及越来越智能化的数据处理设备的技术发展与普及,各种意义上的监督将无孔不入地进入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8]。人们在享受互联网技术提供的高速传播服务的同时,也在被一种看不见的目光监管,将自己置身于“全景监狱”当中。既如此,摆在众人面前的一道选择题已经无法回避:是彻底躺平放弃抵抗,用个人隐私权利的让渡换得便利快捷,还是坚持保守主义信条在数字革命的浪潮中做一个逆流抵制的孤勇者。这两者似乎都不是好选择,此情此景中的人们更像是圣经故事中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面对着禁果的诱惑游移于欲望天平的两端,踟躇不已。
三、数字化生存模式:从“定向推送”到“大数据杀熟”
如果单从服务性质而言,大数据应用在现代信息社会的人类日常生活中几乎能涵盖人们所需要的一切领域,这种便利能给人带来愉悦的、让人忽视危机的麻痹感。然而代价是什么?或许现实生活无法给出答案,只能通过科幻作品进行苍白的预警。在小说《圆环》(The Circle)中描绘了这样一个未来世界:所有人的个人信息都以数据的形式被一家名为“圆环”的IT 公司把控着,人们也不在意隐私是否受到保护,社会的各个角落都被安装了隐蔽摄像头,整个社会陷入毫无隐私的状态[9],而许多人悲观地认为现代社会正向着如此描绘的隐私消弭的方向发展。这样的论调或许略显出技术霸权主义的极端偏向,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下的人类生活正向着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预想中“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的场景无限趋近;在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时代,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依赖数据的传播与数字化技术的支持[10]。
在尼葛洛庞帝的时代,人们还无法预演数字技术给社会带来的权力结构变动,但时至今日我们讨论大数据时几乎已经默认要将其总结为一种资源——一种不能被平均分配的资源。互联网及数字科技公司承担起时代淘金者的角色,对“数据金矿”满怀雄心地收获近乎天价的利润,而用户们望而兴叹的同时又集体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大数据技术作为纽带连接着技术掌控者与用户,却成为了一杆失衡的秤,无法保障二者形成对等位置。以线上购物为例,用户在填写个人信息、上传头像、绑定银行卡的同时,每一步操作都在将个人信息的主导权向外交付,而网站作为数据收集方则通过一系列专业分析获得“用户价值观”“兴趣和生活方式”“性格与选择倾向”等高水平定向信息[11]。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用户能获得的保障仅仅是平台发布的告知不会滥用他们信息的“免责声明”,然而实际情况是:平台不会承担隐私泄露的风险,因为“定向推送”的目的并不在于兜售隐私本身,但不可否认的是,平台作为推送方确确实实掌握了用户的私密信息流向。步骤规范增强了用户的信任感,信息的广泛性又让他们感到性价比升级,继而认为网购行为是安全可靠的,殊不知自己已经成为了“被定义”的弱势群体。
除此之外,“大数据杀熟”也可堪为一项极恰当的诠释。近年来因用户遭遇平台差异定价而提起的诉讼新闻已不胜枚举,商家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仗着掌握海量数据信息的便利对消费者进行筛选并调控定价,造成“新客便宜老客贵”的局面。在传统技术时代,顾客的承受力阈值是无法被测算的,但如今大数据使之成为可能。个人信息被编制汇成海量的数据,并在强大算力的加持下让互联网零售商几乎在瞬间就能与自己的目标客户相匹配;而在这一系列逐利动因的驱使下,用户的个人信息及隐私彻底成为了可供利用的资源。
四、“被遗忘权(Right To Be Forgotten)”:与大数据监视的有限对抗
生存在如上述般的数字化环境之中,公众隐私的保护需要新的手段,人们的恐慌心理也需要得到安抚和疏解。2012 年欧盟公布的第72、73 号草案首次提出了用户作为数据的主体应该享有对其擦除、撤销的权益,即“被遗忘权(Right To Be Forgotten)”。其中阐明,数字信息的相关个人应有权利要求数据控制者将其记录永久删除,从而擦除在互联网上的痕迹并将其遗忘[12]。从用户的角度出发,被遗忘权是令其通过对于信息源头的掌控来规避被控制被监视的风险,这也为公众逃脱大数据编织的“全景敞式监狱”提供了一个途径。但对于掌握核心技术的互联网公司而言则是从两个不同层面对其形成约束,其一是现实层面的商业运行增负;以互联网巨头谷歌公司为例,数据显示在短短一年间平台内通过“被遗忘权”审核的比率就高达41.8%[13]。另一层约束则来自公众意识,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掌握大数据集成技术的“监视者”与形成大数据的“被监视者”保持着一种单向收割的不平等关系,“被遗忘权”的提出刺激了公众对自身权利的认识与再构,更让其二者关系转变形成有限的对抗。
根据意大利学者安德拉德·诺伯托(Andrade Norberto)的观点,“被遗忘权”可看作是当今数字化信息社会中“个人身份特质权”的体现;不作为隐私权存在,而作为人格特质权存在[14]。通过“被遗忘权”,公众将获得捍卫自我的手段,移除过往的身份来确立当下的“自我”的利益和安全。虽然迄今为止没有持续性的追踪数据来证实“被遗忘权”在何种程度上与大数据的监控特性达成对抗及制衡,但就其本质而言,能令作为个体的被监视者挖掘并行使自身之于大数据监视的对抗权利,即已进一步推动了公众意识中的身份变革。
结语
在大数据科技发展先期主流论调大肆宣扬其利其惠,为求普及甚至贬斥框架规则对其进行调控,这种意向倾斜也导致了当下数据资源化与用户话语权极端对立的局面。不可否认,数字技术参与下的人类生活在诸多方面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大数据监视及对个人信息的滥用可与既得利益做等价交换般的让渡。回归本文所探讨的主题,大数据实则与此前任何一项技术革命无异,利与弊交织,双刃共存;为用户提供方方面面的便利联络网,也为构成现代性“全景敞视监狱”提供最适宜的土壤。只言利好而忽视弊端无疑是不可靠行径,而想要在善用科技的同时规避其副作用下的隐性风险,作为用户的人的态度至关重要。由“被遗忘权”的推行立法可以看出,公众对数字霸权进行反抗意识并不是来源于简单的阶级对立,而是一种关乎个人意志的根本需求。诚然,几条法案的推行无法从根本上打击数字霸权主义的建构,但其为用户聚合了一种对抗大数据监视与滥用的反抗立场;另一方面,其也为“不敏感”用户敲响警钟,提示其直面大数据风险议题。在大数据面前,个人的意愿似乎略显渺小,但对大数据的警惕性和对隐私保护的危机意识恰恰要从用户自身层面引起重视,提升数字媒介素养与统合认知,形成对数字工具的掌控力以及对技术垄断霸权的对抗性,从而脱离随波逐流的蒙昧状态,成为数据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