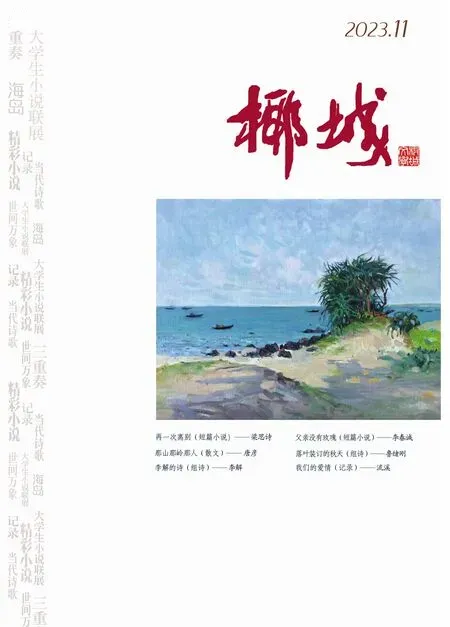绿道境遇
◎李 汀
绿道,城市的另一个秘境。
每天早上的绿道漫步,像是一门必修课,已经在身体里形成一种习惯。其实,比人醒得早的,永远是那些鸟儿。我在绿道慢跑时,晨光翻过一道山梁,照在初醒的江水、植物上,一只鸟停在芦苇杆上一摇一荡,一声又一声地叫。叫什么呢,更像是对大地的诵读。这也是它的必修课吧。
绿道随着一条江的流动而蜿蜒伸展。这城市绿道有时让人想到乡村小路,小路连接田地,连接一家一户。小路上走人,也走牲畜。乡村小路绝对不分贵贱彼此。我恍然大悟,城市绿道为何如此受欢迎,原来在城市只有这一条路是不分贵贱的。不管白领、蓝领,甚至是乞丐,都可以也只能走在一块儿。我喜欢这种感觉。
绿道两旁长着各种树木,是水冲击形成的,也是水种下的。水无师自通呀,大自然最杰出的园艺师。人只要像这些树木一样懂得避让,处处皆风景。枸树、桤木树、麻柳树、水杉、野桃树、野梨树等十余种树长在绿道两旁。最汹涌的是那巴茅草,一丛一片疯长。绿道上慢跑还是慢走,都可以随意。慢跑,耳边是呼呼热风。慢走,可以饱眼福,看树,看水。树是我们最忠实的伙伴,一直站在那里,永远保持一种俯瞰关注我们。水的柔软让我们心静。
城市内部太挤了,当我们走上绿道的那一瞬间,内心开阔了。这些年来,我不再开车上班,不再受堵车的折磨。我提早一个小时,绕绿道慢跑或者慢走去单位。几乎每天我都是第一个到单位,我享受到了那种从未有过的寂静。当我洗漱完毕,神态自若坐在办公室,在从未有过的心静中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这么多年,我借助绿道慢走,平复了自己烦躁的心理。
每天绿道慢走,都有不一样的境遇。我曾多次看见这样的情景:两个老人紧紧握着对方的手,在绿道上慢走。男的脚步不太灵便,走得歪歪扭扭,像是患了什么病。女的紧紧抓着手,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扶着男的走。他们走一小段,就要坐在绿道石凳子上休息一会儿。他们相互给对方擦汗,轻言细语说着话,微笑挂在他们脸上,平静得像那缓缓流动的江水。在这平凡的日子里,让我这个旁人也能感受到他们那种对生活的热情,和怦怦心动的那种浪漫的心。什么海誓山盟,只要此刻的相守足矣。
有时我驻足一棵树旁,一棵枫杨树。江边枫杨树多,树干长在岸边,树枝却伸到江水之上。枝叶婆娑轻柔,与江水辉映成趣。那一串串果荚垂下来,成熟掉进江水,江水带着种子远行。种子靠岸生根发芽,又一棵枫杨树长起来。静静站在树下,听江水的述说。江水打着璇儿,江水一路奔涌。江水一刻也不敢懈怠,原来是因为这一棵又一棵树。站立江边两岸的树,是江水最厚道的观众,是不离场的啦啦队,它们日夜为江水加油助威。
中途离场的往往是我们这些不堪一击的人。这天早上,阳光翻山越岭,照着绿道上三三两两散步的人。清新的空气里有一丝丝甜味。微风拂面,多好的一个早晨。我迷恋这样的早晨,安静地行走在绿道上。突然,我眼前桥上跳下一个人,“扑通”一声掉进江里,腾起的浪花打破了早晨的宁静。我惊讶,这是怎么了?有人喊:遭了,有人跳江了。很快桥下围拢了许多人;很快江水恢复了平静;很快来了蓝天救援队。人群中议论声四起。是个女的。咋了,为啥要跳江呢?肯定是感情问题啰。不要乱说,你咋晓得是感情问题呢。不是感情出问题,咋会跳江呢。救援队船只在江水中穿来穿去。我祈祷着早早把人救上来。我没有等到把人救上来,就离开了现场,我不愿意去目睹那凌乱的场面。一路上,我都在猜想:也许是她的男人辜负了她,她一时想不开吧。她是经历了怎样的挣扎,才最终选择从桥上跳江。有勇气选择跳江,咋就没有勇气选择活下来呢。其实,生活中的男男女女,选择中途离场真不少。当时女孩跳江的情境,以及那最后的“扑通”声,都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这种离场的决绝,让我有一种久久的悲痛。
绿道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场域。来这里牵手拍婚纱照的不少。情侣在绿树下、草坪里摆拍,摄影师一会儿让他们搂腰,一会儿让他们热吻,折腾来折腾去,两个小情侣始终保持着热度,脸上始终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在他们身后,刚好听到他们一段对话。女的咕噜一句:好累哦。男的浅笑着说:累嘛,这不是人生只有这么一次累嘛。幸福的累呢。
也是,累并快乐着。
这叫快乐累,幸福累。
摄影师接着说,你们说的好,把这温馨的对话做进相集里了。我边走边想,这一对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情侣,现实的柴米油盐也消磨不掉他们的热情吧。
绿道一段艺术墙。墙上一幅画,画着无数张嘴巴,涂着口红的小红嘴,吐着烟圈儿的嘴巴,咧着嘴笑的嘴巴,赌气的嘴巴,骂人的嘴巴,还有鲤鱼嘴巴,牛嘴巴,马嘴巴,甚至还画了几只鸟的嘴巴……这幅画没有命名,一天,我站在艺术墙边,再次端详这幅画,在无数嘴巴中间,我惊奇发现,一张小小嘴巴吐出很小的两个字:慎言。我恍然大悟,这就是这幅画的名字。即便是在这么宽松自由的场所里,也要慎言。
绿道也是鸟儿的表演场。每天,绿道上有不少晨练的人,他们或慢跑,或聚集在一起交流。无数鸟儿站在绿道树枝上,叽叽喳喳盛装出席清晨的辩论会,每只鸟儿都是激情满怀的演说家。鸟声人语,一时间难以分清。也许是一群麻雀,也许是一群伯劳。每个演说家都歇斯底里,都试图技压群芳。实在急了,演说不下去了,低头啄自己的爪子,也啄一下对手的头发。当然,也有甘愿飞起,在空中鼓掌的,更多的是站在一根高枝上互不干扰的海阔天空。两三个男女围坐在绿道木凳上,你一语我一言,时而嬉笑,时而哀叹,人语里落鸟声,鸟声像是人语。
江里有野鸭露头了,野鸭是潜水高手,它们潜入水下追寻那些漂浮的水草和小鱼小虾,再次探出头时,已经到了江水中央。成对的野黄鸭停在水中央,把头钻进羽毛里。野鸭潜过,也打扰不了它们,它们尽情享受着晨阳的柔和。偶尔仰头嘎嘎嘎叫几声,像是一种赞叹。有时,迎着晨阳张开翅膀,泼溅起晶莹的水花,晨阳的碎片落在江水里闪闪发光。
一对一对斑鸠在绿道草坪里肩并肩散步,滴溜溜的眼睛,被金黄的阳光照耀得格外水灵。我有时轻手轻脚跟在身后,怕惊扰到这对斑鸠。走一会儿,停下来,这斑鸠也停在草丛里,惊喜地望着我。一双温和的眼睛里,全是清澈的光芒。真有与它们说话的冲动。低声说一句:你们好!斑鸠咕咕咕叫着,点点头。我笑了,斑鸠笑了。它们眼睛里全是干净的阳光呢,看到它们,感觉自己更像是个傻子。
一群沙燕在一堵沙墙上飞起落下。沙墙是江水涨水留下的,一窝一窝的小沙燕张着稚嫩的小嘴巴。沙墙成了几百号沙燕的家,一眼眼沙窝精巧温暖。每天早上,一批一批沙燕在江边低飞练翅,有的沙燕飞回,身子贴在沙墙上欣赏着自然江水。有的在沙滩上跳跃追逐,沙滩上印着无数爪印。不过,很快,高低起伏的爪印被江水收纳。
在一处开阔滩涂上,各种鸟儿在这里觅食。成群的苍鹭和白鹭混在一起,有时也为争食打架。它们或站在江边,或站在石头上,都是不紧不慢,不慌不忙,纹丝不动,像沉稳的垂钓老者,它们比赛着各自的耐心,只有江风撩起它们或灰或白的羽毛。一天,一只苍鹭在江水边抓起一条小鱼,小鱼还在长长的嘴里扭动,嘴间也尚滴着泥水。一只白鹭不服气了,追赶过去争抢。苍鹭把小鱼放在脚下,小鱼在泥潭上蹦跳,一闪一跳,苍鹭张开翅膀,用长长的嘴啄飞跑过来的白鹭,嘎嘎嘎叫嚷着。很显然,白鹭不占优势,几个回合,败下阵来,苍鹭尽情享受着美食。这时,江风把一堆凌乱的羽毛吹得到处都是。突然,苍鹭对天长唳,张开翅膀,飞上对岸的高树上,高跷似的缩着脖子站在树枝上。树枝一摇一晃,水里的影子也一摇一晃。
夜给绿道增添了不少的隐秘。夜里在绿道上走,是另一种状态,别一样的心境。一次,同一个小年轻聊天。我问他,现在你们恋爱都去哪里?他毫不避讳地说,当然是去绿道。夜里绿道就是我们的恋爱场。我惊讶不已。他笑笑说,那里没有窥视者,那里还空气清新。好几次,我夜里在绿道上行走,看见那些隐秘的树丛下、长廊上,拥抱在一起的男女,我赶紧走远。我不想成为窥视者。有时剧情迅速转换,让人始料不及。一天晚上,我目睹了一对男女在绿道上吵架的情景。女的一遍又一遍推搡着男的,男的一步又一步往后退,退到一棵树下,男的靠在树干上,无奈地问女的,你还想怎么样呢?女的哭着说,你说,你说我想怎么样?最后,女的边哭,边跑,男的在后面追着。绿道上幽暗的灯光一闪一闪,眨着眼睛。这时,绿道像一个永无止境的收纳场,收纳激情,亦收纳寂寞。
当城市的灯暗下来,才发现皎洁的月光泄到绿道上,那种悄无声息的美丽,那种淡淡的神秘,沿着深邃的苍穹抵达大地。绿道是每个城市人心中各自的秘境。这时我有时间一遍又一遍辨识身边这些树,白杨,芙蓉,桂树,银杏,水曲柳,水杉,枫杨,能喊出名字的,也有喊不出名字的。它们保持着美好的距离,它们的根却在地下穿行缠绕,它们的枝叶也在半空中相遇依偎。突然发现,绿道上的月光纯净,为这臃肿的城市增添了一抹妩媚的色彩。其实,这时适合默默哼一首《城里的月光》:“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它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撒满整个夜晚……”歌声在月光里升起,在月光里飘远。最妙的是,月光下虫鸣啾啾,偶尔几声蛙声,此起彼伏,一起演奏着一曲小夜曲。
只要走上一段绿道,人的内心就少了许多风暴。绿道上没有急躁,没有暴力,没有拥挤。熙熙攘攘的人一致放下手上以及心中的忙碌、焦灼、困顿,来绿道找寻短暂的悠闲、安宁。当然,绿道上也有猝不及防。一次,我在绿道漫步,距离十多米,在我前面走着一对中年男女,他们轻声交谈、说笑,安静、祥和地说着家长里短,岁月已经磨掉他们英姿挺拔的棱角,换来的是沧桑般的沉静。突然听到咚一声,中年男子倒在绿道上,没有一点声息。中年女人蹲下身子,声嘶力竭地呼喊着男人的名字。绿道上的人也跑过去,帮忙拨打120。医生赶来,一阵紧张急救,人还是没有救过来。中年男人的生命戛然而止。中年女人安静下来,神色黯然坐上救护车,突然地超然死别在她心中排山倒海,但她又不得不淡定接受。
这天,我在绿道漫步,再次莫名其妙想到乡村小路。那种崎岖不平、坑坑洼洼的小路。进城的父亲在鸽子笼的房子里呆不住,他好像只是晚上回家安放疲倦的身子,一睁眼就要出门。一次,我问他,睁眼就出门,去干什么呢?他叹了一口气说,找了好久,终于晓得城市最好的地方,是那搞得红红绿绿的沿江的那些路了。我说,那是城市绿道。
父亲笑笑说,城里总是哄人得行,明明是红色的,他说是绿道。
我无言以对。
父亲又说,你说,这绿道跟我们村里的那些放牛呀、走亲戚呀的小路有啥区别。要我说,那些小路才是真正的绿道。
我一阵惊讶,依然无言以对。我最后说,那一样嘛。
父亲与我较上劲了,咕噜说,哪不一样呢,我们村里是放牛,城里不就是放人嘛。
我恍悟:原来城市绿道是一条放牧人的绿道。事隔多年,想到父亲这句话,我依然觉得父亲就是一个哲学家,他说的那么透彻、那么干净。
一次,我问父亲,你在绿道干什么呢?父亲诡秘一笑,说,我当自己在乡村小路上放牛呢。
原以为年逾古稀的父亲离开乡村,会像我一样陶醉于这丰富多彩的城市,今天我才明白自己的无知。父亲没有陶醉,更多的是与城市的和解。我应该也不是陶醉,而是一种相处久了固化的麻木吧。但我深深知道,不管父亲把城市和乡村如何比较,他依然不会让我放弃城市,他依然鼓励我像一只飞蛾蹈火般扑向眼前这热腾腾的城市。
绿道上各种声音你方唱罢我登场。最欢快的是那些宠物狗,它们相互撕咬在一起,草坪上蹦跳发出各种撒娇的声音。鸟儿的声音自然流淌,布谷鸟在绿道深处滴血地叫,声音孤单凄凉。麻雀叽叽喳喳一群,惊乍乍从这棵树扑腾到另一棵,黑压压落在树丫上,压得树枝惊慌摇摆。自行车飞驰的声音,是年轻的风声。绿道宽敞处有人弹琴,有人唱歌,他们制造的声音空旷无力。这些声音有时懒懒地消失在风中,有时也被江水的漩涡吞噬。
有一年夏天,暴雨如注,很快绿道被洪水淹没吞噬。绿道隐在深深的洪水里,那些缤纷的声音也被一同淹没,一片静默。我忧戚地来到江边,奔涌的洪水已经覆盖绿树,一些树被洪水拉扯,倒在水中一摇一摇的,像是在喊救命。在洪水面前,绿树显得那么无力,我们人也显得一样无力。我耳边全是洪水冲击堤防、撞击岸边树木的咆哮声。我的眼睛也有些恍惚,土黄色的洪水晃得眼睛生痛。我别无选择,我只能呆呆看着洪水一遍又一遍咆哮奔涌。洪水一个漩涡打着一个漩涡,一个漩涡熔化一个漩涡。我像那些被沦陷巨大漩涡的各种声音一样,被一次又一次按倒……直到永远消失。
暴雨停了,洪水很快消退,绿道重新展露出来。绿道上堆积着泥沙,倾斜的树枝上挂着各种垃圾,有塑料袋,有撕烂的衣物,甚至还有一只只皮鞋。城市环卫工人上场,把倾斜的树立正,把泥沙清扫干净,很快绿道又恢复了往日的面目。很快城里人又开始在绿道上漫步歌唱。很快各种缤纷声音又在绿道上聚集鲜活起来。
一时间,我竟然不知该为这短暂的淹没悲伤,还是该为这迅速的复活欣喜。
从我家高楼窗户望出去,能看到一段绿道蜿蜒开来。有时,我靠在窗户边上,望着绿道上三三两两的行人,他们或慢跑,或溜达,不免在心里感慨:在这条绿道上我看见或者没有看见的,一如既往地发生着。有些人我们彼此机缘相遇,有些人我们永远错过了。
在绿道上,我偶尔会遇见那些拄着拐杖、坐着轮椅的人,他们也是看风景的。一次,一位拄着拐杖的大哥站在一棵栾树下,栾树正是满树繁花,一簇簇小黄花,晶莹灿烂,在九月的阳光里,细小稠密,艳艳灼灼的花随风飘落,一会儿,绿道空地上就铺满了金黄一片。大哥身上也落满了点点栾花。随后,大哥艰难蹲下身子,把地上黄澄澄的栾花用双手扫在一起,然后装进小塑料袋中。大哥见我一直看着他。他眉开眼笑地说:“这花是一味药呢。”他颤抖着双手,把地上的那些小黄花捧进塑料袋中。然后,一拐一瘸走了。这花是一味药。我忍不住在手机上收搜,度娘这么说:栾花清肝明目。主治目赤肿痛,多泪。用法,煎汤,内服。回家后,大哥肯定会把栾花从塑料袋倒出来,小心清洗,用心熬制一碗黄酽酽的汤汁。不出几日,多泪的眼睛也许会清亮许多。
在绿道上,我无一例外地和那些树,那些鸟儿,那些人一样,是别人眼里的一道景观而已。这么多年,我在这条秘境里,目睹太多的鲜活扑腾,看到一些生离死别,也感悟到了生命的恍惚、悲伤和欣喜。
我知道,我在发现这一切的时候,我一样被别人在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