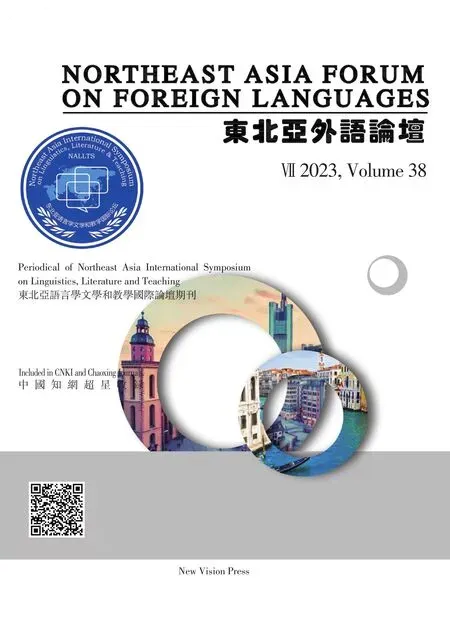论促进余华作品成功韩译的文本外因素
李 琦 郑怡鹏
天津师范大学 天 津 300387 中 国
一、引言
当前,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心已经从“引进来”转向了“走出去”,而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推动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虽然中韩两国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但由于冷战的影响,中韩两国的外交关系曾经长期被迫中断,文学译介及研究也陷入低迷。直到1992年两国正式建交之后,韩国读者对中国民众和中国社会充满了好奇心,迫切地想要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中国,于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开始被大量译介到韩国。而在被译介到韩国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余华的作品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1997年余华作品的首部韩译本——《活着》韩译本《살아간다는 것》出版后,韩国学界几乎每年都有关于余华小说的研究论文发表,余华成为了韩国人最熟悉的中国作家之一。
余华作品在韩国译介的成功具有鲜明的代表性,详细梳理余华作品韩译成功背后的各种因素,对今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韩国译介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中国国内主要有张雨晨(2018)、辛喜晶(2019)、王乐(2022)等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探讨了余华作品在韩国译介成功的原因。而操控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曾提出:翻译受到译者或目的语当权者的意识形态、文学系统的诗学及赞助者的操控。译介学创始人谢天振也认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学、文化要译介到另一国、另一民族去,除了翻译家个人对读者的吸引力外,译入语国家或民族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是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谢天振,2003:62)。因此,本文将从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三方面探讨促成余华作品在韩国成功译介的文本外因素。
二、影响余华作品在韩国译介的文本外因素分析
2.1 意识形态
翻译研究的重心不仅应该放在语言、认知及审美层面上,而且更应该关注研究其政治社会效果及影响。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译作必然要涉及翻译作品和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关系,而意识形态是译作与社会生活反映的最典型代表(刘军平,2010:425)。
一方面,韩国读者长期接受西方文化与价值观的影响,更倾向于欣赏欧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余华、莫言等中国当代文学作家正是在西方获得广泛关注之后才进入了韩国读者的视野;另一方面,韩国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疏于研究,正如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姜镇锡认为:韩国从古代到朝鲜时代为止认真地完成了中华文明的翻译,翻译囊括了哲学、文学、政治、经济、法律等所有领域,但是新中国建立到1992年中韩建交之前,两国文化交流的中断造成的文化隔膜至今无法消除,韩国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有很强烈的疏离感甚至是排斥感,以新中国建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初这段时期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大多无法获得韩国读者的共鸣(王乐,2022:110)。而余华作品大多以土地改革、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为背景,这样历史与文化对于韩国读者来说具有强烈的疏离感。例如,改编自余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的韩国电影《许三观》中,导演对原著故事情节进行了文学化改编,将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的时代背景改为韩国五六十年的历史背景,避开了原著中许三观经历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令韩国人感到陌生的历史进程。
不过相较于其他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格外深受韩国民众的认同。这两部作品之所以能风靡韩国,与当时韩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密切相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社会陷入混乱,大大小小的企业接连倒闭,许多家庭生活难以为继,“1997年之后的几年的韩国金融危机时期,是悲观主义情绪泛滥的时代。所以,当时韩国人民需要的,是一种克服困难的希望(河贞美,2010:54)”。也正是在1997年,余华开始进入韩国读者的视野。虽然中韩经历了不同的历史进程,但两国人民感受到的压力和痛苦是具有相似性的。正如《活着》中福贵在时代背景下的个人悲剧引起了韩国读者的情感共鸣,而《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一家人一次又一次渡过难关,也让韩国读者从中得到了相似命运下的鼓励和慰藉,正是这种跨文化的认同感促进了两部作品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
2.2 诗学
诗学由两个组成部分:文学要素和功能要素。文学要素包括文学手段、文学样式、主题、原型人物、情节和象征等;功能要素指文学在社会系统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或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刘军平,2009:424)。这就造成了译者在选择翻译文本时,往往会选择符合当时社会诗学的作品,以期得到广泛的认可。
余华的作品在文学手法上符合韩国读者的期待。进入90年代后,余华的创作风格转向现实主义,开始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放弃了以往对语言作陌生化处理的策略,叙事结构完整清晰、叙述语言简洁明了,深受韩国读者欢迎。例如,《许三观卖血记》的语言为了接近人民的口语,作者多用短句、少用长句,不使用繁复华丽的词句,符合人物形象。提到文革,许三观对文革的印象是“我这辈子没见过街上有这么多人,胳膊上都套着个红袖章,游行的、刻标语的、贴大字报的,大街的墙上全是大字报,一张一张往上贴,越贴越厚,那些墙壁都像是穿上棉袄了。”余华没有对包括文革在内的中国近现代史进行全景式的描绘,而是通过描写历史背景下底层小人物逼真而穷苦的生活细节,展示中国当时真实的民间生活状态。
其次,从题材上来看,余华的作品大多数是叙述底层小人物的苦难与救赎,这与韩国读者喜爱阅读的题材不谋而合。有韩国学者曾指出“韩国读者历来喜爱民间故事,特别喜欢阅读从极为恶劣的环境给人们造成的极限性困境中摆脱出来的各种故事(金炅南,2013:105)”。例如,《活着》中,福贵一次又一次直面亲人、朋友突如其来的死亡;《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以“卖血”的方式艰难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余华笔下的“小人物”在面对生活带来的种种苦难之时,展现出了强劲的生命力:福贵选择用忍受化解所有苦难;许三观经历了十二次抽血后仍然顽强地活着。
正如李旭渊在《新时期文学里的民间和国家:莫言和余华小说的情况》中也谈到了余华写作的一种“民间现实”,从民间日常生活中取材,小说里家庭史是中国现代史的象征,有丰富的关于现代中国的消息。另外一个重要的是,这一“民间”,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同时,也最好要具有普遍性(河贞美,2010:49)。也就是说,在余华构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小说背景中,韩国读者能够从中间接体验到当时中国社会的生活场景和气息,进而产生细致、逼真的感受。综上所述,余华简洁朴实的叙述风格、从底层小人物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当代社会现实逼真而细致的描述、反映苦难与救赎的题材等都符合韩国当时主流诗学的文化价值取向,从而深受译者和出版社的喜爱,成为了韩国读者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渠道。
2.3 赞助人
勒菲弗尔提出了翻译赞助人的概念,他认为赞助人指“有权势的人或机构,能促进或阻碍文学阅读、文学创作和文学改写”。赞助人可以促进或干扰文学文本或翻译的生产和传播,强化其意识形态的观点(刘军平,2009:422-423)。也就是说,一部翻译作品的出版,从原语文本的选择、译本的产生、出版,甚至到接受,都会有赞助人这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起作用。而赞助人往往会选择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及诗学的作品,排斥那些与主流意识形态及诗学背道而驰的作品。
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最重要的赞助人就是出版社。如前文所述,受意识形态的影响,韩国出版界倾向于选择倍受西方认可的中国文学作品。韩国学者李旭渊也曾说过:“我们出版界出版的时候不是自己选择中国作品,而是西方读者认可的作品(河贞美,2010:43)”。余华一直被韩国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与其曾多次获得西方著名文学奖项密不可分。余华最先走向海外的作品就是《活着》,随着改编自余华同名小说的电影《活着》接连斩获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1994)、第48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外语片奖(1995)等西方主流电影节奖项,韩国迅速上映了这部电影。改编电影的成功上映促进了文学译介的传播,两年后,小说《活着》在韩国经由青林出版社译介出版,译本命名为《살아간다는 것》。由此开始,青林出版社成为了余华作品在韩国译介出版的主要阵地之一,1997年至2022年共26年间,韩国共出版了24部余华作品的韩译单行本,其中有15本均由青林出版社出版,占57.69%;其次是人文主义出版社(4本)和文学村出版社(5本),分别占20.83%和16.67%。总而言之,韩国众多主流出版社对余华作品的青睐,促成了其多部作品成功在韩国译介出版。
三、结论
本文从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的角度分析了余华作品在韩国译介受到的文本外因素影响。余华部分作品在韩国译介的成功经验深刻体现了韩国文化语境对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的制约:首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韩国的译介深受西方文学界的影响;其次,韩国读者需要的是既能间接体验异国文化,又能引起情感共鸣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这类文学作品语言风格简洁、叙述结构完整、饱含中国近代社会真实的生活细节。
在对外文化交流重心转向“走出去”的今天,译本的选择就变得尤为重要,忠实于原作不再是评判译本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倘若一味注重文学作品输出的数量而不考虑文学作品输出的有效性,对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来说只会是事倍功半。一方面,译作需要在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层面与译语文化高度契合,另一方面又应当反映中国当代真实的社会风貌。今后应该鼓励更多的译者新译、复译符合上述两点的中国文学作品,推动中国文学作品真正有效地走向韩国、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