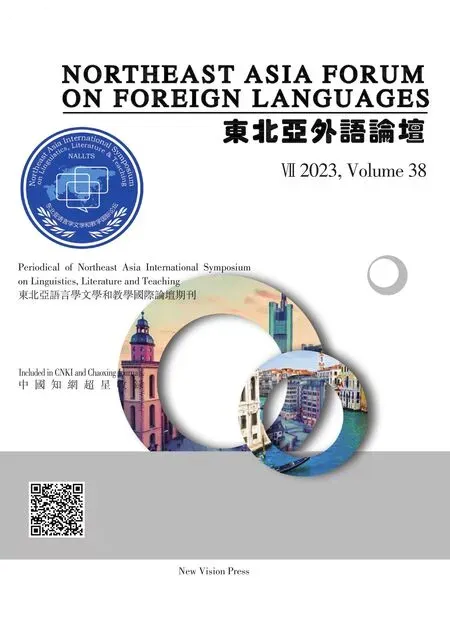共同体视域下《道格拉斯自述》中的身份建构与归属
傅 娆 宋 薇
大连外国语大学 大 连 116044 中 国
引语
文化研究中所关注的文化身份的建构,其实质是追问自己在社会上是“谁”(身份),以及如何和为什么要追问“谁”(寻求“认同”)(伍叶琴,2014:107)。首先,身份是整个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总称,用来描述个人对自己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的理解。身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释,如自然、民族、社会和文化身份,而社会认同的体系将分散的个体统一为一个整体。其次,在社会学中,人的身份认同包括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人类是群居动物,身份的划分可以使人在群体当中获得归属感,从而得到一定的安全和庇护。
在建构个人身份的过程中,大多数人都有一些隶属于某些群体或共同特征的意识,如宗教、性别、阶级、种族和国家。这些特征是归纳性的,以确保主体及其身份意识,这些都是文化认同出现的标志。文化认同的建构包括两个平行的识别过程:个人与文化之间的认同和其他文化中的主体认同。归属感和意识形态化都意味着个人开始对自己的文化进行认同。
本文基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个美国奴隶的生平自述》进行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分析。自传这种体裁本身就与“身份”这个话题紧密相连,自传的作者总是以一定的身份进行写作,并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自觉地接受叙述者建构出来的身份。道格拉斯在他所写的附录和致老主人的信中试图让白人世界接受的就是他作为自由、平等的作家及思想家的身份。他以逃奴的身份直接现身抨击白人的宗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极其罕见的,而且能对如此敏感的话题进行解释和评述,这本身就能充分体现出自传作者应有的身份权威(Douglass,2004:13)。整部自传以道格拉斯的自我保证、亲笔签名以及具体日期结束,这有着震撼人心的非凡的意义:亲笔签名意味着黑人对自身文本真实性的保证,打破了白人为黑人作品作保的传统,摆脱了白人霸权的压制,是一种自我身份的宣告,使其能真正被铭记;具体的信息则更进一步凸显了自传文本的真实性,与序言末尾的格式一样,签名加地址和日期,这就是道格拉斯对加里森的回应及强力反击,与白人文本相同的格式,同样具备可信度及叙述权力(罗旋,2018:26-27)。
同时,奴隶叙事是美国非裔传记文学、探寻小说、成长小说的源头,也是新奴隶叙事文学对话与改写的对象。奴隶叙事的纪实性使我们得以探讨识字之外促使奴隶向自由人转变的其他因素(方红,2016:126)。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生写过三部自传,其身份之复杂不言而喻。因此,在关于他的那些传记里,道格拉斯只是作为一股历史势力或一个历史存在而存在,根本看不到那个多姿多彩的极富人性的个人。毫无疑问,他是后者(Gates,1987:109-110)。所以舒尔茨曾说:“黑人自传的特点是,个人和社群不是对立的两极;尽管自传模式和自传作者的视野不同,但这个社群的任何一部自传里都存在着‘我’与‘我们’的基本认同”。通过自我教育、通过社群学习、通过整个黑人种族的求知,道格拉斯试图指出一条“从奴役通向自由的途径”,这才是他终生的使命(赵白生,2002:57)。
一、身份的转变
在美国这片土地上,从殖民地时期开始,有关奴隶制的争论将其分为南方和北方,没有人比南方的奴隶更渴望自由。道格拉斯作为一名前奴隶,他不仅像其他奴隶那样切身体会过奴隶制带来的惨痛伤害,他还亲自把它写成文字,告诉更多人。通过与主人强加的身心统治作斗争的解放过程,他提供了一个深刻的视角来理解奴隶们对自由意识的觉醒。通过艰苦的努力和不屈的精神,道格拉斯最终获得了自由。
陶行知先生曾说过:“文化身份不是一个固定的和永久的东西”。它会随着客观世界的变迁、主观思想的转变而不断发生变化。决定一个人文化身份的不仅仅是他的出身,还可以是他的自我意识使然。
1.黑奴到自由
奴隶是一个被剥夺了各种人权和机会的存在。在当时,美国黑奴还受到种植园内的持续监视。道格拉斯通过描写奴隶如何抵制主流的压迫,探究自由意识的觉醒,并在此过程中体现出了他身份的建构。
最初,道格拉斯知道自己是黑奴,并从外祖母那里得知他自己的文化身份带有边缘文化的特征。他认为自己和其他奴隶一样,只是有主人的动产,一生都要为主人劳动,仿佛这就是他们的使命。他们没有自己的想法,因为奴隶劳作的疲惫使得他们无法思考。在奴隶主的心中,只要他们奴役的劳动工具尽可能地继续为他们工作就足够了,奴隶主只关心在有限时间里发挥奴隶的最大价值。至于其他事情,如他们是否健康,主人都无动于衷。
颠覆道格拉斯思想的是奥德先生对他禁止识字的举动。从那时起,他的主人越是努力阻止他的女主人教他,他就越是知道其重要性。后来,道格拉斯开始有了不同于他人的意识。因此,他为自己的生活奴役状况感到非常痛苦,他甚至羡慕别的奴隶的麻木和愚蠢,因为意识的产生只会给他带来伤害。同时,道格拉斯开始明白,有些东西必须通过反抗和积极的努力才能得到。他发现,要想成为一个满意的奴隶,就必须让他成为一个没有思想的奴隶。有必要让他的道德和精神视野变得黑暗并尽可能地消灭理性的力量。否则有一天,有人会站起来为自己和他的兄弟姐妹而战。
在道格拉斯的内心深处,他不再感到自己是个奴隶,而是个为正义、为自由而奋斗的公民和战士。获得自由之后,他当过演讲家、作家、编辑、杂志出版商,并且成为第一个在美国政府获得高级顾问职务的非裔美国人。他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直在为人权和奴隶的自由而奋斗(邓建华,2004:76-78)。
自由包括外在的和内在的自由,它是文化身份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当一个人拥有外部的自由时,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活动,接触不同的文化。只有当一个人拥有内部的自由时,他才有意识去思考不同的文化,才有意识去思考生活状况或改变它并认同不同的文化身份。自由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外部自由是一个前提条件,因为它不仅给人们带来了根据自己的内容独立行动的可能性,而且还带来了自由的社会环境,提供和创造良好的条件和足够的空间来独立思考。内部自由是指人的意识的自由。作为一种力量,作为一个人在生活过程中获得的自我决定权,作为人们活动所追求的目标,自由意味着人们要摆脱各种依赖性的奴役和束缚。
2.亲历到叙述
身份建构在自传体写作中多多少少都会有所体现。一个自传体作者在开始写作之前,就已经在脑海中清楚地描绘了他要勾勒的自我形象。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他一直在努力编织着这样一个身份,一方面在社会中宣传自己,另一方面又恰恰是出于社会需要,反过来巩固了社会秩序。
道格拉斯在写作过程中相当于重新回忆了一次奴隶时期历经的种种恐惧和痛苦,但他没有选择回避,而是勇敢地以审视的态度将自己置身于其中。他将自己作为奴隶的一员,一个有色人种、脆弱群体,边缘群体的一员。否定一个人的过去就等于否定了自己的一部分,所以他选择正面这段人生经历。况且,《道格拉斯自述》的问世使得他的前奴隶身份被质疑,他必须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总的来说,这部自传中关于奴隶制的叙述,有助于提高对奴隶制的同情,有助于构建道格拉斯的前奴隶身份(陈斐,2015:20)。
二、寻求归属感
十九世纪的美国是以工业化的北方和农业化的南方之间的尖锐冲突为标志的。这种紧张关系的核心是对劳动力的竞争。南方表现出强烈的倾向性,希望从其他地区购买这种资源,以支持烟草和棉花的生产,这些劳动密集型的作物构成了南方经济的大部分。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增加了对黑人的奴役,并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为了有效地确保奴隶制的完整性,奴隶主精心设计了一些措施,通过操纵和毒害奴隶的思想来更好地支配奴隶。对许多在南方种植园或其他小农场工作的奴隶来说,他们的出生地就像是记录在每个奴隶脑海中的无可争议的事实。在《道格拉斯自述》中第一章的开头,看似简单交代了出生地信息这样一个出身背景,实则是他对自己身份所知晓的全部内容。道格拉斯对他出生地的强调表明了他对自己的美国之根有着强烈的信念,他出生在马里兰州的塔卡霍,这是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合法的美国公民。
在道格拉斯逃离奴隶生活抵达纽约后,他改名为弗雷德里克·约翰逊,再后来到了新贝德福德市发现,叫“约翰逊”太容易重名了,辨识度不高,于是请人最后为他改了一次名字,最终成为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整个过程看似是普通的名字变化,其实表明了身份的改变。从南方来到北方之后,道格拉斯希望通过新名字来进一步证明他新的美国公民的身份。
道格拉斯对整个《自述》的结束语与之前他仿造的通行证相比较不难看出其深意:这种模仿与改写破除了白人对知识和话语的垄断,暂时颠倒了奴隶制下的主奴关系,进而解构了奴隶制体系得以维持的根基——黑人无教育因此适合当奴隶。权力不仅控制话语,也存在于话语之中,对权力的争夺最终都转化为对话语的争夺。这不仅证明他在未来会将自己的全部力量投入解放黑奴的事业中,而且证明他有能力建立和运用自己的权威(凌源,2016:119)。这是对奴隶主和奴隶制权威的一种颠覆和瓦解,更是道格拉斯对与美国白人公民同等的权利及身份的争取。
三、保留异质性
白人抓住了“受教育的机会”这枚棋子来奴役黑人,因为控制住了思想,就更容易规训身体。只有获得教育,黑奴的自我意识才能觉醒;继承自己的文化传统,牢记他们或者他们的祖先是从哪里来的;学习白人文化,更好地融入到新环境中去。除了强调教奴隶学习知识的重要性之外,奴隶主还对奴隶的公共活动和私下生活进行严密监控。他们受尽不公、羞辱,却无法反驳、反抗。奴隶主甚至还会派人混进奴隶当中来试探他们的思想活动,奴隶们只能佯装不知情,并假意表示对种植园生活很知足、对主人没有半点背叛的意图。面对无处不在的监视,黑奴不得不表现出绝对服从,否则就要受罚。在这种环境下,奴隶们必须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才能生存下去。
从这部《自述》中可以看出,“声音”这个层面极大地体现了关于文化身份的认同及建构的内容。此处的“声音”有两方面的含义:顾名思义的发声和社会地位中的话语。黑奴用音乐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用缄默来面对暴力的权杖,无不昭示着他们在美国生存的同时,本身拥有非洲族裔的那份独特性。
1.有声的秘密
在与奴隶制的早期抗争中,极端贫困又压抑的生活状态下,奴隶们用自己的方法来减轻他们的抑郁情绪——唱歌。早在欧洲殖民者入侵之前,非洲人就已经创造出了丰富的口头文学和民间文化。当殖民者将黑人贩卖为奴后,黑奴创造了奴隶歌曲,后来也成为了美国黑人文学中最具独创性、最具艺术特色的瑰宝。黑人歌曲在那时起到了信息共享和精神交流的作用,它们能够将说不出口的想法以另一种形式吐露出来,这一功能在如今的音乐领域当中仍有沿用。奴隶歌曲往往用最兴高采烈的音调唱出最悲伤的情绪,透露了被最剧烈的痛苦折磨的灵魂所发出的祈求和幽怨。那些看似毫无意义的歌词,对奴隶们却具有深刻的内涵,就像一串串神秘的编码,奴隶他们自己则是一个个解码者,在日复一日的悲惨生活中互诉着哀伤的故事。
道格拉斯将黑人歌曲作为一种异质的叙事策略,对白人文化进行批判性的接受、改写和表达,也成为保存本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那些震耳发聩的歌词惊醒了无数黑奴,以此为基础掀起了黑人文艺复兴运动的巨浪,美国文艺界也一度为之颤抖。
2.无声的力量
奴隶们像在农田里干活的牲畜一样,年复一年地按固定模式工作、吃饭和睡觉。主人通过对奴隶进行心理压迫,在很大程度上窒息了奴隶的思想,使大多数奴隶保持无知和沉默。即使没有知识的武装,奴隶们也很清楚奴隶主的罪恶行径,但他们无能为力。所以他们不敢说“不”,即使是私下里,也不敢说主人的一句坏话。一旦他们说了,如果被主人知道,他们会面临更加残酷的鞭打,甚至是更糟糕的境地:他们将被卖到远离家人和朋友的地方去劳动。对于包括道格拉斯在内的绝大多数奴隶来说,离开自己家人所在的生活群体是比严刑拷打还残忍一万倍的事情。这与后来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黑奴宁愿忍气吞声过着非人的生活,也不愿和自己的种族群体分割开来。
奴隶主的恐吓声音是最常见的一种压迫形式,黑人的沉默便成为与之抗衡的异质力量。道格拉斯通过对奴隶主和监工的命令保持沉默、拒绝为他们服务来挑战奴隶制的权威(Messmer,2007:5-22)。在他的叙述中没有多少文字可以记录,这种无声的反抗同时也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而沉默会使反抗更加有力和持久。
后来,道格拉斯到达北方的自由空间时,他对他的未婚妻的存在相对缄默;他在撰写这部《自述》的时候,对于成功的逃跑路线和方式保持了缄默……当奴隶身份转变为自由人的身份,当沉默上升到了缄默,道格拉斯已经不再无知或愚钝,他是为了保护自己、保护家人,保护同胞而主动选择了“无声”。
四、结语
通过整部自传,我们可以看出拥有多重文化身份的道格拉斯自身也有着“有容乃大”的精神,他是非裔美国人,没有抛弃族裔的特点,也没有拒绝美国人的身份。反之,他一生都在积极寻求各方的认同,努力奋斗着去带着特质融入新群体。多重身份和多种文化并存的结局不是边缘化,不是矛盾体,它们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如今的混合文化共同体,这是比任何人都更加强大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