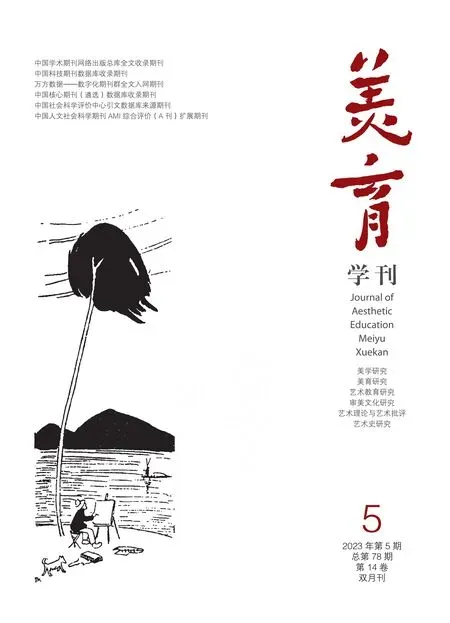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变革与审美救赎
——论本雅明的艺术观及其现代性反思
李 雷,赵 飞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欧洲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基本肇始于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资本与机器大工业的双双崛起标志着与过去发生了历史性的决裂,在宏大叙事中被描述为人类迈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到了19世纪,工业的迅猛发展预示着现代性的成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型技术的出现,为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变革,人类进一步确信自己正处于不断进步的历史进程中。然而,进步神话光鲜华丽的外表下很快暴露出其虚假的一面,这为敏感的文人所捕捉,当泛滥的理性将现代铸就成新的“铁笼”,知识分子开始警觉其背后所掩盖的深刻矛盾并探寻化解的途径,由此构成法兰克福学派试图探讨的核心议题之一——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以及对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的追问。在对现代社会的文化、心理、政治、经济等方面展开整体性批判的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逐步形成了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武器——批判理论。
批判理论的核心概念“文化工业”,最早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区别于“大众文化”而首次使用于《启蒙辩证法》一书。文化工业于“穷困的慰藉和虚假的幸福……培植着一种真实的渴望”[1]。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文化工业社会是一个裹着糖衣炮弹的单向度社会,是巩固现存社会秩序的“社会水泥”,在看似人人平等的自由中藏匿着对人性的深刻压抑,正如马尔库塞的提示,“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但仍然是奴隶”[2]。这种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的可怖之处不在于统治集团依靠资本主义早期的血腥暴力奴役大众,而是借助媒介、机构、体制等实施思想管控,借助意识形态的灌输使大众从根本上实现思想认同,进而试图扼杀一切否定性的思想。科学技术在不断的迅猛发展过程中逐渐发展为统治人的异己性力量,是使法兰克福学派眼中的现代性危机成为可能的基础。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揭示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统治中起到的辩护作用,由此批判理论随“科学技术及意识形态”这一著名论断的提出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批判理论的直接思想根源可以上溯到本雅明的文化批判思想观念,由此本雅明被视为欧洲现代性最重要的见证者与反思者之一。在流亡的最后十年间,本雅明致力于为现代社会价值的失落寻求一条出路,众多的作品碎片构成了19世纪现代史前史的研究星丛,并凝结为《拱廊街计划》的思想框架。[3]颠沛的流亡生涯似乎是一种隐喻,本雅明一生也游荡于法兰克福学派的边缘地带,这既是身处异国的迥异经历使然,也是出于阐释路径与批判范式之间难以弥合的巨大张力——后者也可以在本雅明失败的法兰克福求职经历及与其他成员的信件往来中发现端倪。深植于弥赛亚神学的思想土壤,本雅明的目的远超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损毁与拆解,超于对“劫后余生者的历史”(after life)的颠覆,而指向重塑与回归,通过铺设救赎之路以无限接近于弥赛亚降临的时刻,实现的途径在于在捕捉现代性事件的过程中勾连起过去、现在与未来,在永恒当下中聚焦于个体的内在时间及整体感受。对技术的反思仍然是逻辑的起点,本雅明口中的技术既有艺术手法、创作技巧的含义,也将工具器械、物质媒介囊括其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申明了艺术的物质性,为本雅明在艺术生产理论中为技术所赋予的重要地位提供了理论合法性。由此,对技术的反思以艺术领域为中间环节转向个体经验感知的探索,本雅明在对技术不遗余力地热情赞颂之时,不忘揭示其在人与物、人与人、人与都市的关系方面带来的深刻变革,正如杨小滨所言,“本雅明对现代文明的估价是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是对现代技术的革命力量的激情的赞美,另一方面是对现代工业社会下人性的异化的深刻忧郁”[4],而后者在本雅明的思想后期显然更受关注。
一、“灵韵”的消逝与艺术的祛魅
在1936年7月致阿多诺的信件中,本雅明道出《拱廊街计划》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紧密联系,如果将前者视为工业影响下的19世纪艺术史,后者则是“去审美化”进程在20世纪的阶段性结果,[5]192即以“灵韵”(Aura)的消逝为特征的艺术裂变时代的降临。“灵韵”是本雅明在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之间划定出的一条分界线。传统艺术最初起源于巫术与宗教礼仪,其最初的神秘性、庄严性及历史感在随后漫长的艺术演变过程中逐渐淡化、凝练,最终成为附着于艺术作品之上,以独一无二性、即时即地性为特征的“灵韵”。本雅明对“灵韵”的集中阐释可以追溯到早期的《摄影小史》(1931)一书,随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6)中再次涉及。借助夏日午后“一座连绵不断的山脉或一根在休憩者身上投下绿荫的树枝”[6]90的自然经验,本雅明将“灵韵”描述为人处于自然环境而融于自然环境的独特主观感受,从中揭示的是近乎被现代人所遗忘的人与自然合而为一的生命体验。“照片从现实中摄取出光韵”[7],本雅明笔下的“灵韵”关涉自然景物是为了说明早期仪器捕捉“灵韵”的能力,其观照的核心对象仍在于艺术领域的物质实体。在晚期作品《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1940)中,本雅明对“灵韵”的定义再次进行了细微调整,认为“灵韵”需要“将回看我们的能力赋予这个对象”[8]241。这是一个将人与人之间交涉博弈、相吸相斥的互动模式移植到无生命客体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出若隐若现的本雅明式神学色彩。无生命体凝视主体,等待主体的到来,准备向主体言说;同时拒斥主体的真正到来,试图拉开与主体的距离,在回环往复的体认过程中,主体所感受到的微妙的平衡感就是“灵韵”。
技术复制时代的到来打破了“灵韵”本就岌岌可危的平衡状态,正如本雅明所说,“人们可以用照相底片复制大量的照片,而要鉴别其中哪张是‘真品’则是毫无意义的”[6]94,因大批量复制而得以四处散播的艺术作品颠覆了原作的权威性,审美领域出现的膜拜价值的没落正与马克斯·韦伯口中的“祛魅”(disenchantment)相对应,不同的是艺术依靠的是物质性的技术而非思想上的启蒙。巴赞认为摄影和电影被发明的意义正在于将主体的创造性干预由无生命的媒介手段所取代,在最大限度上满足人类的肖似性情结(resemblance complex),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复制技术可以被看作是一场现代性的集体幻梦。在新时代艺术中,本雅明将摄影工业的兴起视为典型,尤其以肖像照的出现为代表。肖像照消解了原有艺术观中肖像与上帝相连的神圣意味,继而引发既有观看之道的崩塌,同时,影像与新闻业之间所建立起来的链接很快为摄影赋予了全新的价值意义,昭示着一种现代性体验的交替过程,由此人与物之间的互动发生了本质的转变。
一方面,人与艺术品之间的距离被取消了,艺术迈下神坛走向大众,达到空间的同一。“现代大众具有要使物在空间上和人性上更易‘接近’的强烈欲望”[6]90,大众试图消除与艺术品在空间上的距离感,当最初供奉于神庙的雕像经过复刻出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复制技术满足了人类近乎偏执的占有欲。然而具有悖论意味的是,由技术解放出来的复制艺术恰是其依赖于物质的证明,人与艺术品都未能达到真正的自由:对艺术来说,艺术品正是刚刚挣脱出宗教礼仪的寄生关系,便被赋予观赏价值而成为大众凝视下的禁闭物;对大众而言,艺术的解放在本雅明看来无非是“‘世间万物皆平等的意识’增强到这般地步”[6]91的体现,是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继精神物化之后对个体经验层面的侵蚀。后者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根本否定的对象之一,被视为现代人异化问题的关键环节,印证了本雅明与其在思想上的亲缘性。
另一方面,由于机械的介入,人与艺术品之间相互回看的过程被迫中断,当下时间的连续性发生断裂。本雅明在此考察的是电影艺术。区别于一般的艺术复制,电影艺术中以精确、严密为标准的复制品被视作艺术作品而存在,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建立人与机器间的平衡”[6]54。在电影的生产过程中,观赏活动的整体性被技术割裂为两个在时间上相互错位的独立环节:由拍摄仪器捕捉演员的动作和声音,再由放映设备呈现给观众。沿用阿恩海姆的阐述,本雅明将演员视为一个精心选择的道具,[9]机械对表演的极大限制意味着演员不得不在镜头与镜头之间、幻象与现实之间穿梭自如,以适应在不断切割的拍摄过程中的自我流放,正如伊格尔顿所说,“社会所需要的是一种重构的身体,一种与技术密切联系、能适合于都是生活的突然的连接与不连接”[10]。同时,蒙太奇式的材料拼贴与陌生化的镜头调度扭转了观众原先的感知方式。阿恩海姆指出慢镜头不是简单地将快动作延缓后呈现给观众,而是将不可捕捉的画面真实化,替代人们有意识的编织出一种真实的体验感受,“通过摄影机了解视觉无意识”[6]120。不难看出,观影的两个步骤具有同一的指向性,即本雅明提出的技术复制时代人与机器之间的危机实则是一场现代社会中人有关自身的危机。
二、经验的贬值与小说的诞生
不同于德里达将经验与在场相联系,本雅明所反思的另一重现代性的感受方式在于经验的缺失。沃林将本雅明散落于文章中有关经验的论述归结为两个层面:一是根植于历史哲学的思想,经验被赋予了与康德认识论中的先验条件相契合的形而上意义;一是在审美范畴内,经验被赋予了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现实批判意义。[11]1924年本雅明与拉西斯的结识激发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就此而言,后一层面的意义是本雅明对脱去神学外衣的经验在社会历史层面的考察,也是约翰·伯格所承续并试图恢复的东西。在《讲故事的人》中,经验被视为“农田上安居耕种的农夫”或是“泛海通商的水手”[12]96口中与永恒真理相通的智慧与教诲,农夫与水手赋予经验以时空上的距离感,使“灵韵”的气息烙印其中。在《经验与贫乏》中,经验以谚语、故事、传闻等叙事艺术的形式呈现,通过人与人的口口相传成为超越于时间的集体性历史记忆。然而,为本雅明所担忧的,是现代社会中经验逐步走向贫乏的状况,这在本雅明的早期论述中来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个体心灵所造成的巨大创伤,并归结为内在体验及外在表达的冲突,到后期则转向揭示技术操纵对日常生活的渗透,更倾向于阿甘本所说的内外边界的不确定性。[13]
经验贬值的灾难首先降临到了个体的精神图景上,与巴塔耶将现代人视为非连续的存在相类似,本雅明认为相比于叙事形式由故事向小说及新闻的自然迭代,技术对个体生活的现实影响更具有危险性。一方面,本雅明指出文人为适应资本主义的运作而造成了自身价值的断裂。“小说家闭门独处,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12]99,印刷术替代远游者完成了空间上四散传播的任务,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种便利也是创作者与他人沟通交流的阻碍,“生命的深刻困惑”[12]99正是文人感受到自然整体的破碎后向媒介背后的资本主义控制机制发出的诘问。同样的境况发生在新闻出版行业,本雅明将马克思异化观念延伸到了咖啡馆里的工薪阶层身上,员工在顺应社会节奏的过程中遗忘了自我的价值,最终也沦落为换取报酬而出卖劳动力的被压迫的一员。另一方面,读者经验的完整性与统一感也随着信息的碎片化以及意义的剥离而被逐渐瓦解。过去讲故事时人与人、人与自然相统合的松弛状态已经无可挽回,沃林将现代生活中的经验结构概括为“散漫的、孤立的、绝对的私人特征”[5]192,这种个体的封闭性与阅读之间的内在逻辑在《小说的危机》中被揭示出来,作为“灵韵”消逝之后的新型艺术样态,读者所面对的是过滤掉永恒的人类经验之后剩下的信息化工业废渣,小说的价值只存在于它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那一瞬间。个体的贫乏不过是更大范畴内的贫乏的一部分,本雅明指出经验的衰退不仅仅局限于个体层面,更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人类整体的经验现状。古老的讲故事技艺是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将人类的当下与过去相连,然而机械的崛起既在时间上斩断了现代人与前人历史的承续,也在空间上隔断了人与人之间经验的联结,个体遭受到的双重剥离使人类无法再成为整体的聚合,先前自由的听故事者成了现代都市中冷漠、麻木、彼此孤立的抽象的个人。
面对经验的日益萎缩,齐美尔试图借助内在体验的审美化抵御外部世界对人的规约,与之相同,本雅明为现代人开出的药方在于返还个体的内在世界。作为内在生命经验的自传式书写,《追忆似水年华》具有唤醒经验的世俗启迪(profane illumination)意义,继承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将经验与记忆紧密联系的哲学传统,本雅明将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小说视作恢复传统经验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基于早期与海德格尔共同参与生命哲学选修课的相关经历,对柏格森的批判继承使本雅明与传统相背离,将经验理解为“在记忆中积累的往往无意识的材料某种汇聚的产物”[8]193,相互渗透的当下时间被视为衡量生命的价值尺度。在这一层面上可以看出本雅明尝试将沃林所划分的两种经验拼合到一起所做出的努力,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呈现于个体的经验层面,本雅明聚焦于普鲁斯特的“非意愿记忆”(involuntary memory)。现代人的记忆是理性压抑之下屈从于现存制度的线性记忆,而非意愿记忆则是在非理性的追忆下以心理时间为线索的无序性记忆,本雅明认为后者才是真正属于个人的历史经验。非意愿记忆表现在艺术中包括以故事为代表的传统叙事艺术,以及以意识流小说为代表的新型叙事艺术,二者的共通之处在于融入纯粹信息之中的生活化的个人经验。在本雅明看来,这正是解开叙事艺术中“灵韵”的密钥,为本雅明所否定的现代叙事艺术是断裂的、瞬间性的,借助记忆起停留在意识表层的意愿记忆构架而成;意识流小说则是流动的、生成性的,在空间化的时间中打破历史的连续性并联通过去的经验,起到唤醒个体真实经验的重要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意识流小说以新的形式延续了传统叙事艺术中的“灵韵”之美。
三、艺术的大众化与政治化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大都市是人造的第二自然,一个失去“灵韵”的自然,经验的极端碎片化以及信息的无限膨胀将个体抛掷于各种感官刺激当中,震惊体验(shock experience)成为现代人感知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在危险的穿越中,神经紧张的刺激急速地接二连三地通过体内,就像电池里的能量”[14]146,电流穿过的刺激感是本雅明用以描述震惊体验的现代性隐喻,揭示个体受到外部刺激的刹那迅疾、强烈而无所适从的心理体验。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经验能力的流畅性与体验状态的紧绷感属于两个相互拮抗、此消彼长的体验范畴,当个体受到过于强烈的外部刺激时,为避免个体受到过度刺激的压力,未能被既有经验接受的部分会经由意识的防御系统进入无意识领域,然而防御机制的代价在于,个体内在经验的连贯性为体验的碎片化所取代。从审美经验角度来看,震惊也是“灵韵”消逝带来的连锁反应,二者处于绝对的对立关系中——笼罩着“灵韵”的传统艺术与柏格森的绵延、普鲁斯特的追忆相联系,是一种对于内在时间流的领悟,在艺术创造中具有永恒的价值;相反,以震惊为接受方式的现代艺术援引自弗洛伊德的《超越快乐原则》,是一种对于外在世界的感官刺激,其特质在于可修正性。
本雅明将城市的人群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城市感受者的普通大众,他们“不得不去适应一种新的、十分陌生的环境”[8]101,而适应方式是醉心于机械的统治,疏离自己的同类并成为机械的一员。与被动的普通大众相对应,另一类作为城市体验的承受者与揭示者而存在,被本雅明称之为闲逛者(flaneur),他们是藏匿于人群中、观摩着人群的人。不同于一般人群的观摩方式,他们看似无所事事的懒散背后是“一个观察者的警觉”[8]105。由爱伦·坡开创的侦探小说是闲逛者艺术表达形式的内核,其中神秘、颓废、超自然的气息正来自令人错愕的城市体验,这种适应于现代都市的感受方式与描写风格为波德莱尔妥善保留了下来,并借此完成了对现代巴黎的书写。本雅明依附于波德莱尔的躯体游走于街道、百货商场、拱廊街等城市的各个角落,在《拱廊街计划》中将闲逛者的幻梦刻画为城市的缩影。与帕克边缘人(marginal man)的处境类似,自诩为闲逛者的波德莱尔被困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处,洞察的眼睛并不能使他成为拯救大众的英雄,甚至不能改变自身生活的困窘,本雅明不无嘲讽地公布了波德莱尔出卖自己的作品换得一万五千法郎的微薄收入,这也正是闲逛者的普遍处境——“他们好像是一个闲逛者走进市场,说是到处看看,实际上是寻找买主”[8]92,他们最终屈从于资本主义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迷失在商品触发的震惊体验之中。
本雅明显然看清了在技术发展下的现代艺术的两种走向——商品化与政治化,将文人同妓女的类比既是对文人为金钱而写作的近乎刻薄的同情,也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强烈批判。延续现代哲学中尼采对同一性问题的探讨路径,本雅明继人的标准化之后,又揭示了物的同一性谎言,即绝大多数艺术作品在以金钱衡量一切事物的时代沦落为了附庸于资本主义的文化商品。另一方面,尽管看到了艺术在技术复制时代走向堕落的一面,本雅明同样意识到流行艺术与技术革新中动人的革命潜能。与后期日渐浓厚的“激进共产主义”的思想相契合,本雅明为失去“灵韵”的现代艺术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以适用于现代人的体验方式唤醒大众的革命意识。本雅明的立足点在于复制艺术在自由走向大众的过程中赋予了复制对象以现实的活力,并蕴含着平等和民主的意识。“没收电影资本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项迫切要求”[6]96,这是本雅明提出的革命路径——在文化领域争夺自主权,在这一点上本雅明更接近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文化并非单方面的服从之地,更是一个充斥着协商、支配与对抗的斗争之所。在大众化的复制艺术中,本雅明将无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希望寄托于以电影为代表的反叛性艺术上,与卢卡契把先锋派等同于法西斯主义的批判态度不同,本雅明认为“在达达主义者那里,艺术品由一个迷人的视觉现象或震慑人的音乐作品变成了一枚射出的子弹;它击中了观赏者”[6]123,无论是拼贴画、蒙太奇还是自动写作,无论是构成主义、超现实主义还是达达主义,先锋艺术通过迅猛、强烈的触觉冲击传输出批判和否定的能量,以现代的方式撕毁了现代性谎言。
如果说本雅明将超现实主义界定为一场政治运动[15],那么电影作为最具有震惊效果的艺术形式,无疑因最大化地继承先锋艺术的反叛行为而受到本雅明的青睐。恩格尔指出,“感知的现代方式和环境条件创造了新的感知手段”[16],正是出于“对刺激的新的急迫的需要”[14]191,蒙太奇式的剪辑手法应运而生,并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手段使电影由复制品进入艺术的领域。受到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启发,本雅明认为蒙太奇电影不断变换的画面可以起到史诗剧般的间离效果,通过打断观众的情感共鸣来恢复观众的理性思考,督促观众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价值判断中,重构法西斯政治审美化的凝神静观模式。“个人反应的总和就组成了观众的强烈反应”[6]52,当个体的反思凝聚为集体性行为,大众便构成了革命的行为主体,本雅明在现代艺术灵光消逝的裂隙中看到了政治实践的潜能。在对包括《战舰波将金号》在内的苏联电影的观察中,本雅明将艺术的大众化归因于复制技术强大的表现力。技术作为一种中立性存在,其功用取决于使用者,由此,面对法西斯主义不断向战争迈进的政治生活审美化,本雅明呼唤共产主义由技术引领艺术的政治化对抗法西斯的技术奴役。这种将复制艺术视为政治宣传工具的观点,为阿多诺所激烈批判并由此引发了著名的阿多诺-本雅明学术论战。正如郭勇健所指出的,艺术的政治化以牺牲艺术为代价,以政治功能为主导而附带艺术功能的电影已经不再属于艺术范畴了。[17]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受制于所处时代,本雅明将技术与艺术、政治相连的理论思考对理解现代艺术无疑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四、结语
可以看到,作为人类肢体与感官延伸的技术媒介异化为统治人类的工具,外部物质世界由于过度泛滥滋生着丑恶与野蛮,当这一切发生之时,令本雅明感到忧虑的是人类内部精神世界的危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光怪陆离的都市影像刺激着现代人的神经,为抵御现实的偶然性与不可预见性,个体的经验感受能力在不断萎缩中变得麻木,并不可避免地倒退到冷漠疏离的孤立状态中。从审美角度来看,可以解释现代艺术在丧失“灵韵”之后何以给人以晦涩不明、荒诞不经而支离破碎之感,这其实是艺术家对现代化图景的精神性表达,也是对一个陌生世界的再次思考。基于现代性岌岌可危的末日图景之上,本雅明赋予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以救赎的最终使命,并由此提出了指向审美途径的救赎之路:其一,在新型艺术中再现“灵韵”,借此回溯到人类的历史中寻回个体以及集体的历史经验,在寓言式的象征中审视当下,寻求未来的希望。其二,借助新型艺术的震惊效果驻足当下,在反思中完成对未来的实践。也许本雅明对历史、当下与未来的勾连只能停留在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中,但他对现代世界的理论介入无疑能够带给人希望的力量,这正是本雅明之所以令人着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