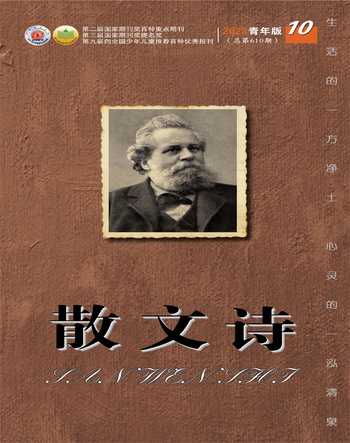梦花树
陈颉
火引子
一棵树,准确地说是松树,一直在等待松油的溢出。树干留下的刀痕,一双双眼睛,擦亮乡村夜色。
外地人跑来湘西,目光落在山岭深处,异乡的夜,枕着松油的清香,含风,饮露。
总是在六月,父亲带上斧头,翻山越岭,找寻皴裂的树干,而后劈下一道道深沉的影子,汗水流动的缝口,半个时辰的简捷动作,被落日填满。
乡村摇晃的烛火,如同父亲的身世,淡黄色木块碎屑泛着青光,丢给了我的童年,袅袅炊烟,留给人间的,除了朴素的芬芳,记忆的色彩,还有日夜不息的温暖。
收蜂
四月,外来或拆分的蜂群,偶尔会落在堂前的一棵树上。黑压压一片,上下微微滚动。
反反复复,形状在不停地转换。
父亲搬来梯子,口中念念有词,扛在肩上的蜂桶,白得耀眼,洒在桶内的糖水,一道深渊,停下或腾飞,隐藏一个更大的舞台。
时光缓慢,蜜蜂是一把铜锁,安身立命,是一片林海的高度,一朵花的神妙,一个季节的法则。父亲,木工手艺,韵脚平仄,早已备好梧桐木蜂桶。
小小精灵,敬畏需要轻脚轻手,循循善诱,需要坚持和拘谨,需要把时间还给呵护和沉稳,距离是技巧,也是一枚螫针的心跳。
与蜂对话,恰当的场景,熟悉的味道,如此紧密。一只蜂王,有些僵硬的身板,在乡村一角,看到了自己精灵般的影子。
梦花树
屋当头,一棵梦花树有些兴奋,萌生的嫩芽,已经适应山村的天气,一点点,疏朗,谨慎。
细微的声音有了年轻的模样,一些温暖的记忆,在晨雾中露出了春的破绽。
母亲告诉我,她梦见了过世的奶奶,乡村的夜晚,总是留有一些端口。
早晨起来,我看见梦花树上,又多了一个用树枝挽成的结,念想已经藏在母亲落满雪花的头顶。
换瓦
落下的瓦片,让静寂的山村在晨雾中醒来。一缕清风,梳理着木屋剩下的骨架。
六十年,山坳的一个窗口,在黑夜的灯光里,隐藏着两位老人,他们早出晚归地劳作,上雨旁风的木屋,落满了尘世的雨雪。
八十多岁的岳父,弯下腰,捡起小片碎瓦,而后又轻轻放下。时光封存的内心,放在瓦片后面,那么抽象,那么具体。
感恩寺
我走过去的时候,一个音符,跳过漫长年轮。
时光缝隙,桃花编织细雨,群山墨绿。
石头在风中摇晃,一滴眼泪,红颜女子的颂词。
目光做成梯子,一朵白云,在风中变轻。
一件器皿,凡尘香火,轻烟荡漾,一根金针,兑现时光苍茫,众多言辞,低于灵魂宿命,时间刀刃上,隐忍梦境。
尘世的光线,验证记忆。
岁月的尘埃,是镶嵌在经声里的宝石。
旧衣情结
这么多年,母亲一直对旧衣念念不舍。
童年的我,弟弟和妹妹,总是一个接一个,穿着母亲从城里亲戚家带回的旧衣。
或大或小的衣裳,的确良、的确卡,尼龙和灯芯绒,各种材质,最后都由母亲亲手改制而成。
油灯下,母亲飞针走线,细描细绣的身影,若隐若现。三个儿女依偎在火塘边,欣喜穿胸而过。
几十年了,母亲仍然对旧衣情有独钟,从未忘记艰辛岁月里为孩子绣出的喜悦。
每到城里,母亲不忘翻箱倒柜,把我们没穿的衣服一件件收起。戴着老花镜,母亲缓慢迟钝地裁剪着,村上邻居家孩子们的沉默和温暖。
时光依旧,母亲淡薄的身影,让我退回到童年的春天,丝丝白發,点点感伤与悲苦,沉默的注脚,仍然有着慈悲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