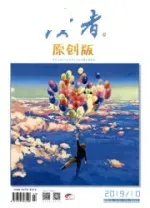外婆家
文 | 熬糖大姐

一
外婆五六岁时就被送到外公家,是那个年代所说的“童养媳”。倒不是外公家多有钱,只是一家穷,另一家更穷罢了。
小时候,每到阳光灿烂的星期天,妈妈就牵着我去外婆家。那时我们住的家属院院子里有棵大梧桐树,邻居奶奶们在树下面支张小桌子,放几把小竹椅,烧了饭菜、切个西瓜端出来吃。她们坐在竹椅上跷着腿扇扇子,不紧不慢,晃晃悠悠,妈妈牵着我路过时,她们热情招呼:“回家啊?”我妈笑着回复:“是啊,回家。”
那时候,我不懂,明明是从自己家去外婆家,怎么能叫回家呢?
等人到中年才明白,妈妈也有妈妈,有妈妈可喊,就有家可归。
走出家属院,爸爸骑上“二八”大杠,前面坐着我,后面坐着妈妈,骑大半个小时就到了乡下。那时候,路上没有那么多交警,也没有那么多汽车。
外婆家在王家村,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个城中村。村里大部分人姓王,家家户户算起来都沾亲带故。每户人家都有自己安身立命的小生意,有炸猪皮的,有炸豆腐果的,有做豆腐、磨豆浆的……外婆家门口有个小猪圈,几只白花花的猪仔拱来拱去,猪圈外面守着我4岁那年抱回来的小黑狗。出了屋门,走几分钟就是菜地,种了青菜、长豆,记忆里似乎还有些草莓。冬天支起大棚,妈妈把澡盆和热水提进去,我就在大棚里洗个暖烘烘的澡。
印象中,外公不太管家里的事情,房前、屋后、菜地、家禽都是外婆在张罗。外婆太辛苦了,妈妈时常叹气。这叹息里,有对外婆的心疼,也有对外公撒手不管的小小抗议。
进了家门,第一件事就是被外婆用三轮车拉着去村口唯一的小卖部,买两包话梅,一瓶“香槟酒”。想来那不是真正的酒,大概就是充了气的葡萄汁,但已足够让我欣喜。这些都是只有去外婆家才能享用的美味。
这美味我不会一个人独享,村上有个大我几岁的女孩,胖乎乎的,愣头愣脑,大家叫她“小傻妞”。
她每天在村里无所事事,看看这家的鸡鸭,和那家聊上两句,日子倒也称得上无忧无虑。讲起来,我和她是老熟人了,但我一直搞不清楚她的家人是谁,因为她总是一个人出来晃悠。小傻子很喜欢我,每次听说我要来,就早早在门口候着,见到我,一脸憨笑:“糖糖,你来啦。”我就把手上的话梅分给她一些,有时候,她也会带一包麦丽素分给我。
我们在空旷的屋前逗弄小黑,小黑带了些狼狗的品相,长得高大粗犷,脾气却像个温顺的小孩,总爱赖在我怀里。那时候,我很是有一些“本领”,比如跳绳、吹笛子、转呼啦圈,总想着显摆两下,唯一热情捧场的观众就是“小傻妞”。她总是耐心地站在一边,用欣赏的眼神看我表演,最后喃喃总结:“糖糖好厉害。”
那个时候我不懂,现在想来,她也许确实不聪明,但话里和眼神里,似乎常常透露出一些复杂的羡慕。
到了晚饭时间,外婆叫我吃饭,也会喊她一起吃。
她从未答应过,外婆的邀请对她来说仿佛是在赶客,于是,她带着憨憨的表情和我道别。她知道,吃完晚饭,我就该回家了,下一次碰面,得过上两三个星期。而我也是过了很久才意识到,我也许是她童年里唯一的玩伴,即便她有些愚钝,但这愚钝不足以掩饰她见我时的开心与分别时的不舍。
晚餐的饭桌上永远有我爱吃的嫩炒猪肝,外公递给我一个小酒杯,让我郑重地满上“香槟酒”,认真和每一个人碰杯。
有时候,我们会去看住在村子另一头的太婆—外公的妈妈。太婆在我记忆里一直是很老很老的样子,她的脸上布满沟沟壑壑,眼睛是凹进去的两条缝,听说是年轻的时候遇到意外导致的。
每次去看望时,裹过小脚的太婆都要颤颤巍巍拎一个小凳坐到屋外,絮絮叨叨和我们说好久的话。说实话,我和她之间,隔了太多的年岁,没有多少能聊的话题。她的家门口有一棵不那么茂盛的鸭枣树,夏天会结不那么饱满的果子,看起来和不那么有力气的太婆很相配,那是我去看她的最大动力。外婆可以陪太婆聊一整个下午,她们是婆媳,但更像母女。我就慢悠悠嚼着鸭枣消磨时光,把果核摆成画,偶尔把咬碎的果肉扔在地上,看蚂蚁把它们慢慢抬走。
二
相较而言,我的爷爷奶奶颇有些严厉,每次去见他们,我总要带上成绩单和三好学生奖状,然后聆听一通教诲。他们时常让年幼的我感到沉重。而去外婆家的心境是特别轻松的。他们从不问我读书怎么样,考了多少分,有没有新奖状。他们只关心今天烧的菜我爱不爱吃,零食有没有吃够,这一天玩得开不开心,然后夸我是个特别厉害的小孩。
那真是一段最纯粹的日子,闪耀着清澈童年的万丈光芒。
时光就这样慢慢走,慢慢走。守着猪圈的,从一只小黑,变成小黑和她的一群宝宝;再走着走着,狗宝宝们各自被领养或者跑丢;最后,小黑也没了。
随着年纪渐长,外婆不种地了。外公拿出临街的一间房,开了个小卖部,我不用再去村口的小卖部买话梅了。
小黑没了,菜地和猪圈没了,到后来,村子也没了—王家村要拆迁了,在原地盖楼房,建小区。大家各自出去租房过渡,待楼房盖好了,还搬回来原地安置。
可是到那时,就不是原先样貌的王家村了。大家陆续搬走,村民们互道“保重”。在这里住了60多年的外公外婆,对着墙上画了圈的“拆”字,坐在刻满岁月的门槛前哭红了眼。
妈妈倒是松了一口气,老两口终于也能住楼房、吹空调,冬天不用去大棚洗澡了。“安度晚年”这几个字,听起来就很幸福啊。
我也长大了,课业日渐繁重,纯粹的童年渐渐远去。等再去外婆家时,大家已经搬进新小区里的新楼房,王家村的村民们在时隔两年后,又聚到了一起,只是再不能像以前那样,每天随时在田间地头相见。
三
住进新房子仿佛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一年,我们经历了两次刻骨铭心的悲伤。
第一次,是很老很老的太婆去世了,漫长的生命定格在百岁。搬进楼房的太婆,终日困在她的小房间里,这里的一切都已不是她熟悉的王家村。她再不能自己摸索着出门,摸索着摆弄土灶,摸索着去照顾那棵飘摇的鸭枣树。我想,在她的生命体征消失之前,心就早已先行一步了。
第二次,是外婆病了,胃癌晚期。这时我才发现,外婆越来越小了,不知不觉,已经矮了我整整一个头。
我们去外婆家的次数又变多了,妈妈总是找各种名目把大家凑在一起:过生日,过完阴历生日过阳历的;过各种节日,“来得人多,家里热闹,病人高兴。”妈妈这样说。
外婆在病榻上缠绵了3 年多,最后的那些时日,她已分不清白天黑夜,大部分时间在昏睡,偶尔低声喊疼。外婆是一直在忍,实在忍受不了了,才低低喊两声,不知道她是以怎样的毅力在支撑。这个五六岁就当了童养媳的女人,穷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种了几十年地,刚要过上好日子,就再也没能爬起来……
外婆安葬那天,王家村上下四代、几百号人都来了,我站在坟头,看着下面黑压压一片人头,感慨万千。这一个村的人,平时也有磕磕绊绊,但关键时刻谁也不缺席—这种一个村随时拧成一股绳的壮观场面,我们这一代城里的独生子女,怕是再也没有机会见识了。
我没在意人群里有没有“小傻妞”。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她已被我遗忘了好多年。
外婆走后,妈妈说她没有家了。“以前总说,回家去,回我妈家去,现在妈没了,不知道要怎么说。都说回娘家回娘家,没有说回爹家的。”
也许自小就被送走的外婆没有体会过母爱,因此不愿让女儿再有爱的空白,妈妈最懂妈妈。
如今妈不在了,女儿再无妈妈可喊,再无娘家可归。
妈妈没了妈妈,我去外公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今年过年,我去探望外公,走到小区门口,居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她穿着肥大的棉衣,像一只笨拙的鸵鸟慢慢走到我面前,咧嘴冲我憨憨一笑:“糖糖,你来啦。”
那一刻,天光乍亮,时间仿佛倏然回到30年前,一切都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