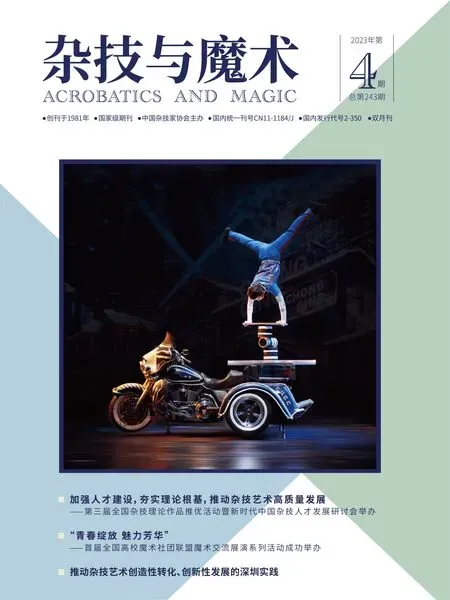评杂技剧《化·蝶》的艺术之美
文|于哲
杂技剧《化·蝶》由广州杂技艺术剧院创排,是中国杂技剧在舞台艺术美学视野、美学高度和深度上的重要尝试,代表着杂技剧艺术互融的发展导向。
一、故事题材展现传统美学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文化历来推崇“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明确指出了要运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百世阙文中吸收精粹,在千载遗韵中博纳众长。
杂技剧《化·蝶》取材于中国古代民间四大爱情故事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梁祝”故事具有积极的浪漫主义色彩,展示了主人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未来生活的期盼,充斥着对古代封建主义丑恶的憎恶与批判。这个故事之所以能广为流传,经久不衰,就是因其具有现实性和典型性,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冲破封建牢笼、追求美好爱情的精神实质。可以说,杂技剧《化·蝶》从取材方面,就已经站在了美的基础上。
一是形象之美。杂技表演艺术家吴正丹扮演的祝英台,身形纤纤、服饰飘逸,展现了东方女性的柔美;化身男儿郎、读书明志,又展现出俊朗之美;勇于追求爱情、向往自由婚姻,表达出民间女子果敢坚毅的心灵之美。二是人性之美。人性的光亮之处在于追求、向往一切美好的事物,要想释义人性之美,就不得不与“悲”紧密联系,因为“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正因为把崇高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所以能使人悲愤,给人力量”①。《化·蝶》中“生不同衾”令人悲愤,生出极度怜悯;“死欲同穴”让人有所寄托,产生强烈的愿望。悲剧中的美是充满抗争的,是能够激发人们的同情和敬仰的,是激动人心后最能表现人文主义精神的人性之美。
所以说,《化·蝶》是站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人文精神的进一步弘扬;是以杂技艺术的创新表达方式,对流传千年的民间文化的脉脉相承;是将戏剧的“悲情”的美学观念用杂技语汇来塑造实践;是将美的故事与美的技艺碰撞融合后,呈现于舞台之上的中国故事之美。
二、杂技语言诠释舞台艺术之美
舞台艺术的美是直观存在的,是最表象的视觉、听觉的感官刺激,即“眼见为实”。通过感官带动,美的感觉直达内心,这就是我们说的美是感性的,需要结合感觉和思考来解读和诠释美。在《化·蝶》的舞台艺术之美的表达中,美和丑都是对立出现的,美的“身旁”无时无刻不伴随着丑的衬托。
“亲变”一幕中,主色调以红、黄为主,代表喜庆和金钱,手技道具都变成了金银元宝、珍珠、铜钱等,以表达贪慕钱财、势利拜金、卖女求荣的故事情节。用为人父母最丑陋不堪的一面和人性最丑恶的嘴脸来反衬梁山伯与祝英台纯洁爱情的美好。在剧中,滑稽丑角“媒婆”也被赋予了戏剧化的作用,是全剧由喜至悲、由善转恶、由生到死的转折点。“媒婆”柔韧、力量等传统杂技技艺的展示,将“美”与“丑”扭结和人性的贪婪展现出来。
在舞台艺术中,“情趣”是感染力的重要源泉,也是表演获得成功的诀窍。《化·蝶》在展示杂技技巧时,更注重情趣的表达和情感的抒发,并提倡情感的共鸣。在情趣共鸣上,《化·蝶》有两个值得借鉴的特点:一是“共读”时抛接技巧组合使用的扇子、毛笔,“情别”时蹬技用的伞,这既是一种传统文化氛围的渲染,也是梁山伯和祝英台生情的志趣相投、情别时的情感寄托。这种通过杂技道具来作为情趣的激发点,引发舞台上下的共鸣,是创作中的巧思。二是纵观《化·蝶》全剧,肩上芭蕾暂且不谈,其他十幕鲜有高难度技巧展示,这就是杂技“剧”化的特点,一切艺术形式皆须服从叙事、铺陈情节、助推矛盾、升华思想,从而高度凝结对美好爱情的追求与叹息。
笔者认为,杂技无论是在表演还是在技巧上,从不曾“程式”化。无论是杂技节目、杂技晚会还是杂技剧,一直以来就是“为我所用”,千人千态,从不拘泥一格。这种表现的自如,不仅是技艺高度娴熟的展示,也是舞台艺术的魅力所在。比如,《化·蝶》“抗婚”一幕中,以双人绸吊为表现基点,以自如娴熟的技法为表达途径,以技巧美为主旋律,调动绸带、服饰、表情、肢体等一切美的因素,共同奏出以柔克刚、勇敢抗争、冲破束缚的自由心声。
三、艺术美的递进式表达
“艺术创造艺术之美……并且还可以通过主体的意识作用把现实中原本不美的或丑的事物转化为艺术美”②。这就是之前所论述,《化·蝶》中的“丑”时刻与“美”对立,丑始终伴随于美。但与现实美不同,艺术美是高于现实美的,是通过技、艺、意境三个层次的递进,最终到达美的彼岸。
杂技技艺中,具有明显的趣味性,这种趣味是有悦耳、悦目的性质,并带给观众轻松、明快和愉悦。在杂技剧中,技艺得到了升华,达到“物我唯一”的美学境界。《化·蝶》中的暗线——道具空竹贯穿全剧,从“蝶生”中的男子集体空竹到“情生”中的四人空竹,至“幻境”中的双人空竹,空竹成为全剧情起、情聚、情断的代表,赋予了“抖空竹”新的含义,将一根丝线比作情丝,裹挟于梁山伯的腰间,直至入心入血。传统技艺在经过再次创作中得到升华,加持人物角色情感的精髓,直抵观众内心,形成热烈真切的审美环境。
“在杂技技巧演绎的形式中更强调其内在的审美功能,即把‘技’的表演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文化意义的肢体语言”③。中国杂技剧的发展,绝不可能是杂技技巧单一的纵向突破,必然是多重艺术的融合式的横向发展。《化·蝶》中除通过舞美、灯光、音乐、服饰等手段的烘托外,极具特色的是舞蹈与杂技艺术的完美融合,以达到悦心悦意、神形兼备的美学效果。“闺念”中舞蹈与柔韧顶技并存,“梦聚”中双人舞深情演绎,“化蝶”“蝶恋”中“肩上芭蕾”惊艳亮相,全剧以“技”起舞,从容而舞,形舒意广,令人远思长想。
杂技艺术的审美价值,还在于通过“技”和“艺”展现出的意趣,直达于观众的理智,唤起求解的心情,激发理想之美。从《梁祝》故事原型看,梁山伯与祝英台为爱殉情,属极悲;双双化蝶,自由相伴,也算是挣脱世俗的美好结果。杂技剧《化·蝶》中深度创作“蝶恋”,将化蝶后的大悲再次推向高潮,对美好爱情的期盼向往达到顶峰。“肩上芭蕾”演绎“化蝶”“蝶恋”全过程,指尖轻盈的飞舞,足尖灵动的旋转,臂膀强劲的依靠,头顶全力的托举,将梁山伯与祝英台至纯至净的爱情赋予最美的表达,意与境二者浑然融彻。
《化·蝶》的演绎,是中国杂技剧在舞台艺术美学视野、美学高度和深度的重要尝试,它蕴含着杂技美的奥秘,寄托着美的理想。《化·蝶》用言简意赅的舞台语言、凝练节制的情感传递,将技艺融合、意境深远的杂技美表达在艺术的舞台,是对中华传统美学思想、文化立场和文化基因的坚守不渝。
注释:
① 霍松林:《文艺学简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第313 页。
② 王宏建:《艺术概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 年,第82 页。
③ 高伟:《当代杂技漫评》,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20年,第1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