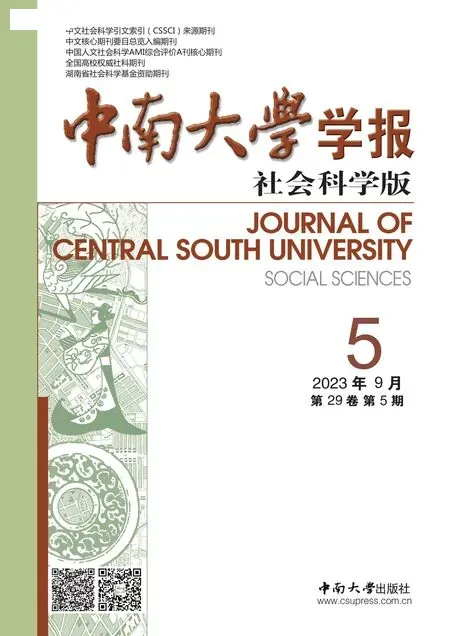支遁般若“即色义”的内涵及相关问题
汪伟
支遁般若“即色义”的内涵及相关问题
汪伟
(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魏晋佛学名家支遁提出的般若“即色义”在哲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但因为直接史料的匮乏,其含义一直众说纷纭。全面分析支遁的存世文献,发现般若“即色义”具有三层含义:色由于因缘无常、不能自有,有事用却是空(“色即为空”);色毕竟有事用,并非断灭虚空(“色复异空”);证悟般若要求以“凝神”状态打破“色”“心”二执,既超脱于色的事用,也不执迷于般若本身。“即色义”中色、心二分的思维结构不仅构成了支遁诠释“逍遥新义”的理论基础,还深刻地影响了其弟子郗超的般若空观。支遁“即色义”已然十分接近僧肇的般若中观理论,“色即为空”便意味着“缘起性空”,但“色复异空”不同于“缘起假有”,只是强调了色的事用。
支遁;即色义;因缘;凝神;至人之心
一、引言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来,就逐步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到了魏晋时期,在玄学的概念语词与佛玄融合的方法论影响下,时人对佛学体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支遁作为当时“六家七宗”中“即色宗”的代表人物,不仅在佛学上开创了颇具影响力的般若“即色义”,还化用佛学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逍遥新义”,推动了佛学的本土化传播。因此,把握支遁般若“即色义”的深刻内涵,是了解佛教早期本土化进程的关键一环。但支遁研究《般若经》的作品几乎全部亡佚,导致后世学者对般若“即色义”的确切含义一直争论不休。汤用彤先生考证发现,现存完整的支遁文献只有《大小品对比要钞序》和若干篇诗文创作,另有后人引用的《妙观章》《即色论》《即色游玄论》三文片段[1](172−173)。与般若“即色义”直接相关的史料,只有后人所引的这三文片段。
一是《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所引的支遁《妙观章》:
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色而空。故曰色即为空,色复异空。[2](263)
二是惠达《肇论疏》所引的支遁《即色论》:
吾以为即色是空,非色灭空,此斯言至矣。何者?夫色之性,色不自色①,虽色而空。如知不自知,虽知恒寂也。[3](59b4−6)
三是安澄《中论疏记》所引的支遁《即色游玄论》:
夫色之性,色不自色。不自,虽色而空。知不自知,虽知而寂。[4](94a21−23)
另外,僧肇在《肇论》中批评“即色义”的文献,也很可能与支遁有关:
即色者,明色不自色,故虽色而非色也。夫言色者,但当色即色,岂待色色而后为色哉?此直语色不自色,未领色之非色也。[5](152a17−19)
支遁的般若思想与“色即为空,色复异空”一句直接相关,但直接史料只有只言片语,没有明确交代“色不自有/色”和“色复异空”的内涵。于是后世出现了三种争论意见,分别以安澄、元康和文才为代表:安澄认为僧肇批评的是“关 内即色义”而不是支遁。他以缘起法来理解支 遁的“即色义”,主张支遁既认识到了色无自性而为空,也把握到了“假有”,与“不真空”等同[4](94a27−b2),即“然不偏言无自性边,故知即同于不真空也”[4](94b1−2)。但安澄没有对这一解释提供任何证据支持。元康认为支遁“即色义”对缘起法的理解已经较为深刻,但仍然与僧肇的般若中观理论有一定的差距,这导致了僧肇对支遁“即色义”的直接批评。在元康看来,支遁只知道色是由因缘而成,却没有理解色的“空”性与“假有”,即“但知言色非自色,因缘而成,而不知色本是空,犹存假有也”[6](171c23−24)。文才也认为僧肇批评的是支遁“即色义”。他主张,支遁“即色义”是指青黄等相不能自为青黄,人心计虑才名之为青黄,心若不计则青黄之名皆空,所以支遁只知名假而不知相空[7](209a13−29),即“未达缘起性空,然缘起之法亦心之相分,能见之心随相而转,取相立名名青黄等”[7](209a25−27)。然而,文才对支遁“即色义”的解读与“六家七宗”中“心无宗”的主要观点太过相似,而支遁“即色义”的直接史料中并没有提到“心”,其存世文献中也没有用到过“名相之色”。
本文拟通过全面分析支遁的传世文献,并参考其弟子郗超的般若思想②,阐释支遁“即色义”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分析支遁“即色义”与“逍遥新义”的关系及其在佛学史上的地位。
二、支遁般若“即色义”的内涵
本文认为,元康对支遁“即色义”的诠释框架大体可取,但支遁“即色义”应该理解到了“缘起性空”,只是没有注意到“缘起假有”。“即色义”的内涵应该是:“色”由于因缘无常、不能自有,因而为“空”(“色即为空”);但色毕竟有事用,并非断灭虚空(“色复异空”);证悟般若要求以“凝神”状态打破“色”“心”二执,既超脱于“色”的事用,也不执着于般若智慧本身。
支遁“即色义”的直接史料将“色即为空”解释为“夫色之性,色不自色/有,虽色而空”,表明色的“空”性由某种条件决定。这种条件是指因缘吗?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澄清支遁对“有”“无”“空”这组概念的理解。
在《大小品对比要钞序》中,支遁通过分析 “存/无”“所存/无”“所以存/无”这组概念,揭示了“有”“无”与般若“空”的复杂关系。相关段落为:
夫般若波罗蜜者,众妙之渊府,群智之玄宗,神王之所由,如来之照功。其为经也,至无空豁,廓然无物者也。无物于物,故能齐于物;无智于智,故能运于智。是故夷三脱于重玄,齐万物于空同,明诸佛之始,尽群灵之本无,登十住之妙阶,趣无生之径路。何者耶?赖其至无,故能为用。夫无也者,岂能无哉?无不能自无,理亦不能为理。理不能为理,则理非理矣;无不能自无,则无非无矣。是故妙阶则非阶,无生则非生,妙由乎不妙,无生由乎生。是以十住之称,兴乎 未足定号;般若之智,生乎教迹之名。是故言之则名生,设教则智存;智存于物,实无迹也,名生于彼,理无言也。何则?至理冥壑,归乎无名。无名无始,道之体也;无可不可者,圣之慎也。苟慎理以应动,则不得不寄言,宜明所以寄,宜畅所以言。理冥则言废,忘觉则智全。若存无以求寂,希智以忘心,智不足以尽无,寂不足以 冥神。何则?故有存于所存,有无于所无。存乎存者,非其存也;希乎无者,非其无也。何则?徒知无之为无,莫知所以无;知存之为存,莫 知所以存。希无以忘无,故非无之所无,寄存以忘存,故非存之所存。莫若无其所以无;忘其 所以存。忘其所以存,则无存于所存,遗其所以无,则忘无于所无。忘无故妙存;妙存故尽无,尽无则忘玄,忘玄故无心。然后二迹无寄,无有冥尽。[8](55a14−b10)
支遁在赞颂了般若的高妙神通之后,认为《般若经》中至无空豁的思想,能使修习者发挥齐物、用智的效用,甚至达到十住妙阶、涅槃无生的境界。般若虽然至无空豁,但不是彻底的虚无;“无”无法独立呈现,必须与“有”相对而存,可以说“无”就是“非无”;“理”也无法脱离名言而独存,“理”也就是“非理”。类似地,妙阶就是非阶,无生就是非生,因为妙、无生分别要依托不妙、生来对比呈现。因此,般若智的传承无法脱离教迹、名言的辅助。般若智慧虽然保存在教迹、经文之中,本身却是无名无始的道体,没有任何形迹。先圣为了在世间传承般若智慧,不得已而借助名言经传,但如果体悟到了般若至理,就应该废弃名言;只有忘记知觉之心,般若智慧才能保全。若心中执着至无、般若智,妄求寂灭与忘心,就不能真正做到“尽无”和“冥神”。心中若执着于经文“所存”的般若智,或经文“所无”的至无之理,反而不是《般若经》原本想传承的般若大道。因为这样的人只知道 妄求至无之理,却不知经文表达至无之理的所以然;只知道般若智的存在,却不知经文保存 般若智的所以然。只有忘记保存“般若智”“至无之理”的经文本身,其心才能真正超越对般若智、至无之理的痴迷。唯有如此,才能证悟般若妙阶,把握至无之理,以至于“忘玄”“无心”,最终对传承般若的经文(“有”)与经文中保存的般若智(“无”)一视同仁,达到“无有冥尽”的至人境界。
由此,引文中的“存”应该指“般若智”的保存,“无”指“般若”的至无,“所存”“所无”都是指所传承的般若至无之理,“所以存”“所以无”则表示传承般若智的经文。如此解读,既能逻辑自洽,也可以与上下文一以贯之。其一,引文中“智存于物,实无迹也”与“理冥则言废,忘觉则智全”两句清晰地解释了般若智与名言的复杂关系—— 般若既需要依赖经文来传承,又必须在体悟到般若后及时摆脱经文的束缚,避免沉溺其中。“存/无”“所存/无”“所以存/无”的三重层次本来也是对这两句话的深入发挥。其二,该序文的主旨不是阐发般若思想,而是借论述般若与经文教迹的关系,来调和大品、小品《般若经》之间的巨大文本差异。上文的解读,也符合支遁在该序中的行文宗旨。
般若与经文的关系,只是支遁般若“即色义”的一个具体方面。引文“二迹无寄,无有冥尽”中的“二迹”原本是指“存/无(般若智)”“所以 存/无(般若经)”,“无有冥尽”句将“二迹”的含义进一步引申成了“无”“有”。“智存于物,实无迹也”和“般若之智,生乎教迹之名”的说法分别对应了般若的“无迹”与《般若经》的“有迹”。支遁也多次提到了证悟般若的至人“无迹”,如“泯迹泥洹”和“绝迹迁灵梯,有无无所骋”[9](356,460)。诗句“即色自然空,空有交印迹,冥知无照功”[9](445)更是以“空”“有”二迹相对的;“冥知无照功”则与序文中“无心”便能“无有冥尽”的观点如出一辙。这些都提示了“空”与“无”的密切关联。
那么,究竟该如何全面理解支遁般若思想中的“有”“无”“空”呢?本文认为,支遁与弟子郗超一样,都认为“空”具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指“无”,意味着万物的因缘无常、不能自有。另一方面指“有”“无”两忘,心既不执着于外物,也不迷恋于般若智慧本身;“有”则凸显了万物的事用,事物既非断灭虚空,也不是“假有”。
(一) 支遁论“空”的第一层含义:“无”与因缘无常
郗超在《奉法要》中明确提出了“四非常”的概念,依次为“无常”“苦”“空”“非身”,涵盖了万物、得失、身体的因缘无常。在论述“加种禅等四空”时[10](88c28−29),他以“四空(无)”指代了“四非常”,且将“背有著无”与“种非常禅”并提,提示了“无”与“非常”的紧密关联。由此可见,郗超论“空”的第一义便是指的“无常”。
支遁同样认为万物是无常变化的。在支遁的现存文献中,只有《文殊像赞》提到了“无常”一语,即“斯其所以动不离寂,而弥纶宇宙;倏无常境,而名冠游方者也”[9](578)。该文在赞颂文殊菩萨的同时,也承认了外境的无常变化。支遁对无常的认识,还可以从四个方面得到印证。其一,支遁直接对比了“物”的变化与“圣”的不变,强调了万物的无常,即“无穷之变,非圣在物,物变非圣,圣未始于变”[8](55b25-26)。其二,他认为世事千殊万别、得失无常,都将归于空无,因而没必要心生烦恼。他的诗文“廓矣千载事,消液归空无”[9](61),与郗超的“一切万有,终归于无,谓之为空”[10](88b22−23)相似,都具体地表达了他们对无常的理解;“无矣复何伤,万殊归一涂”[9](61),认为世事变化莫测、同归空无,故而不应烦恼其得失。其三,支遁也认同“无身”说,认为身体也是在无常变化、流转变迁的。“我身非我”[9](299)、“咄矣形非我”[9](146)等诗文都表明,他认为身体不是值得牵挂的真我。他十分重视“三界”“五道”等观念,与郗超一样认可五道轮回说③。他在《阿弥陀佛像赞》中提到,修行者诚心诵读《阿弥陀经》,就能在死后前往阿弥陀佛国,见佛悟道,即“命终灵逝,化往之彼,见佛神悟,即得道矣”[9](400),这呼应了郗超在“神无常宅,迁化靡停,谓之非身”[10](88b23)中对“无身理”的追寻。其四,支遁在《座右铭》中所言“人生一世,涓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谁施。达人怀德,知安必危”[9](299),也强调了人生、身体、安危得失的无常,与郗超的“四非常”观念一致。
支遁师徒都认为是因缘导致了万物的无常。郗超很重视因缘概念,其言“且当年所遇,必由宿缘,宿缘玄运,信同四时”[10](88a16−17),“夫欣得恶失,乐存哀亡,盖弱丧之常滞,有生所感同,然冥力潜谢,非务恋所留,对至而应,岂智用所制”[10](88c19−21),都强调了因缘对万物无常的主导地位;“出息不报,便就后世,是为无常”[10](88c5)中,同样强调了“缘报”与万物“无常”的紧密联系。支遁同样认为万物的无常是由因缘导致的,这既不同于庄子的“道生万物”论,也与郭象的“自然自化”观有别。其一,在支遁看来,般若只是不具有本体意义的实践智慧,是因缘而不是般若主导了万物的无常。“设教则智存,智存于物,实无迹也”中的“智”便为实践智慧,特指需要依靠经文传承的般若。其二,他在《弥勒赞》中提到“挺此四八姿,映蔚华林园;亹亹玄轮奏,三摅在皆缘”[9](431−432)。“皆缘”在大正藏等各版本中都作“昔缘”,指弥勒佛在华林园说法时,诸弟子证得阿罗汉果位所依靠的往世因缘④。这说明支遁对因缘论的认识已经比较深刻了。其三,支遁在《大小品对比要钞序》中指出,众人在“分”上的差异导致了他们需要接受不同的教法,即“不同之功,由之万品,神悟迟速,莫不缘分”[8](55b27−28);今世“分”的不同很可能是由前世的因缘业报决定的。其四,对比引文中的“理不能为理,则理非理矣;无不能自无,则无非无矣”与“即色义”直接史料中的“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色而空”在表达结构上的相似性,推测“色不自有”也是指“色”需要依赖他物而存在,暗示了支遁对因缘论的理论自觉。
由此可见,支遁师徒都认为“空”的第一层含义为“无”,指万物由于因缘无常、不能自有,终将归于空无,即如郗超所言:“一切万有,终归于无,谓之为空。”[10](88b22−23)
(二) 支遁论“空”的第二层含义:“无有冥尽”与“凝神”
在支遁师徒看来,“空”的第二层含义是“有”“无”两忘。郗超曾言:
或以为空则无行,行则非空。既已有所行,无乃失空乎?夫空者,忘怀之称,非府宅之谓也。无诚无矣,存无则滞封;有诚有矣,两忘则玄解。然则有无由乎方寸,而无系于外物,器象虽陈于事用,感绝则理冥。岂灭有而后无,阶损以至尽哉?由此言之,有固非滞,滞有则背宗,反流归根,任本则自畅。[10](89a19−26)
这里的“夫空者,忘怀之称”和“感绝则理冥”⑤,直接从“忘”的角度诠释了“空”。此外,郗超还依据“心系于有”“背有著无”“有无两忘”区分了凡夫、罗汉、佛的三重境界。他继而认为,三界众生都因为贪恋于外物,心中生出了无限烦恼;若心中常明因缘无常之理、安于无常,便能无往而不通;若执着于无常之理本身,也将陷入“背有著无”的困境,只能证得罗汉果位;只有“有”“无”两忘,“不忌有为,不系空观”[10](89a3),才能彻悟般若智慧,实现佛之涅槃。
支遁也认为证悟般若不仅要认识到万物的因缘与无常,还应该以“凝神”的状态超越对般若本身的执着,实现“有”“无”两忘,避免陷入郗超所谓“背有著无”的“罗汉泥洹”。支遁没有直接提到罗汉境界,却认为“存无”“希智”与证悟般若背道而驰。支遁对“存无”状态的批评,表明他也认为只是洞察到万物的因缘与无常还不足以证悟般若智慧,其人还必须以“凝神”来超越感官知觉对万物的事用差异(有)和因缘无常之理(无)的执着,摆脱“存无”的桎梏。可见,支遁在事实上也区分了凡夫“心系于有”、罗汉“背有著无”、诸佛“有无皆忘”的三重境界。
支遁十分重视“神”的概念,经常用它来刻画他心目中理想的“至人”形象。在《大小品对比要钞序》中,他一方面,他将佛教至人称为“体道尽神者”[8](55c23−24),认为至人能够“揽通群妙,凝神玄冥”[8](55b18−19)。另一方面将“尽无”和“冥神”作为证悟般若智慧的标志,认为“尽无”则能“冥神”,“冥神”便能“尽无”。在诗文作品中,他也提到了“体神在忘觉”[9](464)、“栖神不二境”[9](460)、“独与神明居”[9](61)、“损无归昔神”[9](85)等,都将至人境界与“神”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他在《阿弥陀佛像赞》中还说道“见佛神悟,即得道矣”[9](400),直接将“悟神”与证得般若智慧等同。因此,支遁认为“凝神”便能忘怀一切,从“有”“无”的双重羁绊中解脱出来,最终证悟般若智慧。
对于“有”,支遁师徒都只强调了万物的器象事用,没有认识到其“缘起假有”的本质。郗超在上列引文中便指出“器象虽陈于事用,感绝则理冥,岂灭有而后无哉”;他在“然则五度四等,未始可废,但当即其事用,而去其忮心,归于佛则无解于佛,归于戒则无功于戒”[10](89a16−18)的论说中也认为,“有”是指“五度四等”的斋戒之事。支遁对“有”的理解与郗超基本一致,这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说明。其一,支遁在《大小品对比要钞序》中讨论经文教迹与般若的关系时,曾暗示他理解的“有”是指万物的器象事用,不涉及“缘起假有”。其二,支遁与郗超一样,所有讨论因缘和无常的文本都只解释了万物的因缘无常、不能自有,没有提及“缘起假有”。其三,支遁笔下的般若与万物之间存在明显的割裂感,表明他只认识到了“缘起性空”,没有理解到“缘起假有”。他固然主张证悟般若智慧就能妥善应对外物的诱惑,但他也经常表现出一种“般若超然于万物之上”的思想倾向,忽略了从般若之中体会万物“假有”的本质,如“游无蹈虚者,不可求之于形器”[8](55c24−25)。其四,支遁“崇虚习本照,损无归昔神”[9](85)的诗句与郗超“末用与本观同尽”的观点都将“空(无)”视为“本观”,将“有”视为“末用”,表明他们认为“空(无)”具有比“有”更高的地位。
综上所述,支遁般若“即色义”认为,修行者一方面需要察知万物的空性,理解万物“色不自色”的本质——万物是由因缘而起、无常变化的,另一方面要以“凝神”的状态超越对万物和般若本身的执着,达到“无有冥尽”的至人境地。因此,支遁“即色义”直接史料中的“色即为空,色复异空”便是指:万物因为因缘与无常而不能自有,故而为“空”;但万物并非虚空无物,毕竟还有器象事用。
三、支遁的般若“即色义”与“逍遥新义”
整体来看,支遁追求的是佛玄融合的思想体系和一以贯之的理论脉络。他利用般若“即色义”创造性地诠释了“逍遥新义”,使两者具有了相同的色、心二分思维结构和统一的“至人之心”诉求,进一步印证了本文对支遁“即色义”的诠释。
支遁通过分别注解“逍”“遥”二字,巧妙地化用了般若思想来阐发其独特的“逍遥”观。面对郭象“各适性以为逍遥”的旧义,支遁批评道:“不然,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11](160)他认为,“适性逍遥”只是有待者足于所待这种当下欲望的满足,无法彻底解脱;至人的逍遥需要做到既不“失适于体外”,也不“有矜伐于心内”:

支遁对“逍”的理解为“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逍然”解决了营生路旷的鹏失适于体外的难题,即“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玄感”“不为”可以分别联系支遁《座右铭》中的“又玄其知”“抗志无为”[9](299−300)来理解;“不疾而速”的类似表述经常出现在支遁对佛境界的描述中,如“非无待者,不能游其疆;非不疾者,焉能致其速,其佛号阿弥陀”[9](388−389)或“圆应密会,以不疾为影迹;斯其所以动不 离寂,而弥纶宇宙,倏忽无常境,而名冠游方者也”[12](199a7−9)。这说明支遁对“逍”的注解也深受其般若思想的影响。
支遁在“逍遥新义”中提出的“明至人之心”,其实与“即色义”中的至人“无心”大同小异。其一,两义追求的是一以贯之的至人理想。支遁在存世文献中经常混用“至人”“圣人”“佛”等称呼,但没有提到过老庄式的圣人形象。他在《大小品对比要钞序》中交替使用了“佛”“至人”“圣人”来指证悟了般若智慧的诸佛,在《释迦文佛像赞》中也以“至人”“大圣”“佛”同时指称释迦。既然这些语词在支遁的存世文献中都是指佛,“逍遥新义”中的“至人”也不太可能是例外。其二,支遁诗文“苟简为我养,逍遥使我闲。寥亮心神莹,含虚映自然”[9](51)中的“心神莹”既然与“逍遥”出现在了同一语境中,又与“即色义”中的“凝神”十分相似,那么“逍遥新义”中的“明至人之心”与般若“即色义”中的至人“无心”也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其三,由于般若思想的影响,支遁在诠释“逍遥新义”时特别强调了“无欲”的问题,与郭象的“适性逍遥”观形成了鲜明对比。支遁经常强调佛境界的“无欲”,如“五阴迁于还府,六情虚于静林,凉五内之欲火,廓太素之浩心”[9](330),也认为诸佛想以般若智慧拯救“溺精神乎欲渊”的众生,即“是以诸佛因般若之无始,明万物之自然,众生之丧道,溺精神乎欲渊”[8](55b10−12)。“无欲”也在佛境界与逍遥的至人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因此,支遁的“逍遥新义”其实是般若“即色义”思想的自然延伸,两者具有相同的“色”“心”二分思维结构和统一的“至人之心”追求。这又呼应了前文从“色”“心”二分的角度对般若“即色义”的诠释—— 证悟般若既需要认识到万物的因缘与无常,又能够做到“有”“无”两忘。
四、支遁般若“即色义”在佛学史上的地位
僧肇同时批评过“心无”“即色”“本无”三家义,但都没有提及他们的代表人物。南朝陈时惠达在《肇论疏》中最先认为,僧肇批评的矛头是直指支遁的[3](59b3−8),本文也认同这一看法。
其一,僧肇评语第二句“夫言色者,但当色即色,岂待色色而后为色哉”属于支遁与僧肇的思想共识,暗示僧肇批评的是支遁“即色义”。该句可能出自支遁解释“色不自色,虽色而空”观点的原始文献,也可能是僧肇对支遁“即色义”的总结,不太可能是僧肇在以“当色即色”来批评支遁“色色而后为色”的观点。首先,僧肇评语第二句与支遁的般若思想基本相符,元康便认为“此犹是林法师语意也”[6](171c18),洪修平先 生也从其说。洪先生指出,支遁通过该句强调的是,真实的“有”应该靠本身的自性成为“有”,无需其他条件性支持[14](67,70)。支遁在存世文献中间接提到了“真”与“色”的关系,印证了“当色即色”的说法。他在“咄矣形非我,外物固已寂,吟咏归虚房,守真玩幽赜”[15](350b7-8)和“故千变万化莫非理外,何神动哉,以之不动故应变不穷”[8](55b23−25)等诗文中,都将无常变化的身体、事物置于“守真”的反面,暗示了“真”的不变性。“既丧大澄真,物诱则智荡”[9](247)句,将“丧真”与“物诱”对举,也表明物并非“真”。他又说“静拱虚房,悟外身之真”[15](350a22),认为“外身”才符合“真”,“色身”则为不“真”。基于此,倘若支遁直接谈论“真色”,应该认为“真色”能够超越因缘与无常,是当下自有的存在。其次,僧肇在其他语境中也表达过与评语第二句类似的观点,只是没有直接用到“当色即色”的说法。他对“真色”的理解十分直接,认为“真有”“真无”应该“常有”“常无”,不应该待缘而后“有”“无”,即“夫有若真有,有自常有,岂待缘而后有哉?譬彼真无,无自常无,岂待缘而后无也”[5](152c2−3)。僧肇的这一观点,乃至“夫……岂待……哉”的反问句式,都与他对“即色义”评语的第二句一致。最后,从反面来看,倘若僧肇是以“当色即色”来批评支遁的“色不自色”与“色色而后为色”等观点,僧肇怎么会多次使用与“色不自色”类似的“有不自有”,如“若有不自有,待缘而后有者,故知有非真有”[5](152c3−4),“且夫心之有也,以其有有,有不自有,故圣心不有有”[5](156a18−20)。
其二,僧肇评语第三句“此直语色不自色,未领色之非色也”,认为“即色义”只理解了“色不自色”,而没有领悟“色之非色”。本文也认同这一观点。上文提到,僧肇曾两次用到“有不自有”,或者在解释“缘起性空”,不涉及“缘起假有”,或者在解释“圣心非有非无”中的“非有”,没涉及“非无”。这提示僧肇认为支遁的“色不自色”与“有不自有”一样,都只是在强调“缘起性空”,没有领悟到完整的“色之非色”思想。在僧肇看来,“色之非色”意味着“空色不二”,既包括“色”即为“非色”,也包括“非色”即为“色”,即“是以经云‘非色’者,诚以非色于色,不非色于非色。若非色于非色,太虚则非色,非色何所明?若以非色于色,即非色不异色。非色不异色,色即为非色”[5](156c9−12)。
其三,僧肇批评的不是“关内即色义”,吉藏和安澄的观点很难成立。首先,吉藏提出“即色义”有两家,认为僧肇批评的是主张“色无自性,故言即色是空,不言即色是本性空也”的“关内即色义”,支遁“即色义”则“不坏假名而说实相”,与“道安本无”“周氏假名空”“肇公不真空”理论一致但表达各异[16](29a18−25,c8−10)。然而僧肇对“即色义”观点的概括“即色者,明色不自色,故虽色而非色也”,既没有提到吉藏所谓“关内即色义”的“自性”一语,也与支遁“即色义”直接史料中的“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过于相似。况且支遁认为般若只是实践智慧而不是万物的本体,与道安“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16](29a5−6)的本体论观点相差甚远。吉藏的观点可以说是问题重重。其次,安澄认为两家“即色义”都强调了“色不自色”,但“关内即色义”只知“色非自色,因缘而成,不知色本是空,犹存假有也”[4](94a1−19),支遁“即色义”则与僧肇的“不真空”一致,应该“不偏言无自性边”。但安澄没有为其观点提供任何证据支撑。本文认为,吉藏与安澄都只是在为支遁这一佛教界名流讳饰罢了。
既然支遁的般若“即色义”只关注到了“缘起性空”,忽略了“缘起假有”,那么他自然就会被僧肇批评了。支遁认为万物是“有”“无”的统一,“有”指其事用,“无”指其因缘无常、不能自有。僧肇的“非有非无”论则主张,“非有”指万物是待缘而有、不能自有的,即“若有不自有,待缘而后有者,故知有非真有”[5](152c3−4);“非无”指万物已经因缘而起了,并非断灭虚空的“真无”,即“万物若无,则不应起,起则非无”[5](152c6−7)。因此,支遁论“无”与僧肇的“非有”说基本一致,论“有”却只提到了万物的形名事用,没有领悟僧肇的“非无”说。
虽然支遁的“即色义”被僧肇批评,但他对“知”的理解很接近僧肇的理论水平。支遁用到的“知”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感官知觉,如“投一灭官知”[9](172);二是与般若相关的“忘知”,如玄其知、灵知、恬智、无智于智、般若迁知等。他借否定“官知”来肯定“忘知”的观点,与僧肇的“般若非有知非无知”之论十分相似。僧肇认为“名相靡因,非有知也;妙存即真,非无知也”[5](156b14−15),“非有知”批判了凡夫“有虑之知”对俗谛的执着,“非无知”则肯定了般若智对真谛的圆照。支遁主张凡夫因为“官知”而贪恋万物,对应了僧肇否定的“有知”;至人的“忘知”则不仅要抛弃感官知觉,也必须放下对般若本身的执迷,达到“虚灵响应,感通无方”[8](55b19−20)的境地。这与僧肇的“非无知”之论展现的“境智合一”状态颇为契合。
支遁与僧肇也都承认“无心/圣心”的地位和它“无知而无不知”的特点。支遁将“心”区分为“有心”(思虑之心)和“无心”(至人之心),“有心”借“官知”思虑而执着万物为实有,继而产生物欲;“无心”却能洞见万物的空性,做到“无有冥尽”。僧肇主张“圣心”是“非有非无”的,“非有”指“圣心”没有凡夫的思虑之心,“非无”指“圣心”不是绝对虚无的,即“是以圣心不有,不可谓之无;圣心不无,不可谓之有”[5](160c14−16)。在僧肇看来,“圣心”虽然没有思虑之知,却能遍知真谛实相,即“是以圣人以无知之般若,照彼无相之真谛”[5](153c11−12)。可见两人在拒斥思虑之心的同时,都肯定了能圆照真谛的“无心/圣心”。
五、结语
综上所述,支遁般若“即色义”对“知”与“心”的理解十分透彻,在诠释“色”“空”关系时却只注意到了“缘起性空”的一面,忽视了“缘起假有”的另一面,与僧肇的般若中观之学仍然存在一些差距。但支遁的般若“即色义”仍然是六家七宗中最接近僧肇般若中观之学的一派,这奠定了支遁在早期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17](154−156)。僧肇对支遁“即色义”的评述则应该理解为:支遁认为色由因缘而成、不能自有,虽然有色的事用,却是空无;真色应该当下自有,不须依赖因缘而产生。支遁“即色义”只提到了“色不自色”这“缘起性空”的一面,没有领悟到“色之非色”的完整含义。
① 原文中“不自色”三字缺失,依据支遁的《妙观章》和《即色游玄论》等文献补全。
② 郗超(公元336—378年)是支遁(约313—366年)的忠实弟子。两人的时代和年龄相近,言论思想也十分契合。郗超曾向亲友提到“林法师神理所通,玄拔独悟,实数百年来,绍明大法,令真理不绝,一人而已”。他对“色”“空”关系的看法,有助于理解支遁的般若“即色义”。参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第161页。
③ 支遁存世文献中“三界”的用例有:《座右铭》的“茫茫三界”、《善宿菩萨赞》的“三界皆勤求”、《土山会集诗·其一》的“三界赞清休”、《释迦文佛像赞》序的“三界殄悴”;“五道”用例为:《咏八日诗·其二》的“扬声五道泯”。参见张富春:《支遁集校注》,巴蜀书社,2014年,第299,464,137,356,215页。郗超的“五道”说即“三界之内,凡有五道,一曰天,二曰人,三曰畜生,四曰饿鬼,五曰地狱。全五戒则人相备,具十善则生天堂。”参见僧祐:《弘明集》卷十三, CBETA 2023, T52, no. 2102, p86c14−17。支遁对“三界”和“五道”的看法与郗超类似,两人都认同五道轮回说。
④ 该赞叙述了弥勒华林园的三次说法,鸠摩罗什译《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载其事:“尔时弥勒佛于华林园……初会说法,九十六亿人得阿罗汉;第二大会说法,九十四亿人得阿罗汉;第三大会说法,九十二亿人得阿罗汉。弥勒佛既转法轮,度天人已,将诸弟子,入城乞食。”参见鸠摩罗什译:《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CBETA 2023, T14, no. 454, p. 425a29−b5。“昔缘”是使弥勒诸弟子能够证得阿罗汉果位的往世因缘。支遁当时应该可以看到竺法护译本《佛说弥勒下生经》中的同一故事,即“或复有众生见迦叶身已……九十六亿人皆得阿罗汉……所以然者?悉由受我训之所致也,亦由四事因缘:惠施、仁爱、利人、等利”。参见竺法护译:《佛说弥勒下生经》,CBETA 2023, T14, no. 453, p. 422b28−c3)。
⑤ “然则有无由乎方寸,而无系于外物,器象虽陈于事用,感绝则理冥”中的“有”固然是指事用,“无”应该是指因缘无常,因为“存无则滞封”中的“存无”与“种非常禅,皆谛背有著无,则得罗汉泥洹”中的“种非常禅”“著无”相呼应,都是指执着于因缘无常之理。参见僧祐:《弘明集》卷十三, CBETA 2023, T52, no. 2102, p.89a2−3。“感绝则理冥”则是指“忘”,不执着于“有”“无”的任何一面,“不忌有为,不系空观”(同上,p. 89a3),最终证悟般若智慧。
[1] 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2] 余嘉锡. 世说新语笺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3] 惠达. 肇论疏: 卷一[DB/CD]. CBETA, X54, no. 866. 2023.
[4] 安澄. 中论疏记: 卷三[DB/CD]. CBETA, T65, no. 2255. 2023.
[5] 僧肇. 肇论[DB/CD]. CBETA, T45, no. 1858. 2023.
[6] 元康. 肇论疏: 卷一[DB/CD]. CBETA, T45, no. 1859. 2023.
[7] 文才. 肇论新疏: 卷一[DB/CD]. CBETA, T45, no. 1860. 2023.
[8] 僧祐. 出三藏记集: 卷八[DB/CD]. CBETA, T55, no. 2145. 2023.
[9] 张富春. 支遁集校注[M]. 成都: 巴蜀书社, 2014.
[10] 僧祐. 弘明集: 卷十三[DB/CD]. CBETA, T52, no. 2102. 2023.
[11] 释慧皎. 高僧传[M]. 汤用彤,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12] 道宣. 广弘明集: 卷十五[DB/CD]. CBETA, T52, no. 2103. 2023.
[13] 王颂. 支遁“逍遥新义”新诠—— 兼论格义、即色与本无义[J]. 中国哲学史, 2019(4): 82−91.
[14] 洪修平. 肇论[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8.
[15] 道宣. 广弘明集: 卷三十[DB/CD]. CBETA, T52, no. 2103. 2023.
[16] 吉藏. 中观论疏: 卷二[DB/CD]. CBETA, T42, no. 1824. 2023.
[17] 蒲日材. 谈《世说新语》中的僧人形象[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4): 154−159.
A new exploration into the connotations of Zhi Dun's Jise Theory of Prajna and its related issues
WANG Wei
(Shool of Humaniti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The Jise Theory of Prajna proposed by Zhi Dun, a renowned Buddhist scholar at Wei-Jin period had great influential valu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Due to the lack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it is hard to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s of Jise Theory.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surviving literature of Zhi Dun, it is found that the Jise Theory has three layers of implications. Everything is impermanent due to its unexpected fate and resulting from sunyata and karma(Se is karma); anyhow, Se is existing, unalienated from sunyata(repeated Se differs from sunyata); the enlightenment of Prajna requires neither being infatuated with the temptation of everything, nor being infatuated with Prajna itself, but breaking the two obsessions of "things" and "mind", and being indifferent to everything via concentrating. The dichotomy between things and mind in Jise Theory not only constituted the basis for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new meanings of "the peripatetic", but also deeply influenced his disciple Xi Chao's idea of sunyata. Zhi Dun's Jise Theory is very close to the thoughts of Seng Zhao on the Prajna in that when it says that Se is sunyata, it means that fate is sunyata. But "repeated Se being different from sunyata" differs from "the fate pretending to be" , just that the function of Se is emphasized.
Zhi Dun; Jise theory of the Prajna; Karma; concentrating; the mind of the Saint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23.05.004
B235.9
A
1672-3104(2023)05−0033−09
2022−12−28;
2023−01−09
中南大学博士后科研启动项目(140050002)
汪伟,男,安徽安庆人,中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伦理学,联系邮箱:ww20101992@163.com
[编辑: 胡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