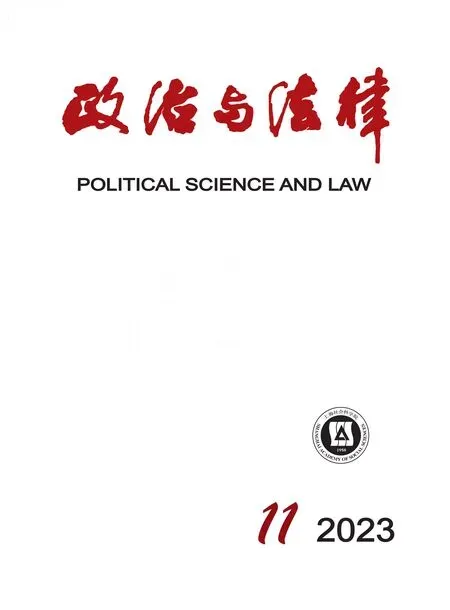洗钱罪的成立应当以上游犯罪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为前提*
张 磊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875)
一、问题的提出:自洗钱入罪及其带来的挑战
随着科技、网络和经济的发展,洗钱的行为方式日益变化。洗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升级为非传统性安全中的突出问题,具有自己的独立属性,〔1〕参见王新:《国际社会反洗钱法律规制概览与启示》,载《人民检察》2022 年第19 期。成为维护整体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参见王新:《总体国家安全观下我国反洗钱的刑事法律规制》,载《法学家》2021 年第3 期。在此背景下,为了应对洗钱行为方式的变化,并响应《关于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监管体制机制的意见》的战略性要求,〔3〕参见陈山:《期待可能性视域中 “自洗钱”入刑的教义学建构》,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2 年第5 期。我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修正案(十一)》)对于洗钱罪再次修改,将自洗钱入罪,给理论界和实务界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对于洗钱罪和上游犯罪之间界限和罪数形态的认定问题,特别是在上游犯罪行为和下游洗钱行为是同一行为的情况下,或者上游犯罪行为人通过洗钱的行为方式来获取犯罪所得的情况下,如何厘定洗钱罪和上游犯罪之间的关系就值得思考。例如,毒品犯罪分子贩卖毒品的时候,下游犯罪人为其提供多个资金账户帮助其接收赃款;又如,受贿人让行贿人直接将贿赂款汇到自己的境外账户,或者让行贿人直接将行贿的财物转化为现金交给他指定的人;等等。这类行为的认定,实质上是在上游犯罪实施过程中是否有可能同时成立洗钱罪的问题,或者说洗钱罪成立的前提是什么的问题,是认定洗钱罪和上游犯罪罪数形态的关键。本文以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近年来颁布的关于洗钱罪的两批典型案例为切入点,对于洗钱罪的成立前提以及其与上游犯罪的罪数形态认定问题进行论述。
二、对最高检典型案例中关于洗钱罪成立立场的梳理
界定洗钱罪与上游犯罪之间关系的前提是明确洗钱罪与上游犯罪的不同性质。洗钱罪在性质上来说是上游犯罪的事后行为,〔4〕参见王新:《自洗钱入罪后的司法适用问题》,载《政治与法律》2021 年第11 期。目的是为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披上合法外衣,实现犯罪所得的安全循环使用,这种行为不仅放大了上游犯罪的危害后果,而且对国家的金融稳定产生了额外伤害,〔5〕参见王爱立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691 页,第695-696 页。侵犯了新的法益,不能被上游犯罪所评价,具备独立成罪的条件,〔6〕参见贝金欣、王拓:《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批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解读》,载《人民检察》2022 年第23 期。是对上游犯罪在获取犯罪所得后,对该犯罪所得又进一步积极实施“漂白”的二次行为。〔7〕参见王新:《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洗钱罪的立法发展和辐射影响》,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 年第2 期。由此为界定洗钱罪和上游犯罪之间的界限奠定了基础。
(一)最高检典型案例中关于洗钱罪与上游犯罪关系的表述
在自洗钱入罪前后,最高检先后发布了两批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8〕第一批案例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银行于2021 年3 月19 日联合发布,包括6 个典型案例;第二批案例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22 年11 月3 日发布,包括5 个典型案例,其中首次包括了自洗钱案例。在这两批案例中,都有一个案例涉及洗钱罪与上游犯罪之间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分别是(第一批典型案例)雷某、李某洗钱案和(第二批典型案例)马某益受贿、洗钱案。
1.雷某、李某洗钱案中的立场:洗钱罪的成立不以持续性上游犯罪的结束为前提
案例一,雷某、李某洗钱案:2016 年年底,朱某出资成立瑞某公司,聘用雷某、李某为该公司员工。2017 年2 月至2018 年1 月,雷某、李某除从事瑞某公司自身业务外,应朱某要求,明知朱某实际控制的腾某公司以外汇理财业务为名进行非法集资,仍向朱某提供多张本人银行卡,接收朱某实际控制的多个账户转入的非法集资款。之后,雷某、李某配合腾某公司财务人员罗某等人,通过银行大额取现、大额转账、同柜存取等方式将上述非法集资款转移给朱某。其中,大额取现2404 万余元,交给朱某及其保镖;大额转账940 万余元,转入朱某实际控制的多个账户及房地产公司账户用于买房;银行柜台先取后存6299 万余元,存入朱某本人账户及其实际控制的多个账户。2019 年11 月19 日,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做出判决,认定雷某、李某犯洗钱罪。2020 年6 月11 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
该案“典型意义”〔9〕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公布的两批典型案例中,都包括“基本案情”“诉讼过程”“典型意义”等方面的内容。部分强调:“在非法集资等犯罪持续期间帮助转移犯罪所得及收益的行为,可以构成洗钱罪。非法集资等犯罪存在较长期的持续状态,在犯罪持续期间帮助犯罪分子转移犯罪所得及收益,符合刑法第191 条规定的,应当认定为洗钱罪。上游犯罪是否结束,不影响洗钱罪的构成,洗钱行为在上游犯罪实施终了前着手实施的,可以认定洗钱罪。”〔10〕该案的基本案情和典型意义的内容均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国人民银行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https://www.spp.gov.cn/spp/xwfbh/wsfbt/202103/t20210319_513155.shtml#1,2023 年8 月16 日访问。据此,最高检和中国人民银行在该案中的观点是:上游犯罪持续期间帮助转移犯罪所得及收益的行为,可以构成洗钱罪;上游犯罪是否结束,不影响洗钱罪的成立。
2.马某益受贿、洗钱案中的立场:洗钱罪的成立以上游犯罪的完成为前提
案例二,马某益受贿、洗钱案:2002 年至2019 年,马某益之兄马某军(已判决)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2004 年上半年,马某军使用收受徐某贿赂的人民币100 万元投资的理财产品到期后,马某益使用本人的银行账户接收马某军给予的上述本金及收益共计109 万元,后马某益将此款用于经营活动。2015 年8 月,马某军收受赵某贿赂的8 万美元现金后,马某益直接接收了马某军交予的8 万元美元现金,后分16 次将上述现金存入本人银行账户并用于投资理财产品。马某益除为马某军洗钱外,还与马某军共同受贿,马某军授意行贿人向马某益的账户汇款。……两级检察院根据犯罪事实会商研判后认为:(1)马某益按照马某军的授意,直接收受贿赂,属于帮助接收受贿款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共犯;(2)马某益在马某军收受贿赂款即受贿完成后,使用本人银行账户接收马某军转入的受贿所得并用于投资经营的行为,构成洗钱罪。2020 年12 月22 日,黑龙江省大箐山县人民法院判处马某益构成受贿罪和洗钱罪,数罪并罚。
需要注意的是,在该案中马某益使用本人账户帮助马某军接收贿赂的行为被认定为受贿罪的共同犯罪,而对于马某军收受贿赂完成后,再使用本人账户接收马某军的受贿所得及投资经营行为,被认定为洗钱罪。该案“典型意义”中也强调:“洗钱罪是在上游犯罪完成、取得或控制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后实施的新的犯罪活动,与上游犯罪分别具有独立的构成。在上游犯罪实行过程中提供资金账户、协助转账汇款等帮助上游犯罪实现的行为,是上游犯罪的组成部分,应当认定为上游犯罪的共犯,不能认定洗钱罪。上游犯罪完成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才成立洗钱罪。”〔11〕该案的基本案情和典型意义的内容均参见《检察机关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211/t20221103_591486.shtml#2,2023 年8 月16 日访问。据此,最高检在该案中的观点是:上游犯罪完成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才成立洗钱罪;洗钱罪的成立以上游犯罪完成为前提。
根据上述两个案例及“典型意义”的文字表述,可以看出两者存在一定出入:案例一认为在持续性上游犯罪持续期间的洗钱行为,应当认定为洗钱罪,而案例二则认为在上游犯罪实行过程中的洗钱行为,应当认定为上游犯罪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洗钱罪。两者实际上是针对不同类型上游犯罪得出的不同结论,如果不明确说明和区分,容易造成误解。
(二)两案都坚持洗钱罪的成立以上游犯罪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为前提
虽然两个案例的文字表述存在出入,但通过深入分析两个案例,可以发现这两个案件具有不同特点:案例一上游犯罪的非法集资行为具有持续性,案例二上游犯罪的受贿行为则不具有持续性,两者上游犯罪的完成和上游犯罪行为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的时间并不完全一致,两者本质上都是以上游犯罪行为人是否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作为洗钱罪的成立前提的。
1.对案例一中洗钱罪的分析
在案例一中,雷某二人所涉嫌的洗钱行为实际上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人应朱某要求向朱某提供多张本人银行卡,接收朱某实际控制的多个账户转入的非法集资款;第二阶段是:二人配合腾某公司财务人员罗某等人,通过银行大额取现、大额转账、同柜存取等方式将非法集资款转移给朱某。在第一阶段中,二人向朱某提供的多张银行卡是用来接收从朱某已经实际控制账户转来的非法集资款。这些非法集资款的来源是朱某实际控制的账户,而不是被害人的账户。所以,这些非法集资款在转到他们银行卡之前就已经被朱某实际控制,在性质上已经是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二人使用自己的银行卡接收该犯罪所得,是对朱某已经实际控制的非法集资款进行转移、隐瞒,当然构成洗钱罪。在第二个阶段中,雷某二人将本人银行卡已经接收到的非法集资款通过取现、转账、同柜存取等方式转移给朱某,自然也构成洗钱罪。所以,雷某二人这两个阶段的行为都发生在朱某已经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之后,都构成洗钱罪。
对于该案来说,“典型意义”强调“在上游犯罪持续期间帮助犯罪分子转移犯罪所得及收益,应当认定为洗钱罪。上游犯罪是否结束不影响洗钱罪的构成”是正确的。因为,朱某实施的上游犯罪即非法集资行为持续时间较长,在此过程中,被害人的集资款被陆续转到朱某账户(被朱某实际控制),再转到雷某二人提供的银行卡上,然后再被二人取现、转账给朱某。在雷某对于朱某转来的犯罪所得进行洗钱的同时,朱某还在持续进行非法集资。所以雷某二人的洗钱行为,是和朱某的非法集资行为(上游犯罪的行为)在一定时间里同时进行的。朱某不断地获得非法集资,雷某二人则不断地对于朱某陆续收到并控制的犯罪所得进行清洗。从这个角度来说,上游犯罪持续过程中当然可以成立洗钱罪,上游犯罪是否结束并不影响洗钱罪的构成。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连续或者持续犯罪的过程中,以及在集团犯罪中,完全有可能一边是上游犯罪一边实施洗钱犯罪。所以,没有必要将上游犯罪的既遂作为洗钱罪的前提条件。”〔12〕张明楷:《自洗钱入罪后的争议问题》,载《比较法研究》2022 年第5 期。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该案“典型意义”中首先强调“非法集资等犯罪存在较长期的持续状态,在犯罪持续期间帮助犯罪分子转移犯罪所得及收益,符合刑法第191 条规定的,应当认定为洗钱罪”,但是在没有明确指出持续性上游犯罪和一次性上游犯罪不同情形的前提下,直接得出“上游犯罪是否结束,不影响洗钱罪的构成”的结论似乎过于绝对。本案的上述结论只适用于具有持续性、连续性的上游犯罪,而不适用于一次性的上游犯罪。
此外,对于持续性、连续性的上游犯罪来说,在上游犯罪持续或者连续过程中可以成立洗钱罪,并不意味着该洗钱行为就是上游犯罪的一部分,也不意味着洗钱行为和上游犯罪的行为构成想象竞合。对此有观点认为:“雷某、李某明知腾某公司以外汇理财业务为名进行非法集资,仍向朱某提供多张本人银行卡,接收朱某实际控制的多个账户转入的非法集资款等行为,其实也构成集资诈骗罪的共犯。所以,雷某、李某的上述行为既是上游犯罪行为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洗钱行为的一部分。既然如此,雷某、李某的行为就并非仅成立洗钱罪,而是洗钱罪与上游犯罪的想象竞合,应当从一重罪处罚。”〔13〕张明楷:《自洗钱入罪后的争议问题》,载《比较法研究》2022 年第5 期。这种观点似乎也没有区别一次性上游犯罪和持续性、连续性上游犯罪的不同。如前所述,雷某二人的行为虽然和朱某持续的非法集资行为具有同时性,但是其行为的性质是对朱某之前已经控制的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进行掩饰隐瞒的行为,不同于朱某同时持续实施的非法集资的行为,或者从被害人处获取、接收非法集资款的行为。进而言之,即使在同一时间点上,朱某非法集资行为和雷某二人的洗钱行为同时进行,朱某非法集资的款项和雷某二人所清洗的款项也并不是同一笔款项,非法集资的款项要等到被朱某实际控制以后才能被雷某二人所清洗。所以,就不能说“雷某二人的上述行为既是上游犯罪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洗钱犯罪的一部分”。综上,雷某二人的行为并不是上游犯罪的一部分,更不涉及和上游犯罪行为想象竞合的问题,而是独立的洗钱罪。
2.对案例二中洗钱罪的分析
在案例二中,马某益构成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和洗钱罪两个犯罪:(1)受贿罪共同犯罪是指马某益按照马某军的授意,直接收受请托人现金、银行转账汇款、银行卡及房产,这是帮助上游犯罪人接收受贿款的行为;(2)洗钱罪是指马某益在马某军收受贿赂款(受贿完成后),使用其本人银行账户接收马某军转入的受贿所得并用于投资经营的行为。该案“典型意义”中强调“洗钱罪是在上游犯罪完成、取得或控制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后实施的新的犯罪活动,……上游犯罪完成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才成立洗钱罪”。〔14〕参见《检察机关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211/t20221103_591486.shtml#2,2023 年8 月16 日访问。最高检检察官在对此案例解读中也明确指出“上游犯罪实施过程中的接收、接受资金行为,属于上游犯罪的完成行为,是上游犯罪既遂的必要条件,不宜重复认定为洗钱行为,帮助接收、接受犯罪所得的人员可以成立上游犯罪的共犯。”〔15〕参见贝金欣、王拓:《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批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解读》,载《人民检察》2022 年第23 期。
笔者赞同该观点,同时也认为该表述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完善。(1)和雷某、李某洗钱案一样,在没有明确一次性上游犯罪和持续性、连续性上游犯罪不同情形的前提下,笼统地得出“上游犯罪完成后才能成立洗钱罪”的结论过于绝对。如前所述,对于一次性的上游犯罪来说,上游犯罪完成才能成立洗钱罪(犯罪完成以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为条件)。但是对于持续性、连续性的上游犯罪来说,上游犯罪即使没有完成,只要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实际控制了部分犯罪所得,就可构成洗钱罪。(2)不宜将上游犯罪的完成和上游犯罪取得、控制犯罪所得两者并列,同时列为洗钱罪成立的前提条件。事实上,上游犯罪的完成和上游犯罪行为人取得、控制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并不是一回事。即使是对于一次性的上游犯罪来说,上游犯罪中的接受、接收资金的行为也不一定是上游犯罪的完成行为或者上游犯罪既遂的必要条件。例如在受贿罪的情况下,根据通说收受贿赂是受贿罪完成也就是既遂的标准。〔16〕参见《刑法学》编写组:《刑法学(下册各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版,第272 页。但是洗钱罪的七类上游犯罪的完成(或既遂)标准并不一致,部分犯罪的完成和实际控制犯罪所得没有任何关系,如毒品犯罪以毒品犯罪行为实施完毕为完成,贩卖毒品罪以毒品实际转移给买方为完成,运输毒品罪以使毒品离开原处或者转移了存放地为完成,制造毒品罪以实际制造出毒品为完成,〔17〕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2021 年版,第1514-1515 页。都和上游犯罪行为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没有直接关系。对于这些犯罪,一方面在犯罪完成时可能并未获得犯罪所得,另一方面也可能在犯罪尚未完成时,已经获得了部分犯罪所得。又如,在走私犯罪中,根据司法解释,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既遂的标准是在海关现场被查获,以虚假申报方式走私的申报行为完成,以及作为走私对象的货物在境内销售或者申请核销完毕。〔18〕2014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3 条。其他走私犯罪则以所走私的物品到达本国港口或者领土的时候为既遂。〔19〕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2021 年版,第961-962 页。但是,作为洗钱罪对象的走私货物变现后所产生的盈利,在走私犯罪完成时并不一定能够获得,〔20〕虽然关于走私犯罪中走私的货物是否是犯罪所得,理论界和实务界还存在较大争议,但是销售走私货物变现后的盈利是走私的犯罪所得是没有争议的,而在走私既遂的情况下,这部分盈利尚未实际获得。该犯罪所得可能在走私货物销售出去之后才能获得,两者并不具有同一性。〔21〕参见刘晓光、金华捷:《洗钱罪的犯罪认定问题研究——以上游犯罪和洗钱罪构成要件的联系为切入》,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22年第1 期。所以,对于洗钱罪来说,只要上游犯罪行为人实际控制了犯罪所得,下游犯罪人就有可能开始实施洗钱行为,至于上游犯罪是否完成或既遂并不影响洗钱行为的进行。如果以上游犯罪完成或者既遂作为洗钱罪成立的前提,必然因为上游犯罪既遂标准不同、实际控制犯罪所得的时间不同而造成上游犯罪和洗钱罪关系的混乱。由此,前述观点所认为的“上游犯罪实施过程中的接收、接受资金行为,属于上游犯罪的完成行为,是上游犯罪既遂的必要条件,不宜重复认定为洗钱行为”,如果是针对“马某益受贿、洗钱案”的话是很中肯的,因为对于受贿罪来说,收到贿赂款就是犯罪完成和既遂的标志。但是对于毒品犯罪、走私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来说,则并不一定妥当,因为对于这几类犯罪来说,在上游犯罪实施过程中的接收、接受资金的行为,并不一定是上游犯罪的完成行为或者犯罪既遂的必要条件。
3.洗钱罪的成立应当以上游犯罪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为前提
经过上文的分析,笔者认为洗钱罪的成立前提应当以上游犯罪行为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为前提。
第一,这是从最高检典型案例得出的结论。前述就最高检典型案例的分析表明,两个案例实质上都是以上游犯罪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为洗钱罪成立的前提,准确揭示出了洗钱罪和上游犯罪之间的界限。对于案例一,虽然雷某两人的洗钱行为发生在朱某非法集资持续过程中,但是发生在朱某实际控制(部分)非法集资款之后,所以该案例中“典型意义”的实际观点也可以表述为:“在上游犯罪持续期间,上游犯罪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后帮助犯罪分子转移犯罪所得及收益,应当认定为洗钱罪。虽然上游犯罪是否结束不影响洗钱罪的构成,但是洗钱罪的成立应当发生在上游犯罪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之后。”对于案例二,虽然马某益构成洗钱罪的原因表面上来看是在马某军收受贿赂款(即受贿完成或者既遂)后所实施的洗钱行为,但是由于受贿罪的完成以受贿人实际控制贿赂财物为标准,马某益实质上是在马某军实际控制受贿款后才构成洗钱罪。由此,该案的“典型意义”的实际观点也可以表述为:“洗钱罪是在上游犯罪实际控制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后实施的新的犯罪活动,……上游犯罪行为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以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才成立洗钱罪。”这样表述可以统一两个案例关于洗钱罪与上游犯罪的区分标准,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的适用依据。
第二,如果不以上游犯罪行为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为前提,有可能导致最终判决不能全面评价上游犯罪并对行为人正确适用刑罚。洗钱手段千变万化、犯罪形态多种多样,如果洗钱罪不坚持以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为前提,而将上游犯罪实施过程中具有洗钱性质的非法获取犯罪所得的行为评价为洗钱罪,进而认定为洗钱罪和上游犯罪的想象竞合,那么将有大量的上游犯罪都存在想象竞合的问题。如前述的受贿人让行贿人直接向自己境外账户汇款的行为,受贿人直接让行贿人用行贿款购买理财产品、房屋等送给自己的行为,或者将贿赂的财物转化为现金送给自己的行为,都符合洗钱罪的行为方式,都可能构成洗钱罪与上游犯罪的竞合。如后文所述,对于这些行为如果按照想象竞合犯处理的话,最终判决有可能难以对上游犯罪进行全面评价。
以“犯罪所得的产生”作为洗钱罪成立的前提将由于犯罪所得产生的具体时间难以判断而缺乏可操作性。有观点提出应当以“犯罪所得产生”作为上游犯罪和洗钱罪两者的时间节点,认为上游犯罪所得的产生既是洗钱罪的成立条件,也是洗钱罪介入上游犯罪的时间起点。理由包括:将犯罪所得的产生作为时间节点是洗钱犯罪的应有之义,也有利于统一实践争议;下游行为介入时间点只能在下游犯罪对象产生之后,否则就不存在需要下游犯罪帮助的对象,下游犯罪也无从谈起。上游犯罪所得产生之后即有清洗的必要,此时的掩饰隐瞒行为即属于洗钱行为。同时该观点还指出,犯罪所得的产生并不完全等于上游犯罪行为人取得财物。犯罪所得虽说最终归于上游犯罪行为人,但其毕竟产生于上游犯罪行为,产生时间与得到时间有时并不一致。〔22〕参见孙静松:《依据“通谋”区分洗钱犯罪与上游犯罪共犯》,载《检察日报》2021 年9 月24 日,第3 版。笔者赞同该观点所认为的下游行为介入只能在下游犯罪对象产生之后,上游犯罪所得产生之后即有清洗的必要的说法。但是该观点的问题在于并没有提出如何认定“犯罪所得产生”的时间点,特别是在明确提出“犯罪所得的产生并不完全等于上游犯罪行为人取得财物”后,并没有指出两者之间到底如何区分。笔者认为,以犯罪所得产生作为洗钱罪的前提并不妥当。一方面,洗钱罪的对象是上游犯罪所得,但是犯罪所得的产生和行为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并不是一个概念,两者的时间点并不一定相同,洗钱罪的成立显然必须以上游犯罪行为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为前提,如果犯罪所得已经产生,但是行为人并没有实际控制,同样不能进行洗钱。另一方面,由于洗钱罪七类上游犯罪的不同特点,如何界定犯罪所得产生的时间点也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制造毒品罪来说,通过一定生产程序制造出来毒品,当然可以认定为犯罪所得的产生时间;但是对于受贿罪来说,到底是行贿人准备好贿赂款是犯罪所得的产生,还是受贿人接收到贿赂款是犯罪所得的产生?事实上,持“犯罪所得产生”观点的学者所举的部分例子当中,也是将犯罪所得的产生时间等同于上游犯罪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的时间,如认为毒品犯罪中贩毒人员取得毒资,走私行为人取得犯罪所得都是犯罪所得产生时间。〔23〕参见孙静松:《依据“通谋”区分洗钱犯罪与上游犯罪共犯》,载《检察日报》2021 年9 月24 日,第3 版。所以笔者认为,以犯罪所得产生时间作为洗钱罪成立的前提并不妥当,而应当以上游犯罪行为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为准。
三、洗钱罪与上游犯罪不构成想象竞合关系
自洗钱入罪之后,行为人在实施上游犯罪过程中实施洗钱行为,到底是构成洗钱罪与上游犯罪的想象竞合,还是只构成上游犯罪或者构成两罪数罪并罚,是洗钱罪认定中的一个难点。笔者认为,在明确洗钱罪的成立必须以上游犯罪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为前提的情况下,洗钱罪就难以与上游犯罪构成想象竞合关系。
(一)洗钱罪事实上难以与上游犯罪形成想象竞合关系
关于洗钱罪和上游犯罪能否构成想象竞合,第一种观点认为,想象竞合“前提必须只有‘一个行为’,即行为是单数。反观自洗钱入罪后,洗钱罪与上游犯罪是不同的犯罪行为类型,两者存在复数行为的关系,不符合想象竞合犯‘一行为侵害数法益’的前提条件,故难以成立想象竞合犯”。〔24〕王新:《自洗钱入罪后的司法适用问题》,载《政治与法律》2021 年第11 期。第二种观点认为,洗钱罪和上游犯罪可以构成想象竞合。如有观点所认为,受贿人要求行贿人将行贿款直接汇往境外账户构成受贿罪与洗钱罪的想象竞合,受贿人直接将公款汇往境外构成贪污罪与洗钱罪的想象竞合,在非法集资等犯罪持续期间帮助转移犯罪所得及收益的行为,可能构成洗钱罪与非法集资等犯罪的共犯的想象竞合。〔25〕参见张明楷:《自洗钱入罪后的争议问题》,载《比较法研究》2022 年第5 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吸收资金行为本身也是其客观方面要件,使用他人账户吸收资金的,同样会出现构成要件之间的重合。对于这类情形应根据竞合的原则,择一重罪论处。〔26〕参见刘晓光、金华捷:《洗钱罪的犯罪认定问题研究——以上游犯罪和洗钱罪构成要件的联系为切入》,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22年第1 期。也有学者认为以下两种情况可以成立想象竞合。其一,自洗钱行为属于上游犯罪实行行为组成部分。如行为人开设了多个银行账户,接受吸毒人员汇款,收受毒资的行为与自洗钱行为之间是想象竞合犯。其二,自洗钱行为属于上游犯罪共犯行为。如行为人与毒贩约定在其收获毒资后为其投入基金营利,行为人与毒贩事前有通谋就属于贩卖毒品罪的共犯,同时符合自洗钱的构成要件,属于想象竞合犯。〔27〕参见陈山:《期待可能性视域中 “自洗钱”入刑的教义学建构》,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2 年第5 期。
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事实上,在将上游犯罪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作为洗钱罪成立前提的情况下,洗钱罪和上游犯罪之间就具有了明确的区分界限,难以形成两罪之间的想象竞合。因为行为人在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之前的行为,即使具有洗钱的性质或者和洗钱罪的行为方式类似,也只是上游犯罪的组成部分,只构成上游犯罪,不构成洗钱罪。行为人在控制犯罪所得之后的洗钱行为,就是上游犯罪之外一个独立的洗钱罪,应当与上游犯罪数罪并罚。上述第二种观点所列举的五种情况实际上都不构成想象竞合。
第一,在行贿人跨境汇款的情形中,当行贿人按照受贿人要求将贿赂款汇出并到达受贿人的账户时,受贿人才实际控制了该款项(在此之前没有洗钱的问题),具备了洗钱罪成立的前提条件。行贿人的跨境汇款行为是受贿人收受汇款的行为,是受贿罪的组成部分,只成立受贿罪,不成立洗钱罪。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该行为“实质上属于行贿罪的必不可缺的客观构成要素,已经被处于上游实行行为的行贿罪评价完毕,就不应再将该行为作为构成洗钱罪的事实根据”。〔28〕王新:《洗钱罪的基础问题辨析——兼与张明楷教授商榷》,载《法学评论》2023 年第3 期。
第二,在行为人将公款汇往境外自己账户的情形中,将公款转出国内账户并到达其境外账户时,实现对于公款的实际控制,向境外汇款的行为是贪污行为的组成部分。只有该款项到达境外账户之后,才可能成立洗钱罪。在前述这两种跨境汇款的情形下,犯罪所得在到达境外账户以后,行为人如果再实施洗钱行为,将构成新的洗钱罪,应与上游犯罪并罚。
第三,在非法集资的情形中,如前所述洗钱罪发生在非法集资犯罪持续过程中,并不意味着就构成洗钱罪和上游犯罪的竞合。一笔资金一旦通过非法集资被上游犯罪行为人实际控制,就意味着针对该笔资金的非法集资行为完成,该笔资金由非法集资的对象转变为了洗钱罪的对象。此时,不论上游犯罪是否在持续,上游犯罪行为人是否还持续获得新的犯罪所得,已经被实际控制的犯罪所得就只能成为洗钱罪的对象,而不能再同时是正在进行的非法集资行为的对象。即使上游犯罪持续的同时也实施了洗钱行为,那也是上游犯罪人持续获得新的犯罪所得和针对前阶段犯罪所得的洗钱的同时进行,两者针对的实质上并不是同一批犯罪所得,不可能存在洗钱罪和上游犯罪的竞合。
第四,在贩卖毒品者开设多个银行账户接收吸毒者汇款的情形中,该汇款只有到达银行账户后,上游犯罪人才实现了对于该财产的实际控制,此时只构成贩卖毒品罪。此外,关于上游犯罪人自己提供资金账户的行为是否构成洗钱罪,也值得思考。事实上,作为洗钱罪的第一个行为方式,“提供资金账户”是上游犯罪所得进入金融机构循环系统的重要入口,是最为常见的洗钱犯罪手法。《修正案(十一)》虽然通过删除洗钱罪客观行为中第二、第三、第四项的三个“协助”以及主观方面中“明知”的表述,从而突破了洗钱罪只能由他犯构成的限制性框架,但是并没有对第一项方式即“提供资金账户”做出任何修改,那么根据立法规定,该项行为方式就只适用于“他洗钱”,而不能适用“自洗钱”情形。〔29〕参见王新:《洗钱罪的司法认定难点》,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2 年第6 期。并且,最高立法机关也明确指出:“提供资金账户是指为犯罪行为人提供金融机构账户等的行为。”〔30〕王爱立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691 页。既然是“为犯罪行为人”提供账户,那么该行为的主体自然就不包括上游犯罪人。有学者就认为:“作为上游犯罪实行行为组成部分的‘提供资金账户’……等行为,系犯罪实行行为本身,不应再评价为洗钱罪。”〔31〕何荣功:《洗钱罪司法适用的观察、探讨与反思》,载《法学评论》2023 年第3 期。所以,在贩卖毒品者自己提供资金账户的情形下,也不能认定其构成洗钱罪。
第五,对于与上游犯罪人事前通谋约定事后洗钱的行为,不论是否按照上游犯罪的共同犯罪处理,都不构成想象竞合。对此,我国刑法对于类似的行为都规定按照上游犯罪共同犯罪认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310 条第2 款针对窝藏罪、包庇罪,第156 条针对走私罪,第349 条第3 款针对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都规定了与上游犯罪人事前通谋的,按照上游犯罪的共同犯罪论处。〔32〕类似的还有《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 条针对盗窃罪、抢劫罪、诈骗罪、抢夺罪等的规定。虽然有观点认为,对于洗钱者与上游犯罪行为人(毒贩)事前虽有沟通,但仅限单纯的事前允诺,没有实行事中行为,只对犯罪所得有认知,缺乏参与共同犯罪的意志因素,与上游犯罪行为人主观故意不同,与事前通谋有本质不同。〔33〕参见孙静松:《依据“通谋”区分洗钱犯罪与上游犯罪共犯》,载《检察日报》2021 年9 月24 日,第3 版。那么这种行为也只是洗钱行为,不与上游犯罪构成想象竞合关系。
(二)洗钱罪不宜与上游犯罪构成想象竞合关系
通常情况下,在上下游犯罪量刑问题上,下游犯罪入罪标准以及法定刑升格条件的设定,会考虑对上游犯罪的依附性,量刑一般较上游犯罪轻。〔34〕参见陆建红、杨华、曹东方 :《〈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15 年第 17 期。但是因为我国当前相关司法解释没有规定洗钱罪的具体追诉标准和“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3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 条对于《刑法》第312 条第1 款规定的 “情节严重” 进行解释,该解释第二项规定: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10 次以上,或者 3 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5 万元以上的。根据洗钱罪和上游犯罪的法定刑的设定,在两罪之间很容易出现“量刑倒挂”现象。〔36〕参见楼丽、方悦:《贪贿“自洗钱”犯罪司法困境及其破解》,载《中国检察官》2022 年第15 期。例如,上游犯罪可能处于一般情节的量刑档次,而下游犯罪的犯罪数额与次数却可能达到“情节严重” 的量刑档次。〔37〕参见庄绪龙:《上下游犯罪 “量刑倒挂”困境与“法益恢复” 方案——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视角展开》,载《法学家》2022 年第1 期。如果按照想象竞合对于行为人按照下游犯罪定罪量刑,造成部分行为具有洗钱性质的上游犯罪最终按照洗钱罪定罪量刑,将出现以下不合理的现象。
第一,有可能使最终的定罪量刑难以实现对于上游犯罪的全面评价。假如受贿人受贿18 万,按照受贿罪一般应当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而如果受贿人在收受该贿赂的同时对该贿赂进行洗钱的行为达到了情节严重的标准(如多次洗钱等),按照洗钱罪的法定刑就可能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根据想象竞合犯从一重处断的原则,最终很可能对其按照洗钱罪定罪量刑,而不是按照受贿罪定罪量刑。但是整体来看,上游犯罪是法益侵害的直接制造者,洗钱罪本质上是赃物犯罪,并不能完全评价上游犯罪所侵害的法益,在法益侵害性质上无法与上游犯罪相提并论。〔38〕参见楼丽、方悦:《贪贿“自洗钱”犯罪司法困境及其破解》,载《中国检察官》2022 年第15 期。所以,如果对行为人最终按照洗钱罪量刑,虽然根据现有的定罪量刑规则没有问题,但无法全面评价上游犯罪的行为性质。由于当前越来越多的上游犯罪中取得犯罪所得的行为具有洗钱的性质,那么不少上游犯罪将因为构成与洗钱罪的想象竞合而最终按照洗钱罪定罪量刑,这种状况并不能全面评价和体现上游犯罪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事实上基于同一笔犯罪事实的前提,“下游犯罪量刑不高于上游犯罪”原则已被普遍承认,并且为了应对实践中上下游犯罪 “量刑倒挂” 的不合理现象,近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也着力探索进行改变。〔39〕参见庄绪龙:《上下游犯罪 “量刑倒挂”困境与“法益恢复” 方案——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视角展开》,载《法学家》2022 年第1 期。如果出现上游犯罪最终按照下游犯罪定罪量刑,短时间内将难以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接受。
第二,有可能最终导致对于行为人的轻判。虽然在分析行为性质的时候,可以单独评价既具有获取上游犯罪所得性质又具有洗钱性质的行为,但是在实践中上游犯罪人获得犯罪所得之后(资金到达其账户后),往往还会继续再实施洗钱行为。例如,受贿人的境外账户收到汇款之后,往往后续还要进行相应的转账、投资以及其他掩饰、隐瞒该资金性质的行为。这种后续的行为是完全独立于上游犯罪的一个新的洗钱罪。如果对于上游犯罪按照想象竞合从一重处断,在行为人后续又实施了新的洗钱罪后,不论是按照同种数罪还是按照连续犯,就都不可能进行数罪并罚,而只能按照洗钱罪一罪从重处罚。如果将跨境汇款的行为认定为上游犯罪收受贿赂的行为,对于该行为则认定为受贿罪,可以与行为人在境外所实施的后续洗钱行为进行数罪并罚。所以,如果认为上述案件中的跨境汇款行为构成洗钱罪,和上游犯罪构成想象竞合,在洗钱行为被认定为“情节严重”的情况下,很可能最终导致对于行为人的轻判。
四、上游犯罪行为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的具体认定——以受贿罪为例
明确洗钱罪的成立需要以上游犯罪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为前提之后,对于上游犯罪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的具体认定就成为正确认定洗钱罪的关键。上游犯罪人对于犯罪所得的实际控制,是指上游犯罪人对于作为犯罪所得的财物在事实上的控制。这种控制需要达到行为人对于该财物自由使用的程度,既可以由行为人直接控制(如资金进入行为人自己的账户),也可能通过其他人进行控制(如犯罪所得进入行为人可以控制的朋友的账户中)。只要行为人实际控制了该财物,即使对财物没有实际占有、使用或者得到收益,也应认定已经实际控制。〔40〕参见彭巍:《论受贿款由行贿人保管的定性》,载《中国检察官》2014 年第6 期。通常情况下,上游犯罪人对于犯罪所得的实际控制比较容易认定。如毒贩实际收到购买者所支付的现金或者将钱打到其指定的账户,受贿人的个人账户或者其指定的账户收到行贿人汇来的行贿款,都属于上游犯罪人对于犯罪所得的实际控制。对于受贿财物是房屋、汽车等贵重物品的,是否办理权属变更并不影响对于受贿的认定,〔41〕参见马克昌主编:《百罪通论(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187 页。应当以受贿人实际收到(或者开始使用)该房屋、汽车时认定其实际控制该财物的时间。
但是实践中行贿受贿的方式各式各样,特别是经常出现的受贿人并不实际收受贿赂财物,而是让行贿人代为保管的情况,对此是否应当认定为受贿人实际控制该财物,值得思考。笔者认为,在行贿人应受贿人的要求代为保管贿赂财物的情况下,判断受贿人“实际控制”的关键是行贿人按照受贿人的要求对于该财物进行了处置,并且使得该贿赂款脱离了行贿人的控制而进入了受贿人的控制,才能认定为受贿人实际控制该财物。具体来说,对于受贿人实际控制贿赂财物的时间点的判断,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受贿人收到行贿人的财物后又交给行贿人代为保管的。对此有观点认为受贿人索取或者收受财物后将财物交给行贿方保管的,构成受贿既遂。〔42〕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2021 年版,第1608 页。笔者赞同这种观点,这种情况下应当以受贿人首次收到财物作为其实际控制该财物的时间,其又将财物交给行贿人保管,是实际控制该财物的一个表现。如果受贿人要求行贿人在保管中实施洗钱行为,就又构成了洗钱罪,和上游犯罪数罪并罚。
第二,受贿人同意行贿人行贿后,直接让行贿人将财物汇到受贿人指定的账户,或者交给受贿人指定的第三人保管,或者按照受贿人要求进行某种投资(投资受益人为受贿人或者其指定的第三人)。在该财物脱离行贿人的控制后到达该账户,或者交给第三人,或者投资到位后,即认为受贿人对该财物开始了实际控制。
第三,受贿人同意行贿人行贿后,直接让行贿人代为保管该财物,行贿人对于该财物进行了单独保管。对此有观点认为“国家工作人员同意接收行贿人给予的金钱,并要求行贿人保管金钱,行贿人按可以识别的方式管理的,宜认定为受贿既遂。”〔43〕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2021 年版,第1608 页。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同时认为此时根据行贿人单独保管的方式分为两种情况。(1)如果受贿人可以随时取用该财物,获得该财物没有客观障碍,一般应认定受贿人实际控制了该财物,并以其能够自由取得、使用该财物的时间为实际控制时间点。例如,行贿人以受贿人的名义存入银行,并且告知了受贿人银行密码,受贿人可以不通过行贿人的帮助而随时取用。此时,以受贿人得知行贿人告知其银行存款密码、可以随时取款的时间作为其实际控制该财物的时间点。(2)如果受贿人取得财物需要行贿人的帮助,则要具体判断受贿人是否对该财物实际控制。例如,行贿人将财物以自己名义单独存入了银行账户,就要考察受贿人取得财物的难易程度、行贿人的心态及财产状况等因素,来判断受贿人能否对该财物进行实际控制,以及实际控制的时间点。〔44〕参见李丁涛:《准确认定约定受贿的犯罪形态》,载《中国纪检监察报》2021 年10 月20 日,第6 版。
第四,受贿人同意行贿人行贿后,只是笼统要求行贿人代为保管,但行贿人并没有对财物进行单独保管,依然保持该财物的原状。如贿赂款仍在行贿人自己的账户中没有动,和行贿人的其他财产混同。但直至案发,受贿人并没有支取或者再要求行贿人处置该财物。此时受贿人一般不能根据自己的意志随意支配该财物,不宜认为受贿人对该财物进行了实际控制。〔45〕参见吴金波:《查办贿赂款由行贿人代管的案件需注意什么》,载 《中国纪检监察报》2022 年3 月23 日,第7 版。如果受贿人要求行贿人代为保管,但是没有证据证明行贿人准备了行贿款,受贿人也没有使用或者要求使用该款项,也不能认定受贿人对该款项进行了实际控制。〔46〕参见刘一霖、方弈霏:《由行贿人代管贿款系受贿未遂还是既遂——从四川省南充市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秘书长蒲国案说起》,载《中国纪检监察报》2022 年4 月13 日,第5 版。如果受贿人在行贿人代为保管后,受贿人要求交给自己部分贿赂款,其他部分继续由行贿人代管直至案发,那么对于行贿人已经收到的部分则认定为实际控制,对于继续由行贿人代管部分不能认定为实际控制。〔47〕参见沈岩:《约定受贿后尚未兑现应怎样定性》,载《中国监察》2012 年第5 期。
第五,受贿人与行贿人笼统约定行贿受贿,但没有任何实质行贿行为的,双方也没有就如何行贿进行商讨,那么两人之间的约定最多是犯罪的预备或者是一种犯意流露,不会使受贿人产生收受财物的现实危险。〔48〕参见李丁涛:《准确认定约定受贿的犯罪形态》,载《中国纪检监察报》2021 年10 月20 日,第6 版。由于在实践中,对于约定收受普通财物的犯意流露和犯罪预备不处罚已成为我国的司法裁判规则,〔49〕参见魏东:《约定受贿定性处理的法理研讨》,载《河南社会科学》2017 年第2 期。对此一般不认定为受贿罪,也不能认定为受贿人对于财物具有控制力。
第六,行为人碍于情面和压力,无法直接拒绝行贿人的行贿,而以委托行贿人保管的方式拒绝该财物,后续其也没有要求行贿人处置或者使用过该财物,由于其主观上没有受贿主观故意,〔50〕彭巍:《论受贿款由行贿人保管的定性》,载《中国检察官》2014 年第6 期。不构成受贿罪,更不能认定其对于该财物进行过实际控制。
五、结 语
洗钱罪性质上是对上游犯罪所得进行漂白的行为,具有和上游犯罪完全不同的性质。洗钱罪的构成以上游犯罪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为前提,在上游犯罪人没有实际控制犯罪所得的情况下,洗钱罪也就没有行为的对象,不可能构成洗钱罪。有学者所指出:“如果尚没有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也就无从谈起‘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而从事洗钱的问题。”〔51〕何荣功:《洗钱罪司法适用的观察、探讨与反思》,载《法学评论》2023 年第3 期。“洗钱罪的犯罪对象,就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等上游犯罪人已经实际控制或者支配的所得和收益。”〔52〕黎宏:《“自洗钱”行为认定的难点问题分析》,载《法学评论》2023 年第3 期。在明确了洗钱罪的成立前提是上游犯罪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之后,对于上游犯罪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之前所实施的类似洗钱的行为,或者使用洗钱的方式接收犯罪所得的行为,应当作为上游犯罪的组成部分认定为上游犯罪。如果行为人实际控制该犯罪所得之后,继续实施洗钱行为,就应当按照上游犯罪和洗钱罪数罪并罚。如果上游犯罪人实际控制该犯罪所得之后没有继续实施洗钱行为或者案发,就按照上游犯罪一罪进行定罪。同时由于其上游犯罪的部分行为具有洗钱性质,可以将其作为上游犯罪具有严重情节的认定因素或者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53〕这种严重情节认定因素如贪污罪、受贿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其他较重情节”“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实现罪刑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