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译语人考
索南才旦
(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青海西宁 810001)
7-9 世纪是青藏高原历史演进的一个全新时代,雅砻悉补野统一西藏高原并逐渐与周边民族或政权建立政治、军事、文化等多层面的联系。8 世纪下半叶,吐蕃从泥婆罗、箇湿密、乌仗那等地迎请了多名佛教徒,开始了历经近一百年的兴佛运动,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印度班智达与吐蕃译师合作翻译佛经,所译佛典的数量达近千种,这一活动同阿拉伯帝国时期的“百年翻译运动”相比毫无逊色。因译师对藏译佛典形成史的无量功德,西藏传统史家在他们的教法史中总会留一篇幅来记录各时期翻译家的名录,如今名垂史册的吐蕃译师或翻译家至少有七十多位。但在吐蕃时期还有一类对政治、军事、经济等对外交流方面极为重要的、汉文正史中一般被称为“舍人”或“译语人”,如今被称为口译者的翻译人,这一职业人主要负责不同语种之间的传导。笔译者(translator)或所谓的译师因翻译文本并留有跋文而被后人所知,而口译者(interpreter)若没有特殊历史事件或历史编纂者的特意书写,只能淹没在独属笔译者舞台的翻译史滚滚长河中。不管是西藏历史上还是其它地方的历史编纂传统中,口译者的名字和语言传导的活动等记载寥寥无几,这对我们了解不同语言背景的人们在古代何以交往和交流的日常生活史造成了障碍,也对人类文明史上的对外政治交往、军事行动、贸易往来等历史事件的语言沟通方面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关注口译者对不同族群之间交往、交流、交融史的贡献,更需要研究这类职业人的翻译能力的入门、训练、实践等培养机制。
一、关于职业名称的讨论

二、坌、麴的随从译语人




三、箇湿密译语人阿难陀
在吐蕃译经史上,除了异域和本土培养的诸译师以外,最为重要的是那些精通佛法而不懂吐蕃语的南亚次大陆众多班智达,因他们的到来和授经活动,吐蕃王庭不仅需要文本翻译者,而更多地去培养能够当场翻译班智达所传经文的同声传译人才。我们对吐蕃时期授经译语人的历史建构困难重重。西藏传统史籍也多处记载天竺班智达授佛法于诸赞普的多种案例,因译师在西藏佛经形成史的圣神地位和闻法录的传承,众多史家不太留意口译情形或期间传导的译语人;口译虽在吐蕃讲经说法活动中虽最为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但我们也不能在缺乏原始史料的情况下去想象和构建吐蕃授经译语人的历史情景。所以,授经译语人一直是西藏佛教史研究领域内诸多学者不敢涉及的一个空白。
自敦煌藏文文献Or.8210/S.9498A+Or.8210/S.13683B号《拔协残卷》发现以来,[17]我们对西藏传世史籍诸《拔协》版本的源流和传播有了新的认识,[18]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残卷中恰好记载了与授经译语人有关的部分内容,这对吐蕃译语人的历史活动研究方面有了比传世史籍更早的版本,虽然其大部分内容已见于教法史、抄写年代也不属于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所以,笔者将敦煌文献Or.8210/S.9498A+Or.8210/S.13683B号《拔协残卷》和拉萨哲蚌寺罗汉殿藏外ra.175号《韦协》缀合,以此探讨吐蕃早期兴佛时期译语人的族群来源、身份变迁以及对传播佛教所起到的作用等问题。以下译文的正文是敦煌本,[19]括号中的内容译自哲蚌寺罗汉殿本,①《韦协》一书收录于百慈古籍研究室编《藏族史记集成》第36册中,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2011:13-15.由于篇幅过长,这里就省略了原文。

上述《韦协》缀合本的内容为《吐蕃兴佛记》所载“由善知识之协助又聆听佛法”一句的续补,[20]此处“善知识”为阿阇梨菩提萨锤,③同样的称呼见于《声明要领二卷》序言中。见西藏博物馆编.旁塘目录·声明要领二卷[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70.敦煌藏文文献Pel.tib.149 号《圣普贤行愿王经序言》中也记作天竺之堪布菩提萨锤,[21]又名寂护。阿阇梨菩提萨锤于761 年不久后到达吐蕃之际,④《吐蕃兴佛记》记载墀松德赞(742-802)二十岁时因身体不适,遂迎请善知识聆听佛法;《底吾史记》也曾记载赞普二十岁、牛年(761)迎菩提萨锤于吐蕃。底吾·璆赛.底吾史记[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122.或许像提婆达多兄弟、阿难陀这样在各地集市能够充当贸易译语人的古印度人更多,因为西藏史家声称上述三位箇湿密人本身就是吐蕃集市的译语人,[22]只是因阿难陀曾学过各种典籍而有了能够传导佛法教义的特殊技能而已。缀合本中可看到阿难陀至少两次充当过译语人,第一次是阿阇梨菩提萨锤与论章·颊扎勒色、森果·拉隆色、韦·桑希之间,时间达两个月之久;第二次是阿阇梨菩提萨锤与赞普之间,时间长达半年。
拉萨哲蚌寺罗汉殿藏外ra.175号《韦协》记载,当吐蕃君臣为创建桑耶寺举行奠基仪式之际,挖出了两合白米和白色青稞,而不见有其它不祥之物,于是堪布欢喜并把手放在赞普头顶道:“硕德硕德!八喇八喇!善成!”[23]有意思的是,这段内容在另一部《拔协》版本中则记作,“挖出了未曾混合的两合白米和两合白色青稞,于是阿阇梨欢喜道:‘八喇八喇!硕德硕德!’,赞普未懂其意,向译语人问:‘阿阇梨何意?’,译语人传导:‘意为善成!’”此处译语人也应该是箇湿密人阿难陀。像这种在赞普和阿阇梨之间的译语人传导情形理应为吐蕃早期兴佛之史实,可惜我们在藏文传世史籍中很难找到此类记载,以致佛教传入吐蕃时期的译语人传导活动一直湮灭于历史大潮之中。
四、姑臧大军镇的回鹘语译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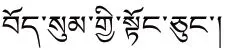
关于吐蕃(töpüt)派遣使者到突厥的记载见于《阙特勤碑》东面第4行,[26]与此同样的叙述又见于《毗加可汗碑》东面第5行,[27]两者所记载的诸吊唁1903-1951)于1936 年首次抄者前来均与突厥土门(?-552)及室点密(?-576)可汗的逝世有关,这样叙述内容之时间最晚也公元6世纪70年代左右。仅从吐蕃方面考虑,上述两通碑对吊唁使团的记载言过其实,不足为信。笔者以为,《阙特勤碑》东面第4行和《毗加可汗碑》东面第5 行内容为《阙特勤碑》北面11-13 行的简写,毗加可汗(684-734)只是把诸国使者参加阙特勤(685-731)葬礼的事实移至他们祖先可汗的葬礼上而已。《阙特勤碑》北面第12行记载“从吐蕃可汗处来了论(töpüt qaγanta bölün kälti.)”,[28]年代为731年1月至9 月之间的某个时间段。从弃隶蹜赞(704-754)《请修好表》(718)所述“中间有突厥使到外甥处”、③弃隶蹜赞.请修好表[M]//陈家琎.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259.《吐蕃编年史》720年条“默啜使者前来致礼”等互动来看,[29]731年吐蕃派往后突厥汗国参加阙特勤葬礼的使团一事也完全符合当时两边政治层面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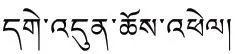

表1 回鹘—吐蕃语词汇对照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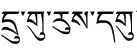

五、汉语译语
《旧唐书·吐蕃传》记载,641 年唐蕃联姻后吐蕃遣其酋豪子弟入国子监学习汉文典籍,又请唐朝文人主持吐蕃表疏。[33]说明在赞普墀松赞(617-649)时期吐蕃已经有能够藏汉互译的译语人,尽管不能确定其族群、人名、官职等身份。进入国子监学习的酋豪子弟中,后来成为唐与吐蕃之间能够藏汉互译的有仲琮、钦陵等大臣,他们虽不是王庭的职业译语人,吐蕃赞普与李唐使者之间需传导时,先前同仲琮等入国子监的子弟中应当有充当传导的职业译语人。《吐蕃兵律》之“将军以下、千户长及税务官以上之琼与库龙规定”条目已证明,8 世纪初,吐蕃麴·莽布支腊松和坌达延赞松两位大臣有王庭配备的诸多译语人,说明此时吐蕃除了王庭以外,连年在外征战的领军人也配有译语人,可知当时在吐蕃精通藏汉双语的译语人相当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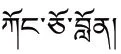


结语
自吐蕃统一青藏高原以来,逐渐与周边民族或政权在政治、军事以及文化上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互动,这一举动的促进者无疑与当时精通双方语言文字的译语人息息相关,与周边民族之间交往、交流的历史序幕也是由译语人拉开的,可知其在吐蕃对外交流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译语人作为吐蕃王庭和边缘军政单位的职业官员,尤其是姑臧大军政的官职序列表足以证明,其名望与地位同其它高级官职一样被所属军政机构格外重视,也应译师一样被世人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