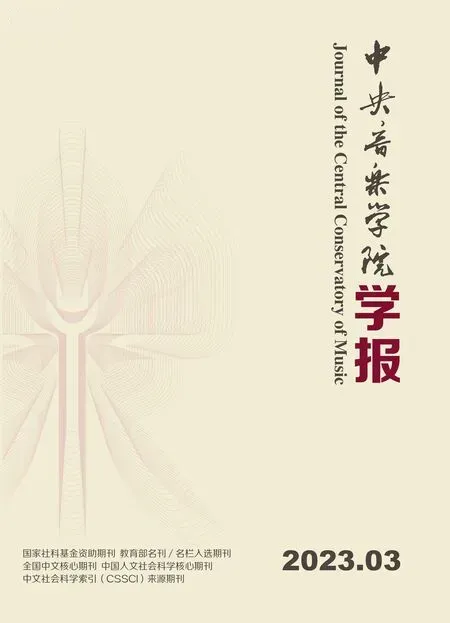音乐书籍史是一种怎样的历史?
——以16世纪欧洲音乐书籍史研究为例
刘丹霓
引言:从书籍史到音乐书籍史
“书籍史”(book history)(1)书籍史在英文中有多种表述方式:“book history”“history of books”或“history of the book”。德文中情况类似,有“Geschichte des Buchwesens”和“Buchgeschichte”。法文和意大利文分别为“histoire du livre”和“storia del libro”。中文语境下通常有“书籍史”“书史”“图书史”三种表述。是当今国际史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其学术渊源至少可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19世纪在英国和北美产生的文献目录学(bibliography),尤其是发展于20世纪初的分析性文献目录学(analytic bibliography)着重研究“书籍的生产制作过程、文字内容的呈现、它们从手稿到出版书籍的历程,以及它们的纸张和装订”(2)〔英〕詹姆斯·雷文:《什么是书籍史》,孙微言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51页。,为后来的书籍史奠定了重要基础。通常认为,现代书籍史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尤以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吕西安·费夫贺和亨利-让·马尔坦《印刷书的诞生》(3)Lucien Febvre et Henri-Jean Martin,L’ Apparition du livre,Paris:Albin Michel,1958,中译本为〔法〕费夫贺、马尔坦:《印刷书的诞生》,李志鸿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为标志。书籍史冲破了此前书籍研究囿于版本学和资料史的局限,步入年鉴学派社会经济史的论域,不仅观察书籍的排版、印刷、装帧等技术层面,而且探讨书籍的生产、传播、消费与社会的关系,将书籍史与社会史、计量史、心态史等法国史学界的优势学科相结合。到了20世纪80、90年代,随着“新文化史”的强势崛起,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等新一代欧美学者引领了书籍史的新走向——他们在此前偏重社会经济考察的基础上,强调“文化”的维度,解读书籍的文化意涵,思考其与“人”的关系,最终形成了当代书籍史的主流形态:“以书籍为中心,研究书籍创作、生产、流通、接受和流传等书籍生命周期中的各个环节及其参与者,探讨书籍生产和传播形式的演变历史和规律,及其与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是统合关于书籍的各种研究——编辑史、印刷史、出版史、发行史、藏书史、阅读史——的全面的历史”(4)〔英〕戴维·芬克尔斯坦、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书史导论》,何朝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译者前言”,第6页。。长期以来,书籍史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印刷书籍(以及报纸、杂志等其他印刷品),达恩顿甚至将书籍史定义为“经由印刷而进行的信息交流的社会文化史”(5)Robert Darnton,“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Daedalus,Summer,Vol.Ⅲ,No.3,1982,pp.65-83.,但如今书籍史的范围不断扩大,“手写文化”时代的各类抄本、数字时代新的知识传播载体均被纳入研究视野。
在西方音乐史学领域,虽然20世纪后期对手抄本和音乐印刷技术的研究为音乐书籍史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明确从社会文化角度切入、立足书籍史核心范畴的音乐书籍史研究,直到20世纪的最后几年才开始出现。目前的研究成果多数集中于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16世纪,这一时期既是音乐印刷繁荣发展的第一个百年(6)音乐印刷并非始于16世纪初,最早大约出现在15世纪中叶。但音乐印刷作为一种产业的蓬勃发展是在进入16世纪之后。其标志性事件是奥塔维亚诺·彼特鲁奇(Ottaviano Petrucci)在1501年出版了历史上第一部采用活版印刷技术制成的乐谱书籍,也是复调音乐的第一部印刷品。参见唐纳德·克鲁梅尔:《音乐出版发展史》,戴明瑜编译,《交响》,1998年,第2期。,也是西方音乐文化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过渡转型阶段,与音乐有关的实践活动、社会建制、思想观念均呈现出旧事物依然强势、新现象日渐成型的复杂面貌和动态张力,因此,对这一时期音乐书籍的研究不仅符合一般书籍史强调印刷文化革命性意义的总体趋势,似乎也最能全面展现书籍史典型的史学议题以及音乐书籍史的特殊性。
在音乐书籍史发展初期(20、21世纪之交),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音乐印刷,特别是意大利、法国等印刷重镇所在地,如伊恩·芬伦的《16世纪早期意大利的音乐、印刷与文化》(7)Iain Fenlon,Music,Print and Culture in Early Sixteenth-Century Italy,London:British Library,1995.、蒂姆·卡特的《文艺复兴晚期佛罗伦萨的音乐、赞助与印刷》(8)Tim Carter,Music,Patronage and Printing in Late Renaissance Florence,Aldershot and Burlington:Ashgate,2000.、简·伯恩斯坦的《16世纪威尼斯的印刷文化与音乐》(9)Jane Bernstein,Print Culture and Music in Sixteenth-Century Venice,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凯特·凡·奥登主编的《音乐与诸种印刷文化》(10)Kate van Orden ed.,Music and the Cultures of Print,New York:Garland,2000.等。2010年之后的成果显示出更为丰富的维度,更加注重书籍史众多要素的结构关联:不仅关注书籍的出版传播这些中间环节,而且关注“作者”与“阅读”;不仅研究书籍的生产技术,而且注重挖掘书籍物质形态的文化内涵;不仅关注社会上层和精英群体,而且更关心普通读者的日常消费;不仅立足印刷文化,而且始终强调印刷与手抄、书面与口头、文本与表演的交叠和勾联。本文将以16世纪欧洲音乐书籍史研究为主要依据,从中管窥和论析音乐书籍史的核心主题和方法论特色,凸显音乐书籍史不同于一般书籍史的独特性。
一、音乐书籍史的核心主题
罗伯特·达恩顿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何为书籍史?》(11)Robert Darnton,“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Daedalus,Summer,Vol.Ⅲ,No.3,1982,pp.65-83.一文中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理论模型“交流线路”(communications circuit),意在为书籍史过于繁杂的学科视角和研究方案提供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基础模式,该模式主要是一个由六大环节串联而成的循环线路:作者→出版商→印刷商(包括排字工、印刷工、仓库保管员)→运输商(包括代理人、走私者、转口仓库保管员、运输车夫等)→销售商(包括批发商、零售商、街头小贩、装订商等)→读者(包括购书者、借阅者、书友会、图书馆)→作者。在这个闭环之外,与印刷商有关联的还有原料供应商(供应纸张、油墨、铸字及劳动力);与读者关联的还有装订商。各个环节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经济、社会、政治、法律、思想的影响和控制。可以看出,所有纸质书籍的生命轨迹以及对书籍任何维度的历史研究大体逃不出这个模式,音乐书籍亦不例外。对所有环节的讨论将超出本文所能涵盖的范围,故以下将提炼出对音乐书籍史最为关键、也是目前研究成果最集中的四个主题展开论述。
(一)物质形态的基础地位
20世纪末西方史学中出现了所谓的“物质转向”(material turn),形成了专门的“物质文化史”。不同于经济史仅关心物品的商品价值及其反映出的市场结构、消费水平等可量化分析的方面,物质文化史研究的是物与人的关系,将物品视为洞悉人的行为和观念的重要资料,(12)Maureen C.Miller,“Material Culture and Catholic History”,The Catholic History Review,Vol.Ⅰ,No.1,2015,pp.1-17.看重的是物品作为文化符号所承载和映射的意义。而书籍作为文化的一种典型的物质载体,其实体形态可以说是支撑一切书籍史研究的基础,也是贯穿各类书籍史课题的“主导动机”。上述达恩顿的“交流线路”中所有环节都离不开对书籍物质维度的考察。书籍史家认为,文本的物质形态具有传递、构建意义的功能。一方面,字体、版式、页面布局、段落切分等方面的种种惯例有助于理解作者或出版商所表达的意图及其以何种方式控制书籍的接受状况(13)〔法〕罗杰·夏蒂埃:《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吴泓缈、张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1页。;另一方面,“任何一种对文字的理解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读者所接触到的实体形式……物质形式一定会影响到读者的期待,召来新读者或导致新读法”(14)同注①,第92—93页。。可以说,书籍史首先是一种物质文化史。
讨论音乐书籍史,首先要厘清的问题是:何为音乐“书籍”?不同于面对文字文本的普通书籍史,音乐书籍史虽然也涉及文字著述类图书的研究(15)例如Cristle Collins Judd,Reading Music Theory:Hearing with the Ey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但占据最大比重的中心研究对象是乐谱书籍,包括一部乐谱印刷品(或手抄本)上的一切内容:乐谱、声乐作品的唱词以及连带的各种“副文本”(paratext,下文将详细解释)。就16世纪而言,虽然有大量乐谱以“书”冠名,如Primolibrodimadrgali(《牧歌第一卷》)、Premierlivredechansons(《尚松第一卷》)、Liberprimussexmissascontinens(《六首弥撒曲第一卷》)(16)此三处原文中均包含“书”之意,为更符合中文表达在译名中使用了“卷”这一量词。,“书”(libro/livre/liber)这个词在标题中频频出现,但当时复调乐谱的常态往往不完全具备书籍的常规属性。首先,根据书籍的现代定义,“装订”是成书的必要条件,而16世纪的音乐“书”在更多情况下是以散页形式出厂、运输、销售,从达恩顿的交流线路中也可看到,印刷与装订是两个分立的环节。少部分出版商或销售商会将乐谱装订起来,这种乐谱的价格要远高于散页形式;也有不少购书者和收藏者选择购买散页乐谱后自行装订,目前留存下来的乐谱书籍中有相当数量属于这样的“藏书者装订本”(称为collector’s volume、binder’s volume或tract volume)(17)Kate van Orden,Materialities:Books,Readers,and the Chanson in Sixteenth-Century Europ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17.。
其次,16世纪的复调作品通常以两种形式出版:合唱谱(choirbook)和分谱(partbook)。合唱谱包含一首作品的所有声部,在每一组对开的两页上分别列出各个声部,主要用于弥撒曲、经文歌、圣母颂歌等宗教体裁,通常是为整个合唱队演唱使用,往往采用较大的对开本形式。分谱仅包含作品的某一个或两个声部,可用于多种宗教、世俗体裁,由于规模小(常用四开本或八开本)、节省纸张、成本低,在16世纪商业性音乐印刷中更为普遍。但即便是装订起来的分谱,在书籍属性上也存在问题:一部分谱形式的音乐“书”其实是由多本尺寸很小、极其单薄的小册子(18)以当时常见的四声部尚松为例,一首尚松的一册分谱通常是只有16页的横版四开本或八开本。组成,其物质形态完全无法与当时其他类型的书籍相提并论。合唱谱和分谱的共性是都将各个声部分别列出,而非所有声部纵向排列的总谱形式,这显然是为了便于表演使用。总谱在当时非常罕见,且主要用于“默读”(即研究作曲技法)而非表演。与此同时,在音乐进入印刷时代之后,传统的手抄本依然是音乐作品流通的一种相当持久的形式,“藏书者装订本”中也时常出现将印刷品和手抄本装订在一起的情况。
以上关于合唱谱、分谱、总谱的简单区分已经表明,对文本的研究不能脱离承载文本的物质实体,文本正是通过这个实体被赋予不同的社会属性和文化意义。再如,早期音乐中一种重要的手抄或印刷形式“进献本”(presentation copy),通常为献给上层社会重要人士的礼物,以求得对方给予的资金支持、工作机会、出版特权等利益,或是作为赞助的回报。进献本往往有着奢华精美的装帧制作和充满致敬姿态的副文本(献辞、插图等),大多用于收藏和展示。马肖的手抄本“Vg”(19)“Vg”是马肖作品一部重要手抄本的简称,该抄本亦称为“费雷尔-弗格手抄本”(Ferrell-Vogüé Machaut manuscript),以其现任拥有者詹姆斯·费雷尔和伊丽莎白·费雷尔(James E.and Elizabeth J.Ferrell)及曾经拥有者弗格侯爵(Marquis de Vogüé)的姓氏命名。、拉絮斯的《西比尔的预言》(ProphetiaeSibyllarum)都属于这种进献本。这样的书籍显然不具有商品属性,而是赞助体制下“赠礼经济”(gift economy)的产物。(20)Kate van Orden,Music,Authorship,and the Book in the First Century of Pri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3,pp.85,116.又如,奥登在研究16世纪尚松如何被用于贵族的礼仪教育时提到,当时炙手可热的字体设计师、印刷师罗伯特·格朗荣(Robert Granjon)为突显本土语言的民族性而为法文印刷专门设计了著名的“Civilité”字体(本义为“礼仪”),同时也为其出版的一系列尚松和经文歌乐谱设计了相应风格的音符,比以往的音符造型更为纤巧优雅,由此将音乐书籍的“字体”与贵族文化、民族意识联系在一起。(21)Kate van Orden,Materialities:Books,Readers,and the Chanson in Sixteenth-Century Europ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175.
(二)副文本的交流功能
与书籍的物质形态密切相关的是“副文本”。这一概念由法国文学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在其1987年的专著《门槛》(Seuils)(22)该书的英译本书名为《副文本:诠释的门槛》,见Gérard Genette,Paratexts: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trans.Jane E.Lew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中提出,指的是围绕书籍主体文本的周边元素,具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处于书内的“边文本”(peritext),包括一本书的标题、封面、献辞、题词、前言、卷首语、插图、宣传插页、注释、跋等。此外,热奈特将书籍的字体、版式、装帧、目录、索引、出版社的名称标识等出版印刷元素也纳入边文本的范畴。另一类是处在书外的“外文本”(epitext),包括与该书相关的评论、访谈、通信、日记等。热奈特认为,副文本的作用是“让文本成为书籍,并由此呈现给读者”(23)Gérard Genette,Paratexts: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trans.Jane E.Lew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1.,换言之,副文本是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中介要素和交流地带,向读者传递着关于文本的背景、内容、价值等方面的诸多信息。读者站在副文本这道“门槛”上,决定是否真正步入文本之内;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也受到该门槛的框范。副文本的实质是文本生产者(写作者和出版者)对文本的交流和接受施加控制的策略。由此可见,副文本在从文本到成书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也成为书籍史研究的重要议题。
早期音乐的乐谱书籍经常含有颇为丰富的副文本,这一方面是由于在赞助体制之下,作曲者(或出版商)与赞助人、题献者与受献者的关系主要借助副文本得以明示。上文提及的“进献本”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如卡彭特拉(Carpentras)1525年献给教皇克雷芒七世的《耶利米哀歌》中有教皇的纹章、一段声明作者与受献人关系的题词,以及一首采用古典挽歌对句诗体、赞美教皇的诗作。(24)Ignace Bossuyt etc.ed.,“Cui dono lepidum novum labellum?”:Dedicating Latin Works and Motet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Leuven:Leuven University Press,2008,p.99.此外,由于像进献本这样的书籍主要用于陈列展示而非阅读表演,一些视觉性的副文本要素便格外重要,例如使用材料昂贵的装帧、华丽精美的图像元素等。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14—16世纪众多教堂为自己量身定做的专用合唱谱手抄本,除了供唱诗班演唱之用外,也是会众瞻仰的对象,意在引发会众的敬畏之情,因而此类书籍的副文本强调庞大的规模和精良繁复的视觉元素(如微型画、设计考究的首字母、页边的装饰纹样),语词性的副文本反而较少。
另一方面,随着音乐印刷的兴起带动了音乐书籍的市场化发展,副文本有了更多展示的需要和真正被“阅读”的机会。这是因为,在传统的赠礼经济和利益交换时代,某部手抄本是专属于某一受献者或赞助机构的独一无二的物品,该抄本的接受者和使用者对其内容、背景等信息心知肚明,无需解释。(25)同注①,p.83。而音乐印刷品面对的是广大、无名的消费“公众”,便有必要通过副文本向这些“局外”读者介绍相关信息:曲目的性质,作曲家、编者、出版商、印刷商及受献者的身份、地位,题献者与受献者的关系,制作和题献该书的原因,等等。因而这类乐谱书籍的副文本常包含篇幅较长的文字著述。也正是因为公众这个“第三方”的存在,通过献辞、序言、纹章等副文本对受献者的颂扬才真正发挥了其应有的宣传、展示功能。
对于后世学者来说,副文本也是一种极为珍贵的史料,不仅阐明了某部音乐文本产生的日期、语境、功能,而且在有些情况下也是了解某位作曲家或出版商生平信息和职业生涯的重要渠道,有时甚至是唯一渠道(26)例如16世纪佛兰德作曲家里纳尔多·德尔·梅尔(Rinaldo del Mel)的生平信息基本上全部来自他的七部乐谱书籍中的献辞。参见Ignace Bossuyt etc.ed.,“Cui dono lepidum novum labellum?”:Dedicating Latin Works and Motet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Leuven:Leuven University Press,2008,pp.269-292.。此外,我们将在下文看到,副文本还是书籍生产者确立作者身份的一种有效手段。(27)关于音乐书籍副文本的更为详细的研究,参见刘丹霓:《16世纪复调音乐书籍中的“副文本”研究》,《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
(三)作者身份的多重样貌
书籍有作者,书籍的作者即为其文本的写作者——这一点并非不言自明。在中世纪手抄本时代,“作者”通常是指文本材料的抄写者、汇编者、注解者和评论者,即出于不同目的、以不同方式对他人材料进行处理和重塑的人。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随着印刷的到来,对作者的职能及其意义的解释有所改变,作者被视为一种个人创作行为,在文本上署名成为一种“获得认可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潜在工具”。(28)〔英〕戴维·芬克尔斯坦、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书史导论》,何朝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17、120—121页。从中世纪式作者(auctor)到文艺复兴式作者(author)的转变过程在如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这样的文学家身上已然实现,而作曲家成为“作者”的进程要缓慢得多,其间伴随着作者身份(authorship)的复杂演变。
首先,不同于神学、科学、文学著述,音乐书籍长期忽视作者身份。一方面,如弥撒曲这样的宗教体裁手抄本并不以作者身份为成书的基础;另一方面,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音乐书籍以选集(anthology)和杂录(miscellany)为主,为单独一位作曲家制作或出版的作品专集相对少见。不同创作者、不同体裁的乐曲被混杂在一起。许多声名显赫、作品等身的作曲家的乐曲被收录于这些选集,但他们的姓名身份却并不随之显示在书中。玛莎·费尔德曼在其对威尼斯牧歌出版的研究中指出,出版商即便选择印刷非佚名的乐曲,“他们似乎也将某些作品、某些类型的作品,尤其是某些作者群体的作品视为本质上是‘佚名’的”。(29)Martha Feldman,“Authors and Anonyms”,in Music and the Cultures of Print,ed.Kate van Orden,New York:Routledge,2017,pp.163-199。例如,当时许多出版商普遍需要在他们所掌握的有作者署名的作品之外,广泛收集和征集其他曲目以“填充”一部常规牧歌集或尚松集所要达到的体量规模,即所谓的“filler music”。于是便出现了不少为出版商提供新曲的“自由职业供稿人”,他们提供的乐曲可能是他人的作品,也可能是他们自己新写的作品,而这些乐曲在出版时通常是不署名的。奥登也提到,巴黎著名出版商皮埃尔·阿泰尼昂(Pierre Attaingnant)似乎认为尚松曲集就是一种完全不需要作者名字的出版物,他的乐谱书名强调的是数量和“新品”(如《新歌27首》《新曲第一辑》)而非这些新歌的创作者。(30)Kate van Orden,Music,Authorship,and the Book in the First Century of Pri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3,p.47.由此可见,书籍没有作者未必只是因为其中的乐曲找不到著作归属(attribution),而是缘于当时书籍生产文化的某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和约定俗成的惯例。
其次,书籍的作者并不理所当然地等于其文本内容的创作者。实际上,“author/autore/autheur”的含义远不止是文本的“作者”,而是指多种事物的“制造者”“创始者”。因此,书籍的作者在当时被视为图书的制造者似乎是理所当然之事:编订者、印刷商、出版商、销售商等直接参与书籍产业的人构建了作者身份,他们也毫不犹豫地在书籍的副文本上彰显这一身份。例如意大利出版商安德烈·安提柯(Andrea Antico)在1516、1517年先后出版了题献给教皇利奥十世的《弥撒曲十五首》(Liberquindecimmissarum)和《管风琴弗罗托拉》(Frottoleintabulatedasonareorgani)(31)前者是历史上第一本以合唱谱版式印刷的弥撒曲集,后者是意大利键盘音乐的第一本印刷乐谱。,将自己的画像置于两本书标题页最醒目的位置,以标榜自己对书籍的“权威”。(32)同注②,pp.63、67。
再次,即便在进入16世纪之后作曲家的名字开始逐渐出现在乐谱书籍的标题上,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参与和控制了自己作品的出版。最早印刷出版的单一作曲家的作品专集是彼特鲁奇发行于1502年的《若斯坎弥撒曲第一卷》(LiberPrimusMissarumJosquin),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若斯坎本人参与了此书的出版工作,而且“若斯坎”这个名字在书中仅出现在一处:最高声部分谱的标题页上,也就是说其他声部的分谱中完全没有显示创作者的身份。(33)同注②,p.78。在一个作曲家的生计和声望几乎完全不依赖作品出版的时代,靠出书赚钱的是书业从业者而非音乐实践者;在一个尚无著作权概念和版权立法的时代,出版商可以在作曲家完全不参与、甚至不知情的情况下出版后者的作品。印在书上的作者之名不等同于创作者本人,正如福柯所说,作者之名有别于日常的人名,它是一种经过文化构建的地位,是一种话语功能,它将若干文本聚集在一起,使之与其他文本区分开,表示某个社会中某些话语的存在、传播的特征。(34)〔法〕米歇尔·福柯:《作者是什么?》,载《后现代主义的突破》,王潮选编,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78—279页。这一时期的出版商经常将一些著名作曲家的姓名用作一种类似商标的推销手段,“阿卡代尔特”“拉絮斯”是当时的尚松曲集最喜欢贴加的“标签”,而这些作者之名甚至无法确保书中歌曲全部出自这位作曲家之手。(35)Kate van Orden,Music,Authorship,and the Book in the First Century of Pri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3,p.119.
最后,面对乐谱书籍的作者身份,作曲家们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有像阿卡代尔特这样完全不关心出版的人,虽然他是16世纪作品被印刷和重印最多的作曲家之一,但我们对他在出版界的作为一无所知。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具有强烈作者身份意识和冒险精神的为数极少的作曲家,他们自费出版并承担相应的经济风险,例如帕莱斯特里那1554年出版的弥撒曲集(Missarumliberprimus)预支了他一年的薪水;拉絮斯在1571、1582年分别获得了法国国王查理九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授予的出版特许权。也有一些作曲家通过说服自己的雇主资助出版来规避风险。
(四)阅读行为的社会实践
在当下书籍史的发展中,最受重视、最具活力的领域当属对阅读行为的历史理解和历史解释。大体涉及三个方面:1.书籍的流通、流传、订购、收藏、借阅等情况,即何时、何地、何种书籍、以何种方式到了何人手里;2.阅读行为本身,即如何、为何阅读,涉及阅读的能力、期待、习惯和方式(如默读还是朗读,精读还是泛读)、社会空间等;3.阅读效果和读者反应,即读者如何理解他们读到的文本,读者与其阅读经验如何相互影响。可见阅读史自身脉络庞杂,结构复杂,被视为书籍史“最具挑战性的部分”(36)〔英〕詹姆斯·雷文:《什么是书籍史》,孙微言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51页。。与其他书籍相比,乐谱书籍的阅读更为特殊:它的“读者”既有特权阶层的受献者,也有具备不同程度音乐素养的职业音乐家、业余爱乐者、儿童初学者等群体;它要求的“读写能力”(literacy)是识谱写谱和视唱视奏;它的“阅读行为”与表演实践密不可分。
拿读写能力来说,16世纪欧洲上层社会的初级教育开始将识谱视唱纳入读写能力的培养体系。此类教育通常从拉丁语学习开始,继而是本国语学习,最后是音乐和算术的基本训练。可见,读谱代表了读写能力的高级阶段,在当时被普遍视为良好教育的组成部分。除此之外,歌唱在文字语词的阅读学习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奥登详细研究了16世纪的入门读本如何将多声音乐应用于儿童的基础教育,把简单的交替圣歌、祈祷歌、连祷歌与教义问答相结合,将同度卡农的演唱作为初级音乐训练的基本组成部分。(37)Kate van Orden,Materialities:Books,Readers,and the Chanson in Sixteenth-Century Europ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chaps.pp.5-7.
需要再次强调,书籍的物质形式对阅读有全方位的直接影响,因而也是阅读史必须考察的维度。例如,乐谱是否有装订、装帧品质如何,决定了其流传和使用的命运:进献本或收藏者装订本被珍藏在私家书房或公共图书馆而保存完好;分谱被歌手乐手反复使用直至破旧不堪;散页在运输中遭到损坏、遗失、盗窃。分谱常用的横版印刷更便于乐谱排版,柔软的纸张和较短的书脊也让书本易于摊开,方便表演中使用;竖版乐谱则便于读者根据自己的喜好将之与其他书籍合订在一起。乐谱的页面布局影响了表演者之间的身体关系,如合唱队成员要依据合唱谱上各声部的排列分别站在相应的位置,同时包含女声和男声声部的尚松分谱则为男女歌手提供了亲密互动、眉目传情的契机。正如夏蒂埃所言:“阅读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智力活动,它还涉及运用身体的活动,在具体空间中建立与自身、与他人的关系。”(38)〔法〕罗杰·夏蒂埃:《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吴泓缈、张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92页。
二、音乐书籍史的方法论特色
音乐书籍史成长于众多领域学者之间的广泛交流和通力合作,具有极其鲜明的跨学科性质,其研究方法也体现出当下史学走向的一些主要特点。
(一)计量的历史与诠释的历史
总体而言,书籍史(以及音乐书籍史)在史学方法上依赖于两大支柱:社会史和文化史。这一点从本文开头简要勾勒的书籍史发展历程即可看到。这里所说的社会史即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社会经济史;而文化史是指20世纪晚期兴起的“新文化史”,前文提及的罗伯特·达恩顿、罗杰·夏蒂埃本身就是新文化史的领军人物。这两种史学范式各有侧重,彼此借力,优势互补,在当今各类史学领域的无数课题中共同发挥着关键作用。
社会经济史倾向在书籍史中的最突出体现是计量分析方法的运用和对长时段宏观结构的关注。计量方法即收集和统计书籍产业中各种可以获得和量化的数据,从各地区出版印刷商的数量、原料供应情况到书籍的印数、销量、价格、分布、存世率(即一部出版物的现存数量与当时发行量的比例),再到阅读人口的规模、识字率、购买书籍的类型和数量、读者的职业和阶层等等。进而通过数据分析得出一些关于总体态势的概括性结论。此类研究运用的史料主要包括国家出版物备案记录、图书贸易目录、物资清单、遗产公证记录、订书单、图书馆的借阅记录等。(39)〔美〕罗伯特·达恩顿:《莫拉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2—139页。例如阿尔伯特·拉巴尔分析了16世纪出自法国亚眠的4442份遗产清单,有书籍的清单占20%,其中仅六份清单列有音乐书籍。这六份清单的主人分别是两名牧师、一名地方贵族、两名商人、一名石匠(40)Albert Labarre,Le Livre dans la vie amiénoise du seizième siècle,Paris:Béatrice-Nauwelearts,1971,p.224.,从中可知音乐书籍在当时当地的拥有情况。再如在印刷大师克里斯托弗·普兰坦(Christopher Plantin)的装订订单中,尚松曲集占据最大比重,表明尚松在当时的音乐书籍中最为畅销。(41)Kate van Orden,Materialities:Books,Readers,and the Chanson in Sixteenth-Century Europ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p.61-62.
不同于社会经济史偏重定量分析、事实描述、模式归纳,新文化史注重的是数据和事实背后的意义阐释。正如克利福德·格尔兹所言:“关于文化的分析……是一种寻找意义的解释科学。”(42)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New York:Basic Books,1973,p.5.新文化史破解意义的途径众多,其中之一是探索语言、仪式、图像、习俗等文化表征的历史内涵,例如通过读解音乐书籍中各种图像符号的象征意义,或剖析卷首诗中的文学意象来理解某位作曲家或出版商制作某书的具体意图。新文化史的史学方法更大的用武之地还是阅读史,如果说社会经济史解决的是“何人在何时何地读何种书籍”的问题,那么新文化史探究的是阅读的目的、方式以及读者个人对文本的理解。此类研究所涉史料主要是个别读者的图书收藏、阅读笔记以及与其阅读经验有关的日记、信件、自传等,其中“旁注”(43)“旁注”(marginalia),即读者阅读时在书中任何地方随手所写的批注。被看作尤为重要的一种阅读史料,它有助于重构特定读者的阅读习惯、阅读结构、思维过程、心理状态,并提供了其生平、喜好、思想的相关信息。(44)参见韦胤宗:《阅读史:材料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3期。例如《海因里希·格拉瑞安的书籍》(45)Iain Fenlon and Inga Mai Groote ed.,Heinrich Glarean’s Books:The Intellectual World of a Sixteenth-Century Music Humanis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就充分借助这位16世纪音乐理论家在其各类私人藏书上所做的文字、图像、乐谱批注,以及他的学生在教材上所写的课堂笔记,由此探究格拉瑞安作为人文主义者、理论家、大学教师的观念、研究和教学方法及其所产生的影响。
(二)微观的历史与日常的历史
从以上社会经济史与新文化史两种路向的区别可以看到,前者从宏观着眼,后者由微观入手。现代书籍史研究起步于宏观的统计分析,但如今以微观透视为主导。这当然与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的“微观史学”(microhistory)(46)微观史学就其本质即是一种社会文化史,根据研究倾向又可分为文化微观史与社会微观史。参见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9—90页。密不可分,微观史学早期的经典名著《奶酪与蛆虫》(1976)(47)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鲁伊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在很大程度上展现的就是一位意大利农民的阅读史个案。与微观史学密切相关的另一史学流派是与之大约同一时期在法国和德奥学界出现的“日常生活史”(Histoire de la vie quotidienne/Alltagsgechichte)。两种史学范式的共性在于:1.关注以往被忽视的普通民众、下层社会、大众文化;2.强调个体、个案、个别性,有助于恢复历史面貌原有的复杂性,并为更宏观的历史认知提供新的线索和洞见;3.观察平凡生活的常态而非特殊、重大的事件;4.不仅关心公共领域,也注重私人领域;5.恢复了“人”——具体、鲜活的个人——在历史叙事中的地位。
这种以小见大、自下而上的方法论特点也体现在16世纪音乐书籍史的研究中。这些研究在对书籍产业进行大量数据统计的同时,也表明每一位出版商、作曲家,甚至每一本书的个案背后都有特定条件的制约,都有各不相同的利益卷入其中,需要具体个案具体分析。上文提到的安提柯献给教皇的《弥撒曲十五首》,让他从彼特鲁奇手中成功夺走了印刷管风琴符号谱的特许权;普兰坦印刷天主教礼拜经文全集的出版计划因赞助人(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财政危机而惨遭重创,为了止损不得不转而出版一位受菲利普青睐的佛兰德音乐家的弥撒曲。(48)Kate van Orden,Music,Authorship,and the Book in the First Century of Pri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3,p.104.同样是自掏腰包出版自己作品的作曲家,莫拉莱斯由于出版合约的诸多限制而必须独自承担经济风险,帕莱斯特里那某些大型弥撒曲集的出版则得益于其第二段婚姻带来的雄厚财力。(49)Jane Bernstein,“Publish or Perish?Palestrina and Print Culture in 16th-Century Italy”,Early Music,Vol.35,No.2,2007,pp.225-235.
在阅读史方面,学者们也十分关注普通人如何阅读和使用音乐书籍。例如奥登对16世纪尚松书籍阅读情况的研究,主要着眼于音乐能力有限的业余实践者,而非经过标准化训练的职业音乐家:主日学校里学习识字发音的孩子们,音乐水平有限但热衷于歌唱的爱乐者,不同阶层的爱书人士等。(50)Kate van Orden,Materialities:Books,Readers,and the Chanson in Sixteenth-Century Europ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也有学者根据个别读者的相关史料,重构其阅读经验,例如约翰·克梅茨搜集到一份1546年用于私家音乐课的分谱教材,其所有者是巴塞尔一名律师的13岁的儿子安伯巴赫,通过这个男孩6个月的音乐学习经历,窥见当时此类音乐教育的进度安排和尚松作为教学材料的应用情况。(51)John Kmetz,“The Piperinus-Amerbach Partbooks:Six Months of Music Lessons in Renaissance Basle”,in Music in the German Renaissance,ed.John Kmetz,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215-234.
(三)在场的历史与缺席的历史
曾经长期占据史学主流的兰克学派认为,历史事实的客观真实性毋庸置疑,只要通过严格的史料鉴别和考证,以不偏不倚的态度从第一手史料中提取出历史事实并置入历史撰述,便可做到“如实直书”“让历史事实自己说话”。如今这种史学观早已被斥为天真的幻想,史实和史述是史家借助史料经过诠释而形成的主观构建,这一点已是学界共识。但除此之外,对16世纪音乐书籍史的研究体现了破除这一“天真幻想”的另一层含义:警惕和识别原始资料中的“幸存者偏差”。
史料虽不能自己说话,但它会误导史家,歪曲后者的历史认知。例如,《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中的“分谱”词条提到,现存分谱的品相过于完好,看上去完全不像被用过的样子,从而质疑分谱是否真的被用于表演。(52)John Morehen and Richard Rastall,“partbooks”,in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2nd),ed.Stanley Sadie,London:Macmillan,2001.问题在于,留存至今的分谱通常来自具备良好保存条件和藏书意识的收藏者,他们通常并非音乐从业者,对这些书籍的实际使用非常有限,但他们的藏书只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海量乐谱的冰山一角,其余更多未能幸存的乐谱恰恰是在音乐实践者们的日常使用中被损坏、遗失,况且当时乐谱的物质形态(常为散页或轻薄的小册子)也注定了它们大多昙花一现的命运。奥登对书籍存世率的研究颇能说明问题:汉斯·海因里希·赫尔瓦尔特(Hans Heinrich Herwart)是16世纪欧洲拥有音乐藏书最多的人物之一,在他收藏的由阿泰尼昂印刷的尚松曲集中,有27部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幸存的副本,但根据相关史料估计,这些乐谱当时的印数应为每部约1000册;另一位重要法国印刷商雅克·摩登(Jacques Moderne)出版的《尚松典范》(Parangondeschansons)系列仅有33册留存于世,实际印数应达到12000册,存世率为0.3%。
更重要的是,音乐书籍史自身的研究范围和史料的幸存者偏差,容易让我们忽视一个关键的问题:书面与表演的关系。至少就16世纪的乐谱书籍而言,它所处的世界是一种以表演为绝对主导的音乐文化。表演是生产这种书籍的最主要目的,表演也是这种书籍最常见的“阅读行为”,此类书籍物质形态的设计和文本内容的构建需将表演的日常实践纳入考量。可见,“表演性”是此类书籍区别于其他书籍的一大根本性特征。可以说,早在印刷出现之前,音乐文本已经通过表演这种口头和听觉行为得到“发表”;印刷出现之后,依然有大量作品并不以印刷的形式问世:作曲家、诗人、剧作家在日常表演中为赞助人服务,应景性的韵诗、歌曲庆祝着贵族生活中的大小事件,推动着欧洲宫廷的社交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publication”一词的理解应回归其最初的本义:公之于众。有鉴于此,音乐书籍史的学者越来越重视表演的维度,理查德·威斯特莱奇坚持表演在书籍史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提出了关于朗声阅读的“景观生理学”(spectacular physiology)(53)John Wistreich,“Introduction:Musical Materials and Cultural Spaces”,Renaissance Studies 26 (2012),pp.1-12.;奥登主张在近代早期表演文化的背景下,通过与音乐有关的实践活动来诠释尚松出版物,观察“被编码在书写文本中的表演”(54)Kate van Orden,Materialities:Books,Readers,and the Chanson in Sixteenth-Century Europ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34.。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表演”不仅指职业音乐家的作乐活动,也包括更为广泛的各种口头/人声/身体实践,从初学者和爱乐者的歌唱,到诗人的朗诵,再到借助歌曲的语言发音练习和符合礼仪规范的谈吐训练。
综上可见,在史料和历史叙事中,在场的经常是例外,缺席的往往是常态。正如奥登所言,音乐书籍史的研究“很多时候走在物质与非物质的界线上”(55)同注②,p.271。,研究的材料是书面记录,但研究的目的往往是透过这些材料洞悉书写世界之外的历史境况,为那些看似没有历史(书面记载)的事象——如歌唱吟诵、丢失的乐谱——探索书写其历史的可能性。
结 语
本文力图在有限的篇幅里尽可能较为全面地论述音乐书籍史的核心主题和最突出的方法论特色。一方面,音乐书籍史脱胎于一般书籍史,必然与后者有着共通的主题和维度,包括书籍生产的技术条件、书籍成品的物质实体、副文本的交流功能、读者的阅读实践及其所伴随的社交行为等。另一方面,音乐书籍史也显示出自身的独特之处及其所带来的特殊问题:其核心研究对象之一是以非语词符号为主的乐谱书籍,此类产品的多样形态挑战和丰富了“书籍”的内在属性;有多种书业参与者(抄写员、编者、印刷商、出版商、销售商)与作曲家共享或争夺音乐书籍的作者地位,与其他类型的著书者相比,作曲家作者身份意识的确立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音乐书籍要求特殊的阅读行为和阅读能力,由此在书面与口头、文本与表演之间建立了不可分割的联系。诚然,本文的论述主要聚焦于16世纪的欧洲音乐书籍,而其他时代、地域、不同媒介的音乐书籍必然呈现出彼此有别的具体特征和相应议题,有待日后持续探索。
音乐书籍史为音乐历史的研究和书写提供了较为新鲜、别样的角度,开掘了以往被忽视的珍贵资料(如异彩纷呈的副文本元素、各类公共和私人的藏书记录),让众多不同身份地位的历史参与者和行为者(而非个别伟大人物)在历史叙事中纷纷亮相,揭示出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下音乐文化鲜为人知的面向。音乐书籍史平衡于社会史的数据计量与文化史的意义阐释,透过日常生活的“显微镜”重现个体的生动经历,在浩瀚纷繁的史料钩沉中讲述着关于被遗忘之人、被遗失之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