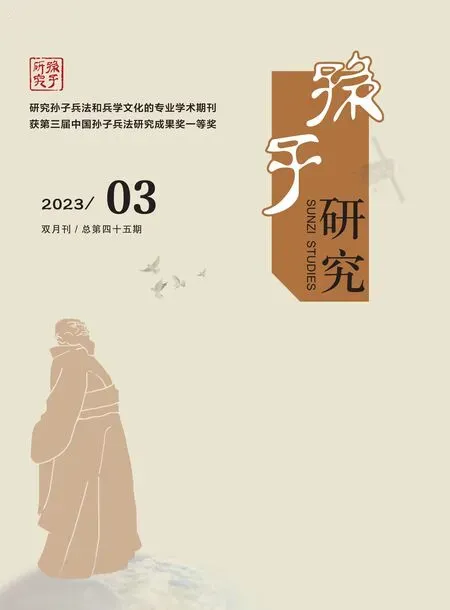简论中国古代战略
段汉中
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谋划。中国古代战略的实践与理论,成果丰富,形成了多种流派。本文尝试梳理历代战略实践,归纳总结中国古代战略理论体系。
一、战略概念源流
(一)战略的词源
“战”在《说文解字》中释义为“鬥也”,“鬥”是“两士相对,兵杖在后,象鬥之形”;“略”,《说文》释作“经略土地也”。可知,“战略”是博弈双方角力对抗、争夺和划分彼此利益的谋略、方法。战争是对立双方最激烈的斗争形式,因此战略首先指谋求赢得战争的规划与方案。
中国古代用“庙算”“方略”等词汇表达指导全局的规划,“战略”则泛指一般的作战方法或谋略。〔1〕20 世纪 初,“战略”一词的概念发生重大转变,由泛指军事策略变为专指关于战争全局的谋划。
近代以前,“战略”一词并不强调指导战争全局的谋略。沈约《宋书》中有“授以兵经战略,军部舟骑之容,挽强击刺之法”〔2〕,唐代高适有诗云“晋宋何萧条,羌胡散驰鹜。当时无战略,此地即边戍”〔3〕,明代茅元仪著有《廿一史战略考》等。可见,“战略”的词义并不固定,均是泛指军事技能或谋略。清末新军〔4〕创立之前,曾国藩、李鸿章等湘军、淮军领袖,在谈到指导战争全局的谋略时,常用“内外主客形势”等表述方法。曾国藩批评清军江南大营失败是由于缺乏全局观念和规划,江南大营统帅,只着眼于南京一城一地,没有争夺长江中上游的安庆、庐州,而且四处出击,终于被太平军各个击破,所谓“内外主客形势全失”。
1901 年后,清朝实施新政,设立新式军校,引进近代西方军事思想,开始出现近代“战术学”与“战略 学”。〔5〕1906 年,通国陆军速成武备学堂步兵科总教习贺忠良出版《战法学教科书》,用战略和战术两个概念分别表示指导全局性战争和局部性战斗的方法。〔6〕1911 年,保定军官学堂学生潘毅等编译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书,定名为《大战学理》,把指导战争全局的谋划翻译为战略;同年,蔡锷编著《曾胡治兵语录》,已经将战略、战术并举,并视为常用术语,例句如“临阵分枝宜散,先期合力宜厚二语,尤足以赅括战略、战术之精妙……先期合力者,即战略上之集中展开及战术上之开进是也”“各国兵家举凡战术战略,皆极端主张攻击”等。〔7〕
至此,“战略”成为专指掌控战争全局的方略,词义日益固定下来,不仅在军事领域广泛应用,而且扩展应用于社会各领域,出现了大战略、国家发展战略、经济战略、文化战略等名词和概念。
(二)中国古代战略理论的缘起
中国古代战略理论从战略活动中总结发展而来,其形成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从概念到体系的过程。
战略的起点是人的分化。分化的动因是生活资料和人口本身分配的不均衡——即利益不均。韩非子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韩非子·五蠹》)在生产力不发达时,人口很少,人们利益分歧未凸显,未产生阶级分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生产的“分工慢慢地侵入了这种生产过程。它破坏生产和占有的共同性,它使个人占有成为占优势的规则,从而产生了个人之间的交换”,最终发展到“人也可以成为商品”,“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8〕利益的分歧和阶级的分化导致矛盾对立。
人群分化为对立的群体,对立群体的矛盾斗争导致战争。孟子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孟子·梁惠王上》)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的分化发展到建立私有制并产生民族时,战争及进行战争的组织“已经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功能。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9〕。
人们意识到彼此之间的利益差别与冲突,并开始用战争手段改变利益分配格局,进而产生了指导战争的理论。战略是人们有意识地促使矛盾、斗争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的谋划活动。战略理论即研究战略活动规律的学问。
中国古代战略理论自成概念体系。战争攸关存亡,人们在指挥战争和研究战争时不得不尽量克服非理性因素的干扰,因此战争状态最接近纯粹形式上的矛盾运动状态,战略作为指导战争的谋划,是研究矛盾转化规律最直接有效的形式。《易经》《道德经》等研究矛盾规律的著作,在中国古代常被直接视为兵书。
《易经》的逻辑起点是“太极”。“太极”类似于黑格尔《逻辑学》中的“纯存在”,是规定性最少的概念。〔10〕《易经·系辞》中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周敦颐《太极图说》称:“太极本无极也。”太极是自然未分化的起始状态,或者说是阴阳未分的混沌状态。太极一经分化,便产生阴阳,即矛盾对立的两方。《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切的矛盾斗争由太极产生。《易经·系辞》中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因此,《易经》是研究阴阳运动规律以趋吉避凶的学问,是中国古代战略的滥觞。
《孙子兵法》等兵家著作及其他学派的典籍,从具体可操作的层面,提出了支撑中国古代战略体系的各种概念,论述了概念间的逻辑关系。中国古代战略在军事实践中自发产生,战略理论随着战略实践的发展和战略决策者认识的深入,最终发展为一套完整的概念 体系。
二、中国古代战略的概念体系
中国古人在数千年的战略实践中,把握了战略的一般规律,构建了一套基于中国历代战争实践、具有中国思想特色的战略理论。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认识与实践的基本规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11〕中国古代战略活动从作出战略判断开始,进而开展战略决策,运用战略力量落实决策方案,最终根据战略方案的执行结果和战略力量对比的变化进行新的判断,形成了从“正名定分”到“运筹帷幄”再到“因势利导”的概念体系。
(一)正名定分——作出战略判断
战略的第一个问题是明确威胁来源,判断敌我友。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2〕中国古代战略通常将此问题归结为“正名定分”,即明确自我与他人的位置关系。
首先,战略判断要判明各方利益及其边界。战略判断的依据是战略利益。战略利益是国家生存发展所必需的资源,既包括领土、人口等有形资源,也包括信誉、声望等无形资源。子曰:“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滕文公上》)“正名”就是要确认自己拥有哪些利益,据此行使权利。“经界”就是确认自己与他人的利益边界,据此处理相互关系。战略决策者要了解己方的战略利益是什么,它的时空边界在哪里,要判断他人的利益及其边界,最终判明人己之间的共同利益与利益分歧,利益相同即为友,利益相悖即为敌。
战略利益不仅包括决策主体实际占有的资源,也包括决策者认为自己应该占有和支配的资源,这些资源可能尚不归其所有。北宋承五代之余绪,以恢复唐代旧疆为己任,把唐末的疆域视为其固有的利益范围。李克用、李存勖父子“血战三十余年,盖言报国仇雠,复唐宗社”〔13〕。复唐旧疆是五代以来基本的利益判断。因此,赵匡胤执意平南唐,卧榻之侧不许他人酣睡,又设封桩库,以图收复幽燕。赵光义则“欲收中国旧地”,称“异时收复燕蓟,当于古北口以来据其要害,不过三、五处,屯兵设堡寨,自绝南牧矣”。〔14〕
其次,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利益的边界也在不断调整。战略决策者根据利益和认识的变化,不断修正敌友的判断,并做出下一步决策。管仲有尊王攘夷之策,在各国间寻找共同利益,树立共同敌人。晏婴有“二桃杀三士”之计,人为制造利益冲突,挑起竞争对手间的矛盾。范雎有远交近攻之谋:人己利益重叠冲突时,双方即为敌我关系;利益不重叠时,即为友邻关系。
(二)运筹帷幄——展开战略决策
“筹”即算筹,又称“策”。运筹或决策,是根据一定规则排列算筹、进行运算,凭借运算结果判断事物的大小、多少等。战略决策或战略运筹,是根据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评估所处的客观形势,对敌我双方可以运用的力量、手段进行运算比较,最终得出运用战略力量达成战略目标的具体行动方案。战略决策的构成要素包括决策的主体——决策者,决策的客体——内容和对象,以及决策的形式与方法。
战略决策的内容和对象涵盖各类敌我主客观条件,包括双方的主观意图、战略目标,所共处的客观时空环境,拥有的力量,运用力量的主观方式、方法。第一,历代战略决策强调知己知彼,首重判明各方意图。洞察对手的战略目标是战略家最看重的能力。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说:“阅人既多,历事亦熟……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乃能翦除强敌,统一海宇。人之情伪,亦颇知之。”晋献公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劝谏虞公说:“晋不可启,寇不可玩。”虞公却说:“晋,吾宗也,岂害我哉?”虞国灭亡的重要原因是误判晋国战略意图。其次,要评估所处的时空环境。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15〕小国而间于齐、楚,就是滕国面临的客观时空条件,且短期内难以改变。特定的时空条件决定了战略主体所能拥有的力量,制约着其战略选择。第三,要计算、比较双方的战略力量。强弱,形也。兵法把客观力量的大小、强弱称为“形”。战略决策的基础工作是计算和比较敌我之“形”。取胜的基本原则是以强击弱。《孙子兵法·形篇》云:“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16〕第四,要选择力量运用的方式方法。岳武穆有言,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战略博弈的一方要在力量对比不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谋求胜利,就要考虑采取恰当的力量运用方法,争取优势和主动。田忌赛马就是在战略力量对比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调整战略力量运用方法取胜的典型。
中国古代战略决策的形式、方法特点鲜明。在形式上,《孙子兵法》云:“是故政举之日,夷关折符,无通其使;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孙子兵法·九地篇》)张预注称:“古者兴师命将,必致斋于庙,授以成算,然后遣之,故谓之庙算。”〔17〕古人战略决策的地点是正式而戒备严密的殿堂,决策的形式是集体会商、定下决心,即“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致斋于庙,授以成 算”〔18〕。战略决策须做到严格保密,即“夷关折符,无通其使”(《孙子兵法·九地篇》)。在方法上,重视观察、运算和推理。孙子将观察的方法称为“相敌”,通过观察获得对敌我双方主客形势的感性认识,作为决策的依据。《行军篇》说:“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孙子重视量的计算,根据力量对比展开逻辑推理,得出行动方案。兵法云:“策之而知得失之计。”(《孙子兵法·虚实篇》)“计利以听,乃为之势。”(《孙子兵法·计篇》)“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孙子兵法·形篇》)所谓“计利”,就是对各种战略因素的运算比较。“地”是敌我双方所处客观形势与条件,“度”“量”“数”是博弈者能够占有和使用的物质资源及其规模,由所处客观形势所决定。双方物质资源的强弱比例就是“称”。强胜而弱败,即“称生胜”。战略决策者通过评估形势、计算力量对比,最终得出运用战略力量达成战略目标的方案。
(三)因势利导——运用战略力量
战略行动是按照决策方案建设和运用战略力量达成战略目标的实践活动。中国古代战略行动可分为练兵、造势和制敌三个阶段。练兵是力量建设,造势是力量调度,制敌是力量的正面对抗。兵法云:“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孙子兵法·势篇》)“形”指力量对比所呈现的格局,强弱是客观存在。“势”指博弈各方为争取主动调度安排战略力量,勇怯是对敌我强弱的主观认识。兵法又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19〕(《孙子兵法·谋攻篇》)伐谋、伐交是“造势”的过程,调度力量以求主动;伐兵、攻城是战略力量的直接碰撞和较量,即角力以制敌。
战争归根结底是一场角力,战略是为了赢得力量较量而展开的谋划。战略行动首重力量建设,增强己方力量以压倒敌人,即赋之以形。历代战略力量建设集中表现为“练兵”。春秋以来,选将练兵之风盛行,孙子吴宫教战,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汉卫青、霍去病所率之骑兵,东晋谢玄、刘裕之北府兵,宋岳飞之岳家军,明戚继光之戚家军等不胜枚举。戚继光所著《纪效新书》《练兵实纪》,集论练兵之大成。清末曾国藩练湘军仍是“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束伍练技”〔20〕。兵法云“先为不可胜”(《孙子兵法·形篇》),盖以“赋形”“练兵”为战略之要旨也。〔21〕
造势是调度战略力量的艺术。《孙子兵法·计篇》说:“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力量强大不等于战略优势。博弈双方的力量对比在一定时期内相对不变,须设法调度力量进行布势,造成我方在时机、地位和心态上的主动。淝水之战,苻坚兵力远多于东晋,但是谢玄等东晋将领奇袭洛涧挫败秦军前锋后,依凭地势驻扎在淝水边八公山下,与秦军隔河对峙,占据了地理上的优势;利用此前奇袭的胜利和当时的山河条件,导致苻坚误以为“八公山上,草木皆兵”,造成了心理上晋军勇而秦军怯的优势;最终,诱导秦军后撤,利用秦军混乱而发起进攻,掌握了时机上的优势。此战系力量弱小一方成功调动敌我双方力量形成战略优势的范例。
角力是博弈双方战略力量的正面对抗,直接决定战争的胜负,检验战略的成败。兵法云:“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孙子兵法·虚实篇》)角力的一般规律是强胜弱败。《谋攻篇》说:“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角力中谋求以弱胜强的基本方法是集中优势兵力,形成局部优势。《虚实篇》说:“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九地篇》说:“故为兵之事,在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巧”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化总体被动为关键局部主动,最终改变全局。
经过判断敌我、决策运筹和造势角力之后,博弈双方的客观力量对比和主观目标意图都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博弈者要根据新的主客观条件再次进行战略判断,重新明确敌我友关系,并制定和实施新的战略方案。于是,战略完成了从实践到认识,到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
三、中国古代战略流派
历代战略可归纳为儒家、阴阳家和兵家等流派。战略主体的身份、立场差异导致其战略实践存在不同侧重和倾向。某种倾向和特点不断传承发展,就形成了战略风格和流派。一种战略流派能提供独特的观察视角、决策流程和执行方法,使决策者在面对复杂情况时能迅速找到战略分析的切入点,并为分析决策提供路径支撑。采用不同流派的分析模型进行比较研究,可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情况,保证战略判断和决策的准确、有效。
(一)儒家战略传统
儒家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历代战略,儒家在战略判断上强调义利之辨,重夷夏之防。儒家认为夷夏的本质区别是对义利的态度。夷狄单纯逐利,以利益为最高指导原则。《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华夏则不以利益为唯一标准,认为基于利益冲突而展开力量对抗,必然造成博弈双方的力量消耗,陷入零和博弈甚至两败俱伤,提倡从超越利益的层面化解矛盾。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仁”,指忠恕之道,推己及人。“义”,指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仁义在战略上强调对立双方有超越利害的共性和相互依存性,要用发展的方法消除对立,而非消灭对手。
儒家在战略决策方法上讲求格物致知。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这就是要全面考察对手的现状、历史和主观动机,从而决定己方的进退应对。此外,儒家战略决策强调克己复礼,必要时须牺牲短期利益来实现更高层次的目标。
儒家在战略行动上强调修文德、来远人。孟子提出“强为善”,无论在何种力量对比条件下,都把加强自身力量建设作为中心任务。滕文公问曰:“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儒家提倡内圣外王、修己安人,通过不断提升自身实力,形成绝对优势,在避免冲突的条件下将对手转化到自己的一方。在力量运用上,儒家一方面希望尽量避免直接冲突,子曰“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另一方面不回避直接的力量较量,倡导吊民伐罪,征伐与教化并行。汤征葛伯,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22〕
古代单纯依靠武力征服而建立的政权,往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短期内即崩溃瓦解。而在儒家战略传统影响下,中国历代疆域总体上是不断拓展的。儒家战略思维是古代中国政权维系统一、化外而内的关键工具。所以孔子才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论语·八佾》)。
(二)阴阳家战略传统
中国古代战略有鲜明的阴阳数术特色。阴阳数术是中国古人探讨自然法则和人类社会规律的学问,囊括天文历算、五行占卜等,旨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历代所重。殷商凡战争必占卜,周代以降形成了以《易经》为核心的阴阳数术之学。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意在探微寻理、兴周灭商,因此,《易经》本身就是一部总结战略运筹经验的典籍。历代战略家都以之为运筹决策的重要工具。
阴阳家在战略判断上强调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做出敌我判断时,要团结顺应规律的大多数,打击逆潮流而动的极少数。《易经·坤卦》卦辞说“西南得朋,东北丧朋”,《蹇卦》卦辞说“利西南,不利东北”。〔23〕姬周在渭水之滨,殷商在黄河以北、太行以东的河内之地。周在西南,商在东北,卦辞启示周得道多助,商失道寡助。在战略实践中,不仅己方要顺天应人、主动适应规律和潮流,还要设法置敌于“不德”、逆潮流的被动地位。郑伯克段于鄢,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左传·隐公元年》)商汤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商汤反而主动帮助葛国,派人“往为之耕,老弱馈食”(《孟子·滕文公下》)。葛伯杀害了送粮的“童子”,商汤才讨伐他。“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24〕此即将对手置于道义和规律的对立面,从而达到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目的。
阴阳家在决策方法上强调由象数推理。《易经》构建了一套战略决策模型,可通过象、数进行推演,得到具体卦爻,即具体的情景,根据情景做出行动决策。卦象是某一客观情景的简约、抽象表现,反映该情景的核心要义。人们可据“象”判断自己所处的位置,同时决定应采取的行动。《坤卦》六三爻爻辞说:“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姤卦》九五爻爻辞说:“含章,有陨自天。”“含章”即“戡商”,谓周伐商之事。〔25〕《易经》还可通过数的运算得到具体卦爻,即用数推算具体的战略情景。《系辞上传》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26〕此法可依次求得六爻并组成一卦。六十四卦是六十四种时空条件和力量对比情境,卦中的每一爻是时空和力量格局发展变化的特定阶段,卦辞和爻辞则是总结得出的该阶段、该条件下应采取的行动。人们可根据所得之卦,辅助做出决策判断。
阴阳家在战略行动上重视时与位,要求行动与时、位相符。《易经》认为人所处的时空环境、人我之间的力量对比都是在不断发展的,事物的发展遵守从产生、发展、壮大、衰亡到重生的循环规律,因此,人在特定的时空环境、力量对比格局中,应当采取特定的行动,以趋吉避凶。《左传》记载,狐偃请晋文公南下勤王。晋文公使卜偃卜之,得到“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判为吉兆。又使人筮之,得到《大有卦》变为《睽卦》,筮者说:“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于是,晋文公决定出兵勤王。据此卦例可知,《易经》辅助决策是“象”“辞”兼取,重在分析博弈者所处的环境地位,进而给出行动建议。
(三)兵家战略思想
战争通常具有突发性、紧迫性,要求在有限时间内运用现有力量展开较量并争取胜利,是最直接的力量对抗形式。兵家直接为战争服务,特别重视阐发力量对抗的规律。
兵家在战略判断上的特点是严谨慎重。兵法云,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判断敌我必须严格以利害为标准,“非危不战”“非利不动”(《孙子兵法·火攻篇》),对己方安全、利益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或集团是明确的敌人,其他次要矛盾都是可以利用和转化的对象。《三十六计》有云:“敌已明,友未定,引友杀敌,不自出力,以《损》推演。”〔27〕此之谓也。
兵家在战略决策方法上,强调分析力量对比,计利以听。中国古代兵家的战略分析模式,特重分析强弱、利害,以决定行动方案。兵法云:“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孙子兵法·九变篇》)又说:“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孙子兵法·九变篇》)五代后唐庄宗李存勖向高季兴咨询统一战略,庄宗问:“今天下负固不服者,惟吴、蜀耳。朕欲先有事于蜀,而蜀地险阻尤难,江南才隔荆南一水,朕欲先之,卿以为何如?”季兴对曰:“臣闻蜀地富民饶,获之可建大利;江南国贫,地狭民少,得之恐无益。臣愿陛下释吴先蜀。”〔28〕李、高的对话生动反映了兵家据强弱利害而定决策的特点。
兵家在力量运用上强调奇正相生。《孙子兵法》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孙子兵法·势篇》)《李卫公问对》云:“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若非正兵变为奇,奇兵变为正,则安能胜哉?”(《李卫公问对·卷上》)古代兵法中所谓“正”是指作战所需的物质力量、人物关系和客观条件。如陈琳所说:“长戟百万,胡骑千群,奋中黄育获之士,骋良弓劲弩之势,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济漯,大军泛黄河而角其前,荆州下宛叶而掎其后。雷震虎步,若举炎火以焫飞蓬,覆沧海以沃熛炭,有何不灭者哉?”〔29〕这里的“长戟百万,胡骑千群”就是物质力量,“奋中黄育获之士,骋良弓劲弩之势”就是发挥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济漯,大军泛黄河而角其前,荆州下宛叶而掎其后”则是充分运用客观形势条件。一支军队具备了这样的“正”,就拥有了“炎火”、拥有了“沧海”,自然就具备了消灭一切敌人的摧枯拉朽之势。所谓“奇”,是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即作战人员对物质力量、人物关系和客观条件的主观调动与应用。有了物质基础和一定的组织运用方法,只是具备了战胜敌人的条件,要取得战争的胜利,还必须发挥作战者的主观能动性,这个能动性就是“奇”。毛泽东同志指出:“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30〕
结论
中国古代战略实践与理论,本质是中国古人认识矛盾、处理矛盾的经验与一系列观点方法。古代战略实践是一个辩证运动过程,以辨敌我、定名分为起点,继而由象数推理,判明主客形势,料敌定策,最终通过练兵、布势争取主动,并力求在角力斗争中屈敌伸己,赢得胜利。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发展向前。中国古代战略理论以太极为起点,用阴阳概念表达矛盾的对立统一,演绎出虚实、主客、敌我、攻防、刚柔等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以逻辑顺序将判断、运筹、决策、赋形、造势、角力等概念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是内涵丰富、逻辑严谨的概念体系。中国古代战略理论与实践真正实现了知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