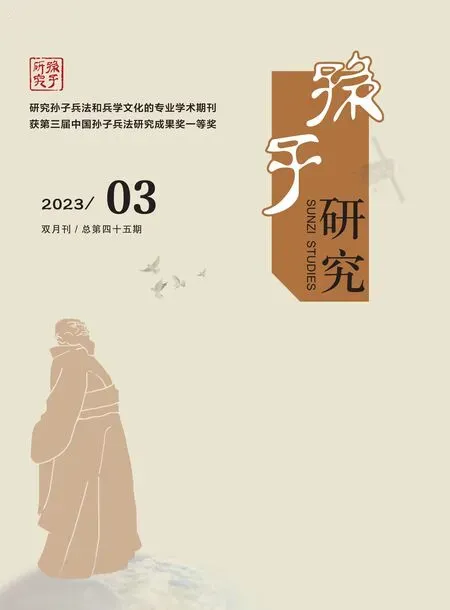《老子》兵书说再商榷
——以老子之“道”为考察
高 凯
老子生于春秋时期,与孔子同时代,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的战乱时期。受时代影响,儒、墨、道、法等几大学派无一不谈兵,所以说春秋时期也是一个“百家言兵”的时期。〔1〕老子作为道家学派创始人,其书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独具特色。所以,不少人将《老子》一书视为兵书。如《隋书·经籍志》将《老子》列入兵家类著述;唐代王真认为《老子》一书:“原夫深衷微旨,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2〕清代魏源也持类似观点,说:“《老子》其言兵之书乎!‘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吾于斯见兵之 形。”〔3〕近代学者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认为:“《老子》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又是一部兵书。”〔4〕相反,也有学者认为《老子》不是兵书,比如华钟彦认为《老子》八十一章中的辩证法思想虽对兵家有指导作用,但其言行涉及言兵者只有十章,其中积极言兵者只有五章,故无论从数量与质量上都无法承认《老子》是一部兵书。〔5〕李泽厚也持此观点,他说:“虽然承认《老子》与兵家有密切关系,但是,《老子》本身并不一定就是讲兵的书,决不能说《老子》书的全部内容或主要论点就是讲军事斗争的。”〔6〕
通行本《老子》一书共八十一章,其中有十二章直接谈及兵学思想,那么《老子》一书是否就可以被视为兵书呢?如果不是,《老子》谈论兵学的目的又是什么?要想解决这两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道”的基本内涵,在此基础上审视《老子》兵学思想及其意义,就可以对《老子》一书的立论方向做出判断。
一、“道”与兵学
(一)“道”的地位和提出
“道”是《老子》一书的核心主题。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说:“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故见素朴以绝圣智,寡私欲以弃巧利,皆崇本以息末之谓也。”〔7〕依照王弼所说,五千言的《老子》其实说的就是一个主要意思——崇本息末。本是什么?本就是“道”,即自然无为,崇本就是遵循“道”。末是什么?就是与“道”(自然无为)相对立的经验世界中人为行为或者人为事物,比如儒家所倡导的仁义。可见,《老子》一书的主题和宗旨就是言“道”,书中也正是以对“道”的探讨为逻辑起点展开其对宇宙人生等全部哲学问题的论述。那么何谓“道”呢?或者说“道”究竟是何物呢?
“道”的原始意义是路,本义是人所行走之路。《说文解字》:“道,所行道也……一达谓之道。”〔8〕由此来看,“道”也就是人行走活动中的路,从行走活动本身即现象学所说的事情本身而言,“道”是形而上的,处于人所经验意识之外。随后,人们将行走之后产生的路对象化、意识化,即由动词的“道”到名词的“道”,从而形成抽象的观念——“道”。朱熹讲“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9〕,也有此意。“道”作为老子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则具有更多的哲学内涵,至少有三层含义:本体论意义上的“道”、生成论意义上的“道”和作为行为原则的“道”。下面,结合兵学具体论之。
(二)本体的“道”与兵学
“道”是老子哲学中的本体,那么其性质和作用就相当于后来程朱理学中的“理”。在先秦哲学中,并没有“理”的哲学概念,但并非没有“理”的内涵。“道”这一概念就包含“理”的内涵。在程朱理学中,“理”是人类理性的一个预设,在经验世界中“与物无对”,是一种超验的、抽象的、绝对实在。那么,作为本体的“道”(理)有哪些性质呢?
首先,“道”是“与物相对”的“无”,“道”具有不可言说性。《老子》开篇即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可见,“道”具有不可言说性,这里指的是不可“道”之“常道”,“常道”也就是本体意义上的“道”,也就是王弼所说的“无”,“无”即“道”。在王弼看来,“道”在经验世界中并没有具体的形象可以感知,是无法用语言来诉说和描述的。王弼认为任何语言和文字都具有确定性和指称性,一旦对其赋予名称,就指向了具体形体的意义,都只会偏向一极,便立刻破坏了其绝对性、无限性及圆满性。老子将其称之为道、玄、微、远、大,都只是从某一方面来描述作为本体的“道”某一方面的特性。因此,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说:“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10〕由此来看,老子所言的本体之“道”,是不可以用言语文字来表述的,在经验世界中并没有具体事物与之相对。所以,王弼将之称为“无名”更加合适。
其次,“道”是超越现象和具体事物的实在,“道”还具有先验性。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一章》)老子的“道”是浑然不可得而知的,但并非不存在。万事万物因“道”而存在,道是经验世界中各种现象和万事万物的始和母。或者说,“道”是万事万物的生存根据,我们所看到事事物物活动背后的指向就是“道”,现象只不过是“道”的呈现而已。
再次,“道”具有抽象性。老子说:“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老子·十四章》)这是说,“道”不可感性直观。正是因为“道”是超验的抽象之物,因此是无形无象,不可直接经验直观的。亦即在经验层面,人无法通过耳眼鼻舌身来获取“道”的材料,即康德哲学认为感性无法直观“道”,唯有通过人的理性才可以把握,所以老子称为“恍惚”。
由此来看,“道”的性质完全符合“理”的性质,“道”即“理”。作为理的一面来说,“道”是经验世界中万事万物存在的依据,是事物生存和活动的客观法则,即经验世界中的一切事物及其行为存在的合法性就在于“道”。反之,不符合“道”的,就是不合理的存在,也就丧失了存在的本体依据,必然走向灭亡。作为本体的“道”与兵学有什么关系呢?老子思想中的兵学是否符合“道”呢?
从本体之“道”来看,战争是非法存在的,不为“道”(理)所规范。老子直接指出战争是与“道”相悖之物,有道者不为。老子说: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三十一章》)
老子认为,穷兵黩武之人是不祥的,一切事物都排斥和厌弃这种人,因而符合“道”的人是不会和这种人相处的。兵家和兵学的存在是非法的,其存在并不依据“道”(理)而存在。从现实层面来看,用兵和兵者都是与代表“道”的君子相对立的,符合“道”、代表“道”的“有道者”对兵事采取的是极其厌恶的态度,即使不得不采取用兵行动,最后也是以“丧礼”的方式来对待此事。因此,老子用“不祥”“恶之”“凶事”等大量的否定词来描述“佳兵者”。总之,“佳兵者”站在了“道”的对立面,用兵的行为也失去了“道”(理)的规范,其本身就不具有合法性。
(三)行为准则的“道”与兵学
对人而言,“道”是人的行为准则;对天地万物来说,“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原则。这就意味着人同万物都必然遵循“道”。那么,作为行为准则的“道”是什么呢?老子认为,“道”就是“自然无为”,“自然无为”就是人和万物的行为准则。
对此,老子直截了当地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人的根本大法,是其生存活动必须遵循的客观行为准则,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效法自然。也就是说,人同天地一样都要按照“自然无为”的“道”去行为去活动。王弼对此也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法,谓法则也。人不违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 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道[ 法] 自然,天故资焉。天法于道,地故则焉。地法于天,人故象焉。[王]所以为主,其[主]之者[一]也。〔11〕
在王弼看来,“法”即法则,而“自然无为”就是根本大法。首先,人、地、天、道之间依次相法,这是一个逻辑递进关系,归根到底都要因循自然,不违背自然,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其存在的合法性。其次,所谓“法自然”,即指“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这样方可不违背“自然”,此处的“自然”就是说人的一切生存活动(行为活动)都必须在符合“自然无为”这一大原则下进行,即人的行为准则就是“道”(自然无为),“道”是万事万物生存的一种必然性。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不违背自然,万事万物才能实现自己的本性。由此看来,“道”即自然,自然是对“道”的描述。此外,“无为”也是对“道”的描述,其云:“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三十七章》)
可见,“无为”就是顺应“道”,正因为“无为”,天地万物由之以成,这也就是“无不为”。而人(侯王)所要做的就是“无为”,就是效法“道”。如此一来,自然没有邪念恶欲,天下自定。老子赋予“道”以新的内涵,将“自然无为”视为人和万物的本性,人的本质生存状态就是“自然无为”的状态,人所要做的就是抱朴归真以至于“自然无为”。如果背“道”而行,那么将会招致严重的后果。“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老子·三十九章》)这些都是违背“道”的结果。
作为行为准则的“道”与兵学有什么关系呢?老子思想中的兵学是否符合“自然无为”的行为准则呢?在老子看来,显然不符合。用兵非“无为”而是人为,兵学非自然而是造施。可见,老子言兵的目的是为其“道”服务的,只不过是从反面来论证其“道”之“自然无为”罢了。
虽然从“道”的角度看,老子兵学并不与之相符合,甚至与“道”相悖,那么是否就可以说《老子》一书中不存在兵学?其实不然,《老子》一书五千余言,其中有不少直接谈及兵学的章节。不可否认,老子思想中蕴含着独特的道家兵学思想。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老子谈兵的目的还是论述其“道”之“自然无为”。
二、老子“道”的兵学
老子兵学与兵家、法家、墨家、儒家等兵学思想相比,有其独特的思想魅力。其特点是在反战、反兵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的用兵思想。也就是说,在迫不得已发动战争的情形下,老子强调要在“道”的规范下来用兵,军事行动要符合“道”的行为准则,否则就是非法的。
首先,老子对战争的态度是反战、反兵。春秋时期战争频发,民众饱受战争摧残,“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得胜数”(《墨子·非攻》)。老子早就看到战争的极大破坏性,他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 三十章》)正是基于此,老子坚决反对兵事,认为战争乃“不祥之器”,有道之君不会轻启战端,不会主动选择“兵强天下”;“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老子·四十六章》)。在老子看来,战争和用兵不仅是一种非自然的人为干预,更是一种妄为,与“自然无为”之道背道而驰,与个体生命的自然长生截然相反,这是老子所不能允许的。
其次,老子坚持“自然无为”的用兵原则。“自然无为”(道)是老子哲学中的根本行为准则,或者说是事物的生存方式。老子谈论兵学也是为了要证明任何事物都要在这一根本准则下去行为。“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三十六章》)老子认为要除暴消乱,就要因物之性、顺其自然,就会达到不攻自破、不战而胜的神奇效果。王弼在《老子道德经注》中更加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将欲除强梁、去暴乱,当以此四者。因物之性,令其自戮,不假刑为大,以除将物也,故曰‘微明’也。”〔12〕要想避免战乱,就要顺应事物的自然本性,因势利导,“强梁”“暴乱”自会不攻自破,“不战屈人之兵”的神奇妙用自会实现。由此看来,老子虽然谈兵,但是他追求的是一种自然的威慑力,在遵循“自然无为”的前提下,达到兵不血刃的效果,这是一种“无兵胜有兵”的自然而然的理念,也是老子不争而胜的兵学战略。“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八章》)老子以水喻“道”,水是最接近于其“道”的,水的特征就是柔弱不争。在用兵方面,老子认为将帅在领兵打仗过程中,要像水一样“不争而善胜”,或以退为进,或以守为攻,总之不主动用兵。“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老子·六十八章》)善于领兵作战的统帅不主动侵犯别人,后而不先,故不会被激怒,只有不争才会战胜敌人。“不争”就是老子的无为之道在领兵作战中的具体体现,主动的争夺就是人为、妄为,与“自然无为”之道相矛盾。
在“道”的行为原则下,老子指出兵者的特征是柔弱,柔弱是“自然无为”之道的一种具体体现。他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章》)万物生来就是柔弱的,这是万物自然禀赋的本性,柔弱意味着生。生死两个极端状态的体现就是柔弱和坚强,柔弱代表着万物的生存状态,而坚强则代表着万物的死亡状态。老子最终追求的就是以自然的方式活着,也就是说自己的生存不受外力和人为的干预。所以,老子反复强调柔弱胜刚强的道理,体现在用兵之道上:“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强大处下,柔弱处上。”(《老子·七十六章》)万物之中最能体现出柔弱的莫过于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七十八章》)老子以水为喻,点出了水就是“道”在经验世界的最好体现。相反,兵强士勇则是至刚至强的体现,柔弱则生则寿,刚强则死则夭,“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老子·七十三章》),用兵逞强、士卒好勇,必败无疑。
再次,“以奇用兵”并非老子兵学。学界有些学者认为老子兵学思想的一大创新是“以奇用兵”〔13〕。其实不然,老子对“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是持反对态度的。在国家的治理中,老子反复强调君主要始终把持“自然无为”之道,“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三章》),不要一丝一毫的人为造施。具体来看,“正”借“政”,指的是刑名政术;奇,王弼解释为“诡异乱群”。“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老子·五十七章》),意思是君主以“道”治国则国治,以刑名法术等人为的政治行为去治理国家必然导致奇兵兴起,而只有“以无为为居,以不言为教”〔14〕才能取得天下。所以,老子所说的“以奇用兵”的意思是非以“道”用兵,奇与“道”相反,是一种错误的用兵思路。
总之,老子兵学思想为道家兵学涂上了极具特色的一笔,在先秦百家论兵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老子言兵而意不在兵,在于论“道”之自然无为。
三、老子的人生追求与兵学
“道”在老子哲学中意义非凡,既是万事万物的本体(理),也是万事万物的行为准则,落实在个体生命上,就是天长地久,与天地同寿,这也是老子在现实层面上的个人追求。或者说,人按照“道”去生存的目的就是自然长寿,即不以“生生之厚”刻意追求个人生存的自然长生。
老子说:“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老子·七章》)老子认为,天地是永恒存在的。而天地之所以能永恒存在,是因为它们的一切运作、变化都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作为,正因为“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地生养万物而独不生自己,反而得到了长生。这其实也正是“道”之自然无为的体现。所以,老子认为圣人(道家意义上符合自然无为的圣人)也应该如此,无为,不争,不去主动追求生命的长存,这样方可自然长生。所以,老子又说:“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老子·七十五章》)自然长生的圣人也就是“善摄生者”。
兵者与老子的长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老子说:“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老子·五十章》)在此,我们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带来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主动人为地去追求“生生之厚”,反而造成短寿甚至死亡的结果;反之,不主动人为地自然而然地生存,却成就了长生。没有兵戎相见的危害、没有野兽的侵害、没有兵器的伤害,自然也就实现了个体生命的长寿长久。在这个意义上,战争和兵事明显是与老子的人生追求背离的,用兵带来的结果恰恰是人为地去伤害个体生命,甚至导致无数生命死亡。这是老子所不能允许的,老子言“入军不被甲兵”“兵无所容其刃”正是要说明这一点。
结论
老子以“道”立论,构建了一个理论体系,“道”既是万事万物的存在依据,更是其生存的行为准则,还是其对一切事物及其行为的评判准则。符合“道”的就是合法的,凡是与“道”相违背的就应该“弃之如敝履”。作为形而上的绝对存在,无论是王侯、圣人还是民,其存在和行为的依据都应该是“道”。老子的兵学也是“道”的反面论证。在兵学思想上,一方面,人为的兵事与老子所崇尚的自然无为的“道”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另一方面,老子的终极追求是“无以生为生”的个体生命的自然长生,破坏力极大的兵事会对人的生命造成最为致命的伤害,这与老子的终极目的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兵家之事不为老子所容。《老子》一书虽然包含独特且丰富的兵学思想,但并不能说其是兵书,从其立论宗旨来看,它还是一部哲学著作。老子论兵在意不在兵,目的是以兵为喻,就像以水为喻一样,其意在于强调道之自然无为,这才是《老子》一书的根本。
——刘家文
——徐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