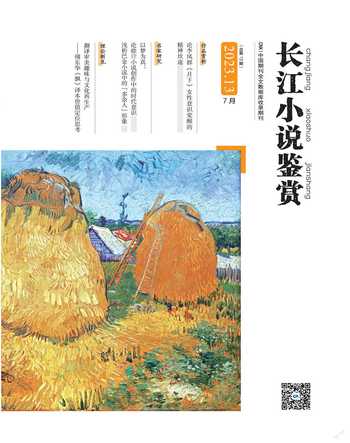魏晋六朝小说中人神恋与人鬼恋的异同
[摘 要] 异类姻缘故事在魏晋南北朝特殊的社会文化土壤下葳蕤滋长、枝繁叶茂,魏晋六朝不仅是人鬼恋故事的发轫时期,而且沿袭着神话传统的人神恋故事在这一时期也大放异彩。二者在故事发源、情感意蕴、宗教影响等方面有其同质性,也有显著的不同之处,探究此问题对研究魏晋六朝时期社会状态、文化内涵、心理意识等方面具有一定意义。
[关键词] 人神恋 人鬼恋 比较异同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13-0078-05
魏晋南北朝时期,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志怪小说难登大雅之堂被排斥在主流文体之外,但正因此,其受到附加的雕琢修饰较少,在反映魏晋时期人们纯粹质朴、隐秘而真实的内心世界上有天然优势,而志怪小说中的异类婚恋故事更将这种心理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学界在异类婚恋故事的研究中,对人神恋与人鬼恋两种故事类型多有着墨,却对二者之异同少有系统详尽的论述,从多方面论述人神恋与人鬼恋的异同也是对魏晋时期社会关系与心理情感进行全新而又深入的诠释。
一、渊源肇始:神话传统与社会风气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魏晋六朝志怪小说发源时便谈道:“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1]由此可见,魏晋六朝志怪小说中离奇荒诞的情节内容不仅肇始于当时社会生活的纷繁多面,也与历史经验下神话传统的沉淀绵延有着密切联系。
1.人神与人鬼恋发源相同之处——神话、巫风祭祀
《周易·说卦传》有云:“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2]人与神相结合的观念存在于蒙昧时期古代先民崇敬自然寻觅未知的集体意识中,如《诗经》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远古感生神话,此时的神人形象大都隐喻为男子,且人神之间并无情感依托,而后在《楚辞·九歌》中“神”的形象完成了由男子向“神女”的转变,并且人与神之间别有一番“留灵修兮憺忘归”“怨公子兮怅忘归”的幽怨缠绵之情。以此为蓝本,后世相继出现形形色色遍布于诗赋小说中的人神恋题材,经过种种流变,至魏晋时期此类题材已“涉情涉性”趋于成熟,为魏晋志怪小说中的主要类型。人神恋以其独特的发展脉络与结构模式,成为经久不衰的文学传统。
而同为非常规婚恋的人鬼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人神恋的影响,刘守华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就认为“人鬼夫妻”型故事应与人与仙侣婚恋以及其他异类婚恋故事相关联[3]。在诸多文学作品与日常生活中,“鬼神”也通常合称为一词,鬼与神的指意有了重叠,对死去魂灵的“祖先崇拜”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是另一种形式的“神灵崇拜”。但无论是人神恋还是人鬼恋都沉酣着神话色彩,都表现出神话“泛灵”的特点,体现出先民对人与自然的混沌认知。茅盾在《神话研究》中认为:“神话中包含初民的宇宙观、宗教思想、道德标准、对于自然万物的认知和民族历史最初期的传说等。”[4]早在《周易·乾卦》中便有:“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2]诸多儒家经典指出“鬼神”这一概念与自然息息相关。蔡根堂在《中国文化中的人神恋》中对人与神之间关系广义定论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神恋”中的“神”包括神、仙、鬼、怪,完全来源于自然物,是自然物的幻化或者说精神存在,神、仙、鬼都是一种超人的存在[5]。
人与自然之间“天人沟通”的联结还体现在先人祭祀上,尤其是楚地巫风祭祀,《汉书·武五子传》言:“而楚地巫鬼……使下神祝诅。”[6]与面朝黄土背朝天以农耕为主的中原地区不同,楚地地貌复杂,多山川湖泊云梦大泽,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楚地民众选择了效益更高的渔猎生活,但渔猎生活极不可控,这种难以凭经验估测的不可控状态延展为楚地百姓的命运观念与生命意识,祈求顺遂的巫风祭祀也就应运而生,而祭祀中人神结合的形式以及上古祭祀场地——水边,都在后世魏晋时期人神恋抑或是人鬼恋中能够窥见一隅。如人神恋代表作《幽明录·河伯女》:“阳羨县小吏吴龛,有主人在溪南。尝以一曰乘掘头舟过水,溪内忽见一五色浮石,取内床头。至夜,化成女子,自称是河伯女。”还有人鬼恋代表作《搜神后记·张姑子》:“行至一溪,日欲暮,见少年女子,采衣,甚端正。”两者故事发生的场所都是在水边,这种高度相似的巧合并不是個例,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巫风祭祀的影响。
2.人神与人鬼恋发源不同之处——隐逸风气、社会风俗
2.1隐逸风气影响下的人神恋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乱世,朝代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堪,身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普罗大众对安稳平和的生活也就更加向往,生命的易逝与脆弱让人们纷纷想要逃避现实的苦痛去往彼岸世界以求精神上的安宁。当时玄道神仙思想昌炽,求仙问道隐逸之风大行其道,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作为体现隐逸之风的典型代表作,在国人心中建造了一座纯粹浪漫的东方式乌托邦,“桃花源”也随之成为人们精神乐园的代名词。而进入“桃花源”的媒介便是洞窟,“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可见“洞窟”意象在某种程度上潜藏着“隐逸”这一深层文化内涵,洪树华就曾以原型理论来解读“洞穴仙境”所蕴藏的我国古人集体无意识中对大同世界的渴求心理。相应的,魏晋六朝志怪小说中多有洞窟故事便是时代隐逸风气盛行的表现,李剑国在《唐前志怪小说辑释》中说:“六朝洞窟传说极多,大抵事关神仙或隐者。”[7]
受此风气影响,魏晋志怪六朝小说中的人神恋也多次出现洞窟意象,如《幽明录·黄原》中“……行数里,至一穴,入百余步,忽有平原……”,以及《搜神后记·袁相根硕》:“……羊径有山穴,如门,豁然而过。”
2.2社会风俗影响下的人鬼恋
与受神仙思想影响颇深的人神恋相比,人鬼恋的世俗化程度更为显著。
魏晋时期“鬼道愈炽”大谈神鬼,因乱世中人命如草芥,尤其是那些极易凋零丧命的弱女子。苟延残喘的生者带着现世的祈愿对死后的世界充满了凄美幽迷的幻想,催化了人鬼恋模式的发展。日本学者繁原央认为中国古籍中某些以人鬼恋为题材的故事“大多与幽灵相关,均取死女与生男相交往的形式”[10],《搜神后记》中《徐玄方女》《卢充》等篇,都是女鬼与凡间男子结合后产下子嗣的“立嗣型”模式。
二、情感投射:悲剧意蕴与世俗化表现
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升华。魏晋六朝志怪小说中的异类婚恋故事必定是当时人们生活的曲折反映和情感的真实表达,它们有同质的悲剧意蕴和不同的世俗化表现,但二者皆为当时志怪小说创作者,即乱世中一批底层文人的情感投射。
1.相同的悲剧意蕴
长期战乱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最痛苦的时代,几百年动荡不断,各种社会矛盾交织,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正如曹操《蒿里行》中所描述的那般,“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相应的,带有深刻时代烙印的悲哀和伤痛之感自然氤氲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而荒诞离奇外壳包裹下的魏晋六朝志怪小说便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深沉的悲剧意蕴,因此无论是人神恋或是人鬼恋,其悲剧意蕴的形成基础都是相似的。
首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殊的门阀士族制度所造成的悲剧。这一时期“世代簪缨”的门阀士族采用九品中正制操控了官吏选拔,不以才能为标准,而是更看重身份地位门第高低,《全唐文》中有记载:“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矣。”[11]这种世袭垄断阻绝了无权无势的普通文人的晋升之路,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使“洛阳纸贵”的一代文学家左思发出“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之苦闷感慨!这种现象在魏晋六朝志怪小说中同样有所体现,由于门阀制度森严,各大士族之间通过姻亲联结,也就形成了严禁士族与庶族通婚的规定,因此底层文人只能徜徉在幻想世界里通过文学创作来跨越这难以逾越的鸿沟。志怪小说中平民男子与代表高门的“仙女”或“高门鬼女”成婚进入高门实现阶级跨越,如《搜神记·卢充》中,卢充追獐至一高门瓦屋,高官崔少府将自己早夭的女儿嫁给他并为其孕子,最终“儿遂成令器,历郡守二千石。子孙冠盖,相承至今”。
其次是男女性压抑下的悲剧意蕴。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创作者大都是寒门庶族男性作者,而这一群体在门阀士族社会制度的压迫下无缘攀结上层阶级,现实的缺憾便以白日梦式的文艺创作来补偿心理诉求,无论是人神恋中的“神女降临”还是人鬼恋中的“自荐枕席”,这种“奔女情结”表现了他们寄希望于神异力量以求改变人生命运。这也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观点相吻合,他在《作家与白日梦》中认为文学作品和白日梦都代表着那些现实未曾满足的愿望,而创造型作家写出的文学作品就是白日梦的衍生物,文学作品是改装后的白日梦。而志怪小说中大胆追爱的神女或鬼女是魏晋时期女性思想解放、反叛封建压迫、追求自身幸福的观照。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人格极度自由张扬的时代,社会动乱礼制崩坏,礼法对女性的束缚有所松动,过往女性作为父权夫权下的附庸无法左右自己的婚姻,长久的性压抑使女性更加渴望真正的幸福。但女性意识逐渐觉醒后,反叛抗争并追求世俗爱情便是她们努力挣脱命运悲剧的开端。
最后是生命意识高涨背后所潜藏的悲剧意蕴。“乱世的杀夺,生命的无常,使得魏晋南北朝人的生命意识陷入执着与颓唐”[12],长久的动乱,生命的脆弱,使人们的心灵世界也难以安定,无数文人志士不断思考着生命的意义。“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志怪小说的人神恋常常出现“长生”意象,如《幽明录·刘晨阮肇》中主人公与仙女分别从仙境回归人间后,才发现“到乡翻似烂柯人”,人间已过七代,他们获得了长生。而人鬼恋中常常出现“复活”意象,如《搜神记·河间男女》中女主人公因无法与心爱之人成婚忧心而死,从军而归悲痛欲绝的男主人公发塚开棺后,女子竟死而复苏。可以明确的是,无论是“长生”还是“复活”意象,这背后都是魏晋六朝时期人们眷恋生命的生命意识的体现。
2.不同的世俗化表现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虽然只是小说发展的初始阶段,但大体故事情节、人物特色已见雏形,有其自身的丰富性和特殊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小说的世俗化意义,反映世间百态,比如其中的人神恋、人鬼恋等异类婚姻故事虽然都有世俗化内容的体现,但表现程度却有所差异。
人神恋中的神女不同于人鬼恋中的鬼女,神女有其矜貴庄严的神性,且少自荐枕席,大都是男子意外误入异界与神女相遇,即便有神女自降的情节,神女一旦被发现身份便会决然离去或给予惩罚,不如鬼女那般无怨无悔情感强烈。而故事发生的场所虽也偶有人鬼恋般的凡尘景象,如《白水素女》中的神女为谢端“守舍饮烹”,但大多数故事都发生在“桃花源式”的仙境,如《黄原》《袁相根硕》都是凡人误入平和美好的异界。
再者,人神恋与人鬼恋在“生子”方面也呈现出不同的世俗化程度。魏晋南北朝时期普遍存在“女神崇拜”情结,女神地位要高于凡人,人神结合之后几乎不存在生子情节。而人鬼恋却多有生子情节,如《列异传·谈生》中书生谈生耽于读书四十岁还未娶妻,夜半有美貌的妙龄女子与其结合并生下子嗣;《徐玄方女》中徐玄女托梦马子求他助其复活,徐玄女死而复生后与马子结为夫妇并生二男一女。中国民间观念中的生殖崇拜认为“没有完成生殖义务的人生是不完善、不正常的人生,死后也不能做一个‘正常的鬼”,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生殖繁衍后代却可以作为一种生命的延续,魏晋六朝又是一个自觉探索超越生死之法的时代,极力渲染人间世情、贴近真实社会生活的人鬼恋自然不可避免地对“鬼女复活生子”进行戏剧化叙述。
三、阴阳观念与佛教影响
李剑国先生在《唐前志怪小说史》中有论言:“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达到繁荣,最根本的原因是此时期宗教迷信的昌炽及其影响广泛。”[13]魏晋南北朝时期多教林立的盛观也必然会影响到文学创作,这一时期儒学礼教束缚松动,道家的阴阳观念与佛教东渐对志怪小说的创作具有更重要的影响。
1.非正常婚恋中的阴阳观念
《周易·说卦》中论言:“立天之道,曰阴与阳。”[2]无论在儒家还是道家学说中,阴阳这一哲学观念都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张力,作为中国文化哲学的基础,阴阳观念的发展完善对凝聚文化内核、探寻民族原始心理意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内涵的广泛性与包容性使社会生活中众多关系都可以统筹纳入这一结构。异类婚恋中的角色大都是凡间男子与神异女性,在中国传统阴阳观念中,男人属阳,女人属阴,人类属阳,神鬼万物属阴[5],神异的女性则更是具有双重阴性性质。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人神恋与人鬼恋中的阴阳观念除了展现在人与神鬼身份差异、故事发生场所环境的变化上,还体现在跨越阴阳的赠物母题上。异类婚恋故事中多有“赠物”情节,使故事发展至高潮,在某种程度上也暗示着神女或鬼女以信物作为媒介打破阴阳之隔,使本来贫穷潦倒的凡间男子或求得升仙长生或求得功成名就,如《搜神后记·袁相根硕》一文中神女在根硕离开之前“乃以一腕囊与根”,故事结尾根硕灵魂化为青鸟脱离皮囊获得长生。
2.佛教对其不同程度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在魏晋南北朝发展成重要社会思潮,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也指出:“还有一种助六朝人志怪思想发达的,便是印度思想之输入。因为晋宋齐梁四朝,佛教大行,当时所译的佛经很多,而同时鬼神奇异之谈也杂出,所以当时合中印两国底鬼怪到小说里,使它更加发达起来。”[14]
佛教中的时空观认为时间是一种错觉以及时间是非线性的,《华严经》中有言:“三世一切说,菩萨分别知,过去是未来,未来是过去,现在是去来,菩萨悉了知。”“一念普观无量劫,无去无来亦无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诸方便成十力。”[15]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时空观融入志怪小说之中,人神恋《刘晨阮肇》故事结尾:“既出,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复相识。问讯得七世孙,传闻上世入山,迷不得归。”除此之外,文中“君已来是,宿福所牵,何复欲还耶?”与《黄原》中“有一女,年已弱?,冥数应为君妇”“宿福”“冥数”都是佛教解释因缘之概念,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佛教对人神恋的影响[17]。
但佛教对魏晋六朝时期人鬼恋的影响比较有限,佛教死而复生、地狱论等教义早在先秦文献记载中已不算罕见,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丹》便是复生志怪故事的滥觞,《楚辞》中“魂兮歸来,君无下此幽都些”更是已有阴间地府“幽都”的概念。因此可以说,佛教对人鬼恋故事的影响相对有限。
四、结语
魏晋六朝志怪小说中的人鬼恋受到人神恋的影响,二者都可溯源至前代的神话与巫风祭祀传统,但当时喜隐逸的社会风气又使二者有了截然不同的差异。同样的,在情感投射方面,人神恋与人鬼恋因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性压抑与高涨的生命意识被赋予了相同的悲剧意蕴,但不同的世俗化表现不仅反映出人们对待不同地位女性的态度,也体现出志怪小说这一文体走向世情化的演变方向。至于在宗教因素方面,二者都具有阴阳观念的哲学表达,且都不同程度受到儒释道三家的影响。
魏晋六朝志怪小说是我国古代文学宝库里熠熠生辉的明珠,是时代文学自觉和人的觉醒之产物,郭延礼先生在《中国文学精神》中谈道:“志怪小说是一种复杂的文学现象,从人类的心理需求看,鬼神怪异是人性的深层渴求……以缓解现实生活精神压力和焦虑,化解命运带给生命的痛苦和迷惑。”[18]可以说,荒诞志怪本质便是在融入艺术表现力后的社会现实,因此比较解读人神恋与人鬼恋之异同不仅对阐释异类婚恋故事的人文内涵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对研究魏晋南北朝社会现实生活同样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 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 茅盾.神话研究[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
[5] 蔡堂根.中国文化中的人神恋[D].杭州:浙江大学,2004.
[6]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7]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辑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8] 姚彦琳.中国冥婚习俗研究综述[J].民俗研究,2016(1).
[9] 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76.
[10] 繁原央,白庚胜.中国冥婚故事的两种类型[J].民间文学论坛,1996(2).
[11] 柳芳.姓系论[M]//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2013.
[12] 段章平.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悲剧意蕴分析[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9.
[13]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14] 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5] 大方广佛华严经[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9.
[16] 陈世忠.科学、哲学与佛学的时间、空间、物质观[M]//闽南佛学(第六辑).北京:宗教文学出版社,2009.
[17] 傅一岑.魏晋志怪小说中的“宗教观”——人、神、鬼[J].文教资料,2012(26).
[18] 郭延礼.中国文学精神[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夏 波)
作者简介:王艺衡,天水师范学院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