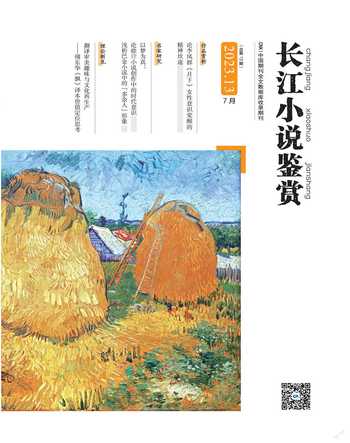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浅析《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中女性的生存困境与成长
张玉娟 胡戈
[摘 要]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是塔拉·韦斯特弗创作的自传体小说,该小说基于塔拉个人的成长经历,描述了家庭、社会与个人成长之间的内在联系,其中的女性生存困境与自我救赎主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本文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全面剖析《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指出小说中父权专制是导致女性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阐述女性应通过对抗父权和接受教育走出困境,实现自我救赎与身份重构。
[关键词] 生态女性主义 生存困境 自我救赎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13-0045-04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讲述的是女孩塔拉的故事。塔拉来自美国爱达荷州的大山里,她通过教育摆脱原生家庭的伤害与束缚,在对过去的不断反思中将自己抽离出来,实现了自我救赎与精神解放。在塔拉的成长过程中,原生家庭就像一座大山,困住她的同时也给她带来不可磨灭的伤害:父亲吉恩与哥哥肖恩是主要的加害者,母亲的懦弱与姐姐奥黛丽的妥协则助长了父兄的嚣张气焰。深受父权专制的压迫,塔拉身心皆受重创,即便如此,她也没有放弃寻求自我救赎与自我成长的生存之道。本文借助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探讨父权专制压迫下女主人公塔拉及其他女性角色的生存困境,通过对比塔拉与其他女性角色的不同点,探讨女性如何通过自身的力量实现自我的解放。
一、女性与自然
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主义发展衍生的产物,融合了生态与女性的观点,是女性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娃·德·奥博纳(Francoise dEaubonne)在《女性主义或死亡》(Le féminisme ou la Mort)中最先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ecoféminisme)这一术语。生态女性主义批判男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和对自然的剥削,强调两性的平等。伊内斯特拉·金( Ynestra King)在《治愈伤口:女性主义、生态学和自然/文化二元论》中对生态女性主义进行了定义:在生态女性主义中,自然是分析的中心范畴。对自然中相互联系的统治——灵魂与肉欲、人类压迫和非人类自然以及跟这些统治形式相关的女性历史地位的分析构成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出发点。”[1]金的阐述表明,女性与自然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自然不存在等级制度,人类社会的等级制度被强加给自然,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实践反对等级制度,无论是施加在自然还是女性身上的枷锁都应被废除。
生态女性主义主张女性与自然存在更为紧密的联系,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与女性视为“他者”,人类对自然界的主宰和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之间具有本源同构性。生态女性主义者将女性与自然相关联,致力于消解父权专制和人类中心主义,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统一体。
在《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一书中,塔拉将巴克峰以女性的角色呈现在读者眼前,巴克峰又被称作“印第安公主”[2],她威严的身躯为塔拉一家打造了牢固的城堡,更阻断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执着于为世界末日降临做准备的吉恩,以此为借口向“印第安公主”[2]疯狂索取,屯粮、挖地洞、开水源、焚烧废弃材料……自然沉默不语,就像母亲包容叛逆的孩子一般。“那是无边无际的静谧,使人沉静,在它的广袤面前人类显得微不足道”[2],塔拉在书中如是形容巴克峰。
塔拉在书中将巴克峰视为人格化主体,而非從属人类的附属品。对巴克峰的描写大多具有诗情画意,错落有致的田野,绿意盎然的植被。塔拉被山间的节律养育,在四季与昼夜的轮回中与巴克峰共生。在开启新生活后,塔拉再一次回到巴克峰,“我一直对公主念念不忘。在大洋彼岸我听到她的呼唤,仿佛我是她牧群中一头离群的恼人的小牛犊……我背叛了她,我想象着她的脸因愤怒而扭曲,她的姿态因沉重而充满威胁……”[2]巴克峰对于塔拉而言更像是一位慈爱的母亲,无论塔拉身在异国他乡抑或大洋彼岸,亲情的召唤从未停止,塔拉将对于亲情的渴望寄托在巴克峰身上,以消解疏离亲人的愧疚和失落。但塔拉也意识到,真正热爱孩子的母亲是不会抛弃自己的,“我意识到自己误会了她,她并未因我的离开而生气……她的角色不是圈养野牛,不是动用武力将他们聚拢起来,加以限制,而是为他们的归来而庆祝。”[2]塔拉在与自然的互动中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和归属,领悟了亲情的真谛,即爱是令其自由而非禁锢,逐渐驱散原生家庭带来的阴霾,实现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
二、父权专制对女性和自然的迫害
波伏娃在其女性主义代表作《第二性》中指出,“女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比女人同所有权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母系制度的特征在于,女人的的确确被大地所同化”[3],并且运用游牧民族对于生育的看法进一步表明,“整个自然仿佛是一个母亲:土地即女人,而且和大地一样,女人身上也有那种神秘的魔力。”[3]弗朗索娃·德·奥博纳认为,女性所受到的压迫与自然所受到的压迫有本质性的联系。在《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中,以巴克峰为代表的大自然被父亲吉恩称为“印第安公主”[2],关于“印第安公主”的描述也是带有女性色彩的:“从远处,你可以看到一个女人的身形在山体正面显现:巨大的峡谷构成她的双腿,北部山脊扇形散布的松林是她的秀发。”[2]这暗示了具有女性色彩的巴克峰同样处于父亲吉恩的控制之下,“山上的生活给人一种至高无上之感,一种遗世独立,甚至统治之感。”[2]吉恩及其妻子是虔诚的摩门教徒,他终日奔波于废料厂和为末日降临做准备,废料厂的存在无疑是对生态环境的一大威胁,“院子正中央是大片成堆的残骸:泄露的汽车电池、缠绕的绝缘铜线……”[2]为了确保在世界末日降临之际,整个家庭已做好充足的物资准备,吉恩疯狂地掠夺与开发巴克峰:焚烧铜线绝缘层,引爆油箱,为开辟水源垦地伐树……他打着“自力更生”的旗号剥削自然,实际上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和证明自己对巴克峰的绝对主宰。
在父亲吉恩这样一个激进的摩门教徒看来,女人的位置是在家里。他反对政府和公共教育,并声称公立学校是政府引导孩子远离上帝的阴谋,孩子们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受伤或生病只能在家就医,甚至七个孩子当中有四个没有出生证明,塔拉便是其中之一。在《第二性》中,波伏娃提出了女性“他者”[3]的概念,即“男性在两性关系中居于主体地位,而女性则处于客体和他者地位”[3]。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论妇女的屈从地位》中指出,“妇女从属于男人是个普遍的习惯,任何背离这种习惯就自然地显得不自然。”[4]塔拉及家中其他女性均被看作是吉恩的附属品,塔拉作为家中最小的女儿,被父亲强制要求加入废料厂的拆解小工队。父亲无视废料拆解工作中隐藏的巨大风险以及塔拉作为未成年女性的弱小无力,拒绝让塔拉佩戴安全帽和皮手套,导致塔拉在废料厂频频受伤。吉恩的父权操纵还体现在对妻子法耶的控制,为了赚取更多的物质财富和实现自力更生,吉恩强迫妻子成为助产士,即便她饱受煎熬也没有违背丈夫的意愿。“母亲常把自己描述成一个讨好者,说她无法阻止自己去猜测别人想要她成为什么样的人,也无法阻止自己极不情愿地强迫自己做出改变。”[2]法耶对丈夫的屈从使她完全丧失自主性和独立性,在吉恩对孩子们进行布道和说教时,法耶会在一旁附和丈夫。
实施父权压迫的并非吉恩一人,患有精神疾病的肖恩继承了父亲的偏执,对妹妹奥黛丽和塔拉以及女友埃米莉都曾施加过暴力,其中塔拉備受其害。肖恩反复无常的情绪时常将塔拉拖入暴力和恐怖的地狱,塔拉被冠以各种带有讽刺性的外号:黑鬼、婊子、鱼眼睛……肖恩曾威胁塔拉要将其杀死。无数的暴力场景使得塔拉常常陷入梦魇的折磨和回忆的侵扰,而母亲的无视与无能更助长了肖恩的嚣张气焰,这给塔拉带来双重的身心重创,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塔拉仍无法摆脱父亲和肖恩的阴影,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可见父权专制与压迫对女性的侵害性质之恶劣,影响之深远。
三、对父权的屈从与抗争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论妇女的屈从地位》中指出,“出于种种社会的和自然的原因,使妇女不大可能集体地造男人权力的反,她们仍处于不同于其他从属门类的地位,她们的主人要求她们的,有比实际服务更多的东西。男人并不只是需要女人顺从,他们还需要她们的感情。女性对男性的屈从,靠的是畏惧,或是对他们自己的畏惧,或是对宗教的畏惧。”[4]法耶和奥黛丽屈从于吉恩的父权操纵,即便产生过瞬间的抗争念头,最终还是选择了投降和屈从。她们长期受控于父权压迫,没有独立的话语权和自主意识,走出“舒适区”会让她们失去归属感,变得无所适从,所以,依附吉恩所谓的强大力量,她们才能在心灵上得到庇护,成为家庭的一部分。
法耶不顾家人的反对与吉恩订婚,渐渐地,法耶与原生家庭切断联系,封闭在幻觉和偏执筑起的高墙里。法耶依照丈夫吉恩的意愿成为助产士,随着其事业的不断发展,法耶的自主性似乎在一步步加强:她开始要求在家里安一部电话;向政府部门申请孩子的出生证明;允许孩子在家里“上学”……法耶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看似在加强,却始终局限在吉恩操纵的范围之内,孩子们“上学”的前提是完成父亲分配的活儿,法耶在这场战斗中始终属于战败方。法耶完全遵从吉恩的宗教信仰,配合摩门教徒的意志和信念,彻底沦为丈夫的附属品和被操控的对象。在明知肖恩患有精神疾病的情况下,法耶在目睹肖恩对塔拉实施暴力的场景时选择沉默和无视正说明了法耶作为男权政治的附属品的软弱与无能,甚至在面对塔拉与父亲吉恩的父女关系即将破裂的情形时,作为母亲的法耶选择站在了女儿塔拉的对立面,与丈夫一起对抗女儿塔拉。相比于母亲这个身份,法耶更愿意遵循作为妻子的义务。法耶借助自然的力量发展精油事业取得巨大的成功,但事业上的成功并未帮助她摆脱和逃离丈夫的控制,自然受控于父权力量,作为女性的法耶同样如此。奥黛丽作为父权压迫的受害者,同样选择了屈服。她曾经试图联合塔拉揭露肖恩的躁郁症对其造成的伤害,却在最后关头背叛塔拉,选择站在父亲一边。法耶和奥黛丽都是父权压迫的受害者和服从者,面对父权压制的社会生态,她们选择沉默和屈从,父权是她们普遍认可的准则,只要遵从吉恩的意志,她们就能“心安理得”地在这个家生存,她们不具备摆脱牢笼的勇气和力量,沉沦是她们的最佳选择,而这种选择只会让她们陷入更深的泥沼之中,无法自拔。
塔拉完全不同于母亲法耶和姐姐奥黛丽,进入杨百翰大学学习是她抗争的开端。通过教育,她领略到更多巴克峰以外的世界,同时在父亲精神操控的影响之下,新世界与旧世界的矛盾冲突使得塔拉陷入深度的自我怀疑。幸运的是,凭借着强大的精神意志和不断增长的知识,塔拉意识到父亲和肖恩的操控给她带来的伤害,在强大意志力的支撑下,塔拉逐步切断与原生家庭的联系,摆脱原生家庭的控制和束缚,通过教育不断实现自我身份的重构,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和救赎。
四、塔拉的精神觉醒与自我救赎
女性摆脱男权的压迫和操纵,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意志力。教育为塔拉打开通向新世界之路的大门,在基础心理学的课堂上,塔拉第一次接触“双相情感障碍”这个术语并将其描述的症状与父亲联系起来,在听到关于得克萨斯州的韦科事件以及爱达荷州的鲁比山事件时,塔拉将自己搜集到的资料与先前父亲陈述的所谓“事实”联系起来,发现父亲出于强调政府阴谋的目的,向孩子们讲述他编造的故事,进而巩固他筑起的与政府相对抗的城池堡垒。“我们一直生活在一种警觉的状态和持续的恐惧之中,我们的大脑充斥着皮质醇,因为我们知道哪些事情随时可能发生。因为爸爸总是把信念置于安全之前……他仍坚持相信自己是对的。付出代价的是我们。”[2]塔拉第一次意识到父亲的权威来源于他虚构的事实,思考其行为所造成的不可弥补的伤害,塔拉开始尝试过正常人的生活,这是她觉醒的第一步。在学习到关于奴隶制和大屠杀的知识后,塔拉开始意识到过去肖恩那带有讽刺意味的“黑鬼”昵称于她而言意味着什么。随着知识的不断增长和视野的不断拓宽,在克里博士、斯坦伯格教授和罗宾等人的帮助下,塔拉逐渐觉醒,在对过去的反思中,她领悟到父亲教导的历史不是大多数人认同的历史,而她可以构建属于自己的世界,由她独立书写历史。
塔拉在追求思想解放的过程中不仅受困于精神层面的矛盾,还深受完全不同于她先前被教导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的冲击。在与室友相处的过程中,塔拉才意识到正常人的生活与她在巴克峰的生活完全不同:生病要去医院并吃药,如厕后要用洗手液洗手,短裙并非意味着“不洁”……塔拉在这些转变中逐渐意识到父亲所教导的偏执理念对她的影响是如此之深,她逐渐开始改变过去的生活方式,尝试适应正常人的生活。
在实现自我解放与救赎的道路上,原生家庭无疑是最大的阻碍。对于塔拉的叛逆,父母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塔拉的逃离超越了他们所能掌控的范围,他们跨越大半个美国来到哈佛,企图通过驱逐塔拉体内的邪魔,使其重新皈依摩門教,顺从他们。塔拉拒绝了。她深知自己所接受的教育不允许她失去对自己思想的掌控权,父亲畸形的神圣权威不过是试图控制塔拉的刑具,她无法接受,更做不到缴械投降。在与父亲的战争中,塔拉赢得了属于自己的胜利,即便后来一段时间里,塔拉深陷与家庭决裂的愧疚之中,但这是她开启人生新篇章的必由之路,她必须做出选择。事实证明,她的抉择是明智的。
五、结语
生态问题与女性话题在当今社会一直热度未减,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析《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中的女性困境与成长,对于探讨当代社会的生态与女性话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追求两性平等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体系是生态女性主义者长期奋斗的目标。本文批判了父权政治对女性和自然的压迫,通过对比女性面对父权专制的不同选择,肯定了教育对于女性实现自我重构和自我救赎的重要意义。塔拉通过自述自己的成长经历给人以启迪:让教育助你一臂之力,使你飞往更远的山。
参考文献
[1] 纪秀明.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回溯、中国经验和叙事启示[J].山东社会科学,2023(2).
[2] 韦斯特弗.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M].任爱红,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9.
[3] 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4] 穆勒.妇女的屈从地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5] Beauvoir D S.The Second Sex[M].London: Vintage Classics,1949.
[6] Tara W.Educated:Memoir[M].New York: Random House,2019.
(特约编辑 张 帆)
作者简介:张玉娟,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通讯作者:胡 戈,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基金项目: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新国标”背景下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体系建设及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2020JGB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