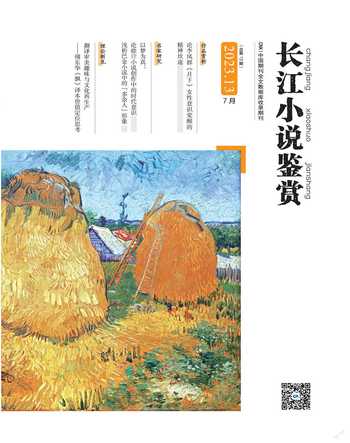浅析巴金小说中的“多余人”形象
[摘 要] 巴金在俄国文学的影响下,目睹了同时代的人的悲剧后,创作了一系列“多余人”形象:接受过良好教育却被封建专制大家庭和旧礼教牵绊的高觉新,无论是爱情还是理想都只停留在高谈阔论中而怯于行动的周如水,被残酷现实磨灭远大志向后苟且偷生的汪文宣等。这些“多余人”是时代的先觉者,但在新旧势力的冲击下,思想与行动的分裂导致他们灵魂逐渐扭曲与异化,只能无奈挣扎于新旧社会的夹缝中,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关键词] 巴金 多余人 人物形象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13-0061-04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巴金曾塑造过一批知识青年形象:他们受到五四新思想的影响,接受过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潮的洗礼,强烈要求个性解放与个体的独立,渴望变革社会,有所作为。但他们所面临的封建势力过于强大,自身性格中的懦弱与妥协无法支撑他们去实现自己的宏伟抱负,他们的命运轨迹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相似。巴金运用高妙的写作技巧将人在困境中的痛苦挣扎以及精神的分裂与异化展现出来,揭露了人性的弱点,这也是高觉新、周如水和汪文宣这些“多余人”的文学价值所在。
一、中国式“多余人”
“多余人”这一文学典型诞生于19世纪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许多作家都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多余人”形象,比如普希金《叶普盖尼·奥涅金》中无所事事、终日游荡的奥涅金,这也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多余人”形象。除此之外,还有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人格分裂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满脑子理想却缺乏行动力的罗亭,以及冈察洛夫笔下因循守旧的奥勃洛摩夫。这些人物形象是当时俄国社会一部分贵族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他们从小生活于优越的环境中,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深刻认识到俄国政府的腐败堕落以及农奴制和专制暴政的落后腐朽,也同情百姓所遭受的苦难,可由于自身所处阶级的局限,所以他们不可能与底层人民为伍来颠覆既有的落后制度,但也不愿违背良心同上流社会沆瀣一气。他们苦闷、彷徨,一辈子庸庸碌碌,空怀理想却缺少行动,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是“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世无损”的“多余人”。这一文学形象并不仅存在于俄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也出现了一系列与之相似的“多余人”形象,如鲁迅先生笔下突破封建礼教后却处处碰壁的涓生与子君,叶圣陶笔下因理想一步步幻灭而绝望病逝的倪焕之,以及巴金《家》中天资聪颖却生性软弱的长子高觉新等。
巴金笔下的“多余人”是接受过新文化洗礼的知识分子,但被旧思想所束缚,于是挣扎于新旧文化之间,在社会转型时期痛苦地生存。他们在传统与现代中徘徊不定,思想和行动的无法统一促使他们成为中国式“多余人”。
二、高觉新:新思潮与旧制度间的徘徊者
在长篇小说《家》中,巴金塑造了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矛盾人物——高觉新。高觉新的悲剧主要来源于封建礼教的迫害和封建家庭的束缚以及自身软弱的性格,他“是一个性格复杂的软弱青年的典型”,“奉行着一种逃避现实、逆来顺受的不抵抗主义和作揖哲学”[1]。他是封建大家庭中的妥协者和牺牲品,是一个能清醒认识自己的悲剧命运却无法反抗的可怜人,是一个接受过五四新思潮熏陶却又向旧思想妥协的“多余人”,从心理层面上深刻反映了知识分子在新旧思想的冲击下以及封建制度崩溃前后的生存状态。巴金的长兄李尧枚是高觉新这一人物形象的原型,一个同样被封建礼教所压迫的“多余人”,巴金在这一形象上寄托着自己对大哥的深厚情感。
正如狄德罗所说:“人物性格要根据他们的处境来决定。”[2]在高家,以高老太爷为代表的旧势力与以高觉民、高觉慧为代表的新力量不断产生冲突。高觉新身为高家的长房长孙,被自己肩负的责任与义务所束缚,自觉地维护着封建大家庭的秩序与体面。在这个新旧势力并存的家庭里,“他被人玩弄着,像一个傀儡;又被人珍爱着,像一个宝贝”。这样矛盾的境况使他的内心倍受煎熬。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风起云涌,民主与科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也不断冲击着高觉新坚守已久的传统理念。高觉新也曾同自己的两个弟弟一起如饥似渴地浏览新报刊,了解新思潮,但迫于自己的长孙身份和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而放弃进步。高觉新性格中的软弱也受到儒家礼教思想的影响。他成长于规矩森严的封建大家庭,自小便被灌输儒家的“孝”思想,自觉遵循着“人生百行,孝悌为先”的宗旨。但封建思想中的“孝顺”更多是顺从、顺服,父为子纲,必须听从长辈的任何命令,无论是学业还是婚姻,都不能忤逆,因为他们象征着“权威”,代表着“孝”。“克己复礼”作为儒家的核心思想,“克己”不仅意味着约束、克制自己,遵守礼仪规范,也蕴涵着一层不反抗与懦弱的意味。这更多的是为了维护封建大家族的稳定,个体生命的独立性被忽略。高觉新属于高家,但他不属于自己。长子长孙的独特身份以及自小接受的传统思想教育使得高觉新成了一个被旧社会抛弃又难以融入新社会的“多余人”。高觉新对新思潮持赞赏态度,但做事瞻前顾后,缺乏行动力,从这一人物身上可以窥见屠格涅夫笔下“多余人”的精神气质。
《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家》寫于1931年,正是一个战乱频繁的年代,军阀割据,动荡不安,腐朽的封建制度已经岌岌可危。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民众思想逐渐觉醒,一些能人志士率先冲破桎梏,奋起反抗,讨伐封建官僚地主,抗击军阀和外国侵略者,为民族的自由和振兴殚精竭虑,将个人的性命与安危抛诸脑后。但已经存在千年的封建思想并未完全从人们头脑中抹去,以高觉新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为封建礼教所束缚,心里明白封建思想的缺陷,却缺乏反抗的勇气,徘徊于革命斗争队伍之外,结果不仅自己成了时代转变中的牺牲品,也连累了自己身边人。巴金作为日益衰落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中的一员,他曾目睹过封建地主家庭的腐朽以及对人身心的摧残,因而开始创作长篇系列小说《激流三部曲》,为的就是“宣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死刑”[3],揭露封建大家庭的伪善与罪恶。高觉新这个人物集中地表现了时代转型时期旧知识分子身上的缺陷,他们也正是需要唤醒和帮助的对象。
三、周如水:封建家庭与自由爱情间的犹疑者
《爱情三部曲》中第一部《雾》的主人公周如水也同高觉新一样,是一个在新旧思想中摇摆不定的“多余人”,面对家庭与爱情的矛盾,难以取舍。周如水的性格恰似他的名字一般,如水一般软弱,任由自己的父母摆布。正如他的好友吴仁民所说,周如水“一生最多也只有一两次的决定”。
在婚姻方面,他听从父母的安排,娶了一个样貌丑陋、身材瘦小的女子为妻,随后又生下一个自己“不认识的孩子”。为了逃避这无爱的婚姻带给他的痛苦,再加上五四运动与新思想对他的影响,他选择了去日本求学。在从日本求学归来的途中,周如水与以前倾慕的女子张若兰在海滨旅馆相遇。但巴金并不只是单纯地描写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而是“借用恋爱关系来表现主人公的性格”[4]。在与张若兰的相处中,周如水隐藏在灵魂深处的优柔寡断以及矛盾性格一览无遗。面对张若兰直白赤诚的情感,周如水以一句“原谅我,我是一个懦弱无能的人”作为回应。可以看出周如水是一个仍未从封建桎梏中脱离出来的人,他没有勇气去反抗封建家庭强加给他的这段婚姻。当他一年后收到家信,得知自己的妻子已于两年前去世时,他才悔不当初,他的犹豫迟疑葬送了他的爱情。周如水同罗亭一样,性格中的瞻前顾后与矛盾迟疑在爱情这块试金石面前显露出来。在事业方面,他也曾有着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他毫不动摇地信奉着“土还主义”,当父亲来信要他回去做官时,生性矛盾的他又开始在理想和现实中犹豫不决:“做官,我不愿意;归农,又不能够。”最终还是选择了逃避。但逃避对于周如水来说,是对父母的不孝,因而他越是逃避,他所承受的痛苦就越深。
周如水接受过自由、平等、民主等新思想洗礼,也曾走出国门去日本留学,按理说这样一个见过世面的知识分子,思想应该是进步的、开化的,但封建思想却如幽灵一般萦绕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处于五四时期的周如水,也有追求自由的渴望,但在封建礼教的羁绊下,他的欲望一次次被自己压抑。每当他被迫妥协后感到痛苦时,“他便拿他对母亲的爱来做挡箭牌。他觉得他付出这样大的牺牲也换到了一点东西,他得到良心的安慰”。他以“爱”和“孝”为借口,将自己囚禁在封建制度的牢笼中,不仅对自己是一种折磨,也让自己的亲人与朋友痛苦。其实,他同高觉新一样,都是封建礼教的妥协者,流淌在血液里的软弱性格无法支撑起他们对理想生活的追求,没有能力向现实反抗,虽然生活在新时代,但灵魂深处依然被旧思想占据。因而在面对一次次人生抉择时,他们或顺从或逃避,无奈地生存于新旧两个时代的夹缝之中,倍受折磨,进退失据,毫无生气。
周如水这一人物的原型是巴金的一个好友,创作这个人物的目的是“给他指出一条出路,把他自己的性格如实地绘出来给他看,让他看清楚自己的真面目”[4]。其实这也是当时部分知识分子的真实缩影。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许多出身封建家庭的知识青年,虽然受到新思想的熏陶,但依旧被封建观念支配着。再加上当时中国战乱不断,动荡不安,“三座大山”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身上,这一部分知识分子无力与现实抗衡,于是埋头于书本,高谈主义,祈求在各种主义间获得片刻安宁,借以逃避现实。巴金以精深细腻的笔触将周如水灵魂深处的封建思想呈现在读者眼前,一字一句都饱含着作者的同情与鄙视,以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无奈。作者刻画这样一个人物,为的就是唤醒当时社会上与周如水一样的青年,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有着和周如水相似的性格,号召他们站起来与封建社会作斗争。从周如水这一形象中,可以看到国门大开后,中国知识分子在各种西方思潮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之间的艰难抉择,与俄国“多余人”不同的是,这种痛苦挣扎只能发生在被封建专制制度影响几千年的中国。
四、汪文宣:多重压力下的病态儿
在20世纪40年代,巴金创作了《寒夜》这部小说,塑造了汪文宣这样一个软弱无能、逆来顺受、怯懦自卑、内向木讷的“多余人”形象。在性格上,汪文宣和高觉新有一定的相似性,也可以说汪文宣是活在抗战后期的高觉新,但和高觉新相比,汪文宣的命运更加凄惨。
青年时期的汪文宣同高觉新和周如水一样,也曾受过良好的教育,作为一名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学生,他一直梦想着创办一所“乡村化、家庭化”的学校,期待着能够在教育事业中奉献自己的一生。在爱情方面,他比高觉新和周如水更加幸运,他打破了旧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配陋习,与同为大学生的曾树生自由恋爱,两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过着自由快乐的日子。可是随着战争来临,为躲避战乱,汪家迁至四川的一个小山城,身为汪家顶梁柱的汪文宣由于自身性格的老实木讷与敏感自尊连续失业三个月,最终在同乡的帮助下找到一份毫无前途的校对工作,靠着微薄的工资养活一家三代四口人。大学毕业的汪文宣有足够的才能,但骨子里的文人气节使他不愿媚上,再加上社会地位的低下,于是他的才能只能被禁锢在日复一日枯燥无聊且毫无创新力的校对工作中。
令汪文宣倍受折磨的不仅仅是拮据的生活,还有汪母和曾树生那难以调和的矛盾。汪母是昆明的才女,但她是封建礼教下培养出来的才女,是一个守旧的封建妇女,重视以三纲五常为主的传统家庭模式。而曾树生接受的是新式教育,追求自由与平等,有自己的事業与生活。思想观念完全不同且毫无血缘关系的二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矛盾自然不可避免。被封建思想禁锢的汪母难以接受儿媳的新式生活方式,无论是外出应酬还是送儿子去贵族学校,她统统反对。婆媳二人势如水火,互不相让。这令在工作中本就不顺的汪文宣更加痛苦,同时他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两个他所爱而又爱他的女人必须像仇敌似地永远互相攻击呢?”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旧思想和新文化无法相容的结果。但这种矛盾本不应该如此激烈,真正激化矛盾的是社会现实,倘若汪文宣有钱有势,那么妻子办教育的梦想可以实现,就不必在娱乐中逃避现实,同时也可以维护母亲作为长辈的自尊,可偏偏他无权无势。作为儿子与丈夫,他没有办法消除两人之间的隔阂,也无法下定决心在两人之间做出取舍,他主张息事宁人,永远都是敷衍与搪塞,周旋于母亲和妻子之间,试图两边讨好但常常两边都不落好,在母亲与妻子无休止的争吵中痛苦地生存。
他本就不强壮的身体在工作和家庭的双重折磨下患了肺病,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残酷的现实阻碍了他对自己理想的追求,最终在抗战胜利后的鞭炮声与群众的欢呼声中黯然离世。同为巴金笔下的“多余人”,相较于高觉新和周如水,汪文宣的悲剧色彩更为浓厚。高觉新的不如意可以在自己的小家庭中得到排解,周如水面临矛盾时也可以用对父母的“孝”来安慰自己,但汪文宣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家庭中都没有可以喘息的机会,只能寄希望于抗战的胜利,可真等到了抗战胜利那天,他却与世长辞。
巴金通过汪文宣这一人物形象批判了黑暗社会对人的摧残,即人在生活重压下灵魂的扭曲与异化。汪文宣常在理想与现实中挣扎,这种思想与行动的不一致,构成了一个人物性格矛盾的“多余人”形象。他的锐气与自尊在一次次的矛盾挣扎中不断被吞噬,最终变成一个胆小自卑,懦弱安分的小职员。他如同苍茫大海上一艘无法自己掌握方向的帆船,随时面临沉没的危险,他的人生似乎永无宁日,面对社会的黑暗,面对战争的威胁,面对无法取舍的感情之间的矛盾,面对肺病的折磨……汪文宣在年轻的时候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勇敢追求自由恋爱,但随着社会形势的瞬息万变,他始终无法在新的社会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于是进退两难,逐渐丧失意志和勇气,陷入更加艰难与无望的“寒夜”。汪文宣思想与行动的分裂以及自我认知的模糊造成他心理的失落与社会地位的低下,最终成为一个对别人、对自己、对社会都无用的“多余人”。
五、結语
在谈及自己为什么要创作这么多性格软弱的人时,巴金表示:“我看见的那样的人太多了。我的兄弟姐妹中大半都是这样的。唯其懦弱,才会被人逼着做了不必要的牺牲。”[5]这些中国式的“多余人”不仅是文学形象,更是当时的社会现实,是中国社会变革时期一部分知识分子心理的真实写照。巴金笔下的这些“多余人”形象,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蕴与思想内涵,它为当时迷茫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很好的反思案例。巴金通过人的精神困境揭示人物的悲剧命运,赋予作品文学、哲学以及社会学等多重意蕴,跳出了时代的束缚,具有永恒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党秀臣.中国现当代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2] 狄德罗.狄德罗美学论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委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巴金专集(第一册)[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4] 巴金.巴金选集(第4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5] 巴金.短简[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 夏 波)
作者简介:廖芝,西南交通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