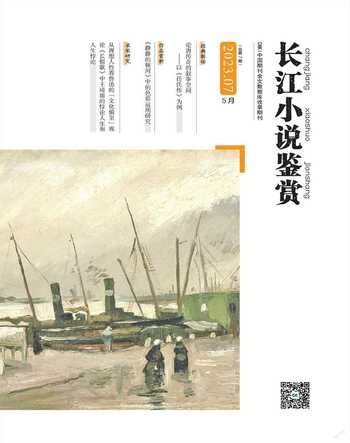论《长恨歌》中王琦瑶的悖论人生和人生悖论
[摘 要] 《长恨歌》将“沪上淑媛”王琦瑶置于叙事中心,以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的上海作为叙事空间,讲述了一个平凡却独具风姿的女性在历史和社会变迁中演绎出的矛盾人生。王琦瑶的身上充分展现了人生悖论和悖论人生的杂糅、绞缠。王琦瑶形象的塑造及其命运悲剧不可逆性的呈现,不仅具有文学史意义,还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关键词] 王安忆 《长恨歌》 王琦瑶 悖论人生 人生悖论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07-0083-06
《长恨歌》由王安忆创作于1995年,这部长篇小说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大众读者当中,都获得极高认可。在《长恨歌》中,王安忆没有采用宏大叙事的手法,而是选择以平和的叙述姿态讲述弄堂女儿王琦瑶的一生,借此折射上海近半个世纪的人事变迁,反映出作者对于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个体命运的思考。“王琦瑶”是中国现代都市女性的一个缩影,她的身上交汇着女性世界里难以厘清的各种矛盾与困惑。本文力图从多个角度去分析她身上充满悖论的人生和人生的悖论,以期加深对那段特定歷史时期中个体命运的认识和思考。
一、婚恋中名与实的悖论
在多数人的婚恋观中,两性交往的最终目的是获得一场“名实俱有”的婚姻,这里的“名”指“名分”“声誉”,是衡量婚姻合法化与合理化的一个重要标准;“实”可理解为“实际拥有物”,特指一些切实可感的事物,如物质财富、感情基础等。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会发现一种有悖于传统婚恋观的现象,即在缺乏必要的物质保障时,婚恋可以忽略名分而专注于物质财富的追求,但在拥有足够的物质基础之后,名分又成为婚恋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对于此种在婚姻的“名”“实”选择上相互矛盾的情形,《长恨歌》里有着极其精彩的演绎。
家境并不殷实的王琦瑶凭借一场选秀比赛成了声名颇高的“三小姐”,随之便得到军政要员李主任的垂青而住进“爱丽丝公寓”,过上优越的生活。这一阶段的王琦瑶在婚姻上面临着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由威风八面的李主任带给她的虽富足却不长久的路,一条则是由痴情满腹的程先生带给她的虽清苦但长久的路。可以说,选择前者还是后者,实际上就是选择“无名分的婚姻”或“有名分的婚姻”。出身于上海弄堂的王琦瑶,既不像好友吴佩珍一样心思浅薄,又不似蒋丽莉那般盲目放逐情感,而是个“奋力向上的,石头缝里都要求生存”[1]的人,所以她清楚地明白自己心里如火苗般炽热萌动的是什么。相比身边的两位女友,王琦瑶的劣势并不是美貌、气质,而是一个足够撑起她所有浪漫想象和欲望满足的物质基础。因此,王琦瑶舍弃传统、保守且早已没了时尚之心的程先生,通过投怀于无法给她任何“名分”的李主任来建造属于她的物质大厦。若只从这一目的的实现情况来看,王琦瑶无疑是成功的,李主任赠送给她的整盒金条就是最好的证明,守着金条,即便在最清贫无助时她也没有绝望。这里,“金条”这一“实际拥有物”被王琦瑶摆在了至高地位,而婚姻中的“名分”被置于无足轻重的角落。那么,王琦瑶是否真的认为婚姻只需切实可感的“物”而不需要一个合理的“名分”呢?答案是否定的,这从后面王琦瑶与康明逊的相恋过程就可得窥一斑。
小说第二部分,重返上海的王琦瑶虽住在人声混杂的平安里以为人打针谋生,实则有着旁人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优雅气质加之那盒保其余生无忧的金条使她对生活有着极大的胜算。如果说此时的王琦瑶真的缺少什么,那就是一场名正言顺的婚姻,这点从她选择与康明逊相爱后又戏称二人的结合只是“野鸳鸯”就可看出。但是,对于王琦瑶的这一需求,康明逊却始终无法满足。究其原因,这与康明逊的身世有着极大关系。康明逊是二房所生的孩子,“却是他家唯一的男孩,是家庭的正宗代表”[1]。此外,他有个老派父亲,平日里为人处事“不越规矩半步,上下长幼,主次尊卑,各得其份”[1]。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康明逊的境况,应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又算怎样的男人呢?……夹缝中求生存,样样要靠自己,就更不敢有奢望了。”[1]由此可知,横亘于王琦瑶和康明逊之间的是一个有着鲜明等级意识和正统观念的传统家族,屹立在他们背后的“父亲”更是代表着这个家族中的最高权威。所以,基于王琦瑶之前的复杂身份,康家不可能接受二人结婚,而受制于自己特殊身份的康明逊也无法逾越严苛的家规去掌控这段恋情。因此,康、王情感的破裂有其必然性。透过这段情感可知,物质基础与婚姻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等的,正如已经具备了充足物质条件和感情基础的王琦瑶本以为可以得到一场有“名分”的婚姻,殊不知,她先前的经历和她拥有的东西恰恰成了他人诟病其人格的凭证,这当然是一场悲剧。
通过王琦瑶的两段情感经历可知,婚姻的“名”“实”有时是相互矛盾的。此种现象至少可以启发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两性交往中,究竟应该如何来行使爱与被爱的权利?显然,应以正确的婚恋观为前提。而要想形成正确的婚恋观,首要一点便是婚恋双方都要敢于寻爱。对于女性来说,尤其对中国现代女性而言,拥有自主求爱的意识以及拥有被爱的权利实际象征着反封建礼教压迫的阶段性胜利,它是女性体验自我意识、肯定其人格尊严和人生价值的重要方式。由是观之,王琦瑶无疑是有其思想进步性的,因为她在两段情感中均清楚地知晓自己的所思所想,甚至在她与康明逊的恋爱中,我们能隐约间看到一个一心追求真爱而漠视周围人目光的现代“自由女性”的身影。但是,敢于寻爱只是正确婚恋观形成的必要条件,另一个重要因素应是理性选择婚恋对象的意识。于王琦瑶而言,她在两段情感中都同时扮演了“求爱者”和“被爱者”的角色,而无论倾向于哪种角色,王琦瑶都把物质条件看得很重,甚至忽略了精神层面的东西。正如在投靠李主任时,王琦瑶是将物质财富视为她人生的基石和退路,而后选择与康明逊相恋并要求获得“名分”,也是因为她把那盒金条作为自己坚实的仰仗。因此,王琦瑶固然是一个精明的女人,精明让她准确地把握到了隐没在繁华都市里的世俗人心,可这也蒙蔽了她的心。所以,王琦瑶在婚恋中是缺乏理性选择意识的,她的选择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明显的失衡状态,婚姻在她心里可谓既清晰又模糊。
王琦瑶的悲剧启示我们,在婚姻的“名”“实”选择问题上,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二者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存在着矛盾,另一方面也要审视两性交往中的婚恋观因素,要深入思考如何在各类复杂情形中进行理性取舍,从而努力去构建一种既个性化又闪烁着智慧之光的婚恋模式。
二、女性意识与依附心理的悖论
王安忆笔下的女性形象是许多学者的研究对象,学者们常借此去完善学界对“女性”“女性意识”等概念的认知。有学者指出,王安忆惯于通过韧性、情性和智性来建构女性形象,如《富萍》中外柔内刚的个性女子富萍,《流逝》里以柔弱肩膀担起家庭重任的欧阳端丽,还有《长恨歌》中的王琦瑶。上面提到的这些女性所具有的“美好品格”在王琦瑶身上仿佛实现了大荟萃。王琦瑶虽处在喧嚣杂乱的平安里,却总能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其言谈举止间皆透露出令人赞叹的从容和优雅。无论处于人生的哪种境遇,王琦瑶似乎都能让自己行走在精致的轨道中,在她身上始终涌动着一种非常强烈的生命意识,而这种生命意识也使得她对自己的生命状态、生存方式以及生活目都有着较为准确的认知。
那么,前面提到的那些美好的品格与“女性意识”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我们是否可以把它们等同于真正的女性意识?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何为“女性意识”。“所谓‘女性意识,既包含着女性作为‘人的意识,也包含着女性自我性别意识,即意识到女性既作为和男性平等的人,然同时又是自立主体的‘另一类的角色、地位和价值问题。”[2]据此可知,上述提及的所谓“美好品格”只是假性“女性意识”的表现,它们虽展现出蕴藏于女性体内强大的生命意识,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女性艰难的生存境况。正如王琦瑶在得知康家反对她和康明逊结合后的妥协,以及她面对康明逊逃避责任的态度时选择容忍的举动,实际上都是为爱盲目牺牲自我的表现,其遵循的正是男权社会中男性为女性制定的类似于“宽容忍让”“温柔体贴”“乐于牺牲”的行为规范,与真正“女性意识”的所指是相悖的。在此之下,女性没有独立的人格,她们仍然屈从和受控于男性的意志。然而,在揭开这层“女性意识”的虚假面纱后,我们又会产生另一个疑惑,即类似王琦瑶这样的现代知识女性为何依然不具备真正的女性独立意识?假性“女性意识”的背后是否暗藏着作者对历史现实更深的诘问?针对这个问题,可从“男权社会的桎梏”和“女性个体认知的歧路”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首先是男权社会的桎梏,即男权文化传统对女性的束缚。在封建社会中,男性凭借其力量与威权对男女角色做了一系列符合男性需求的定义,他们将各式各样的道德规范强加给女性,这些无疑给女性带来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摧残。但是,在意识到反抗只会招来攻击谩骂的现实面前,女性最终主动选择了噤声,慢慢地沦为男权社会中一个个或精致或凄惨的玩偶,整日如鬼魂附体般麻木无知地生存着,直至彻底沦为男性的附庸品。到了近现代社会,五四运动的爆发虽为长期饱受封建礼教压迫之苦的女性带来了盼望已久的生机,但这次运动并非那种通过观念转变到制度变革来使女性获得根本性解放的运动。近现代出现许多以国家形式颁布的保护女性或倡导男女平等的法律条文,如规定男女同工同酬,男女都具有参加社会工作和参与投票选举的权利。但在现实操作过程中,男女平等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此,要想令女性获得真正的女性意识是很难的。
其次是个体认知的歧路。男权社会与男性意识形态的控制固然是造成女性集体“失声”的主要原因,而女性群体中某些个体对于“女性意识”偏狭错误的理解也是导致这些个体长期身陷囹圄的重要因素。如《长恨歌》中有这样一句话:“王琦瑶却不同意,说她反正是逃不了的,何苦再赔上一个;她这一生也就是如此,康明逊却还有着未尽的责任。”[1]按照常理,祸端既是由两人共同酿成的,责任也须由两人共同承担。如果说王琦瑶这种“无惧牺牲”的态度是心甘情愿的,目的是不想给康明逊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或是为了博得他的怜悯和赞美,那实在叫人不敢苟同。这般轻易妥协,岂不到了自我轻贱的地步?再有就是对“女性意识”的错解,这里仍以王琦瑶为例。作品中有两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一个是王琦瑶发现自己意外怀孕后把“祸端”轉嫁给了无依无靠的浪荡弟子萨沙,另一个则是王琦瑶意图用李主任所送金条来换取老克腊的陪伴。这与李主任赠金条给王琦瑶、康明逊因王琦瑶怀孕而畏惧承担责任的情形,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如果说,在王琦瑶与李主任、康明逊构成的关系中,她扮演的是被消费和被伤害的角色,那么在王琦瑶与萨沙、老克腊构成的关系中,萨沙和老克腊就成了被伤害和被消费的角色,而王琦瑶于无形中扮演了支配者的角色;她既可以把灾祸转嫁给别人,也可以用金钱来进行情感交易,由此她便兼有了“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双重身份。针对这一现象,借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来加以分析可知,王琦瑶在被男性他者化的同时,自己也创造了新的男性“他者”。我们知道,女性即“他者”的言论一直是罩在女性头上的一个“魔咒”,也是数次女权运动在争取女性独立地位的过程中必须突破的一道障碍。但在这一过程中,总有一些觉醒过来的女性会简单地认为,要想实现女性自主就要用女权来取代男权,让男性成为女性世界中的“他者”,这其实是对女性意识的误解。女性若想实现真正的独立和获得他人的尊重,绝不是要再创造一个新的“他者”,而是应从思想上彻底摒弃“他者”观念,否则便是与她们一心想要撼动的男权社会同流合污,也必将与真正的“女性意识”渐行渐远。
“女性意识”意味着灵魂的高尚与尊贵,象征着精神的独立和自由,它超脱了两性之间激烈的对抗形态而伸向更为广阔的现实人生。因此,女性若想具备真正的现代女性意识,就必须洗刷掉自身的历史惰性,破除各种依附心理,通过坚持不懈的反思和自我意识的理性觉醒来实现对自己的拯救。
三、怀旧与现实的悖论
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的兴起使中国进入到一个瞬息万变的发展阶段,许多先前被民众信奉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都面临着被解构和被颠覆的风险。面对这一情形,一些人开始产生出浓烈的怀旧之情,其意图是想通过回溯那些已然成型且稳定的“过往”来重新确立人的存在意义,为自己建造一座跨越当下困境的“心桥”。问题在于,这些人真的能从“怀旧”中获得救赎吗?
以《长恨歌》中所描写的上海都市生活为例,小说中出现了新旧两代人共同怀旧的现象,前者以王琦瑶为代表,后者以“老克腊”为代表。总的来说,新旧两代都渴望回歸属于自己的心灵家园,其区别大概在于“老一代”渴望回归的是一个“早已不存在”[5]的家园,而“新一代”渴望回归的是一个“从未存在过”[5]的家园。小说写到,进入20世纪80年代,王琦瑶频繁出入于年轻人的队伍,在他们的簇拥下,她一面不断地回想自己的青年时代,一面又在暗自哀悼其生命中逝去的不可挽回的遗憾。作为一个自20世纪30年代成长起来的女性,王琦瑶亲眼见证了上海的发展和变迁,她既看到了上海的表层,也触摸到了它的内核。而回望围绕于其身边的年轻人,他们虽整日对旧上海的风物人情表现出极度热爱,实则一直游离在旧上海的外围。换言之,他们其实是一个无旧可怀的群体,因为自有记忆起,他们呼吸的便是新时代的空气,若要论及他们是如何展开对于旧上海风物人情的想象,无非来自以下途径:长辈的描述、历史的遗物,还有书本里模糊的记录。王琦瑶在他们眼中就相当于“历史的遗物”,透过她的笑颜戚容和举手投足,他们得以领悟“上一个时代的风韵和美学趣味”[6],而后想象性地构建出自己心中旧上海的形貌。至于引发这群年轻人怀旧的动机,自然与前面提到的集体性的精神状态失衡有关,由此产生出的正是马尔科姆·蔡斯和克里斯托弗·萧二人所提到的“有缺憾的感觉”[7]。至此可知,身处“怀旧潮”中的“老一代”和“新一代”都是孤独的。正如王琦瑶在起初或许想以其“旧时代守夜人”的身份让新时代的年轻人重新领略旧上海的精髓,最后才发现,属于他们那一代人的上海早已一去不返,在新时代面前,他们并没有属于自己的位置。而对于“新一代”年轻人来说,他们一心想通过“怀旧”来实现自我拯救,却始终未能懂得真正的上海精神,没有领悟到那寻常巷陌里蕴藏着的平淡如水却偶起微澜的上海文化内核。处在外在世界与内心世界同样浮躁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新一代”把“王琦瑶的过去与上海的过去,那一路走来的隐忍难奈、屈辱不甘与绝望痛楚统统都沉潜下去”[8],机械生硬地为“老上海”贴上一连串标签,而后就在那一个个自创的精致的“城市偶像”中自我陶醉,换得一种虚假的心灵慰藉。
应该说,“怀旧”作为人类精神世界里一种不可或缺的情结,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能代表某种类似于“信仰”或“希望”的东西,人们有了这种“信仰”和“希望”,就好像在变幻无常的人生中找到了一条稳妥的退路。《长恨歌》中的王琦瑶从来到平安里的那天起就开始怀旧,在怀旧中她细细梳理着过往岁月中拥有过的一切荣光与落魄,并将其作为自己的人生资本,而这些资本在若干年后又恰巧成了她唯一能拿出来炫耀的东西,因此“怀旧”成了她的一种生存信念。“怀旧”于新一代而言虽无多少厚重的力量,却是时代洪流中他们最快也最直接能抓住的自我救赎的“稻草”,即便被人诟病为附庸风雅,也终是好过无所依托,所以在这里,“怀旧”又成了“新一代”的生命支撑。
不过,在认识到“怀旧”的重要意义后,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没有哪一个人或哪一个时代能依靠“怀旧”实现长久发展,若一味“怀旧”,那无异于与历史规律对抗,无异于在现实面前选择逃避。在小说最后,王安忆为我们描绘了长脚在谋杀王琦瑶时所目睹的令人作呕的一幕:“这时他看见了王琦瑶的脸,多么丑陋和干枯啊!头发也是干的,发根是灰白的,发梢却油黑油黑,看上去真滑稽。”[1]这正是“老一代”怀旧者最为真实的形象,也是不断发展的历史留给一个固执且孤独的“怀旧者”最后的结局。李欧梵在《漫谈(上海)怀旧》一文中曾引用张旭东的一段评论:“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市场上,怀旧是一种时髦,它试图通过回到过去,创造一种物质文化氛围,从而克服幻想和影像的虚幻世界中的失落,追寻和重现上海曾有的崇高。”[9]这段话准确地点明了“新一代”上海怀旧的实质,即它只是“一种时髦的假象,一种‘后现代和‘后革命时代的商业现象,一种文化消费”[5]。也就是说,“老克腊”一代渴望回归的是一个“从未存在过”[5]的家园,他们按照历史的“遗迹”,借助各种充满年代感的物件去想象性地建构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生命支撑。但是,此种“怀旧”说到底是没有归属感的,它那浮于表层和缺乏真实性的特点已使之成为一种典型的大众文化,新一代的“怀旧者”长期置身在这样一种按照固定模式运作的通俗文化当中,最终也将不可避免地沦为一个个缺乏自我意识的“木偶”。
“怀旧”本身没有过错,无论身处哪个历史时期,我们都可以通过“怀旧”来坚守一些信念,去填补精神上的缺憾,但“怀旧”不能作为我们逃避现实的理由,也不能作为寻求自我救赎的全部手段。如果生活在既存现实和现代社会中却选择漠视时代变化,只是一味“怀旧”或仅仅把“怀旧”当成一种即时性的消费,终将难以寻找到一条正确的自我实现之路。
四、结语
在《长恨歌》中,王安忆从婚姻中的“名”与“实”、女性意识与依附心理、怀旧与现实等角度,揭示了王琦瑶充满悖论的生存方式和矛盾纠缠的心灵世界。与王安忆以往的小说相比,《长恨歌》体现了“作者对传统全知叙事的更高层面的回归”[10],也正是在这种全知叙事之下,作者得以更为完整全面地去展现一个女人的一生与众生浮沉的世相,同时也凸显着其对生命意义的深思。
就《长恨歌》诞生的时间点来看,这部小说还具有一种“冲破时代藩篱”的气度。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女性创作,大部分女作家处在人文精神疲软的状态中,她们普遍放弃了20世纪80年代的精英立场,选择用个人话语来传达各种难以言说的失落感和被排挤至边缘的孤独感。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些写作现象,如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私人化写作”、以徐坤、斯妤为代表的“解构性女性写作”和以卫慧、棉棉为代表的“另类生活写作”等,都是对当时社会现状做出的极具个性化的反映。这些新起的创作潮流虽拓宽了当代女性文学对于女性生存经验的叙述空间,填补、充实了许多之前女性写作中空白的或尚处于含蓄隐晦状态中的区域,却因少了一份超然昂扬的力量和一种人文关怀的向度而显得单薄闭守。面对这一情形,王安忆“高擎起纯粹的精神的旗帜,尝试着知识分子精神上自我救赎的努力”[11]。正如在《长恨歌》中,王安忆通过呈现王琦瑶在近半个世纪中所演绎出来的一种“悖论式”的人生模式,一方面为我们映射出时代的风云变幻,一方面展现了她作为一个女性知识分子对现代女性命运的深刻思考和真切关怀,其目的正是为了改善女性的生存境况,乃至实现对女性群体的拯救。
此外,透过《长恨歌》,王安忆的“超性别”意识和“民间”立場同样值得注意。前者主要指王安忆在其两性叙事过程中没有机械地以西方女权主义的相关思想为指导去对两性形象做生硬的定型,而更多是从本民族历史传统与地域文化特色的角度出发来分析那些由男女两性共同建构的情感世界和社会模式,力求在避免各种强力抗争的前提下去传达人类的普遍情感。后者提到的“民间”立场在王安忆的小说中则主要表现为,她时常将现实中的政治冲突或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其讲述故事的背景或小说情节发展的楔子,在此前提下去描绘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去体察那潜藏于民间社会中强大而独特的生命,在揭示人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同时,也为读者打开了一个雅俗并存的民间世界。王安忆小说的这两大艺术特色,不仅使她在众多当代女性作家中独树一帜,也启发读者透过她的书写来对特定时代和地域文化做出更具广度与深度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2] 杨冬红.站起来的“夏娃”——浅析90年代女作家女性意识的高扬[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0(4).
[3] 魏娜.两性和谐与人的发展问题研究[D].郑州:河南师范大学,2012.
[4] 李翠荣.当代女性的科学发展探略[J].社会科学家,2011(12).
[5]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M].毛尖,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6] 程箐.时间之维与生命之思——王安忆《长恨歌》解读[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5).
[7] 包亚明.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8] 周明娟.都市女性的镜像式生存——王安忆《长恨歌》的别一种解读[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4).
[9] 张旭东.批评的踪迹[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10] 赵树勤,李运抟.中国当代文学史[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1] 陈思和,王光东,张新颖.知识分子精神的自我救赎[J].文艺争鸣,1999(5).
(特约编辑 张 帆)
作者简介:刘雪莹,湖南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笔画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