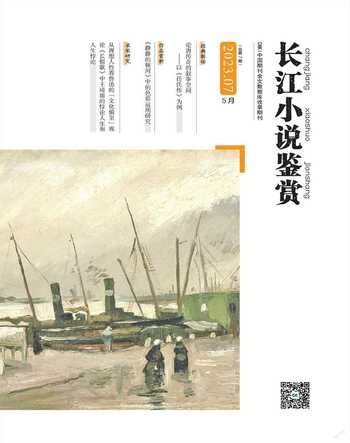《雪国》中的女性形象及其背后的女性主义思考
[摘 要] 《雪国》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岛村与驹子、叶子之间的感情纠葛为主要内容,而驹子和叶子之间“灵与肉”的关系一直以来为评论家津津乐道。驹子代表的是“肉”的一方,她纯洁、热情,充满着生命力;而叶子是“灵”的代表,是缥缈、空灵的。然而不管是驹子还是叶子,都是作者借由岛村所建构出来的女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作者受到了男权思想的影响。但作者通过刻意营造与岛村之间的叙事距离,使驹子和叶子的形象在获得美的升华的同时也突破了天使形象的桎梏。
[关键词] 《雪国》 女性形象 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07-0017-04
《雪国》是川端康成的代表作之一,小说故事情节简单,着重表现了在雪国那独有的地方风光中,舞蹈研究者岛村与艺伎驹子和纯情少女叶子之间的感情纠葛,为读者展现了一种哀怨和冷艳的氛围。小说最后以叶子的死亡為结局,但在岛村的眼中,死亡却是一种美丽的超验体验。在小说中,驹子和叶子是互相对立却紧密联系的两位主要女性形象,作者川端康成潜藏在主人公岛村的背后,并通过岛村的眼光塑造出他心目中美丽的女性形象,在驹子和叶子这两位美的化身背后,隐藏着川端康成心中父权思想所遗留的痕迹。
一、驹子:冷清与热情交织的徒劳女性
《雪国》中作者着墨最多的人物就是驹子,她虽为艺伎,但整个人“洁净得出奇”,拥有姣好的容貌和纯洁的心灵。她的命运是不幸的,从小就被卖掉做舞伎,后来被恩主赎出,可刚过了一年半,恩主就去世了。后来师傅的儿子行男患上肺炎,因此她出来当艺伎为行男赚取医疗费用,但最终师傅和行男都去世了。在正式成为艺伎之前,驹子认识并爱上了岛村,也正是通过岛村的“三临雪国”,读者看到了这位美丽却一直“徒劳”地挣扎的女性形象。
作者对驹子的形象描写更多是对其身体的描写,仿佛是为了符合她“艺伎”的身份,尽管小说中一直强调驹子的“洁净”,但其身体却处处充满了带有性暗示的肉欲之美。小说开头描写了在茫茫一片雪景中,“岛村感到百无聊赖,发呆地凝望着不停活动的左手食指”[1],驹子的形象便通过“左手食指”引出,这个场景带有性暗示的意味。在第一次见面时,尽管“女子给人的印象洁净得出奇,甚至令人想到她的脚趾弯里大概也是干净的”[1],但“脚趾弯”的联想却也带有肉欲的性暗示。在岛村眼中,驹子最具有吸引力的就是她的身体,尤其是她的皮肤,驹子的脸颊似乎总是红彤彤的。然而,与驹子总是红彤彤的脸颊不同,她的一头黑发却总是显得冷冰冰的。正是在这冷情与热情相互矛盾又密切交织的身体描写中,作者展现出驹子复杂而生动的形象。
驹子也有着与其他人不一样的坚持与理想。驹子坚持写日记,她会将发生过的一切都如实记下来,并且平日也经常翻阅旧日记。从十六岁起,她就一直在看书,并且将读过的书都做了笔记。然而这些坚持对于岛村来说,除了有一时的感动之外,他认为这全是无用的。尽管驹子在与岛村交谈起文学时眉飞色舞,但此时的岛村却突然想到驹子投入自己怀抱时的样子,并自认为“看上去她那种对城市事物的憧憬,现在已隐藏在淳朴的绝望之中,变成一种天真的梦想”[1]。除此之外,驹子还弹得一手好三弦琴。在驹子的蚕房里,面对不停调试琴弦的驹子,岛村起初的态度是不以为意的,但当驹子开始弹奏《劝进帐》时,岛村被驹子的琴声所感染,不得不佩服驹子,直到曲终之时才终于从这种震撼之中清醒。驹子所有的努力与坚持、对未来生活的期待、对过去经历的感悟,对岛村而言都是不值一提的,驹子只是他暂时逃避东京现实的寄托物,他对驹子并没有所谓朋友间惺惺相惜的感情,而只是将驹子看作是取悦自己的对象,而她的感情、经历对他而言更是无足轻重的,因此面对驹子全身心的付出,岛村只是以高高在上的悲悯姿态粗略地将其定义为徒劳无用的。
川端康成自幼缺乏母爱,失败的恋情也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挫败,这些经历使他在感情上出现了厌女的倾向,但日本古典文化又使他在文学作品中追求完美的理想女性。《雪国》中,尽管岛村被作者刻意弱化、边缘化,但却是小说中拥有绝对话语权的人,他既是故事的参与者,也是故事的叙述者。驹子不过是岛村逃避现实时的消遣,只是她过于“洁净”,导致岛村一开始不敢直接暴露自己隐秘的心思,然而就是因为这种“不敢”,却让驹子心动,并逐渐将自己的全部给予岛村。然而驹子这种不求回报、如飞蛾扑火般的热情,对岛村而言却是没有意义的,他甚至一直以“女人”来称呼驹子,直到第二次见面时,他才从别人那里打听到驹子的名字。可见,驹子的外在形象和内在品质,乃至其身份,都是男性主动选择的结果,反映了男性自身的诉求。但在对驹子的描写过程中,叙述者也会跳出岛村的视域,不过就整篇小说而言,这种“跳出式描写”也只是零星一角。驹子自始至终就是岛村或说叙述者想象中的女性形象,她拥有叙述者满意的样貌,并给予岛村无私的、不求回报的爱情,这种无私的母亲形象,正是川端康成自小所缺失的。但驹子并不完全是作者笔下的天使形象,真正让岛村沉迷的天使则是他第二次前往雪国时遇见的叶子。
二、叶子:充满虚幻美的天使形象
与驹子不同,叶子是岛村心中只可远观的完美女神。因此小说对叶子的描写充满着朦胧感和神秘感,叶子就像天使一样,她的感情纯粹热烈,整个人就像被一层梦幻的面纱所笼罩,但别人也能轻易感受到她的美。
与驹子带有官能感的出场不同,小说一开始就描写了叶子的声音,那“清澈得近乎悲凄的优美的声音”[1]不停在岛村的脑海中回荡。岛村第三次来到雪国,叶子替驹子送来纸条时两人终于有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交谈,因为行男的离世而显得呆傻疯狂的叶子让岛村感到一阵发寒,她的“笑声清越得近乎悲凄”[1]。
小说全篇并没有对叶子外貌进行整体的描写,而是将更多笔墨集中在叶子的眼睛上,这种局部的模糊性描写使得叶子的形象带有朦胧的神秘感。在火车上,尽管叶子就坐在岛村的斜对面,但岛村却被叶子那种迷人的美所震惊,不敢往对面望去。小说中无数次直接说出叶子的美无法形容而又令人震撼。岛村透过窗户玻璃只能看到叶子模糊而美得惊心动魄的脸,但眼睛却十分清晰:“她的眼睛同灯光重叠的那一瞬间,就像在夕阳的余晖里飞舞的夜光虫,妖艳而美丽。”[1]后来,当驹子送岛村到火车站,叶子急匆匆赶来劝驹子回去,这时岛村终于看到了叶子脸上的表情,但作者却用“面具”一词遮住了叶子的脸庞。在岛村面前,叶子的眼睛充满了魅力,然而她的眼神却总是尖利的,他开始对于同驹子的相会感到拘束,尽管他知道驹子对自己的爱,但却把这看作一种美的徒劳,因此他“似乎觉得叶子的慧眼放射出一种像是看透这种情况的光芒”[1],然而他正是被这一双慧眼所吸引。小说虽然没有对叶子的外貌做细致的描写,但数次强调其眼睛的美丽,叶子的眼睛既是其纯洁心灵的写照,又像是一面镜子,仿佛能洞察岛村的内心深处,因此他会被叶子的眼神所震慑,但出于男权主义的征服欲又不自觉地被吸引。
叶子就像是一个并不真实存在的人,尽管她是雪国土生土长的姑娘,有个弟弟在火车站工作,穿着和村里人差不多的衣服做工,她的情感和美好品质也是真实可见的。叶子对弟弟佐一郎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小说的开篇就体现得淋漓尽致。她对驹子怀着复杂的感情,一方面是对驹子对待行男的态度感到不满,另一方面则是对驹子和岛村之间的遭遇感同身受,但她仍然依赖着驹子,并委托岛村要好好对待驹子。叶子给行男的是和驹子一样无私奉献的、不求回报的爱。她像母亲一样尽心尽力地照顾着病危的行男,行男去世后,她依旧执着地迷恋着他,每天去坟墓前哀悼,表达自己的哀思。驹子对岛村的爱随着岛村一次次的离去而变得虚无,叶子对行男的爱随着行男的死亡也变得虚无。然而叶子的美又是迷幻的、非现实的,充满着神秘感和梦幻感。对她的容貌描写过于模糊,只有一双迷人的眼睛时时迸发出锐利的光芒;她的声音优美清越而又近乎悲凄,仿佛是来自遥远天边的声音;她就像《百年孤独》中的美人儿蕾梅黛丝,同样具有虚幻的美,也具有相似的结局:蕾梅黛丝后来升天而去,叶子也在一场大火中以死亡获得了美的升华与永恒。
三、《雪国》中的女性主义思考
《阁楼上的疯女人》写道:“男性艺术家们对他们笔下女性客体的面容的‘描摹,经常‘并不是根据她们实际上的样子,而是根据他们对她们的梦想創造出来的。”[2]尽管《雪国》中的驹子有实际的原型——汤泽温泉的松荣,但驹子更多还是川端康成想象出来的,叶子则更是作者虚构出来的美的化身。
男性作者创造的理想女性始终是一位天使,“屋子里的天使”又是男性作者强加于文学作品中的女性的最典型形象。在中世纪,西方追求的纯洁的女性化身是圣母玛利亚,她完美地契合了奥特纳定义的作为“仁慈的拯救者”形象的女性职能。而到了更加世俗化的19世纪,女性的纯洁形象不再由天国的圣母玛利亚所代表,而由屋子里的天使取而代之。川端康成作为男性作家,他创作出来的理想女性自然也有着天使的特征。驹子和叶子无疑是作者心中的天使,她们都有着美丽的外表和纯洁的心灵,更重要的是她们都有着母亲般不求回报的无私的爱。驹子对岛村怀着永远得不到回报的无望的爱,她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岛村,而她也知道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岛村在东京有妻子、孩子,一年也不一定能来雪国一次,她也清楚岛村对她的态度,但她依然将自己的身世和遭遇、爱好与坚持都分享给他,甚至后来她察觉到岛村对叶子有兴趣,但她依旧没有戳破岛村的心思,甚至让叶子替她给岛村送纸条。小说中也多次强调驹子对岛村的纯洁的爱,两人第一次见面时,驹子在晚上呼唤岛村名字时的尖声叫喊,在作者看来“这纯粹是女子纯洁的心灵在呼唤自己男人的声音”[1]。岛村第二次来到雪国时,驹子在他的房间像一个娴静的淑女一样勤快地打扫房间,照顾岛村的起居。驹子不是没有尝试过向岛村表达自己的爱意,在岛村第三次来到雪国后,有一次两个人谈论起驹子的工作,驹子从无所谓的语调中表达出自己的心声——“因为唯有女人才能真心实意地去爱一个人”[1],她甚至还补上了一句“你不知道吗”[1]作为最后的挣扎,然而岛村只顾着仔细地观察昆虫闷死的模样而回避了这个问题,其实这也是在无声地拒绝驹子的爱。驹子对行男和叶子也具有母亲般的关怀,因为行男的病,她放弃了成为舞蹈老师的梦想,而是重新做了艺伎为行男赚取医疗费用。同样,驹子把叶子当作亲密的妹妹,而叶子也十分依赖她,当行男病重时,她跑到火车站去找驹子希望得到她的帮助;当驹子看到从着火的蚕房上掉下来的是叶子时,就像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从楼上掉下来那般,她第一时间抱起叶子并发出疯狂的叫喊。叶子同样也具有母性之美,她就像母亲一般对待自己的弟弟,在小说开篇,叶子和列车长的对话以及祭拜行男之后和弟弟的对话都能看出这点。叶子对行男更怀着一种无私的爱,她明知行男病情严重但依旧无微不至地精心照顾他,而正是叶子对行男这种慈母般的照顾吸引了岛村。行男去世后,叶子心中依然充满着对他的爱,并将这份爱深深压抑在心底,表面上她和原来一样生活,但她坚持祭拜行男,甚至不愿再做护理的工作,而正是这份因为行男的离世而永远得不到回应的爱让她疯狂,最后导致了她的死亡。
《雪国》中还有许多对自然风光的描写,这些自然描写又是对女性命运的隐喻。小说描写了一个宛如世外桃源般的雪国,这里到处是和谐静谧的。小说开篇是岛村第二次来到雪国的场景,冬天的雪国白茫茫的一片,岛村随着叶子的声音向窗外看去,发现白雪早已被黑暗吞噬了。小说开篇其实就已经预示了叶子的结局,叶子就像这茫茫白雪,终会被黑暗吞噬。小说中也用雪来表现驹子的纯洁,岛村在镜中看到驹子的脸颊被雪映衬得越发红润,而随着旭日东升,镜中的雪被太阳照耀得越发耀眼,就像燃烧的火焰,这里也暗示了人物最后的结局,无论是驹子还是叶子,终将会在大火中死去。岛村第三次来到雪国是秋天,他在路上看到一个老太婆背着一捆芭茅草,“近处看芭茅,苍劲挺拔,与仰望远山的感伤的花迥然不同”[1],驹子就像芭茅一样,远看以为她只是一个为了生计而成为艺伎的普通女子,但只有认真了解之后才能看到她坚定的内心和美好的品质。秋天也是飞蛾产卵的季节,因此文中多次出现死去的飞蛾,当叶子和岛村交谈之后走出房间时,“岛村感到一股寒意袭上心头。叶子像要扔掉那只被捏死的飞蛾似的打开了窗户”[1],死去的飞蛾暗示了叶子的结局。蚕房的大火原本是一件令人紧张的大事,但岛村的注意力很快转移到天上的银河去了,正是在银河的映射下,“原本驹子那玲珑而悬直的鼻梁轮廓变得模糊了,小巧的芳唇也失去了色泽,她的脸就像一副旧面具,而此时岛村觉得银河仿佛要把这个大地拥抱过去”[1],直到看到叶子从楼上跌落,叶子的脸燃烧着,岛村仍然沉醉于银河,他仿佛就是一个局外人,哪怕他对叶子有着深深的迷恋,哪怕他与驹子有亲密的关系,这场火灾在岛村看来不过是一场美的升华,叶子的死是内在的生命变形成另一种更加自由的东西,甚至叶子身上的火光升华了她的美。银河的描写无疑是美的,它弱化了火灾带来的现实感和恐怖感,但同样也弱化了叶子和驹子的真实性,使得她们脱离了现实,沦为作者表达美的符号。
四、结语
川端康成写作《雪国》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岛村对东京的逃避则是作者本人心态的真实写照。《雪国》中对女性形象和自然的描写,包含了日本传统的审美文化,叶子和驹子更是作者构建出来的理想女性,是男性作家笔下的天使形象。但川端康成也有意突破这种男性话语权力,他通过塑造淳朴、乐观的驹子形象和坚忍、善良的叶子形象,呈现了不同于东京和东京人的雪国之美和雪国人的人情之美,这种美在不幸的命运中具有更加动人的魅力。
参考文献
[1] 川端康成.雪国[M].叶渭渠,唐月梅,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
[2] 吉尔伯特,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M].杨莉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3] 余依林.试论川端康成小说里的“厌女症”现象[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21.
[4] 周莉莉.川端康成《雪国》中的人物形象分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0).
[5] 方爱萍.论《雪国》的自然美与女性美[J].芒种,2015(23).
[6] 孙天琪.川端康成的女性审美意识——以《雪国》中女性角色为中心[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5(13).
[7] 彭远.解析川端康成《雪国》女性形象的建构[J].芒种,2015(10).
[8] 张文静.《雪国》中的女性意识初探[J].文学教育(下),2012(3).
(责任编辑 陆晓璇)
作者简介:公琛,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