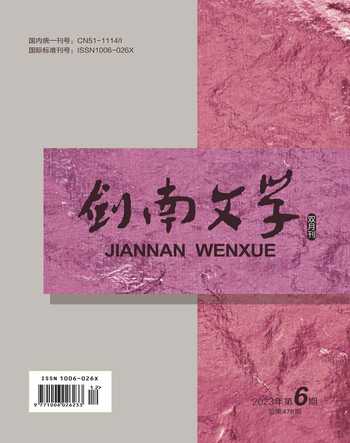桃与逃
1
它一定不是来自无人问津的山林。但凡见识过那个包装盒,一定不会有人否认它的精致。盒子是雅致的青绿色,多一分则厚重,少一分又浅薄了,因此,这颜色的深浅是费尽了心机的。打底嘛,非得如此,才足以显示出独属于它的调性和气质。除此以外,银色的桃状暗纹似有若无,无端让人想起夏日的泳池,阳光从水面上一跃而过,留给水下暗波的,是流动的华贵。
盒子上的图案呢,也是一颗桃。恰好在正中,毛茸茸地勾出半边轮廓,留白的多,唯有桃尖落下一点娇嫩的粉色,如美人半遮的脸,说不上是拒绝,还是诱惑。你每看它一眼,就往你的心尖尖上娇滴滴地掐一下。盒子的大小恰到好处,最外面端端正正地系了一根絲带,纯正的紫,也是精精巧巧的。它们被摆在门店最显眼的位置,灯光透亮地从头顶打下来,坦荡荡的骄矜一跃而出,顿时,遍身浮挂的彩衣疏远出一份只可远观的距离感。
你走过去,忍不住想要往最仔细里看。4颗699元,你最先看到的,是它的价标。金桃么?你差点当场就要闹出声来,还好,是你心里一直绷紧的那根弦及时拉住了你。你第一次来这家水果超市。他们说,这里是出了名的水果刺客。什么是水果刺客?你不知其意,后来,慢慢琢磨明白了,就是贵嘛。嗨,你习惯性地摸了摸额头,新词语幽灵一样飘在日子里,这一次,你又成了掉在词语后面的人。
工作后,你总是掉队,你也时常感到疑惑,为什么用尽了力气总也找不对方向。日复一日,你背上的石头越积越多,那个长队已经走得太远,剩给你的,只有四野的风声和尘土。你为这个发现感到沮丧,并未察觉脚下的积水已将鞋袜浸透,你拖着愈来愈沉重的步伐向前,却被拖入更深的水中。水从你的膝盖一直往上灌,接着,是你的嘴,你的眼睛。你本来已经放弃挣扎,是那个一闪而过的念头救了你。要不,去他们的世界看看。也许,你能在那里重新上岸呢?就这样,你怀揣的半个希望带你走到了这里。
你想走,眼睛却没有死心。反正,看一看也不误事的。你暗暗吁了一口气,身体稍稍前倾,两只手垂在裤缝,连呼吸都在无意间变得轻柔。那是一个朝圣者仰首望天的姿势,这样的姿势,在你,几乎是出自惯性。上学期间,在老师的办公室,在同学的聚会上,在每一个需要你出现的地方。工作后,面对老板,面对同事,甚至是迎面走来的一个过路人。你不是没有想过换一种姿势,抱手?叉腰?还有什么?你想了很久很久,还是没有结果。他们从不这样,在你能看到的地方,他们要么双手插兜,要么抖腿,要么倚墙,要么干脆坐下直瞪瞪地盯着世界里游走过的每一个人。你只好低头,也只会低头。那是你的身体最为熟悉的姿势。
你又想到了盒子里的桃。它们到底长什么样子呢?是黄是红?或者说是别的?你挺茫然。你能想到的,是一棵桃树,一次又一次地被筛选,一茬又一茬地被嫁接,一趟又一趟地被搬运,从古到今,从南到北,从高山到峡谷到平原。在漫长的空白里,你的想象还是回到了一棵桃树。树上,有一颗粉色的桃,拳头大,白乎乎的绒毛挺密地挤在一起,似乎想要以此证明它是一颗真正的桃。
老板走过来,一改往日暧昧的态度,有点矫作地严肃道,正宗的进口货,只此一家。你忽然就掉转了个个儿,你看见各式各样的脚从你的脑袋旁经过,每一只脚都碰了一下你的鼻子、嘴巴,还有下巴,没有人要打算避开你,更没有人为你停下来。红色的汁液经由你的耳朵流到了脖颈,手臂,最后流到地面。那是比昨天还要孤单的颜色。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桃说。
2
它也是一颗桃。不过,它的命运可算不得是桃的命运。它干瘪、瘦弱,就跟养育它的那片土地一样,没什么可说的。在城市的转角处,你遇到了那样的桃。
离开家乡以后,你第一次见到那样的桃。也是,那样的桃能有什么出路呢?在城市里,你见惯了各式各样胖乎乎的桃,哪里还会瞧上那样的桃。没有人会为那样的桃停下来。你从它的身旁走过,又掉转回头,即将走近的那一刻,你闪身进了街旁的便利店。
那只是一个瞬间的念头,你不确定,是否真的要买下它们。便利店里货架拥挤,你的突然造访成为一次意外的海啸。你茫然地在狭窄的空间里打转,你想,总要找到一个趁手的东西才是。收付款的滴滴声此起彼伏,在浪花的空隙里,你选定的,是一盒桃子味的口香糖。包装封面上,也是桃,饱满的桃,娇艳欲滴的桃,忘却前尘旧事的桃。
那个老妇人依旧坐在街沿上,依旧只有那些桃陪着她。老妇人着一身灰色长衣长裤,黑的灰的白的头发搅在一起,斑驳得一如田地里良莠难辨的稗草。污渍斑斑的褐色油布袋上,那些桃也灰扑扑的,活像从老远的乡下赶路而来,一时来不及卸下一身的霜风尘月。这个画面很容易就让你想起母亲,一样的风尘扑面,一样的孤立无援。
你想起了家里的那棵桃。起初,村子里只有一棵桃树,碗口粗,就长在崖边,大半边身子探出崖外。风过,雨过,雪过,桃树依然站在那里,迎接每天的日升一样迎接它的命运。年年月月,月月年年,无数人从那棵桃身边走过,像是随着流年的水波晃过,没有人会关心一棵桃树的光阴。
从新年的第一天起,你就开始了你的等待。屋后的柳梢青了,无数的花苞从桃枝上冒出来,先是指甲盖大小的粉红,跟着,整棵桃树都摇曳成一个粉色的新梦,渐渐地,粉红褪成残红。一场冷雨过后,青色的小果探出了头。在崖下的泥地里,所有的粉色隐入泥土,仿佛掩埋掉一个残破的昨天。
在你的时间里,从一朵花成为一颗桃,会经历漫长的雨季。南风、北风、东风,每一次风起的时候,雨季就开始了。一棵桃就是一滴雨,雨滴落下的时候,雷声就在你的心里游荡,你的担心层堆叠嶂,雷声响起一次,你的夜晚就坍塌一次。雨还是在下。你变得沉默。你揣满一身心事,在无数个清晨爬上岸来。那棵桃树也是一样。终于,在一个昏黄的下午,你看见了一闪而过的浅红。你望着那颗桃,像是望着一位晚归的故人。
你记得它。这棵树上的每一颗桃你都记得。你坐在巨大的喜悦里,想象着会有无数桃羞着脸走向你。那是属于你和桃的心照不宣。太阳藏到了山的后面,你站起身,怀抱着属于一只蚂蚁的虔诚走向那棵桃树。
你做梦都想拥有一棵属于自己的桃树。村子里,除了李树,就是梨树,偏偏那片崖边长了一棵桃树。所有的树都是有主的,唯独那棵桃树没有。鸡蛋大的桃被无数双手摘回了家,你茫然无措地站在一旁,像是无意间闯入别人的命运。
你遇见那棵桃树是在冬天。那是一个雨后,在马路边的草丛里,你一眼就看到了它。极矮小极瘦弱的一根苗,风还没来,就已经抱起身子瑟缩。你蹲下身,耐心地拔掉它周围的杂草,用石块,用指尖一点一点地刨开细碎的石子、硬邦邦的泥土。你看到了它的根,细细的,短短的,初生的乳白还未褪去,浅浅的绒毛如浮在水面的浮草,一股劲儿地朝四面八方张开。像是没有想好它的方向,又或者,在四处打探,一如生命的本能。
你把它带回家,种到了家门口荒掉的坡地里。从你出生,你的命运就系在了这片土地上。在庄稼地里,你跟在父辈身后,笨拙地学锄草,种花生、玉米、小麦、高粱、蔬菜,就是没有栽过一棵桃树。你虔诚地揉细所有的泥土,浇水,施肥,再认真地把它放进土坑里。那是你第一次感受到栽种的乐趣和幸福。桃树站在你面前的那一刻,你把身体放在青草地上,头枕泥土。天空是遥远的蓝色,从你的手缝望过去,云朵蓬松成一朵洁白的棉花糖。你在一个长长的梦里待到了晚上,直到母亲高声把你唤醒,该吃晚饭了。
那棵桃树第一次结果是你上高中那年。你无数次地想象过这棵桃树的花开。你从学校回来,三个指头大的桃已经从日子里跳了出来。你坐在桃树底下,没来由地就想到了以后。你会拥有很多很多的桃,很多很多又红又大的桃。它们会在树上成熟,会被郑重地摆进屋里,会被人郑重地握在手里。关于桃,那是你的第一次拥有,它只属于你。你说不清你是为那么多的桃感到兴奋,还是为你的拥有感到振奋。每一次坐在桃树底下,你都会在举世的想象里靠岸,下一次,下下一次,你每升起一次帆就像升起一次日出。
3
你还是没见着桃尖的那一点粉色。吃的东西人家要就给吧,你都这么大了还争。母亲先发制人,你的话还没有出口,她倒比你先一步委屈了。你一言不发走回房里,要体贴,要忍耐,要先人后己,你看到亘古传续的美德从墙面和屋顶穿过,留下一个金光灿灿的囚笼,庞大的影子里,你也是被照亮的一个。你想起了崖边的那棵桃树。桃的季节结束之前,那棵桃树的虬枝就被割得七零八落。秋天来临,它再一次在崖边长成一棵无人问津的桃树。你留着的那颗桃核已经变得坚硬,在无数遍的抚摸里,你渐渐懂得,可靠的东西从来不会柔软。
你身边总有人在离开。从初中起,课堂里的人群就开始“塌陷”,空椅子悠悠荡荡,多像地里歉收的庄稼。所有人都在后撤,你的同桌、后排、斜对面,他们退回“谷底”,不再回头。你也有了犹豫。麦子成熟的时候,你走进群山,弯腰,拉镰,无数的麦子应声倒下,你告诉母亲,你不想再念书了。母亲没有说话。麦子全部倒下,你坐在田埂的夜色里,忽然就感觉到了孤独。你埋下头,艰难地升起星群,山野茫茫,微弱的光亮几乎只在一瞬之间,你的灯盏摇摇晃晃,一如多年前遗落在井底的遥远月色。
第二年,你的桃开出了一树繁花。桃子成熟的季节,父亲把它们背到镇上,从清晨坐到中午,带回的是一小卷零票。但终于见到收成了。父亲专门给你打来电话说,明年,我打算追点肥看看。哦!你握着话筒,脑袋比嘴还要空荡。这一次,父亲没有过多计较,爽利地挂断了电话。你快要忘掉那棵桃了。
大学毕业,你继续留在读书的城市。村里人见了父亲就说,就等着进城享福吧。父亲抿嘴笑笑,锄头一放,把烟从裤兜里掏出来。包装盒新崭崭的,连折痕都影影绰绰。第一个月的工资到手以后,你给父亲买了烟酒,给母亲买了新衣,不算太好,主要是一点心意。几乎是一夕之间,父亲习惯了揣着烟出门,习惯了把烟分给路过的每一个人。薄薄的烟雾从父亲的头顶升起,黄昏降临,落日裹在烟霞里,有些蹩脚地临摹出一个虚妄的梦境。
母亲重新想起了你的桃树。她浇水、施肥,有些僵硬地举起手机,拍下那棵桃树的冬与秋,桃熟了,又眼巴巴地给你打电话问你要不要回去。你拒绝得干脆利落,毫不犹豫。你有更要紧的事要去做,再说了,山高水远地跑一趟,就为了一颗桃?那不是一个正常人会干的事。
母亲当然不再追问。在你和母亲的时间里,她退回到那棵桃树的位置。你学会了衡量,母亲也是。母亲开始变得很小,小得甚至比不上桃树上的一颗桃。
工作是你头顶镂空的纸塔。从你踏入这座城市,浮梯便从你的心里升起。你不擅水,那么多年了,你只会走岸上。你从你的此岸出发,抱定共存亡的决心,在风打雨倾里,紧抱不属于自己的命运,在想象中伸出一双瘦弱的鸟爪,奋力想要走得更快更远些。从后面看,你弓腰的樣子活像刚从蒸箱里取出来的大虾,遑论优雅,简直跟从容都毫不沾边。
你没有想过要回头,你也回不了头。你早已成为悬崖上的一粒孤尘,单薄得抓不住自己的影子,在你的身后,除了旷古的风,就只剩下旷古的埃尘。你脚下的虚空一日胜过一日,你告诉自己,习惯了就好了,就像习惯一双下雨天漏水的鞋,就像习惯冬天里跑风的棉衣。“见人三分笑,嘴要甜,脚要勤,要受得气……”你自觉不自觉地想起父辈的箴言,那是源自祖辈的天机良策,它们流传在每一代人的血脉中,如同命运降临于你。
三十岁那年,你并没有在城市里买房买车,甚至,连出租房都越搬越远。你坐在狭小的卧室,窗户很小,小得容不下肉身从那个出口飞翔。城市的夜晚和白昼轮番升起,你缩在屋角,偶尔也会想起山里的夜色。漫天的高楼,满街的人群,从过去到现在,没有人能跟你说起一颗桃和一颗桃的区别。
父亲和母亲的脸一天天地萎靡下去,仿佛他们犯下了滔天大罪。你把带回来的礼物堆在桌上,这一次,连母亲都显出了无动于衷的淡漠。眼睛落满你的全身,他们说,你开了一个坏头。
你张开嘴,千言万语最后还是化为沉默。父亲说,再没有见过比你还要无能的人。你的双眼布满血丝,堆积在心里的愤恨与屈辱轰然倒塌。你从椅子上站起,含蓄的双唇失去最后的笨拙。三十年的虚与实、假与真,列车一样呼啸着碾过你的身体,漫天粉尘落下,漫长的日子席卷而去,连故乡都化为乌有。
你是从母亲的视频里得知那棵桃树的命运的。父亲将它砍掉,把枝叶留在地里,把树干扔进草丛。母亲委婉地在电话里说过,留着干啥呢?光占地方,又当不得柴烧。那是你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命运。
4
你还是决定买下它们。你选,老妇人也在一旁仔细挑拣。这个好,这个也好。她出手迅捷,麻利得像是出门觅食的猎豹。她从这堆桃说到了这棵桃树。她说,树是前几年栽下的,就在城边废弃的老屋里。本来也没啥指望,没想到今年大丰收。原生态得很,一滴农药都没打过。也是我年纪大了,牙口不好,要不然,哪还有拿出来的份。
那家里总有人吃吧?你突然当了真,像是要为这棵桃鸣不平,抑或是想要跟她开个小小的玩笑。
你知道的,现在的人哪里会吃这玩意。你潜进水底,决心将自己送入更深的沉默里。你呢,买几个试试就好了,免得浪费嘛。她空出手,专心地看着你。
你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有那么一瞬,你甚至想,干脆全部带回去好了。是她拦下了你。就给两块钱好了。她抓起装桃的袋子,推开你好似推走一艘靠错了岸的船。
你把这些桃带去办公室。你觉得,它就是缺一个被看到的机会。总会有人喜欢的。上班,下班,一扇门接着一扇门地开,一扇门接着一扇门地关。你也曾想过要把它们从背包里拿出来,你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是因为同事带来的那颗桃。
那颗桃从新西兰乘坐专机远道而来,光论出身,就足以造梦。同事举着那颗桃,一边削皮一边细述它的来历,而后总结似的说道,稀缺也是品质的一部分。在附和的人群里,你也是其中一个。
同事一进公司,就被安排到了你的办公室。领导把你喊到一旁,半是玩笑半是严肃地说道,小张,以后要好好配合姐姐的工作。你哦哦应着,从始至终,连拒绝的念头都未曾起过。同事已经辗转了五六个公司,用她的话来说,上烦了就换,本来也不指着这口饭吃。你暗暗不屑,靠家里算什么本事,在每一次被人群拥裹的时候,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是把腰杆挺得最直的那个。
单位在城市的中心,27楼。毕业那年,你是班上第一个拿到offer的人。学校用首页新闻推了你一个星期,那么好的公司,多难得的排面。来找你取经问道的人络绎不绝,你怔怔望着他们,茫然得如同一个问号。
意料之外的惊喜后劲过于盛大,你在宿舍床上躺了整整两天,第三天,你坐公交去公司楼下坐了一天。你想象起岸上的生活,在来去匆匆的脚步里,慌张得如同一条被河流无意卷入其中的牧羊犬。
你打电话给父亲,谈及以后,你说,你一定会好好工作。电话那头兴奋地倾听着,郑重其事地把流传千年的古训交给了你。你们都没有说出来的话是,你一定会留在这个城市。金光大道从你的脚下铺展到很远的远方,你的全部想象都来自面试官雄辩滔滔的绛色嘴唇。你当了真。那时的你,背负一身想象,已经在粉色的原野走了二十多年,你早已习惯用梦境安慰梦境,也用梦境勉励现实。你还不会明白长大的意义。
同一批进入公司的同事有了更高的职位,新来的同事也开始晋级。你始终原地踏步。是你的能力还有待提高。第一次,你如是劝慰自己。总会有出头那天的。第二次,你信得迟疑又迷茫。熏黄的灯光从你的脚底溜开,你追隨灯光而去,在一片白茫茫里,蜿蜒的小道踪迹难寻。回头想起,那多像是一个写给无知者的笑话。他们对你撒了谎。你不舍昼夜地在谎言里跋涉,你不会想到,一个谎言过后,延绵的是由无数个谎言编织出来的群山和羊群。
你已不再相信。从那一天起,无数的针孔从你的身体里张开,你开始变得绵软。你已不再坚硬。那些桃也是。你把背包扔进出租屋的角落,每路过一次,它们就往角落里缩得更小一点。你已经忘记它们了。在不见天日的光阴里,时间没有忘记那些桃。它们认真地变软,认真地腐烂,认真地完成一个被遗弃的命运。那是桃的命运。
若干年后,也许,这些桃核还会发芽。在山间,在林里,在垃圾填埋场,谁知道呢?
【作者简介】
王亦北,本名王亦,1994年生,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主要进行小说、散文创作,作品见于《四川文学》《草原》《西部》《青年作家》《滇池》等刊,有作品被《散文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等刊选载,居成都大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