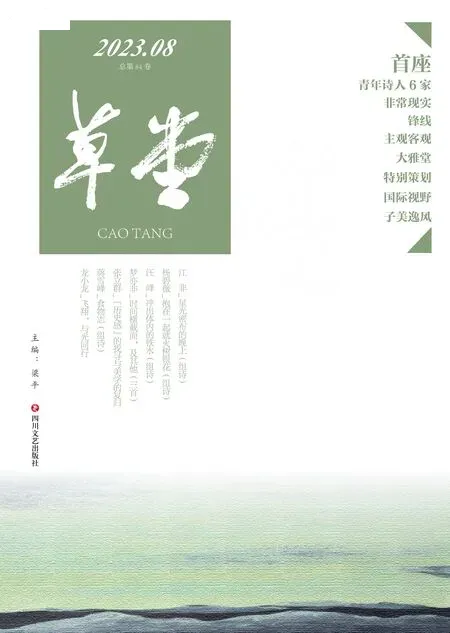昨天像大剧院里展演的情景剧(组诗)
◎程 渝
[外 婆]
黄昏中:她坐在病榻,
望向天空,出现残月的天空,
念叨对死亡的恐惧。
劝导外婆的姨娘,
她们没有临近过死亡,
她们的视野,只是眼前的黄昏。
外婆怎能听得进去,
她拥有苦蒿的大半生:
年轻丧夫,摆摊拉扯大五个孩子,
在晚年安得清福。
她念叨着,像个孩子,望着黄昏。
我和她望见的,是同一片黄昏。
黄昏下,我又看见了:
在某个黄昏里,她追着我跑,叫我慢点儿;
喂我吃冰糖,叫我慢点儿……
——黄昏呀,你能不能慢点儿,
我还没准备好,
接受日落。
[演 员]
昨天像大剧院里展演的情景剧,
演员退场,观众离席,
我在舞台中央的光圈里
期待再次出演。我躺进漆黑的房间,
睡去,像是中场休息。
又逢新的一天。
演员陆续登场,观众先后到来,
今天的我演着昨天的剧目。
厌倦的演员离场;看烦的观众离席。
我照旧表演。
台上依然有演员,台下依旧有观众。
每天有不同的演员和观众。
如果哪天我尽失演员,
我仍会表演。演的是独角戏。
如果,我不再有观众,
不,不会有那天。我是我自己的观众。
直到,我从大剧院退场,
幕布降落;属于我的演厅不再被使用。
[嫂 子]
若不是受够伤害,谁愿选择
离婚。最坏的好结局。我说的是
我的嫂子。她晒出协议书,
我询问她。她像块石头。
之前,他们也离过。那次,
她是个泪人。她开口讲述
哥哥的种种。我看见:她眼里的死水
和她挂满的憔悴。话到一半,
她倚靠着墙,喝了口水,
吞下要说的话,连同其他伤心事。
好一阵,她再次开口:
“明天,我要去往远方
这里有太多羁绊,治愈自己是件难事。”
或许,她想说的都说完了。
我们就这样站着:像山口两岸的崖壁
对断裂的地方,只字不提
[鸟]
雪白的,不知道是什么鸟
在牡丹湖湿地公园,水没草脚的洼地上
站立,啄羽
——有两只,搏击长空
还有一只
在无形的铁笼里,刚写完这首诗
[与友记]
我们在垫江的长兴水库
共赏野鸭泅渡。沉郁的水面
渐被太阳晴朗;滩涂的泥土
还因昨夜的雨水,暗藏忧伤
我们沿着边缘闲步
每一步,都先行试探
尽可能地,不触碰他物的软处
一行人就这样缓慢地行走,梓毅在最前
也是第一个,陷入泥泞
他拔出脚,再对鞋施救
挥手说着无碍。一股豪迈的气息
在我们间上升。夜晚
悄然降临。我们回到酒里
多与少不再是我们
判断感情深浅的标准
因酒诞生的情谊,也不需酒来续命
——以情景剧《半条被子》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