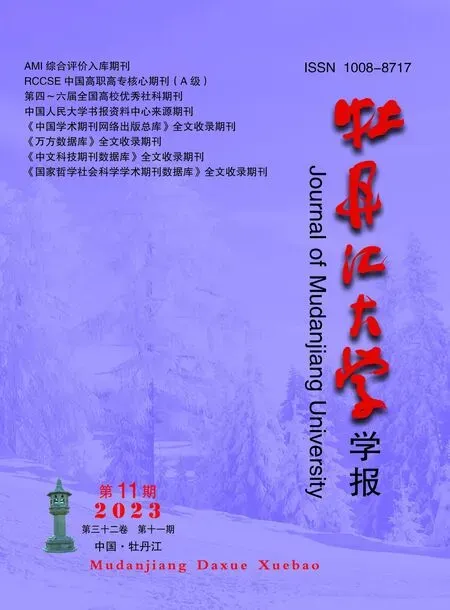自主主体缺位下的母性放逐
——《温柔之歌》中的女性镜像
陈思宇
(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自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中提出女性是相对男性存在和定义的他者以来,自主女性主体的构建一直是女性主义关注的焦点。露丝·伊里加蕾(Luce Irigaray)、安托瓦内特·福克(Antoinette Fouque)、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则进一步强调“母性”及“女性谱系”对女性主体建构的重要性。拥有摩洛哥和法国双重国籍的蕾拉·斯利玛尼(Leïla Slimani,1981- )对女性的自由尤为敏感,多次声明其女性主义者身份,并强调“母性问题在文学中的挖掘不够多,由女性挖掘的则更少”[1],她在不同访谈中说明其写作意图:通过书写生活中出现的事件,打破围绕“‘母亲的本能’建立起来的神话和谎言”[2],并“探寻社会与女性之间的冲突”[3]。斯利玛尼的小说《温柔之歌》(ChansonDouce)2016年问鼎法国文学最高奖龚古尔奖,此书刻画了一对特色鲜明的女性人物——主人米莉亚姆和保姆路易丝。作为母职之替补的路易丝与米莉亚姆紧密相连,二者又因主仆身份、男性/女性气质的差别而互为对立。她们的欲望生成与转变所构成的矛盾张力贯穿全书,成为情节发展的主线,资本社会下两位主人公主体意识的建构及变化由此呈现。保姆杀婴案背后,因自主女性主体缺失、女性谱系消解、主体间性断裂引发的母性危机与人性危机也是小说的关切所在。
一、自主女性主体的缺失
米莉亚姆和路易丝形象迥异,斯利玛尼对她们外貌、性格、欲望、行动的描写揭露了二者的主体意识。作者对女主人米莉亚姆的外貌着墨甚少,似乎有意消解其性别特征。我们几乎找不到关于其身材长相的信息,只知她从不化妆,常穿男装。而路易丝则符合模式化女性形象,作者对其穿着打扮有细致入微的描写:柔弱瘦小,像金发娃娃,优雅温柔,身着蓝色娃娃领裙子,亮皮鞋上缀着蝴蝶结,涂着甲油的手散发花香……若路易丝代表女性固化形象,米莉亚姆则更符合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提出的性别操演。巴特勒认为社会性别由文化建构,性别化的身体及其表现出的行动、姿态与演绎实践均“可以解释为操演性的”[4]。巴特勒利用扮装现象指出性别身份的不稳定性和建构性,呼吁打破二元生理性别,发挥主体身份建构的能动性。米莉亚姆追寻多元个体价值,一直尝试打破性别及少数族裔出身带来的不平等:缺少家人支持,她仍坚持争取受教育及工作的权利;拍摄家庭照时站在镜头后——男性观者的理想位置;在法庭上充满战斗力地为男性辩护……虽无详尽外貌描写,读者却能感受到米莉亚姆的自信与生命力。作者还特别选取不同叙述视角塑造两位女性人物。涉及米莉亚姆的叙述几乎全部采用全知全能的零聚焦,鲜明刻画了她企图把控命运的强烈自主性,偶尔几处透过保罗和保姆的内视角叙述也只是进一步衬托其个性并强化其男性气质:严谨、正直、生硬、遵从规矩,有时甚至不太通融。而上帝视角的描述也从侧面暗示了米莉亚姆被权力话语挟持的命运。对保姆路易丝的描写则运用了更多内聚焦,使其形象飘忽不定:米拉觉得路易丝是天下最美的女人;格林伯格夫人、埃尔韦、瓦法尤为欣赏路易丝的优雅做派;而雇主和房东有时却觉得女性化十足、完美柔弱、沉默寡言的路易丝让人“恶心”。伊里加蕾指出,“女性气质”是男性再现系统强加于女人的角色、形象和价值,女性会在扮演女性气质的过程中失去自我[6]。18世纪以来,尤其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指南中推崇的“屋子里的天使”所代表的病态美已不合时宜。路易丝给读者带来的不确定审美体验也从侧面反映了其独立主体的缺失。
黑格尔(G. W. F. Hegel)将欲望视为自我意识之本质,拉康(Jacques Lacan)则借鉴黑格尔的关系性自我意识(主奴辩证法)揭示个人主体不能自我确立的事实,指出人只能“在另一个对象化了的他人镜像关系中认同自己”[7]。那么米莉亚姆和路易丝的欲望又在何处?路易丝出现前,主妇米莉亚姆渴望像丈夫保罗一样拥有事业,完整其社会角色。白人保姆路易丝不仅能使她走出家庭,实现传统性别身份上的倒置,还能让北非裔的她获得种族身份上的倒置。离开家后,米莉亚姆的欲望指向的是上司帕斯卡的欲望,她疯狂工作以获得认可。福柯(Michel Foucault)将主体看作权力关系的产物,“设定标准、规训、内化标准‘三位一体’的权力的运作方式对每个人进行着全面塑造”[8]。社会文化所宣扬的事业与家庭双赢的“成功形象”已被米莉亚姆内化为理想自我,她完成了自我驯化,所作所为均是为了满足资本社会宣扬的“对于认同以及挑战自我极限的渴求”[5]37。即便主体的能动性在性别操演论的指导下得以建构,主体的塑造仍受制于权力话语关系,而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对传统女性主义的质疑与反思正在于此:“在现存秩序中谋求女性的权利和地位,就存在着被男权话语俘获或被现存体制同化的危险和趋势。”[9]忽略性别差异,寻找无性别或中性化的表达会重回男权逻辑体系的控制。追求平等独立的米莉亚姆看似拥有很强的主体性,掌握人生主动权,收获事业的成功,但也是这一体系的牺牲者,甚至极端地想摆脱他者以获得自由。斯利玛尼的两部小说《食人魔花园》和《温柔之歌》中,作为妻子、母亲的女主人公都产生过相似念头:“人们只有在不彼此需要的时候才会是幸福的。”[5]40“他人”成了我“自由”的限制和重负,是空洞、异己的敌对者。米莉亚姆隐藏起内心苦涩,酒醉时才“抱怨自己所承受的这种疯狂的存在,所有人对她都是那么苛刻”[5]130,但在此之后她收获的却是来自家人的连番攻击,她感觉自己被杀死了。之后我们看到米莉亚姆逐渐将同情心悬置,不再为女性发声,放弃帮助被前夫债务压垮的路易丝,听从保罗建议对她冷漠相待。
处于从属地位的路易丝则一直被限制于家庭空间中,她的幸福与雇主家庭相连:她产生“灼热的、令她感到痛苦的信念,那就是她的幸福取决于他们”[5]77。谢林·奥特尼(Sherry Beth Ortner)曾指出,女性的生理、社会、精神境况使其存在被视为比男性更接近自然,因而在历史上常被界定为社会/文化组织的更低级别,只能负责低层次的自然向文化转化的工作(家务、喂养照顾孩子、帮助孩子社会化、服务男性)[10]。而保姆这一职业群体正承担了上述角色,也更易陷入“身份认同及人际、情感危机”[11]。路易丝是老旧刻板女性形象的化身,前雇主、前夫曾大肆贬低其工作价值,但她仍将自己认同于服务家庭的“天使”并禁锢于角色中:“仿佛是王宫的陪侍女官、总管、英国女护士。……刻意模仿上流社会贵妇人的做派”[5]197。维护在“家”中的地位便是路易丝的事业,她的主体与家相连,以至于存在于任何其他空间都显得不合时宜——“像是走错了故事的人物,身处一个陌生的世界,注定要永远流浪”[5]220。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M.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曾综合数位社会历史学家的研究,指出教育女性温顺、屈从、无私便是让她们放弃自我主体并走向死亡[12]。“即便挣扎也毫无用处。她只能听之任之,这么漂着、被占领、被超越,面对任何情况都处于被动状态”[5]154,路易丝“瓷娃娃”般的外表,她的抑郁症状,对公共开放空间的恐惧也是主体性缺失的表征。成为米莉亚姆的临时替补后,路易丝协助主人实现了理想家庭的幻梦,在主人家慢慢建起小巢,直到米莉亚姆对她说:“您就是家里的一分子”,路易丝产生成为家庭一员的幻觉,却忽略了雇主始终与她用“您”相称以保持距离。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曾强调替补概念中包含的双层意义:替补是剩余物,是丰富另一个完整性的完整性,使在场叠加;替补又是为了取代空缺、标记空缺而存在,双重意义的叠加使替补者(替补物)常常以为自己就是那个完满的实在,而忘记自己其实只是要填补前者的空缺[13]。德里达还援引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忏悔录》中“危险的替补”、吸引人的“致命的优势”说明替补会使欲望脱离自然路径而走上歧途。
作者对路易丝“凝视”的描写清晰地展现她在欲望裹挟下自我定位的变化。路易丝先是统治了公寓中的物:“像个将军,在视察自己征服的领地”[5]27,又用“捉迷藏”制造分离焦虑,驯服了孩子,以胜利者的姿态望着他们。与保罗和米莉亚姆一同度假旅行让路易丝改变巨大。艾瑞克·李德(Eric Leed)强调,凝视客体在表面审美偏好背后反映了旅行者对不同凝视对象和凝视方式的选择,也是旅行者自我身份的定位,通过彼此在凝视对象和方式上的异同与对方产生身份认同或排斥,这是一个将自我与他人归入或排除于某个身份群体的活动[14]。斯利玛尼用详尽笔触描述路易丝在海船上观看一个晒太阳的女人,度假的人群纷纷加入其观者行列。此时的路易丝不再是保姆,而是游客中的一员,家庭中的一员。之后,她当着孩子父母的面把米拉推倒,与雇主共进晚餐……路易丝越来越多的欲望被唤醒,开始欲望着雇主的欲望。与路易丝同样身份的其他保姆只隐约在雇主那里辨认出自己的欲望,以偷窃占有“主人之物”的方式假想自己的主人身份。路易丝则企图成为一家之主,想将保罗和米莉亚姆放置在钟罩下观看[5]77。萨特 (Jean-Paul Sartre)提出,夺回自由需要把自己选择成为注视他者之注视的人,将自我主观性建立在他人主观性的崩溃之上,这种对他人冷漠、盲目的态度可以使“我”表面上摆脱对于在他者自由中存在之危险的恐惧[15]。随后我们看到保姆更具攻击性的“凝视”。在保罗斥责她给米拉化妆时,她没有请求原谅,眼神中透露着冰冷的沉默和骄傲。得知孩子们要离开她去度假,路易丝的阴郁目光中仿佛掠过了暴风雨。丈夫去世、女儿出走后,孤独的路易丝在米莉亚姆家中感受到打破了阶级隔阂、稍纵即逝的温暖。她孤注一掷地想维护在雇主家的地位,一方面由于其附属性主体建立在“服务激情”之上,另一方面则在于她对温暖人情的渴求。可她忘了自己的替补身份,孩子会长大,她终将被抛弃,“月光下的路易丝轮廓模糊,……她即将消失在边界的那一边”[5]220,在路易丝与雇主家庭的联结即将被切断时,她的主体也随之消解。
无论是追求平等与超越的米莉亚姆,还是甘于附庸地位的路易丝,都遭遇了某种异化。正如伊里加蕾指出,“被阉割”的母亲或只知喂养孩子的母亲,都不是母亲的本来面目,而是被父权制文化扭曲了的“菲勒斯的母亲”。拉康将人的欲望视为他者的欲望,婴儿欲望的不是母亲,而是象征秩序下母亲的欲望,是对所匮乏的菲勒斯(Phallus)的欲望[16],而不在场的菲勒斯标志着绝对的空缺,在缺位欲望的裹挟之下,小说中自主女性主体的匮乏更导致了母性的消解。
二、被放逐的母性
伊里加蕾曾指出,西方文化的基础不是弗洛伊德假定的弑父,而是弑母。福克也通过援引神话证明西方文化传统对女性身份的嫉妒和憎恨。《圣经》、希腊神话、希腊悲剧都将女性先祖抹去。如果将女性排除在象征秩序之外是父权文化体制有意为之,斯利玛尼笔下的两位女主人公即便阶级、族裔、职业、追求迥异,却拥有相同命运——将“母性”自我缴械,囚禁在家庭和母亲身份中的她们渴望从中逃离,一如两位命运与杀婴复仇相连的神话原型:莉莉斯(Lilith)①和美狄亚(Medea)②。但斯利玛尼没有拘泥于正、反面女性符号的绝对对立③,两位女性人物穿梭于两极之间,展现出多义性。
米莉亚姆(Myriam)④的名字源自Mary(圣母玛利亚)的古希伯来语或古埃及语变型。名字透露了主人公的法国外来族裔身份,也揭示了其反英雄悲剧。这位生活在巴黎的年轻母亲不如圣母般完美,也没成为婴儿的拯救者。小说开头就已揭露儿子亚当的悲剧——婴儿已经死了。一切似乎始于米莉亚姆无法再从家庭“坐牢般的幸福”中获得安慰,她意识到孩子可能成为“成功和自由的阻碍”,她感觉像“殉道者”一样为别人牺牲了生活的另一面,她不想再扮演勇敢母亲的角色。在工作中找回自我的她不愿回家。我们看到米莉亚姆对母亲身份的排斥,她明确拒绝再次生育,还向孩子讲述宙斯在头颅中孕育战争女神雅典娜的故事。米莉亚姆对父权文化体系的认同正像是追求平等的莉莉斯自我规训的当代讽喻。
路易丝的出现则总伴随着“窗”的意象,喜欢看外面风景的路易丝难免让读者想到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笔下倚窗而望的包法利夫人。临界性视角透露出她心底渴望不同的生活,开始想要逃脱替补母亲的身份,摆脱平庸琐碎的日常:“关在公寓里,她常常觉得自己要发疯”[5]110,她不能“在孩子们身边找到安慰”[5]213,“再也忍受不了孩子们的哭叫、任性”[5]215。但路易丝的存在似乎只能与“家”相连,她清楚地知道,跨出那扇窗,等待她的是无法克服的生存危机:巨额债务、房东威胁……小说结尾,即将走到“窗外”的路易丝也在走向毁灭。她所期盼的新生儿终究没有来临,她在这场欲望主体间的确认之战中以杀戮远离了母性。
不可否认的是,米莉亚姆和路易丝都曾展现出未受外界意识影响的本真母性:“弯腰站在米拉的婴儿床头,米莉亚姆完全忘记了外面世界的存在。她所有的野心不过是让这个虚弱的、喜欢乱叫的小姑娘多吃几克奶”[5]10;“路易丝喜欢用背带把亚当绑在自己身上。她喜欢孩子那胖乎乎的小屁股蹭着她肚子的感觉,喜欢孩子睡着的时候流到她脖子上的口水”[5]31。但我们很快看到象征秩序、社会能指体系对母性的侵袭,母性主体进入了与想象界相联系的镜像阶段,将他人投射为自我。分娩后的米莉亚姆拒绝与外界建立关系,但逃避终究是徒劳的,偶遇帕斯卡后,米莉亚姆想象前者会向别人讲述她的悲惨——没有人人都认为她该拥有的事业。小说揭露了象征秩序中母亲们的失语常态:“目光迷离的母亲。因为最近才分娩,仍然停留在世界的边缘。”[5]111米莉亚姆害怕陌生人知晓其全职母亲的身份:“她根本没什么好说的,她觉得自己差不多就是一具行尸走肉。”[5]12-13出现在雇主朋友聚会上的路易丝也一样,“她就像个外国人、一个遭到流放的人一样不自在,完全不懂周围人的语言”[5]60;除了乱了章法的童话故事,“路易丝讲不了别的,她就像陷入流沙一般陷入了词语的泥潭”[5]213。故事最后,病床上的路易丝被永远禁锢在沉默中,詹妮弗·豪厄尔(Jennifer Howell)则将此视为某种暗示:“路易丝或许从未拥有过自己的话语。”[17]失去话语权便丧失了独立主体身份,这也正是小说中女性人物纷纷想从家中“逃离”的原因。
米莉亚姆从“玛利亚”变为“莉莉斯”,路易丝从无私的罗马育婴“母狼”变为受伤的情人“美狄亚”,这与“母亲”在主流社会中的失语状态紧密相关。加拿大学者丹尼尔·达格纳斯(Daniel Dagenais)在《现代家庭的终结》一书中强调“家庭制度的危机源于波及所有家庭成员的身份危机”[18],伴随着母性的放逐,“家”被抛弃,只能与“窒息”“坐牢”“混乱”“腐烂”“笼子”“囚室”等字眼相连,保罗的噩梦似乎早已隐喻了“家”的异化——“家变成了一个鱼缸,里面满是发霉的藻类,一个动物的窝,空气闭塞,里面都是毛茸茸的动物,一边嘶嘶叫着一边转圈”[5]133。幼子亚当的死亡也正预示着欲望链条之上母性危机所引发的人之危机。
伊里加蕾与福克认为恢复母性谱系才能建构与男性文化相匹配的女性文化,依靠女性间的言说才能让女性拥有自己的话语。而《温柔之歌》也恰恰揭示出女性谱系断裂的事实。小说中的每个角色都很孤独,未能获得外界支持:“这就是她的命,也是很多其他女人的命。没有一刻能有地方容得下她,给她温暖。没有一点建议,可以从一个母亲传给另一个母亲,从一个女人传给另一个女人。”[5]131路易丝曾在米莉亚姆的赞许中发现自我,看到人生的其他可能。而两人关系的破裂及周遭的冷漠态度让路易丝心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冰冷的壳”[5]215,直至成为杀婴凶手。痛斥米莉亚姆没有履行母职的西尔维娅,假装没听懂路易丝苦衷的格林伯格夫人,她们本来或许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小说结尾,女警官试图重现案发前家中的场景,作者也设计了叙事者、女警官与路易丝三者的视角融合以表现女性间的共情。
三、结语
小说书名《温柔之歌》来自于法国家喻户晓的摇篮曲《一支温柔的歌》(Une chanson douce),反语标题为这一取材于2012年纽约保姆杀婴案的小说蒙上了一层反童话悲剧色彩。作品采用的经典叙事模式预示着两位女主人公的关系从平衡走向冲突,二者寻找各自主体性的过程也遵循同一模式,反复手法营造了作品的多重张力,凸显了女性主体建构的困境。小说中的性别讨论、对母性的思考打破了传统的男女二元对立,将阶级、种族等问题融入其中,在彰显女性符号复杂性与丰富性的同时,我们看到资本社会中被忽视的母性,主体间的冷漠及人的孤独无助。斯利玛尼透过女性视角,表达出对主人公境遇的同情以及对“人”之命运的关切,揭露“亚当之死”背后的“人之死”隐喻,更提出了构建女性谱系及面向他者的伦理召唤。
注释:
①据犹太教文本记载,莉莉斯是亚当第一任妻子,与亚当同为泥土所生,她要求平等不愿臣服其下,说出上帝之名后离开伊甸园来到红海魔鬼的领地。上帝每日杀死她与魔鬼的后代作为惩罚,她则不断杀死亚当后代作为报复。
②科尔喀斯的公主美狄亚精通魔法,为帮助一见钟情的伊阿宋不惜杀弟叛父。伊阿宋移情别恋后,美狄亚由爱生恨,杀死两幼子以泄愤。
③林谢·奥特尼在《女性之于男性是否如同自然之于文化?》(Isfemaletomaleasnatureistoculture?)一文中指出女性符号常呈现两极倾向:颠覆的危险女性符号(女巫、邪眼、经期污染、去势母亲)和超越性女性符号(母性女神、救赎者、正义化身等)。
④Myriam或Miryam也译米利暗,此名最早见于《出埃及记》。法老下令溺死所有希伯来新生男婴,摩西父母将儿子放在河边,长姐米利暗在远处观察,见法老女儿对婴孩动了恻隐之心,上前提议找乳母替公主养育孩子并喊来母亲。摩西成为埃及公主养子,还得以在生母身边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