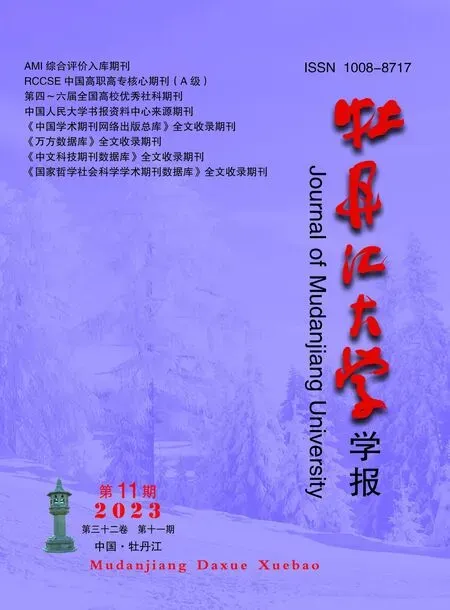时代脉搏的反映者
——程造之现代长篇小说创作论
董卉川 赵艺佳
(青岛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程造之,1914年7月出生于江苏省崇明县(今上海市崇明区),原名程兆翔,笔名有韶紫等。20世纪三四十年代,程造之创作了被后世誉为“抗战三部曲”的三部长篇小说《沃野》《地下》《烽火天涯》,涉及各个阶层的人物,摹写广阔的社会生活,反映人物的悲剧命运,为时代留下了一份生动的见证。程造之的文学创作成就并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长时期以来他成了文学史上的“失踪者”,被学界忽略。程造之的现代小说表现出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文艺作品要反映出时代的脉搏,我想,青年时期的我没有辜负了时代对我的要求吧”[1]。他以鲜明自觉的现实主义立场记录社会众生相,具有史诗的品质。程造之的现代长篇小说在反映时代的同时,又呈现出对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碰撞、交融下生成的畸形社会的批判与哲理深思,既与时代紧密结合,由时代出发,又不囿于时代,具有跨越时代的鲜明特性。
一、抗战时期乡土世界的全景绘制
程造之的现代长篇小说具有广阔的社会视野,构造了一个完整的乡土世界,绘制了抗战时代乡土世界的世相全貌,展现了大变革、大动荡时代下,现代工业文明与原始农耕文明的碰撞。他以敏锐的眼光、犀利的笔触,描写和揭露了乡村中的种种社会问题。
《地下》《沃野》是剧情相连的两部长篇小说,全方位地反映了抗战时期苏北乡村——苏北盐垦区人民的游击战争、垦荒历史和社会世相,共同构成了一部完整的“苏北现代盐垦史”①。
面对敌人的侵略,大旺村、白狼村等苏北地区的农民自发组成游击队,与敌人作战,用生命捍卫家园尤其是土地。在农耕文明中,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大旺村的土地被侵略者占领毁坏后,盐垦区广阔的、未开垦的“沃野”给了他们延续生命的希望,“那咸的而肥沃的黑土,正表明她是有着无限的精力,可以滋长出无限养育人类胃袋的庄稼,小麦呀,蚕豆呀,葡萄呀,……怎么数得清!当然,她现在还没有被人动过,好像以前一径给人家瞧不起,或是忘记了的一样。那就是处女一般待人开发的原野呵。”[2]378小说中将农民对盐土的改良利用进行了细致描绘,“天气好到极点。泥土给犁耙一割开,经不住太阳的蒸晒到傍晚,白皑皑的盐花就晒出来了。夜里下起雨来,盐屑冲到开好的引沟里去。明天太阳又把盐花晒出来了。但盐花会一天天少下去的”[3]29,由此再现了苏北盐垦区的垦殖方式,“开沟排盐和引淡冲洗,也是改良利用盐土的基本措施。当陆地脱离海水影响之后,在自然情况下,虽亦能逐渐脱盐,但历时较久,不合于积极发挥土地生产潜力、促进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要求。如经开沟蓄淡,引水洗盐等的技术作用,就可以大大提早实现改良利用的要求”[4]95。
小说在展现农民与土地血肉相连的同时,也揭示了现代工业文明对原始农耕文明的入侵和影响。“盐垦区委员会”在本质上依然是“若干地主的联合租栈”[4]54,却也形成了现代企业的雏形,“先将什么会的名义改组为公司……什么是都应该科学化一点。像这样蛮荒的盐田,一方面用着人力,一方面我们想起俄罗斯的进步了,去买几部曳引机来……管理方法总之尽可能要科学化……我们应该开设义务小学二所……我们应该四面八方地去经营。不要死着眼在一点上。”[3]64-65客观上推动了盐垦区经济的发展。盐垦区委员会设立了石灰厂、砖厂、草纸厂,分别被命名为盐垦区第一、第二、第三工厂。盐垦区委员会在工厂实行日夜两班的现代化作息制度,并从盐垦区垦殖的农民中招聘工人,从而使农民的社会身份发生了变化,在工厂做工的盐垦区农民,上工时的身份是工人,放工后的身份则是农民。
程造之细致描绘了抗战爆发后乡村衰败、混乱、萧条的现实境况,以及农民的悲惨命运,揭示了造成上述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既是侵略者的暴行所致,更源于人性的丑恶、人类的互害。
《地下》《沃野》中有几路游击队伍,除了“老独”“罗三”率领的队伍一心抗日,“关德”“钢丝马甲”“潘大成”“朱古律”等人的队伍均是以抗日为名,实则行使绑票勒索、杀人越货的勾当。《沃野》中,“关德”和“钢丝马甲”的队伍不约而同的先后绑架了盐垦区委员会的委员长“国柱”。为了争夺盐垦区的控制权,“抗日队伍”内部和“抗日队伍”之间经常发生火并。《烽火天涯》虽描写了抗战时期都市上流阶层的全貌,但也涉及了南京沦陷后南京农村的某些世相。南京沦陷后,“吴昔更”“魏福基”加入了当地百姓和未能及时撤退的军队组织的游击队,在南京周边的乡村同侵略者展开了游击战。由此揭露了同一游击队内和不同游击队之间的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各个游击队相继成立后,队伍内部的成员为了得到队长职位,彼此勾心斗角、心怀鬼胎。各个游击队均妄图一家独大,彼此落井下石、相互吞并。在现代文明的入侵下,乡土世界那纯朴的自然文明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已被破坏殆尽,人性被金钱腐蚀,金钱成为主宰一切的源泉。丑陋的国民性依然根深蒂固。
程造之以温厚的历史意识,为苏北盐垦史作一忠实描绘,通过游击战争、垦荒历史和社会世相全面呈现了抗战时期的壮阔画卷。他以敏锐的嗅觉探寻、揭露乡村中的种种社会问题,揭示现代文明冲击下人性的异化,怀抱启蒙精神对国民性进行批判。
二、抗战时期社会群像的深度塑造
程造之秉持记录时代、书写时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深入沉潜的姿态,观照各个阶层、阶级,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无不网罗其中。在他的笔下,既有理想主义的民族资本家,也有唯利是图的地主乡绅;既有麻木愚昧的旧农民,也有逐渐觉醒成长的新农民;既有进步的时代青年,也有无法抵抗诱惑而堕落的新女性;既有上流社会人士,也有小知识分子……程造之塑造了众多生动的人物形象,绘制出时代人物的精神图谱。
《地下》《沃野》中的“庞国柱”是民族资本家的代表,人如其名,他是盐垦区的柱石,虽有资本家追逐利益的天性,也有着强烈的爱国心与责任感,具有较为高尚的人格。侵略者毁灭了大旺村等村落后,他积极联络并请求各村的地主乡绅向难民们发放赈灾粮食;他组建了“盐垦区委员会”,引入现代化的企业制度,建立工厂,发展经济;他提出“教育普及,男女平权”的口号,积极筹建学校;他面对土匪汉奸的绑架禁锢和攫取盐垦区股份的无耻要求,宁死不屈。他是一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认为只要用心做事,就能成功,“环境?敲碎它呀。困难?在国柱的字典里根本没有这两个字。国柱先生是一位道地的实行家。说起‘做’,就非得做不可。”[3]49理想终败给了残酷的现实,他辛苦筹建的盐垦区先被“关德”的队伍占领,后又被“钢丝马甲”的队伍霸占,反抗的“庞国柱”竟被“朱古律”锯掉了一条腿。“庞国柱”的父亲“庞学潜”则是老式封建地主乡绅的代表。“庞学潜”痛恨侵略者,主要源于他在大旺村的产业被侵略者毁灭。他却不敢反抗侵略者,也不敢反抗侵蚀自己利益的土匪汉奸,害怕财产将在反抗中毁于一旦。他利用自己盐垦区委员会委员的身份,贪污公款、中饱私囊、唯利是图,只求自己家业的壮大。
《沃野》中的“李三斗”是中国老派农民的典型——强悍倔强与善良质朴,迷信愚昧与英勇无畏,粗鲁冲动与吃苦耐劳的结合。“李三斗”偏爱长子“寿发”,对小儿子“阿荣”终日恶语相向,源于爱妻生产“阿荣”时不幸离世,便认为“阿荣”是灾星,克死了爱妻。当“阿荣”被土匪汉奸抓住后,“李三斗”竟下跪为儿子求情。他有着中国农民吃苦耐劳的传统精神,“自己耕起田来,从没哼过一声吃力,打战争中跋涉过来,骨力益发坚硬了。就是做活的时候干不上来,自己相信他还跟儿子们劲道不差到哪儿。”[3]21
“阿荣”“雅兰”是青年农民的代表,面对资本文明的入侵,他们不再安于现状,与土地分离。“阿荣”不像父兄“李三斗”“寿发”那样依恋土地,这也是李家父子矛盾的根源所在。“阿荣”在“雅兰”的介绍帮助下成了盐垦区的一名工人,最终脱离了土地。“雅兰”曾独自一人到城市的纱厂做工,抗战爆发后,纱厂被炸毁,她又回到乡村。城市的经历使她懂得了“资产革命”与“阶级斗争”,“女性独立”与“男女平等”,初步具有了新女性的时代精神。“阿荣”最初有着农民阶层的某些局限性,懦弱自私、眼光窄狭,囿于小我之中,只希冀赚钱娶妻。在现代文明、时代精神的影响下,他逐渐成长成熟并觉醒,后来主动加入游击队,想要在动荡的大时代中成就一番事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曾主动带领盐垦区妇女到委员会示威,要求委员们在新成立的工厂中为女性安排岗位,喊出过“教育普及,男女平权”的口号,作为大旺村乃至盐垦区最早觉醒的青年女性代表的“雅兰”,最终竟迷失于资本文明之中,为了金钱、为了享乐,甘心做了土匪汉奸“高皇经”的姘头,自甘堕落,被众人唾弃。
在《烽火天涯》中,程造之力图描摹抗战时期都市青年的人生之路,“真正有灵有肉的青年,在这大时代里许多动态”[5]2。女主人公“慧平”性格倔强、要强、敏感,甚至偏执,源于她自幼丧父丧母、寄人篱下的不幸身世。她的灵魂是孤独的,渴望被爱,且富有爱国心。她开始时对外貌出众、出身军人世家的“王亮公”充满幻想,到达南京通过接触后,却发现自己的未婚夫空有一副漂亮的皮囊,却没有一颗上阵杀敌、保家卫国的雄心,因此失望至极。她反而对相貌平平、家境贫寒却与自己灵魂相近的“吴昔更”倾慕不已。两个青年人在淞沪会战爆发后相继投身前线。南京沦陷后,“吴昔更”还加入了当地百姓和未能及时撤退的军队组织的游击队。“雯官”“竟新”是“慧平”的表妹、表弟,二人在爱国青年“蒋东平”的鼓舞下相继投身革命事业。在小说最后,“雯官”在战地医院被敌机炸死,将自己年轻的生命献给了抗战事业。“赵也诚”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护士,她原本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享受被男人追逐的感觉。抗战爆发后,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她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态度,发挥自己的专长做起了战地护士,为抗战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烽火天涯》中“长辈们”的角色塑造也极为出彩。作为官方高层的“上官伯周”有着复杂的人物性格。一方面,他想借侄女“慧平”和“王亮公”的婚事,同“王宇”结为姻亲,巩固双方的关系;另一方面,却对“王亮公”的荒唐行径,尤其是大发国难财的贪污行为感到愤怒与鄙视。一方面,他想凭借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王宇”在军方的势力,在政坛大展拳脚;另一方面,在得到撤职的训令后,却没有因仕途的断送而感到愤懑郁结,反而变得轻松洒脱,“赋得归去来兮,十多年宦途可算得了一个结束,我再也不要去钻营,谋官,自己本来‘两袖清风’家中薄有田产……君以喻于义,小人喻以利,我非王宇,可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5]424-425。在“上官伯周”的书房中始终放着一张插着国旗和日本旗的地图,供他每日观察与思考战事走向。被撤职后,他依然关心时局,依然在思考战争的发展变化。作为军方高层的“王宇”,则是抗战时期投机分子的代表。抗战到底的主张只是为了奉迎上峰、迎合民众,是他求得仕途的一种手段与谋略。在“上官伯周”得势时,“王宇”极尽拉拢收买之能事,当“上官伯周”失势后,则竭力撇清二者关系。抗战爆发后,他指使“王亮公”的副官“区振山”谎报牧马营军粮遭受轰炸烧毁,实则偷运转卖。撤退到武汉后,故技重施,指使“区振山”克扣、倒卖军粮,中饱私囊。通过对“王宇”形象的塑造,批判了抗战时期政府、军方上层的丑恶世相。
通过对“上官伯周”与“王宇”家庭生活的描写,展现了艰苦的抗战时期,政府、军方高层纸醉金迷、夜夜笙歌的丑陋世相。“上官伯周”在南京城内的月桂巷和郊区的汤山均有府邸别墅,汤山还有一处面积极大的马场和草场。撤退到武汉后,他又在法租界租赁了极其奢华的别墅,排场依旧。“王亮公”用倒卖军粮来的钱在武汉迎紫街为舞女“江梦茵”租了一所半西式的二层洋房,二人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见微知著,可推断“王宇”的奢靡人生。青年一代中,“上官伯周”的二女儿“淑贤”,“上官伯周”的年轻姨太“费娴如”,“费娴如”的表弟“封修士”,“王亮公”的副官“区振山”,“王亮公”的情人“江梦茵”等,均是都市中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的堕落代表。与都市上流社会奢靡享乐的生活相比,都市中的小知识分子阶层更显卑微与黯淡,民生的凋敝、社会的黑暗,使他们勉力挣扎,却仍然无法抵抗残酷社会的压迫。
在程造之的笔下,各色社会人物上演各自的命运,演绎出一出出时代的传奇。升腾向上的进步青年,纸醉金迷的达官显贵,迷途忘返的女性,愚昧麻木的民众……在这一幅长长的人物画卷中,可见程造之的才气与野心,他以塑造人物群像的方式,为时代留下了独特的见证。
三、抗战时期社会悲剧的哲理沉思
程造之的现代长篇小说多呈现抗战时期的社会悲剧,但他并没有将社会悲剧的生成简单归结为战争,而是以辩证的理性思维、超越时代的深闳眼光,对战争、生命、命运、人生、人性进行深刻的哲理沉思。在创作过程中,他将理性沉思转化为哲理化的语言,“叙述多过描写”[2]5,灌注于文本之内。
《地下》多处描写了大旺村及周边乡村女性的悲惨命运。程造之以粗粝、血腥的原生态语言,呈现女性被欺侮、被残害的惨状,施害者无疑是侵略者,但程造之借角色之口发出了深邃的哲理沉思,“女人为什么总是这样易于遭难呢?”[2]284这是一个超越历史、跨越时代的哲理命题、命运拷问。在战争中,男人同样在遭受劫难、面临死亡,“男人也不一样在遭难么”[2]284。但程造之的视角更为深刻独到,更具人文关怀,更富宏大视野,指向了“女性”。此处的“女性”已经不仅仅是抗战时期的女性,更是一个包含古往今来、超越国界的名词。睿智、理性的作者化身文本中粗鲁、愚昧的角色,将自我的沉思呈现在读者面前,“不,男人们有枪。没有枪,也有力量。可是女人是不能的,连抵抗的方法都没有的。”[2]284战争毁灭了家园,毁灭了大旺村村民的生活,在冬日,人们饥寒交迫、流离失所、与亲人阴阳永隔。在呈现人间惨剧的同时,程造之再次化身文本中的角色,反思战争的缘由,揭露人类可怖的欲望和野心,“不好的事情都是野心的人弄出来的。本来没有你争我夺的事,因为只是想弄得自己舒服,自己快活享受,叫苦难让别人去吃,天下坏了,越过越糟了”[2]290。在《沃野》中,盐垦区建设失败的社会悲剧与侵略者无关,恰是源于人类的欲望野心——土匪汉奸的屡次侵占,盐垦区内部的一盘散沙、各怀鬼胎。《沃野》的语言相较《地下》更富诗意哲理、更加幽婉折绕,“但一经战争,从上到下便开始毁灭了,已往血汗的灌溉统归于无用。那就像洪水的泛滥一样,经过此番洗涤,人们回到原始去了”[3]7,宗教寓言与时代现实相结合,更好地承载和表现了作者深刻的理性沉思,揭示了战争的恐怖、现实的悲惨。
程造之的现代长篇小说虽以抗战为时代背景,却不囿于描写战争,因此,程造之笔下女性的悲剧命运实际与战争无关。《烽火天涯》的女主人公“慧平”有着倔强、要强的性格和现代女性的独立精神,她屡次违背伯父的意志,放弃了代表权势、金钱、美貌的“王亮公”,与出身卑微的“吴昔更”相恋,并离开伯父的庇佑。但现实的困境——金钱,使“慧平”不得不再次回到伯父家中,屈从了与“王亮公”结婚的父母之命。倔强的“慧平”依然拒绝与“王亮公”同房,“王亮公”因情生妒,枪击“吴昔更”,反被对方所伤,令“王宇”大怒,赶走了“慧平”,伯父也与“慧平”断绝了关系。现实的困境——金钱再次使“慧平”陷入了困境,她即将临盆,却身无分文,幸得“赵也诚”的相助得以平安产子。此时的“慧平”终被现实击败,放弃了倔强和理想,给同在医院中接受治疗的“王亮公”写了一封发自肺腑的书信,“她为着你的神经错乱,暗暗的抱憾而心痛欲绝呢!从你的气愤出走,并日和吴的决斗,使我深深的痛悔,深深的感觉你并非全无良心……我的心碎完了,但预备为着你而复活起来!我觉得生活感受威胁,枯燥,乏味!我今日才知道吴并不十全十美,而且他毫无信义……亮公,你能宽容我吗,你能饶恕这个曾和你朋友同居已经作了母亲的罪人吗?”[5]472-473希望并恳求得到他的原谅。这封书信是一个象征,象征了以“慧平”为代表的都市女性的社会悲剧——在金钱的压迫下,对现实的妥协、对自我理想的放弃。作者是借男女感情问题——未婚先孕,来探索社会问题。
程造之对于世界的理解不脱离悲观的本色,因此笔下浮现出一幕一幕惨状、一出一出悲剧。他以深邃的思索面对纷繁的世界,对战争、生命、命运、人生、人性进行深刻的哲理探寻,彰显出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在程造之那里,悲剧成为人的存在本质,这种悲观主义色彩既是时代的使然,也是个人哲学的外化显现。
结语
长久以来,程造之的小说一直被学界忽视。他的长篇创作,个人特色鲜明,深刻、全面、细致刻画了抗战时期的众生相,透视社会问题的千姿百态,书写民族战争中大众的艰难觉醒。程造之饱蘸深厚蕴藉的情感,绘制时代的万千世相,塑造多彩的人物群像,以强烈的人文关怀呵护人性之真、批判人性之恶,对时代、人生等重大命题抒发深沉的哲思。程造之的现代长篇小说立意深刻、题材广泛、风格多样、技艺奇巧,为现代文学贡献出别样的审美经验,实属有待开掘的一座文学富矿。对程造之现代长篇小说创作的综合阐释,钩沉程造之的现代长篇小说,不仅能还原他的文学创作风貌,重审他的文学史地位,对于现代文学来说,程造之的重新“发现”,亦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注释:
①“盐垦”一词最早出现于清朝末年,大约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通海垦牧公司成立。苏北盐垦区是我国著名的棉区之一,也是江苏省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其开发有着上千年的历史。苏北盐垦区主要位于江苏省东北部,东滨黄海、西界范公堤、南起吕四、北至陈家巷。包有滨海、射阳、大丰、如东、阜宁、盐城、东台、海安、南通、海门、启东等地。在近代,苏北盐垦区历经了两次飞跃式的发展。一是在清末时期,张骞等人在通、泰两地设立了大豫、大丰、大贲、华成等大量的垦牧、垦植、垦盐公司,盛极一时。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东顾,民族工业进一步崛起,对棉花需求日益增长,促使苏北盐垦区迅速成为我国重要产棉区之一。而在新文学的创作中,较少有反映苏北盐垦区的小说作品,长篇小说更是罕见,程造之的《地下》《沃野》填补了这一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