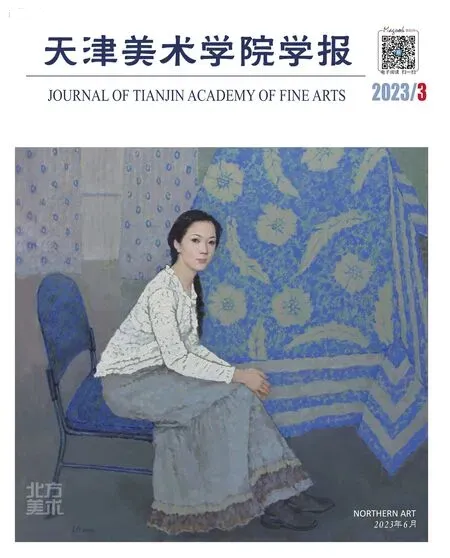身体·真实·时间
——论印象主义视知觉的悖反性
王 县
进入19世纪后,西方社会逐渐步入现代性的一系列后果充分显现的历史时期。此时摆在印象主义面前的不再是一个被规定好的世界,而是一个需要依赖于“观看”来解释的世界。观看作为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是一个文化体塑造世界的基础,体现着该文化体的内在特征。并且,文化体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生产与之相适应的观看方式,并通过观看方式呈现出符合该文化体的价值诉求。在梅洛-庞蒂看来,知觉是一个情境场,知觉总是关于身体的知觉,身体图式的理论是一种知觉理论,我们是用身体去感知世界,身体是一个自然的我和知觉的主体,[1]我们总是通过我们的身体在世界生存,我们对世界的知觉总是伴随着身体的反应。从另一方面来看,一个文化体的知觉模式是其时间意识模式的反映,两者都是“该文化体如何模塑世界和将民族与个体的生活整合为一个可靠的形式结构的基础”[2]。时间意识模式渗透在知觉模式之中,主体对世界的感知同时也是时间意识如何被结构、刻画、折射的过程,两者皆反映了特定文化体的内在特征。
印象主义可视为现代性的产物,因此现代性进程的多重张力关系也可以通过印象主义知觉方式所隐匿的悖论得到有效的揭示。本文由此一方面立足于现代都市文化语境,围绕视知觉身体化、艺术真实观这一组关键词,探讨印象主义的视知觉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则通过对现代性进程中多重时间模式的厘清,力图揭示这种复杂性产生的深层原因。
一、现代都市审美经验与印象主义视知觉方式的发生
印象主义是一种城市艺术,这不仅仅是因为在题材上发现城市,更是因为用城里人的眼睛去看世界,即印象主义对感知的新扩展以及对外界印象更敏感的回应。[3]507较之文艺复兴,印象主义重构了观看方式的构成要素,即“现代时间观”和“现代身体观”参与视知觉机制的建构,这种根本的转变在于一种新的文化经验——都市文化经验的形成。
都市文化①具有与乡村文化截然不同的气质,它诱使人远离传统,造成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断裂。现代“工业制造、资本主义商业运作和科学技术三者结合,把人口、各种资源和财富向城市集合,于是形成了现代社会组织的特有形式:大都市”[4]。可以说,印象主义的产生与第二帝国的形成是恰好重合的。夏皮罗发现,印象主义的绘画展现出感官娱乐的扩散,这与新的商业空间是脱不开干系的,偶然、瞬间的视觉经验与都市漫游者以及奢侈品消费联系在一起。[5]巴黎从1853到1870年期间进行了奥斯曼的“巴黎改造”计划,城市的改造使巴黎成为一座适合于观光、休闲、消费的具有现代性质的大都市。剧院、咖啡厅、拱门街成为闲逛场所,百货超市内的琳琅满目的商品不断地吸引者消费者的注意力。具体来说,印象主义的视知觉机制得益于以下都市经验。
首先,都市经验中的时间呈现为瞬间的切片状态,这是现代都市最强烈的具身感受。本雅明将处于“第二帝国的巴黎”中的艺术家比喻为“闲逛者”(flâneur,又译为浪荡子、游荡者等),他们无所事事,四处漫游,体验着瞬间、陌生的感受。对于艺术家而言,不仅都市中的人群是陌生的、瞬间的,是身份缺失的存在,而且这种陌生感、瞬间感更是艺术家都市生活的具身体验。在都市生活中每个人都是波德莱尔意象中的“人群中的人”,人与实体失去联系,对世界的体验呈现碎片、瞬间的感觉。因此,“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与不变”[6]。现在,转瞬即逝与变化不息成为永恒的“时代精神”,正是这种现代时间观建构了印象主义的基本特征。豪泽尔在.《艺术社会史》.中对印象主义进行考察时也发出同样的感叹:“瞬间压倒长久和永恒,感觉每一种现象都是稍纵即逝的、一次性的组合,是在不可能让人两次踏入大河里的一簇波浪,这就是印象主义的基本特征。”[3]507-508与永恒时间相比,瞬间时间感受更多来自于私人的具身体验,而非来自神或理性的绝对时间,这意味着一种切身时间观念——私人的、主观的绵延时间的出场。这种新的时间观念将意味着时间与自我的等同,而这正好构成了现代主义文化的基础。[7]11
其次,道德的消解以及伴随而来的视觉的欲望化。与古典艺术依赖的“绝对时间”相比,“瞬间时间”是印象主义的专利。当绘画寻觅永恒时间,必把身体作为一个被贬低的对象。不管是古希腊将时间归属于理念领域,还是中世纪将时间归属于上帝领域,又或者是文艺复兴时期将时间归属于理性空间,都是对时间进行等级二分,相应地将身体与偶然、世俗时间相关联而使之成为被贬损的对象。质言之,现象界是要被轻视的领域,继而,身体也是被草草打发的对象。
而印象主义将“世俗身体”拾起,从社会角度来看,与道德的消解脱不了干系。在基督教教义中,眼睛一直与视觉挂钩,奥古斯丁因此把视觉谴责为眼睛欲望,认为视觉会分散心灵对灵性的注意力。[8]xxviii因此,带有生理性质的身体是无法出现在视知觉机制之中的,但“资本主义体制产生于新教工作伦理,它要获得发展,就只有鼓励消费、社会流动性和追求地位,也就是说,通过否定自身超验的道德基础”[7]13。丹尼尔·贝尔进一步认为,促进资本主义精神因素的形成不仅仅是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加尔文教义和清教伦理(严谨的工作习惯和对财富的合法追求促进了理性生产和交换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兴起),同时也是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ort)所提出的“贪婪攫取性”,前者表现为“禁欲苦行主义”,后者表现为“经济冲动力”。[9]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贪婪攫取性”一直受到压抑,与此同时受到压抑的便是身体。但进入现代,“禁欲苦行主义”对“经济冲动力”的约束不断减弱,其所坚持的禁欲苦行的道德准则让位于欲望的不断满足,新教伦理的节俭原则被资产阶级社会所抛弃,剩下的只有享乐主义。享乐主义注重现时,其不追求永恒的价值,所强调的只是眼前的感官享乐。因此,肉体、欲望这些带有偶然和现时属性的因素便参与到印象主义视知觉的建构之中。
总的来说,都市文化语境下的视觉模式呈现为瞬间性和身体化的特征。然而,现代性本身便是一个矛盾体,在马泰·卡林内斯库看来存在着一种资产阶级的现代概念与先锋性所产生的现代概念的自身矛盾。[7]48前者基于客观时间,后者基于人性时间;前者也在不断地寻找机会驯服后者,后者厌恶前者的中产阶级的道德标准,试图反抗,甚至自我毁灭。这两种时间意识显现着现代性的自身矛盾,同时使印象主义的视知觉模式呈现为对立的状态:第一,对立于传统;第二,对立于自身。“对立传统”即对传统观看方式的反叛;“对立自身”体现为印象主义的视知觉模式的自我悖反。
二、视知觉身体化及其悖反
文艺复兴绘画通过透视法捕捉世界,利用暗箱机制观察世界,两者都将身体排除在视觉之外。而印象主义拾起身体,试图凭借视网膜去感知世界,将身体劳作遗留在绘画之中,然其运作方式不可避免地使肉体沦落为机械的存在。
(一)透视法对身体维度的剥离
自文艺复兴以来,绘画通过暗箱机制对对象获得“金字塔式”的认识。但这种观察方式将身体排除在视知觉之外,观察者与被观察的世界处于分离状态。克拉里认为:“观察者在密室的出现,意味着人类主体性和客观装置于时空中的同步存在。因此这个观察者是黑暗中较自由流动的居者,是独立于再现之机械过程的一个边缘的补充性存在。”[10]67当观察者利用机械装置——暗箱——去见证世界,就意味着会以超越者的姿态将偶然、变动的世界规训为秩序的存在。在这个过程中,身体游离在观看行为之外而成为“边缘的补充者存在”。这一结果,早在光学透视法则中就已注定,光学透视法使身体成为永远无法再现的“幽灵”,在光学透视法中主体与客体不存在视觉的交换,客体永远只是臣服于主体的对象。在透视法则中,观察主体是一个超时间、无肉身概念的存在,以“上帝之眼”去观察世界,将世界的偶然现象组织成秩序化、永恒的客观对象。正如约翰·伯格所言:“透视法使眼睛成为世界万象的中心。一切都向眼睛聚拢,直至视点在远处消失。可见世界万象是为观看者安排的,正像宇宙一度被认为是为上帝而安排的。”[11]
但肉体却在观看的过程中消失了,因为肉体属于现时、偶然的存在,除去身体剩下的只能是一只绝对的眼睛。单眼模型毫无疑问避免了身体与世界的交流,避免了双眼所见到的现异的、暂时的画面,视觉时间被系统地建构起来,不协调与不规则统统被单眼机制所消解。[12]可以说,眼睛的共时性权力超过历时性权力,在透视法的观看中,现象被解释为永恒的在场,运动被透视法所删除,“创造出——或至少是试图寻找——一个共时的观看,这一共时的观看将身体和瞥见隐藏在一个无限延伸的将影像作为纯粹理念的凝视中:影像作为幻影”[13]129。对对象的观看不是为了获得关于对象本身的视觉形象,而是背后的理念,所观看的不是“这一个”,而是“种”。观者不再与被观照的对象具有情感上的牵连,观看被还原为美杜莎般的凝视。
(二)视知觉身体维度的出场
这种超越时间的观看方式在19世纪被打破。19世纪以来,现代都市的发展将身体作为消费的主要场所,并且科学把注意力从对光学的几何化定律转移到人类可视的身体维度。②视觉从“笛卡尔的透视主义”(马丁·杰伊语)时期所诉诸的心灵之眼转向具有生理性质的肉眼。
身体维度的出场不仅是因为印象主义者用肉眼去感知世界,更是因为在印象主义的画作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身体劳作的痕迹。在诺曼·布列逊看来,西方传统绘画是建立在对指示的否定基础上,呈现出为“凝视”式的观看之道。[13]121而在印象主义绘画中却呈现出与“凝视”相异的“瞥见”式的观看之道,在那易逝去的光影之中,在看似未完成的画面中,能够看到画家力图保留视网膜的光线效果而做出的不懈的努力,即使画面在这一瞬间停滞,而时间仍旧处于“绵延”之中。如果说“凝视”意味着将事物规训为充满秩序的存在的话,那么“瞥视的绘画诉诸观看主体的延续性时间中的视觉,它并不试图将观看的过程撇开,也不以其自身的方式排斥劳动的身体的痕迹”[13]128。也就是说,印象主义绘画的“瞥视”方式重新将身体维度引入视知觉之中。
(三)身体维度的退场与视知觉的悖论
但是在底子里,印象主义的视知觉方式却呈现悖论式。如果将身体二分来看的话,印象主义的观看方式一方面造成生理身体的出场,另一方面又造成人性身体的退场。
印象主义对视网膜上光线效果的偏爱使“绵延的身体”在创作中被遗忘。画家只是成为机械的感官装置,生命时间的绵延性质演化为机械状态,其实质是科学技术造成的空间对时间的入侵。伯格森认为生命具有绵延性质,真正的时间是和生命的绵延同一的,这里时间概念是指本源时间或生命时间,与机械的可测量的时间相区别。生命的绵延性质从其运动而言“是数学无法掌握的,数学对于时间掌握不了旁的而只是同时发生,对于运动掌握不了旁的而只掌握了不动性”[14]161。这种“不动性”却恰好可体现为瞬间的视网膜映象,视网膜映象说到底是赤裸的感官数据,其将绵延性质的生命时间空间化为机械时间。这种时间观念是对本源时间的折射,虽然其“较符合一般社会的需要”,却把“基本的自我逐渐忘记干净”。[14]87
正如保罗·高更所批评的:“印象主义所研究的只是色彩的装饰效果,这是没有自由的,其被逼真所束缚……他们只注重眼睛而忽视了思想的神秘,陷入了纯粹的科学推理。”[15]的确如此,对于印象主义来说,不可见的思想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可见的视网膜映象。视网膜式的感知方式把社会因素排除在形象的构成法则之外,会“把表现元素限制在视觉性并且排除一切不属于视觉范畴或者无法转换成视觉范畴的东西”[3]509。正是如此,印象主义忽略题材和意义,只剩下不同时间段的光线效果,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莫奈的“鲁昂大教堂”系列绘画。在画鲁昂大教堂的时候,莫奈在教堂对面租了一间小房,莫奈仔细观察这一座哥特式教堂在不同时间段的光线变化,“对于莫奈来说,虽然描绘的是鲁昂大教堂,但它并不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实体出现在画面之中,而是作为光线、色彩、气候的承载体来表现的”[16],莫奈将“外光派”的形象表现到了极致,但也暴露出了印象主义是如何从强调原始的视觉经验沦落为偶然情境的奴隶。其“强调原始的经验(不管是科学控制的还是其他的经验)可能会导致一种对描述者的感性——而不是对描述对象——的拜物教沉迷”[8]134。本质上,印象主义者成为不折不扣的“自然主义者”,因其对偶然光线效果的迷恋而成为视网膜的忠实信徒,沦为了感官的机器,成为光影最忠实的仆人。甚至可以说,视网膜成为类似快门般的无生命的机械装置,虽然身体的劳作在印象主义绘画中出现,但很快又从绘画中消逝。
值得注意的是,身体的退场也表现为印象主义绘画创造出的感官记忆拒绝欣赏者的身体再创造。虽然印象主义的绘画之中保留了画家的身体痕迹,但对变化的记录导致实体的消散,观者在观画过程中很难再次进入绘画之中进行具身体验,而创造出独属观者的经验。
这种“拒绝”与印象主义所塑造的独特空间意识是相关的,印象主义绘画建构来源于一些关于景物的“视觉余像”,而这些“视觉余像”是画家对景物的主观的、瞬间的感官印象、记忆。相对于文艺复兴时期坚固的审美空间和明晰的审美经验,印象派塑造的审美空间和经验无疑是脆弱的、模糊的,如水中所投射的倒影,晨曦依稀可见的港口,耀眼日照下的美人,这些印象更像是一种追忆。其原因是印象主义绘画所塑造的空间是来自于画家的此刻的感官体验,而体验是最易逝的。因此,当此在的欣赏者观看印象主义绘画,其所获得的审美经验只能是来自接受者对自身经历的想象式的回忆。也就是说印象主义的绘画空间是由回忆所塑造起来的光线的空间,通过此空间激起的意象只能属于感官记忆:湿润的泥土、裙子的质感、草地的芳香。从感官记忆的层面来说,它只能将过去的触感召唤出来,但不容许此时的观者加入新的身体体验。也就是说印象主义绘画永远只属于过去,而不是此刻的观者或未来的观者。
原因在于,印象主义切断了与未来时间的关联,所唤醒的只是对过去经验的回忆或想象。在这一点上印象主义绘画与摄影具有相似之处。照片是“强行隔断事件的能指与意义的所指,从时空中粗暴拖出事物,散为孤零零的残渣碎片,透过镜头,泵出一连串不相干、独立存在的化学分子”[17]。印象主义绘画与相片具有相通之处,记忆脱离了亲身的体验,成为无法触及的他者。因此,印象主义的空间所承载的是封闭式的画家的感官记忆,无法召唤观者的具身体验而产生新的经验。
三、现代多重时间观与印象主义内在矛盾
如前所述,知觉模式与时间意识模式共同构成一个文化体的形式结构基础,而时间意识渗透在知觉模式之中,知觉模式则是对时间意识的折射。以此观之,印象主义视知觉方式的悖反,其实质亦是现代时间观多面性的表征。这种多面性主要表现为启蒙线性时间观、私人绵延时间观、世俗时间观。
时间观表征着文化和社会进程的节奏。现代性在时间观上体现为两套不同的时间观念:一套是代表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式的机械时间观;另一套则是代表个人的绵延式的私人时间观。前者承袭启蒙运动的线性时间观,到19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线性时间观更是深入人心。但线性时间观本质上是将绵延的本源时间标记为数学式的空间关系,时间之流的生命体验在空间切割中荡然无存,暗含着对工具理性的崇拜。后者则将时间转换成个人的亲身体验,强调时间的私人化和生命的绵延性质。这两套时间观反映在印象主义绘画上,一方面是将身体从绝对时间中解放出来,创造出了新的视觉经验;另一方面是工具理性将身体压抑为机械式的感官装置。
就第一个方面来说,身体的出场得益于现时时间成为印象主义绘画的主题,绘画中的时间观念不再是古代或中古艺术中的永恒时间,也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时间。对现时时间的关注意味着身体不应是视知觉背后的文本,更不应该消失在视知觉之中,而应此时此刻地现身于观看之中,其结果是肉身化的视知觉。在印象主义绘画中,身体劳作痕迹显现于时间的绵延之中,就像莫奈的《日出·印象》中,层层叠叠的笔触之中能够感受到画家的身体与晨曦的光线一齐在绘画中显现。
但另一方面,身体却从视知觉中退了出来,其实身体的退场对印象主义画家来说是一个“意外”,但对启蒙现代性所展现出的“主体的霸道”来说却是一种必然。当印象主义力图准确再现自然面貌,不惜将光与色从事物实体的表层中分离出来之时,就注定了这一结果。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体的地位不断攀升,并以无比霸道的形式征服时间,将时间表征为钟表上的可测量的机械时间。也许印象主义艺术家的初衷只是为了更好地消除图像中的情感和意义,但是其方式——准确记录视网膜上的光线效果(这种方式本身便是主体霸道的体现)却将具有绵延性质的生命时间降低为机械时间,将具有生命性质的身体降低为机械的肉身,人性的眼睛还原为被动的感官装置。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性的时间意识虽然是沿袭着启蒙运动以来无限进步的时间观念,但商品经济的发展冲破了新教伦理“禁欲主义”的束缚,基督教预设的时间观念被中产阶级享乐主义所打破。因此“在我们的时代,进步的神话似乎已在相当的程度枯竭了。它已被现代性自身的神话取代,未来早已变得像过去一样不真实,一样空洞。对于不稳定和不连续的普遍感受,使得即时享乐成为值得追求的唯一‘合理’之事”[7]265。这种时间观是对线性时间观的反叛,但也是一种对依赖于自我而展开的绵延时间的变种,其显现为中产阶级的世俗时间观。世俗时间观的基本特征是:对变化的“恐惧”,以及流向未来时间的不真实和无意义。[7]248因此,世俗时间观要拦截时间之流,去除未来,将生命凝固为此刻无限的感官体验,这也是印象主义注重现时体验的原因。
在一定程度上,世俗时间观念是对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两者的反叛。它一方面反对启蒙现代性所宣传的线性进步时间观,另一方面反对审美现代性所推崇的生命的绵延。它代表的是中产阶级的趣味,这种趣味正是印象主义的表现对象。印象主义从来不表现中产阶级的工作,只是表现中产阶级的休闲与娱乐,赛马场、咖啡馆、酒吧、露天餐厅这些休闲娱乐场所出现在德加、马奈、雷诺阿等印象主义画家的绘画之中。中产阶级在工作中可以是一个积极进取的阶级,但也可以是一个追求享乐的阶级。追求享乐在本质上是对时间的逃避,逃避时间的方式有两种:沉浸在过去的欢愉或享受此刻的美好。
印象主义绘画正好迎合了这种诉求。首先,印象主义绘画所储存的只是此刻的感官体验,感官体验是艺术家关于某一时空的痕迹;其次印象主义依赖于动荡不安的光线效果而非坚固的实体。因此,印象主义所塑造的空间与现实实体相脱离,使感官体验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之物,从而否定了也否认了未来的不确定,将时间永远停止在此刻的欢愉,并且此刻也将成为关于过去的“感官回忆”。
总的来说,身体中知觉的重新定位一方面是将人类视觉作为机器安排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也是印象主义绘画中创造出令人震惊的视觉经验的后盾。[18]它既是对知觉中身体维度的赞扬,又是对身体的异化,甚至是在接受活动中对身体经验的拒绝。这一悖论可视为是现代性自身矛盾的体现,是现代时间意识多面性的表征。
四、印象主义真实观及其悖反
如果说身体维度在视知觉中出场与否更多地受时代层面的要求,对于印象主义者来说更多是不自觉(他们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身体维度在绘画中或视知觉机制中的呈现状态,因此是不自觉地受现代性的影响)的话,那么对艺术真实性的诉求则应是作为艺术家的印象主义者自觉追求的东西。因此相对于身体维度在视知觉中的不自觉,从艺术真实观出发来考察印象主义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印象主义对现代性的时间观的自觉接受,以及现代性语境下知觉方式与时间模式之间的互动关系。
印象主义追求“现实派”的步伐,隔绝意义与情感,重视视觉经验本身而设法“诉诸事物本身”,呈现出具有现象学意义的“瞬间真实”。印象主义的真实不再是对主题的再现,而是对视觉的再现。这种再现似乎使印象主义能够为自我立法,使其不依附于外部而独立自主,但事实往往事与愿违。
(一)传统绘画的真实:诉诸超视觉存在
从古希腊以来,真实的话语权往往来自“超越势力”,审美判断呈现为知识判断。这是因为西方绘画真实观深受本体论的影响,在柏拉图的哲学中,理念作为本体,现实世界则是对理念的模仿,进而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故此柏拉图从本体论上将艺术贬低为影子的影子。亚里士多德同样从本体论的角度去谈论艺术,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是以神学目的论为基础去谈论艺术本体论。他将现实世界看作是神的艺术作品,神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19]艺术作品是对神的作品的模仿,现实世界呈现有机整一的特征,因此艺术也应该是有机的整体,和谐的统一。艺术的真实便是来源于此。
到了近代,西方绘画的真实观受制于认识论,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对事物的认知不是取决于事物本身而是来自于“我思”主体,艺术真实是主体通过理性对现实世界的认识而获得的。故此在绘画中,艺术真实诉诸智力,利用光学透视法对现实世界获得准确的认知。正如“笛卡尔认为,人‘独特地以心灵的知觉’认识世界,而认识外在世界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将自我稳定地置放于空无一物的内部空间”[10]71。这个稳定的“内部空间”在文艺复兴时期寓意为暗箱空间,通过暗箱将主体与客体相隔,任何对外界的认识不是直接地通过感官获得,而首先要通过内部装置——心灵的抉择,心灵将现象界的偶然整理为充满秩序感的真实。故此,我们能在文艺复以来的古典绘画中感受到理性的秩序美感,这种美感的产生得益于“心灵的抉择”。可以说,主体的注视成为文艺复兴绘画中最重要的因素,正是因为主体的注视,画面才得以构形。
总的来说,西方传统绘画为了“分有”真实的权力,不得不模仿原型——不管是从本体论上还是认识论上。但原型与图像之间存在着不可弥补的界限,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因此绘画能做的只能是以自己的方式去接近这个世界,无论是早期艺术寄希望于信仰获得本体上的同一去接近原型,还是后代诉诸智力,通过各种技术手法复制现实,他们能做的只是根据原型去“制像”。就像赫伯特·里德认为的,不仅希腊罗马的艺术,就算是文艺复兴的艺术都有模仿化的企图,他们都被再现世界的“真实面貌”的愿望所推动,为了弥补观察对象与体现对象之间的矛盾,他们不得不采取超视觉的手段,要么是通过想象改变客观事物的形体而创造出一个理想的空间,要么诉诸智力,通过智力使观察对象在画布上获得准确的位置。[20]总的来说,以上都将真实诉诸超视觉的存在,而非视觉本身。视觉一直被遗忘,艺术的生命力从来不是艺术本身所迸发出来的,要么理念,要么就是具有形而上气质的超时间性的理性。
(二)“真实”的解放与印象主义绘画的“瞬间真实”
印象主义挖掘视觉本身的潜力——“纯粹可视性”,将艺术的生命力放在视觉本身。其真实呈现为“瞬间真实”,这种真实观依赖于两个因素:纯粹可视性、瞬间性。
首先,印象主义将眼睛从“暗箱”中解放出来,知觉模式呈现为“纯粹可视性”。如此,印象主义可以一方面追求纯粹光色效应,另一方面又摆脱了现象界和智力上的倾轧。正如瓦尔特·赫斯所认为的,“对于色彩的纯粹画意的使用,摆脱了物体的材料性质;但也从素描的纯粹线条解放出来,而反过来,摆脱颜色的特征来做物体的分析,把画面从它和立体及透视表象的纠缠中分割出来”[21]3。可以说,在印象主义的视知觉模式中没有了超然的存在,文本从视觉中被清除干净,从此绘画的意义仅来自于体验本身。在印象主义看来“物体本身与其说是一些实体,不如说是吸收和反射光的一些媒介。就纯粹的‘看’而言,我们只能看到色彩和光线的变化。因此,画家应该考虑色与光的问题,而不是物体与实在的问题”[22]。总而言之,印象主义将光与色从物体上分离出来,使事物失去了体积和质量,光与色成为独立的因素并从现象界中解脱出来,因此现象界再也难以成为真实的依据,从而现时的视觉体验成为印象主义绘画真实观的唯一来源,“可见的真实”成为印象主义绘画的题中之义。
其次,在视知觉上追求瞬间性。概言之,古希腊艺术中的时间表现为永恒时间,在艺术上呈现为静穆之风;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时间表现为线性的物理时间,呈现为秩序化的理性之美。然而,不管是永恒时间还是物理时间说到底都是外在于人的抽象时间,实际上是将时间空间化了。正是如此,亚里士多德在谈论悲剧的时候认为情节是六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认为情节是作为“一定长度的行为的摹仿”,将悲剧整合成有机整体,于是“情节是悲剧的根本,用形象的话来说,是悲剧的灵魂”。[23]其原因在于情节将碎片化的“空间长度”整合起来,碎裂的空间在时间原则的指导下结合成统一体,并因此排除了偶然因素,达到对“或然律和必然律的模仿”。也就是说真实成为一种普遍的、永恒的图式,如此使诗比偶然的历史更加真实。这个原则从古希腊流传下来,不仅在悲剧中,同样在视觉艺术中发挥作用。绘画的媒介决定了它只能通过空间的方式来表现出时间,正如莱辛所言:“绘画由于所用的符号或摹仿媒介只能在空间中配合,就必然要完全抛开时间,所以持续的动作,正因为它是持续的,就不能成为绘画的题材。”[24]因此绘画必须表现最“富有包孕性的顷刻”,通过这一顷刻的暗示排除瞬间时间的偶然性,走向真实的普遍与永恒。
以上是传统绘画所遵从的真实观,时间只是绘画中的一条潜流,瞬间只是联结空间因果关系的媒介,空间才是绘画的本质。瞬间的价值不是其本身,而是在于通过“瞬间”获得的对未来空间或过去空间的暗示,使得内容和意义在动作中得以展开,使过去与未来因现时空间而结合成一个统一体。这种时间观使时间沦为空间的形态。在亚里士多德的心目中,时间就只是类似空间的长流,可以进行无数的切割,在他看来,“时间是运动的数”,是“运动和运动持续量的尺度”,时间上的每一个点就是“现在”,现在的前后便是过去和未来。[25]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时间观则基于近代科学成果,科学理性将客观世界独立于人,将时间刻画成外在的、可被测量的物理时间。其结果仍是将时间关系还原为空间关系,真实来自空间的坚固和统一。
但印象主义追求时间的非连续性,切断了与过去和未来的关联,将时间还原为瞬间的亲身体验。从社会层次上说,非连续性时间是一种现代性的时间特性。首先,其根植于都市文化经验,这是一种与传统的乡村式文化经验截然不同的文化经验模式。正因为如此,在时间流上,现代性的时间是对过去的时间持拒绝态度的。其次,受世俗时间观的影响,它去除了未来的不确定,将即时享乐作为唯一合理的事情。基于这两重原因,瞬间便成为时间的唯一范畴。瞬间时间的非连续性打破了传统神性时间的永恒与理性时间的线性发展,时间的本质来自于当下的感知,于是印象主义绘画的真实成为瞬时的视觉体验,呈现为“瞬间真实”。这种真实不属于形而上之物,也不属于现象界,只属于画家瞬间的感官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印象主义绘画也因此具有某种自律特性。
(三)印象主义绘画自律性的悖论
但是,因为印象主义“纯粹可视性”是不彻底的,使得印象主义的真实观陷入尴尬的境遇,自律的同时又显示出他律的特征。在印象主义绘画的作品中,虽然事物实体被遮蔽了,但印象主义的光与色不能结成具有生命性质的艺术实体。其根本原因在于印象主义依旧是在见证世界,如布列逊批评西方传统绘画时说的,“由于缺乏任何来自内部的可见的生产性活动,意义被感受为影像之外的一个想象性空间的插入”[13]75。印象主义一样,其观看方式正不断地培养这一“想象性空间”。瓦尔特·赫斯说得很明白,在印象主义那“多彩的感觉刺激的织成品里仍然把那中心透视的空间构造投射进去,而这却仍是安放在‘纯粹可视性’里面去的‘表象形式’。这表象形式是以集中在一个消失点上的固定的眼光为前提,要求着伸入深处的规定的减缩和一个地平线”[21]10。也就是说,在印象主义的绘画中依旧存在一个观察者的消失点,依旧有个外在的主体在注视着景色或人物,绘画不是属于艺术自身,生命不是从颜色中孕育出来的。只要我们去观看莫奈的《日出印象》和雷诺阿的《青蛙塘》,就能明显感受到注视者的存在。质言之,印象主义绘画的生命力是注视者目光所给予的,而不是绘画自身生命力之表现。从绘画自身来看,它之所以会求助于外部世界,在于印象主义的颜色只是漂浮在物之上的颜色分子,实体只是被遮蔽但没有消失,颜色依旧是属于物的。印象主义自身无法构成艺术实体,不具有自我生产的能力,因此所谓的“瞬间真实”依旧是恪守自然规则的被规训者。
总而言之,印象主义“纯粹视觉”的不彻底,从社会层面来说,归根结底是因为启蒙现代性不断地将印象主义的视知觉方式拉回现实。就创作者而言,印象主义者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们是“波希米亚人”,表现出对传统学院画的反叛精神;另一方面,他们又积极地享受现代的成果——无论是技术上还是主题上。虽然在他们的绘画中不自觉地呈现出审美现代性的绵延时间观,但这只是印象主义希望摆脱传统画派的束缚,用新的视觉方式打破学院派权威的一种策略。在此意义上,启蒙现代性的科学进步为印象主义带来了生命活力,且一直是印象主义所要表达的东西,以至于其绘画中所蕴含的审美现代性因素,其实也可以看成是启蒙现代性的产物。不管从逻辑上还是时间上,审美现代性都是启蒙现代性的产物,其实两者都是资产阶级文化的表现,只是资产阶级内部文化的分裂,产生了反对资产阶级文化内部的价值观。因此,审美现代性是启蒙现代性逻辑的必然。[26]就此而言,对印象主义来说反抗既是客观存在的,又是不自觉的。这表现在他们不可避免地依赖于资产阶级的文化、趣味。对于他们来说,现实依旧存在,只是他们要用另一种方式去看世界——一种符合中产阶级趣味的方式,而不是像现代艺术那般去创造一个“与自然相平行的世界”(塞尚语)。从动机上看,这就注定了印象主义的真实只是依附于现实世界的真实。虽然从形式上看,生理上的视觉经验切断了与外在世界的必然联系;但从内容上看,印象主义所记录的仍旧是中产阶级注视下的易逝的都市景观或依附于都市的乡村③。
五、结语
印象主义是传统艺术走向现代艺术的过渡阶段,任何过渡阶段都是最复杂的时期,是矛盾积聚且尚未显露的时期。但恰因如此,这又是理解传统与现代内在冲突的最佳时刻,也是理解特定文化体内在张力和发展脉络的一个契机。
印象主义观看方式不同于传统绘画,其根源在于传统的文化经验与现代文化经验的断裂。印象主义孕育于都市文化经验之中,以此产生了一种新视知觉方式,即视知觉的瞬间化与身体化。知觉方式的转变带来了真实观的变化,印象主义的真实不再是要再现主题,而是来自“纯真之眼”的观看效果。真实由此成为视网膜上的光线效果,但现代性自身的复杂性使印象主义的视知觉模式涉及两个悖论:首先,虽然其视知觉机制得以从秩序的、无身体的透视体系中解脱出来,令身体参与到观看的过程之中;但由于视觉被还原为视网膜经验,画家与现实的关系便缩减为动物式基础的观看机制,身体因此也成为被动的感官机器。同时,出于对未来时间的恐惧,沦为感官记忆后的“印象”创造了“专属的”感觉空间,拒绝了接收者具身体验的审美再创造。其次,在真实观方面,“瞬间真实”虽突破了理念或现象界的束缚,但艺术没有结成实体。视网膜所呈现出的“瞬间真实”仍是服从于观者的视觉秩序,印象主义绘画仍只是对外部世界的见证。
总的来说,印象主义的观看方式,不管是在不自觉的身体知觉层面上,还是在自觉的艺术真实观的追求上都呈现出悖论性。其实质是现代性时间意识模式多面性的表征:一方面是现代时间模式与传统之间的断裂;另一方面是自身的相互否定,表现为启蒙现代性的时间观与审美现代性的时间观的对立,以及代表中产阶级的世俗时间观对前两者的彻底否定。“否定”是现代时间模式的基本特征,因此在印象主义的视知觉方面呈现为多重悖反。
注释:
①都市文化标志着一种传统与现代之间断裂的发生,断裂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经验的转变,传统的文化-经验是一种“基于农耕-手工劳动的乡村文化模式,其核心是身体劳作的‘生存意向性’与‘物的物性的’交互转让,而现代的文化-经验是资本主义与分析理性以及工业制造所形成的都市模式”(见牛宏宝《西方现代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4—88页)。城市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城市的最早形态“权力之城”,城市主要作为举办宗教和政治仪式的地方;第二是中古时代的城市形态“政治权力+消费之城”;第三个类型是14世纪开始,教会衰落,发展贸易和手工业为核心的城市。但直到19世纪,工业化的进程才发展现代意义的都市(见牛宏宝《都市经验与审美现代性》,《艺术学研究》2021年第2期,第11页)。
②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表示,最显著的例子是歌德1810年出版的《色彩论》(Theory of Color),歌德在讨论中提出一种主观的视觉模型,人体的生理意义被引入到视觉之中,这是“一种新型的生产者观察者的雏形,其身体具有生成各种视觉经验的能力”(详见乔纳森·克拉里《从视觉到视觉系》,田亦周译,载于李洋编,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等,《电影的魔幻现实主义:英美电影文选》,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5页。在其著作《观察者的技术:论十九世纪的视觉与现代性》第三章《主体视觉与感官之分离》中,乔纳森·克拉发现从19世纪开始研究视觉的科学技术,从纯粹的对光和视觉的机械研究转向人类主体的生理构成研究。19世纪开始身体本身成为重点关注的对象,正如克拉里所说,在这个时候“可见的事物从无时间的暗箱秩序中逃逸出来,而落定在另一装置中,进入不稳定的生理机能和人类身体的暂时性”(详见乔纳森·克拉里《观察者的技术:论十九世纪的视觉与现代性》,蔡佩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0页)。
③现代都市与乡村的关系不再是传统的若即若离的关系。在传统社会中,乡村可以独立存在,在现代都市中,依靠强大的流通体系和生产功能,城市摆脱了对乡村的依赖,并且城市的工业制作和市场流通不断扩充自己的影响范围,使得乡村依赖于城市(详见牛宏宝《都市经验与审美现代性》,《艺术学研究》2021年第2期,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