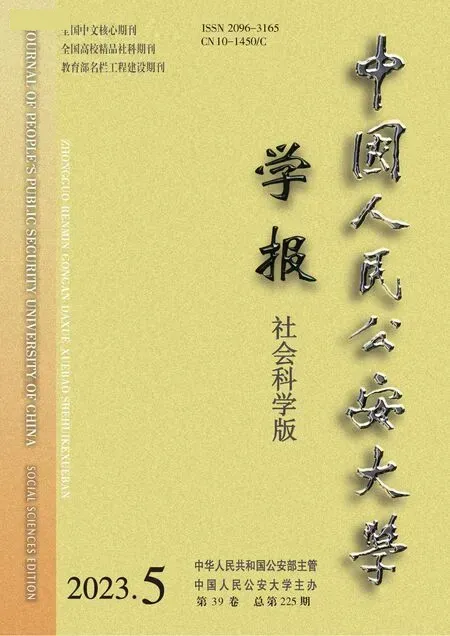公共冲突中对抗性群体心理的生成机理及疏解路径
——基于塔尔德社会理论的分析
张龙辉,王 寒
(1.东北师范大学,吉林 长春 130117;2.南开大学,天津 300350)
党的二十大指出,要及时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以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我国“十四五”规划指出,增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为此需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加强社会治安防控,提升社会治安专业化、立体化水平,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群体心理作为社会心理的组成部分,对于群体行动的开展和社会治安维护具有重要作用。塔尔德(Jean Gabriel Tarde)在对孔德(Auguste Comte)和涂尔干(Emile Durkheim)社会学思想进行继承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认为社会现象在本质上是一种心理现象,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模仿关系,而传播则推动纯粹心理上的集体的形成。在塔尔德看来,传播使基于身体接触的“群众”向没有身体接触的纯粹心理上的“公众”演化,模仿则推动“公众”向“暴民”的转化,群体心理的形成受传播和模仿的影响,从而阐释了社会生活中群体的形成和群体心理的建构问题。
在公共冲突中,群体情感的传播、公众舆论的形成以及个体情绪的酝酿都与冲突的传播密切相关,尤其是在“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公共冲突中,社会冲突的参与者与冲突事件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但却因传播带来的情感和价值扩散效应而形成共鸣,将原本不存在直接利益关系的个体组合成具有共同情感基础和心理特征的群体。传播在作为纯粹精神上的集体形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它推动了基于身体接触的“群众”向作为纯粹精神上的组合的“公众”的转化,但作为具有共同情感基础和价值内核的群体心理的形成还需要模仿的推动。在公共冲突中,身处核心地位的意见领袖和身体邻近的群体成为公众模仿的对象,且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智能传播技术的社会化应用,意识形态的跨境传播速度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公众模仿的对象也更加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身体邻近不再是公众模仿的唯一条件,公众可以借助智能传播平台模仿其他物理空间内的行为,从而使公众的模仿突破了时空要素的限制,群体情绪和群体氛围的传播、个体对他人的模仿成为影响群体心理建构的重要因素。从塔尔德社会理论谱系中的传播与模仿的角度探讨公共冲突中对抗性群体心理的生成机理,为防止冲突扩散、消解极端群体心理对立、提升社会治安防控能力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一、公共冲突中影响群体心理塑造的传播与模仿
作为法国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塔尔德用“模仿说”来解释社会心理现象,认为传播推动了纯粹精神上的集合的形成,传播与模仿成为塔尔德探讨社会秩序建构和社会心理生成的重要理论基础。在公共冲突中,虽然群体氛围、个体经历、个体价值观以及外部环境刺激都会影响群体心理的建构,但这些影响因素对群体心理的影响都可归入传播与模仿互动的角度进行分析,传播与模仿成为影响群体心理建构的重要因素。
(一)塔尔德社会理论谱系中的传播与模仿
塔尔德的社会学理论受孔德影响,他坚持孔德的道德学是生物学也是社会学的二分法观点,认为心理学既是生理的也是社会的,从而推动了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他认为社会学与心理学密不可分,不应将社会与个人分开,而应区分三种形式的心理或心理间关系,即模仿、发明和对立,并将对社会的研究“专注于个人模仿和互动的动态和混合过程”[1]45,认为模仿是一种社会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某人自愿或非自愿地把他或她作为一个模型,而其他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模仿他或她”[2],模仿在本质上是一种复制行为,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思想和行为的复制。
塔尔德用模仿解释社会心理问题,他认为社会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模仿的关系,这种模仿的倾向使人类能够有效地重复动作[1]49,模仿是所有社会相似性的原因,“社会因此可以被定义为一群易于相互模仿的存在”[3]68。塔尔德把社会事实归结为普遍存在的模仿行为,认为社会的人通过普遍的模仿而组成相互联系的整体,“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把单个的个人连接成社会的纽带就是模仿”[4],模仿催生个体的“心理印记”,进而推动人们头脑中集体思维的形成[5]143,模仿的最终结果是普遍对立的存在。基于此,塔尔德认为社会的本质是“一个大脑对另一个大脑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模仿来实现的。“人类聚集现象中的一切都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生命性的,都带有模仿的印记”[6],从而揭示了思想在社会环境中的真正传播。在社会心理的建构方面,他认为精英是模仿之源,他们能够确保社会信念的统一,群体心理的统一是群体成员对群体精英或意见领袖模仿的结果[7],从而强调社会精英在大众心理塑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在群体的形成问题上,塔尔德提出了“群众”和“公众”的概念,①在塔尔德的话语体系中,“群众”“公众”“群体”分别对应英文the crowd、the public 和the mass,因此本文的“群众”概念不具有中国现代语境中的“人民大众”的政治含义。他认为群众是指存在身体接触的群体,而公众则是指纯粹精神上的集合,它由分散的个体组成,不存在身体的接触,传播在此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塔尔德强调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8],他认为,“公众”的形成需要借助特定的传播手段,没有传播的参与就难以打破物理空间对群体形成的限制,也难以超越身体的接触形成纯粹精神上的组合,印刷术等传播技术的发展顺应了这一需求,使公众心理的建构越来越不依靠身体邻近这一基础。因此,传播成为推动群体建构的重要因素,传播技术的发展对于群体的形成速度、群体的规模以及群体的空间分布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整体而言,在塔尔德的理论谱系中,解决社会凝聚力问题的关键是传播社会思想的通信技术以及接触这些思想可能导致的模仿,而不是难以改变的制度或社会存在的基本形式。社会的驱动力是在创新和模仿的过程中发现的,“有效治理的范围受到被统治者的忠诚和身份的限制,这又与模仿和传播的限制相对应”[9],这些限制可以看作是不断扩大产生公众思想的“新闻工作”。传播和模仿成为塔尔德社会理论谱系中解释社会现象和心理问题的重要概念,其中传播是形成群体的重要动力,因为传播的存在使摆脱身体接触的、纯粹精神上的组合成为可能,而模仿则推动群体心理的建构,在使群体的心理趋于统一的同时促进不同群体间普遍心理对立的存在。在公共冲突中,传播是催生群体的重要因素,对传播的需要以及报纸等传播媒介的推动使“群众”向“公众”转化,从而形成了不以身体接触为特征的纯粹精神上的组合。而“信念”和“欲望”是产生模仿的基本要素[10],“信念”和“欲望”是塔尔德人格理论的重要元素,正如塔尔德所说,“信念和欲望通过社会模仿而扩散并逐渐制度化,从而产生与之相应的心理状态:‘轻信’和‘顺从’”[5]28。因此,在塔尔德的社会理论中,传播与模仿是催生群体心理的重要因素,传播和模仿共同推动群体心理的建构。
(二)传播与模仿互动下公共冲突中的群体心理类型
传播和模仿的互动关系存在四种情况,即高传播高模仿的互动关系、低传播高模仿的互动关系、低传播低模仿的互动关系和高传播低模仿的互动关系。在公共冲突中,群体心理呈现多样的形态,既有激进的对抗性心理,也存在沉默心理,还存在“顽固的心理”现象,即虽然受群体情绪传播的影响,但并未对群体激进情绪和对抗心理进行模仿的现象。从传播与模仿互动关系的角度而言,公共冲突中的群体心理形态可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即基于高传播和高模仿的从众型心理、基于低传播和高模仿的模仿主导型心理、基于低传播和低模仿的沉默型心理、基于高传播和低模仿的传播主导型心理(见图1)。

图1 传播和模仿互动下的群体心理类型
基于高传播和高模仿生成的从众型心理是公共冲突中群体心理的第一种类型,也是公共冲突中最常见的一种心理类型。从众型心理有两个向度,一个是激进、对抗向度的心理在群体内的传播和模仿,最终形成对抗性的从众群体心理,这一群体心理会给政府政治过程和社会公共秩序的稳定带来冲击;另一个是温和、理性向度的心理在群体内的传播和模仿,最终形成有利于政治系统稳定的温和型从众群体心理。在高传播和高模仿的推动下,激进对抗的情绪、心理和行为不仅会在群体内部和社会中进行传播,还会在群体传播和环境刺激的影响下引发社会性的模仿行为。其结果是公共冲突中的激进情绪、激进心理和对抗性行为的进一步扩散,从而增加社会治安的防控压力。一般而言,越是具有鼓动性和感染力的情感和心理,其传播和被模仿的速度越快,而群体内的激进情绪和对抗心理恰恰具有强大的鼓动性和感染力,因此,公共冲突中激进的群体心理传播最快,在外部环境刺激下引发的模仿行为也最多。当然,高传播高模仿的群体心理不必然导致激进对抗的群体心理,一些富有感染性和鼓动性的情绪、情境也会催生温和理性的、有利于公共秩序恢复的群体心理。基于高传播和高模仿的从众型群体心理是最为活跃的、影响范围最大的群体心理,其中对抗性从众型心理对社会的破坏性最大,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基于低传播和高模仿生成的模仿主导型心理是公共冲突中群体心理的第二种类型。在这种类型下,受传播速度和传播效率的限制,群体在规模和凝聚力上较弱,虽然群体内部也存在强烈的模仿行为,且形成了特定的群体心理。但由于这一群体及其心理未能在社会中广泛扩散,其结果就是虽然因模仿而导致了社会对立,但这种对立未曾在社会中扩散,因此其对社会的影响仅限于群体本身。整体而言,受弱传播行为的影响,群体的规模得到限制,公共冲突中的激进情绪、对抗怨恨心理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未曾外溢扩散向社会,群体内的模仿行为虽然也会造成对立,但这种对立并未因传播的推动而造成普遍的对立状态,引发社会性治安问题的概率较小。
基于低传播和低模仿生成的沉默型心理是公共冲突中群体心理的第三种类型。在这种类型下,公共冲突中的传播行为和模仿行为都较弱,公众对激进对抗情绪和温和理性的情感都持冷漠或沉默态度,但这种情况在公共冲突中较为少见。这是因为,公共冲突的冲突性使其本身就存在一定的传播性和社会影响性,公共冲突本身也会成为社会中备受关注的焦点,从而得以在社会中快速扩散。而公共冲突在社会中的传播会导致普遍模仿行为的发生,进而推动公共冲突中群体心理的趋同和情感的相似,最终导致基于共同行动的群体行为。而低传播和低模仿则削弱了公共冲突中的激进情绪和对抗心理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公众对冲突心理的模仿,弱化了公共冲突中因传播和模仿导致的普遍的社会对立,化解了公共冲突的破坏性。因此,在受传播和模仿互动而形成的几种群体心理中,这种情况是导致社会对立最弱的情境,也是对社会破坏最弱的情境。
基于高传播和低模仿生成的传播主导型心理是公共冲突中群体心理的第四种类型。在这种类型下,社会中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具有较强的传播性,互联网络、广播、电视等成为推动其扩散的重要传播媒介,借助传播媒介的传播,人们可以了解到其他个体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等,并基于此建构特定的社会关系,形成特定的群体。但群体心理的建构除了依靠较强的传播之外,还需要群体内普遍的模仿行为,没有模仿的介入或公众模仿行为偏弱,难以形成群体的“心理印记”,也难以导致普遍的社会对立。可以说,在塔尔德社会理论看来,传播虽然能够造成情感、思想和价值的扩散,但模仿才是造成对立的根源,只有传播没有模仿,就难以形成普遍的对立。在高传播和低模仿互动情境下,群体成员对群体意见领袖和群体情感的模仿欲望不强,导致群体意见领袖对群体成员控制力的减弱,群体情感传播对群体成员的心理和情感的影响力相对较弱,群体心理表现为较弱的心理对立和破坏倾向。整体而言,传播与模仿互动下公共冲突中的群体心理类型如表1 所示。

表1 传播与模仿互动下的公共冲突群体心理类型
二、公共冲突中对抗性群体心理的生成机理
在塔尔德的社会理论谱系中,传播能够推动基于身体接触和空间邻近的“群众”向纯粹精神组合的“公众”转化,使群体的范畴由邻近空间内存在身体接触的多个个体的组合扩展为不同空间内多个个体纯粹精神上的组合,“公众”和“群众”共同构成了公共生活中的群体(见表2),从而将社会学意义上的群体由群众向公众扩展。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传播技术和传播范式的变革,信息生产的智能化、信息传播的精准化、传播结构的去中心化以及传播渠道的多元化成为现代传播的显著特征。现代传播的这些变革加速了思想、情感的跨境传播,提升了不同物理空间内个体交流的速度和频率,使不存在身体接触的纯粹精神上的公众日益增多,并使塔尔德理论视域中的“传播”呈现新的特征。而模仿对情感的扩散、行为的趋同和精神的统一起着重要作用,通过对他人精神、情感的模仿,在社会中塑造精神和情感的相似性,精神和情感相似性形成的结果就是共同心理特征的生成。整体而言,在塔尔德社会理论视域下,公共冲突中的对抗性群体心理的生成机理如下。

表2 社会学意义上的群众、公众与群体及其关系
(一)传播推动群体的形成和情感的外溢
在公共冲突中,人们基于特定的利益诉求或者以观望的态度无意识地聚集在一起,这些聚集在一起的个体组成了最初的群体形态,即“群众”,他们处于相同或相邻的物理空间,且具有频繁的身体接触和面对面的交流。在这一阶段,怨恨、对抗情绪或者激进观点在相同或相邻空间内的群体成员间传播,但随着怨恨、对抗情绪或者激进观点向群体外的扩散与传播,尤其是在互联网以及智能传播平台日益普及的今天,情感、思想的传播突破了交通及地域等因素的限制,出现了超空间扩散现象,并向虚拟空间延伸。情感和思想的超空间扩散使共同认知的形成和社会关系的建构不再必然依靠相同或邻近空间内的身体接触,超空间交流成为不同个体间交流的重要方式,进而扩大群众的规模,并推动了“群众”向“公众”的演化进程。同时,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传播的个性化、大众化、社会化,提升人们获取信息的能力,借助即时交互性传播技术增强受众对公共冲突的沉浸式虚拟“临场互动”[11],强化受众对其他物理空间内发生的公共冲突的直观感受和切身体悟。而深度伪造技术以及音视频剪辑技术则使谣言和虚假信息的生成和传播看起来更具“可信性”,其结果是进一步使公共冲突内的激进情绪和对抗心理向其他物理空间蔓延,从而导致了群体激进情绪和对抗心理的外溢。
如在美国弗洛伊德事件中,美国警察在逮捕弗洛伊德过程中,对其呼救、呻吟置之不理,最终导致其死亡。警察“跪杀”弗洛伊德的视频在网络上的扩散增强了公众的直观感受,将原本互不关联的个体在网络上或现实生活中聚集起来,并迅速引发了强烈的社会舆论,围绕这一事件形成了基于身体邻近和超越物理空间的网络群体,他们通过互联网络传播视频、表达观点、形成舆论、影响情绪。随着事情的发酵,一些激进情绪和对抗心理也逐渐在社会中传播,进而激发了美国社会中久已存在的矛盾,原本局限于一地的事件以及特定事件的矛盾开始外溢,最终成为治安问题。
(二)模仿催生共同心理印记和共同行动
虽然传播推动了群体的形成和情感的外溢,但作为具有共同情感基础和价值内核的群体心理的形成还需要模仿的推动,在塔尔德看来,社会关系的形成和社会心理的塑造过程都存在普遍的模仿行为。在一个具有强烈激进情绪的场域内,如公共冲突中,厌恶的情感和激进的情绪会很快受到模仿,受此影响,“每个人的厌烦就因此而加倍。群众里的个人在道德上就最大限度地趋同”[5]224。受环境刺激和社会情感影响,很多模仿行为都表现出无意识和不自觉的特征[3]68,这一特征在公共冲突中尤为明显。同时,在塔尔德看来,模仿既存在由内心到外表的模仿,也存在与地位、距离等相关的模仿,“地位最高、距离最近的人是最容易成为模仿对象的人”[12]161,与社会主导性文化越靠近、与制度化的传统越接近越容易被模仿。同时,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传播模式的变革,现代传播中的沉浸式临场感知以及共情传播效应缩短了模仿者与被模仿者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强化了公共冲突参与者对激进情绪、抵触心理和怨恨情感的模仿,任何外显的政治行为都受内在心理的驱动[13],而这能够加快群体内模仿的速度和效率。
模仿的结果是群体内共同心理印记的形成和普遍社会对立的出现,原本分散的个体受情感共鸣、相同或相似经历等的影响逐渐就某一事件达成共识,形成共同社会心理。而对行动的模仿则会催生共同的行动,尤其是在现代传播技术的推动下,个体对他人的模仿突破了身体邻近的条件限制,借助智能传播载体,人们可以及时了解其他物理空间内的群体行为,采取超越物理空间的共同行动。在弗洛伊德事件中,激进情绪、对抗心理首先在与弗洛伊德具有相同肤色、相同阶级阶层和相同境遇的群体中传播,并在明尼苏达州爆发了抗议示威活动。在激进情绪、外部环境的刺激下,对抗心理在越来越多的人中间传播,并被广泛模仿,他们借助传播媒介或具体行动向政府表达不满,最终形成了以反对种族歧视、呼吁社会公平为内容的群体心理。但受外部环境刺激和对抗性心理影响,激进的甚至极端的群体心理开始在社会中传播,并被广泛模仿,最终使一个偶发事件演变成在美国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冲突的社会性问题。
(三)传播与模仿共振形成对抗性群体心理
在公共冲突对抗性群体心理形成过程中,传播与模仿缺一不可。传播与模仿的共振既能够加速公共冲突中怨恨心理、激进情绪等对抗心理的传播与扩散,还能够增强社会模仿效应,扩大对抗性心理的影响范围,通过普遍的模仿在社会中形成共同心理印记,使群体具有了共同的情感特性和稳定的心理基础。正如上文所说,高传播和高模仿会催生从众型群体心理,公共冲突中激进情绪和怨恨心理等对抗心理的高传播与高模仿会加剧对抗心理在社会中的扩散,并可能会在外部环境的刺激下出现大规模的社会模仿行为,进而冲击社会公共秩序,扰乱人们的正常生活。因此,传播与模仿的共振使公共冲突中的激进情绪、对抗心理得以广泛传播,并在现代传播模式的影响下被广泛模仿。公共冲突中的参与者通过模仿他人的思想、情绪,逐渐形成思想、情绪的相似性,不同个体的思想、情绪逐渐相似、趋同,最终在群体中形成集体的共同“心理印记”,继而形成具有共同价值认知、群体特征和情感特点的对抗性群体心理。
在外部环境刺激下对抗性群体心理会演化成对抗性群体行为,引发社会冲突,冲击社会秩序,带来一系列的社会治安风险。美国弗洛伊德事件就很好的诠释了传播与模仿共振对公共冲突中对抗性群体心理的影响,随着事件的发酵和情感的传播,越来越多的民众形成了情感共鸣,同情、支持、声援弗洛伊德及其家属,并反对种族歧视,呼吁社会平等。但随着极端激进情绪的扩散以及公众模仿行为的增多,原本在明尼苏达州一地爆发的抗议示威活动快速向其他地方蔓延,最终演变成多地并发的大规模骚乱、抢劫以及冲突事件。公共冲突中的对抗性群体心理最终演变为对抗性群体行动,且在多个地方出现了失控现象,激进情绪的传播、外部环境的刺激以及社会化的模仿使偶发事件变成了大规模的社会冲突,造成了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
三、公共冲突中对抗性群体心理引发的治安风险
公共冲突中对抗性群体心理的生成伴随着激进情绪和对抗心理的传播与模仿,使公共冲突中的激进情绪和对抗心理向社会扩散,增强了对抗性群体心理的社会化影响。对抗性群体心理的蔓延会加剧政府与社会的对立,弱化政府公信力,导致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的责任意识消失,催生责任分散效应,甚至还会导致群体心理极化,引发严重的社会对立,进而诱发一系列治安风险。
(一)导致信息传播弥散化,诱发政府公信力危机
公共冲突中对抗性群体心理的蔓延会导致群体成员思想的混乱,他们的自主意识受外部环境和群体意见领袖的影响较大,从而出现对群体意见领袖盲目的信任,其思想、情感和行为易被群体意见领袖或外部激进情绪影响。因此,公共冲突中情感、心理的传播会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遭遇意识形态多元、个体意识结构失衡等困境,并强化群体意见领袖对群体成员的影响和控制,导致群体间普遍对立的存在。群体的对立、意见领袖对群体成员控制的加深会弱化政府在社会心理引领中的主导作用,激进的对抗性群体心理也使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难以接受政府的疏导,甚至质疑政府在处理公共冲突时的舆情引导和调查结果。尤其是随着智媒时代的到来,智能传播的去中心化特征弱化了政府对信息传播的主导权,掌握有智能传播资源的公众、社会团体、科技巨头公司分享了原本由政府主导的信息传播权,从而使信息传播主导权向社会扩散,出现信息传播弥散化现象,进而引发大数据背景下政府在治安治理方面专业能力不足的问题[14],出现了信息传播国家叙事与社会叙事分离的情况,严重影响国家与社会在治安治理中的互动合作,不利于国家治安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公共冲突中对抗群体心理传播的这一现象会弱化政府在公共冲突治理中的公信力和治理权威,在大多数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公共冲突中,冲突的双方往往是政府与社会,一般表现为社会大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并在偶发事件的刺激下而爆发公共冲突。而在公共冲突爆发初期,信息传播和舆论导向尤为重要,但在“后真相时代”,真相的传播往往会被谣言所覆盖,且在对抗性群体心理的推动下出现激进情绪,对政府的信息披露和处置措施表现出抵触心理或不信任态度。公共冲突的蔓延、对抗性群体心理的传播进一步冲击了群体成员对政府的信任,引发政府公信力危机,严重的还会冲击政府合法性。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因偶发的社会治安事件演变成社会冲突,进而导致国家政权更迭的现象屡见不鲜。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会进一步消解政府处置公共冲突的权威,降低政府遏制对抗性群体心理传播的效果,严重的还会导致公共冲突的失控,引发社会性的秩序危机。
(二)催生责任分散效应,加剧社会秩序维护风险
公共冲突中对抗性群体心理的高传播性和高模仿性加速了激进情绪、对抗行为的传播和扩散,受外部环境的刺激和个体意识缺失的影响,原本作为独立个体时谨小慎微、敬畏法律、富有责任感的“公众”演变成责任意识缺失、情绪多变且容易诉诸暴力的“暴民”。“公众”向“暴民”的转化会加剧激进情绪对群体成员的心理渲染,个体责任意识的缺失会加剧公共冲突对社会安定秩序的冲击,引发社会治安风险。正如当时众多社会学家,如古斯塔夫·勒庞、西庇阿·西盖勒(Scipio Sighele)、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认为的那样,引发冲突并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的唯一罪魁祸首是因模仿他人而呈现非理性的群众,面对因激进情绪和对抗心理而引发的群体行为给社会秩序带来的破坏,虽然“惩罚群众有道理,但你办不到”[15],这会催生责任分散效应。
在责任分散效应的推动下,个体不再是推动社会和谐、安全、有序的主体,而是在公共危机中出现了法律责任、伦理责任以及社会责任等的缺失[16],个体责任缺失既是公共冲突中对抗性群体心理扩散的结果,也是加剧公共冲突烈度和破坏性的诱因。受个体责任缺失的影响,个体在群体性公共治安事件中变得肆无忌惮,社会伦理、法律规范对个体行为的约束大为减少,并引发不良示范效应,增强公众对对抗性行为的仿效。大多数群体性治安事件中,在群体氛围、激进情绪等的渲染下,个体变得越来越狂躁,且在法不责众心理驱使下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群体的聚集、激进情绪的扩散增强了公众对极端行为的模仿,且群体的规模越大这种趋势越明显,这一特点使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成为勒庞口中的“乌合之众”。这会使原本理性的个体逐渐趋于情绪化和极端化,并在外部环境刺激下导致普遍的心理对立,从而引发对抗性破坏行为。在此情境下,个体会做出原本不敢做的事情,如打砸焚烧车辆、冲击政府机关,给社会公共秩序带来严重冲击,加剧社会治安严峻形势。
(三)导致群体心理极化,激化社会对立风险
公共冲突中对抗性群体心理的大范围传播和社会化模仿会导致群体心理的极化,形成普遍的心理对立,造成极端情感和对抗情绪的社会性化。群体极化指的是群体中的成员经过对其最早具有的某种态度倾向的互动、交流和共振,推动这种态度倾向的强化和发展,最终形成极端的态度和观点[17],群体极化包括群体心理的极化与群体行动的极化。作为一种群体化的心理倾向,群体极化具有情绪化和非理性、去个性化和匿名化等特征,它是极端情绪或观点在群体内传播的结果,对群体情绪和价值具有强化作用。群体心理极化的结果是群体中原本多元的态度倾向、理性的价值判断和个性化的意见表达被情绪化、非理性、匿名性以及单一化的群体特征所取代,导致群体心理特征的内卷化、情绪宣泄的极端化和行为选择的对抗化。群体心理的极化会导致群体行动的极化,极端的群体态度和群体心理会使公共冲突中多元的群体,尤其是对立的群体之间难以形成共识,导致群体在参与政治事务过程中采取极端的、激进的、对抗的或者情绪化的群体行为。
群体心理的极化在导致群体心理极端化和单一化的同时,还会引发群体成员对群体意见领袖的盲目信任,加剧极端情绪在群体内的传播,增强群体成员对群体意见领袖的模仿效应。在公共冲突中,对抗性群体心理的蔓延会强化群体间的对抗性,不同的群体固守自身的认知或情感,并在传播的推动下在社会中形成多元的对抗性群体心理。如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不同的群体秉持不同的立场,彼此冲突的立场间甚至发生激烈的对抗,引发广泛的社会冲突,这些对抗性群体心理有着各自的核心价值和利益诉求,在极化的群体心理驱动下对立,模仿行为的广泛发生则进一步加剧了心理的、普遍的对立,激化社会对立风险。对抗性群体心理的这些影响会导致社会矛盾的不可调和,甚至在固守极化群体心理的过程中发生冲突,给社会秩序带来消极影响。
四、公共冲突中对抗性群体心理的疏解路径
公共冲突中对抗性群体心理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公共冲突之初,对抗性群体心理并未普遍存在,而是在传播与模仿的推动下逐渐向社会扩散,进而催生普遍的对抗性心理,给公共秩序带来冲击。要想控制冲突的扩散、缓解群体心理的对立程度、减少公共冲突对社会的破坏性,就需要从影响对抗性群体心理形成的传播和模仿着手,寻求规制对抗性群体心理的有效路径,以消解对抗性群体心理对社会秩序的冲击。
(一)强化政府信息传播主导权,控制冲突扩散范围
传播是推动冲突扩散的重要力量,互联网络、报纸、电视等传播媒介的传播以及个体间的交流、争论都会推动对立情绪、怨恨心理、激进思想的扩散,冲突的扩散扩大了对抗心理和抵制情绪被感知的范围,塑造了公众的模仿对象,加速了公众的模仿行为,为群体心理的生成和对立提供了组织基础。要想化解对抗性群体心理的消极影响,就需要在公共冲突发生的初期强化政府对社会舆论的主导权,有效引导社会舆论,重塑主流意识形态对公众思想、心理和行为的引导,以控制冲突的扩散范围,有效防止群体极端情绪传播。在传播智能化趋势日益明朗的今天,智能传播的去中心化弱化了政府对信息传播和社会舆论的主导权和控制权,一些科技巨头公司和技术精英凭借对智能传播技术的控制和算法资本的操纵分享了社会中的信息传播权和舆论主导权,从而加剧了政府控制激进、对抗信息扩散的难度。这就需要政府在处置公共冲突时掌握信息发布的主导权,加强对极端思潮、激进情绪等的传播监管,杜绝谣言、虚假信息的传播。
政府在信息披露中的主导性作用发挥需要其顺应当前智能传播的发展趋势,重视抖音、快手、微信、微博、Twitter 等智能传播平台的信息放大效应,增强政府对网络信息传播的控制能力,掌握网络舆论话语权,克服信息披露过程中的“修辞结构单一与表达过于理性”“话语霸权的立场预设”以及“事后补救导向为主”的政府舆情回应范式[18],完善政府应对舆情传播的回应路径,提升政府在舆情应对过程中的话语力。同时还要强化对算法传播的规制,建立制度化的智能传播监管机制,规范算法传播和生成式AI 服务的政策法规,以规范社会传播行为。如2023 年7 月出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生成式AI 不得生成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安全稳定以及宣扬极端思想、暴力的内容,对于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生成式AI 服务还要开展必要的安全评估。
(二)引导社会模仿行为。缓解群体心理对立
思想的形成、心理的塑造和情感的传播与个体的模仿行为密不可分。在公共冲突中,单纯的社会传播虽然能够推动冲突的扩散和群体的形成,但模仿行为的开展才是生成群体心理、引发群体对立的主导因素。随着模仿行为的大范围开展,个体的自我意识逐渐丧失,在群体情感和外部环境的刺激下,群体成员往往做出作为社会个体所不敢做出的事情,从而推动作为群体的“公众”向“暴民”演化。同时,公众在参与社会互动时,往往“具有自动模仿他人动作的倾向”[19],这种模仿既存在动作的模仿,又存在心理的模仿。模仿在个人身上产生的结果是特定“心理印记”的形成,是作为人格基本成分的信念和欲望的制度化,模仿行为的发生会导致两个结果,即控制和对立,其中控制指的是群体意见领袖(社会精英)对普通群体成员(普通大众)的控制,对立指的是基于模仿形成的纯粹精神上的组合间的对立。
因此,要减少对抗性群体心理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和破坏,还需要引导社会模仿行为,在控制冲突扩散的同时,依靠外在的强制力削弱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对对抗、破坏、愤懑、怨恨心理和行为的模仿。如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对于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煽动策划非法集会、扰乱机关企事业单位正常秩序等行为,视其情节予以相应的处罚。这能够有效阻断极端群体行为传播路径,弱化因模仿行为而出现的群体对立,缓解或者遏制对抗性群体心理对公共秩序的破坏。对社会模仿行为的引导还需要借助传播媒介对个体进行思想的引导和榜样的塑造,通过塑造正面榜样来引导公众的模仿行为。同时,还需要提升公众的媒介素养和理性思维能力,防止其在喧嚣的群体情感和外部环境的刺激下出现个体独立个性的丧失和无意识模仿行为,以保持相对稳定的心理状态,从而削弱群体意见领袖以及外部环境对个体心理的控制,推动作为群体成员个体的自主意识的恢复,弱化群体心理对立。
(三)优化传播与模仿互动关系,消解公共冲突破坏倾向
传播和模仿行为对冲突的扩散、群体的形成和群体心理的塑造产生影响,其中,传播在推动作为纯粹精神上的群体生成的同时,增强了个体模仿群体意见领袖、其他个体情绪和心理的可能性,而模仿则能够强化群体意见领袖对群体成员的控制、导致不同群体间的心理对立。在塔尔德看来,模仿是一种从内心到外表的模仿,即先模仿他人的思想和心理,再模仿他人的行为,在模仿的过程中,地位越高、距离越近的人越容易被模仿,认为“生气勃勃的权威人士对柔弱的人具有不可抗拒的影响力”[12]143,从而阐释了社会精英在模仿中的主导作用。正如勒庞在其《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的思想、心理和行为总会被群体意见领袖所左右,群体意见领袖通过将公众塑造成无意识的“乌合之众”来推动群体情感的传播、引导公众心理的塑造。
因此,对公共冲突中对抗性群体心理的规制,消解群体心理的对抗性和破坏性,还需要从传播与模仿互动的角度着手,以消解其破坏倾向。传播与模仿的互动推动着群体情绪的扩散和对立心理的塑造,传播使基于身体接触的“群众”转化为以纯粹精神为内在关联的“公众”,而模仿则使作为“公众”的个体成为具有对立、破坏心理的“暴民”,这些“暴民”受群体意见领袖的控制和外部环境的刺激,以极端破坏行为参与公共冲突。这就需要优化传播与模仿的互动,从整体上实现传播与模仿互动关系的均衡,既要防止因过度传播导致的冲突扩散和群体规模扩大,也要隔断公共冲突中对抵制情绪、怨恨、对抗心理的模仿路径,弱化群体意见领袖对群体成员的控制,使传播成为政府主导下的传播,模仿成为政府主导下的模仿,从而将社会中的传播和模仿行为控制在秩序允许的范围之内,寻求传播和模仿的动态均衡,通过有目的的传播和有针对性地模仿化解公共冲突中对抗性群体心理的破坏倾向。
(四)完善心理疏解机制,防止群体心理极化
当公共冲突中的极端情绪、怨恨心理扩散之后,往往会在社会中形成对立的群体心理,而在这一群体心理形成之前可能并不被其他人所察觉。针对这一情况,当公共冲突中的对抗性群体心理已经形成时,就需要借助心理疏解机制,强化对群体心理,尤其是极端对抗性群体心理的疏导,以防止群体心理极化。群体认同、外部环境刺激、群体情感渲染以及其他个体的支持都会成为影响个体心理塑造和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当个体成为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时,“群际情绪、群体认同将个体内在的情绪唤醒”,从而使群体及作为群体成员个体的“态度极化及行为极化的可能性增大”[20]。据此,对个体的心理疏导需要削弱极端情绪、极端行为对个体的刺激,缓和极端群体心理对群体成员的影响,为群体成员的心理宣泄和情感表达提供多样化的渠道。心理的对抗大多是利益的冲突,这就需要拓展冲突中的利益表达渠道,使冲突双方得以进行积极的沟通,从而消解群体间的紧张对立情绪,弱化群体心理的对抗性。
同时,极端群体心理的扩散和群体情感认知的高度统一会导致群体决策的极端化,群体心理向着冒险或保守的一极倾斜,从而引发激进或保守的群体行为,群体的心理极化往往呈现激进、对抗和破坏特征,因此,规制群体心理的对立和破坏倾向还需要防止群体心理极化。防止群体心理极化需要建构完善的心理预测预警机制,当发生心理对抗时,能够及时对群体心理形成的逻辑进行溯源和分析,对冲突可能导致的群体心理及相关行为进行有效预测,增强对群体心理的预判能力,阻断群体心理极端化逻辑,有效应对因群体心理极化造成的对抗性破坏行为。在应对基层社会治安事件中的群体心理极化时,可以借助“声望”“荣誉”等实现非正式互动,通过对情感资源的动员强化冲突双方的心理融合,并借助个体声望对激进的群体“在更广泛的时空场域发挥引领效应”[21],以消解极端心理对群体的影响,将更多的组织和个体吸纳进社会治安的协同治理体系之中,铲除心理极化的生发情境。
结 论
在塔尔德的社会理论谱系中,传播和模仿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传播为传统的基于身体接触的“公众”向纯粹精神上的结合的“群众”转化提供了条件,而模仿则推动群体内基于共同价值基础和情感诉求的群体心理的形成,对极端群体心理的模仿甚至会推动“公众”向“暴民”的演化。在公共冲突中,传播行为的出现推动了极端情绪、激进思想的扩散,进而形成了存在直接利益关系的群体,并在传播行为的推动下进一步形成了无直接利益关系但有情感共鸣的群体,从而扩大了群体规模和影响范围。受激进情感和对抗心理的影响,公共冲突中传播行为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速个体间的模仿速度和模仿范围,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基于共同“心理印记”的群体心理,且这一群体心理在群体情感氛围和外部环境刺激下大多呈现对抗性和无意识性,进而给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护带来较大压力。因此,需要从传播与模仿的角度探讨公共冲突中对抗性群体心理的疏解路径,以有效防止冲突的扩散、化解激进对抗群体心理的形成,消解对抗性群体心理对社会秩序和政治运行的冲击,切实提升社会治安防控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