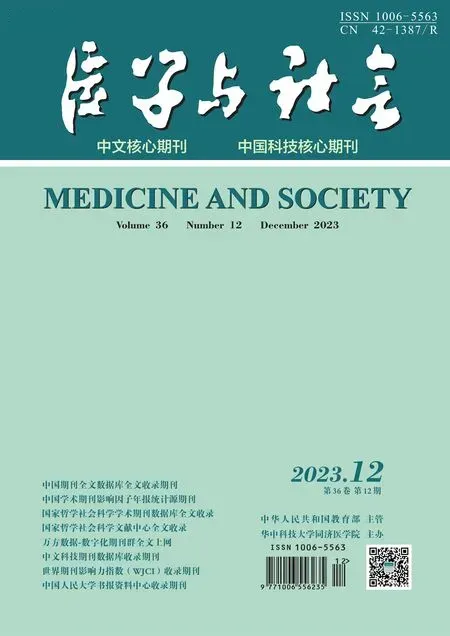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情况及其与认知障碍的关系
朱正杰,施正丽,张 浩,曹望楠,纪 颖,史宇晖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北京,100191
认知障碍(cognitive impairment, CI)是指人体记忆、语言、视空间、执行、计算和理解判断等认知功能的一项或多项受损[1],它已开始成为影响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2]。我国于2020年发表的一项全国流行病调查发现,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认知障碍率为21.58%[3]。我国另一项Meta研究结果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认知障碍率为22.0%。其中男性和女性老年人认知障碍率分别为18.8%和23.2%,60-69岁、70-79岁、8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认知障碍率分别为13.4%、22.0%和36.3%[4]。由于CI病程长、难逆转、暂无有效治疗方案,经常导致患者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减退[5],且经常伴有各种神经精神症状和障碍,因此往往给其家庭和社会带来极大负担[6]。已有研究表明,社会参与情况对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存在影响[7]。世界卫生组织强调,老年人应回归社会,不仅仅参与到体力活动和劳动当中,也参与到社会、经济、文化、精神和公益事务在内的各个实践领域, 参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2021年11月1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及2022年2月21日发布的《“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中也明确提出,要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积极参与家庭、社区和社会发展,践行积极老龄观,鼓励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在社会参与的定义上,根据国外的一项系统综述研究,目前学术界较普遍地认为,社会参与是指一个人在社会或社区中参与与他人互动的活动[8]。但截至目前,社会参与的定义还未被明确界定,其分类及内涵也仍在被不断扩充[8]。
当前,国内有关社会参与和老年人认知障碍间关系的研究多数只分析了具体的活动(如打麻将、上网等)情况[9],较少研究对活动进行分类,以统计分析参与不同种类活动的情况,对活动分类的方法也大相径庭[10]。这种将具体的活动综合归类的方法,对于推断老年人在生活中,在各种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与其认知障碍发生风险之间的关联,可能将更有意义。此外,目前这类研究较少将个体参与活动的频率纳入分析[10],因此无法得知老年人参与各种活动的水平高低是否影响其认知障碍的发生。综上,社会参与中参与活动的种类及参与水平的高低是否影响老年人认知障碍的发生仍亟待研究。目前国内有关分析老年人社会参与和认知障碍间关联的部分研究,由于受主持和执行机构、调查时间长短、地区、样本量大小等条件限制,因此有着权威性及代表性不足的问题[11]。本研究拟利用具有较高权威性和较好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2018年数据,分析我国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情况,研究其社会参与情况和认知障碍之间的关系,为预防及干预老年人认知障碍提供参考建议。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研究利用2018年CHARLS数据进行分析,该调查是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持、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大型长期追踪调查项目,旨在收集一套代表中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经济、健康状况及社区环境情况等高质量微观数据,用以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推动老龄化问题的跨学科研究,具有较高的权威性[12]。此外,CHARLS全国基线调查于2011年开展,采取多阶段分层抽样选取我国30个省、 150个县、450个村约2万人,并于每2-3年追踪1次,样本量较大,具有较好的全国代表性[12]。由于CHARLS最新的第5轮随访调查数据还未向学术界公开,因此截至目前,CHARLS 2018年数据仍然具有一定的时效性。本研究选取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剔除年龄<60岁样本10378人,剔除认知功能信息缺失样本7114人,剔除参与活动信息缺失样本4人。在研究过程中剔除数据中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但并不影响统计推论的有效性,最终得到有效样本3370人。
1.2 变量选取
选取2018年CHARLS 数据的部分变量开展分析,包括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人口学特征、健康状况、健康行为)、社会参与情况及认知功能情况。
1.2.1 研究对象基本信息。 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包括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居住地、教育程度及婚姻状况),健康状况(自评健康情况与残疾状况)以及健康行为(吸烟及饮酒史)。残疾状况包括躯体残疾、大脑损伤、视觉障碍、听觉障碍及语言障碍。
1.2.2 社会参与情况。 本研究中,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情况通过调查其参与社会活动的种类、数量及参与水平进行统计分析。CHARLS的2018年追访问卷中询问了调查对象1个月内11项社会活动的参与情况以及相应的频率。在参与活动种类方面,本研究基于既往部分研究对活动分类的方法[11],将CHARLS 调查问卷中11项社会活动归为以下5类。①社交娱乐类:串门、跟朋友交往;打麻将、下棋、打牌、去社区活动室;跳舞、健身等;参加社团组织活动。②志愿服务类:向不住在一起的亲人、朋友或者邻居提供帮助;照顾不住在一起的患者或残疾人;志愿者活动或者慈善活动。③学习培训类:上学或者参加培训课程。④数字媒体类:上网等。⑤其他类:其他社会活动。
根据现有研究[9],在社会活动的参与数量上,本研究将每参与1项活动赋为1分,不参与赋为0分,参与某种活动中任意1项活动则认为参与该种活动(例如参与打麻将、下棋等活动即认为其参与了社交娱乐类活动),否则认为其不参与。在参与水平上,利用3级量表设置频率变量,将每项活动频率的选项“不经常”“差不多每周”“差不多每天”分别赋值为1、2、3分。设定每项活动的参与水平得分=是否参与*参与频率,并规定每种活动参与水平得分为该种活动下各项活动得分之和。因此,研究对象的社交娱乐类、志愿服务类、学习培训类、数字媒体类及其他类活动的最高得分分别为12、9、3、6、3分。社会参与总水平为所有活动的参与水平之和,最高得分为33分。
1.2.3 认知功能评价。认知功能的测量采用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inimum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13],该量表由定向能力、即时记忆力、计算能力、延迟记忆力、绘画及语言组织能力5个维度共30个问题组成,每个问题回答正确计1分,回答错误计0分,总分共30分,受访者总得分越高,则代表其认知功能越好。根据以往研究,按受访者的教育程度对其是否存在认知障碍进行划分[14]。划分标准如下。①教育程度为文盲水平:MMSE得分≤17分者存在认知障碍。②教育程度为小学水平:MMSE得分≤20分者存在认知障碍。③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水平:MMSE得分≤23分者存在认知障碍。
1.3 统计学方法
利用SPSS 26.0对数据进行分析,定量数据用均值及标准差或中位数及四分位数描述,分类数据用频数及百分数描述。采用卡方检验进行分类变量的单因素分析;采用秩和检验进行数值变量的单因素分析;以是否存在认知障碍为因变量,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分析研究对象在社会参与中参与社会活动的种类及参与水平的高低与其认知障碍的关系,变量筛选采用逐步后退法。检验水准双侧α=0.05。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及社会参与情况比较
在3370名研究对象中,男性2205人,占65.43%,女性1165人,占34.57%。1931人(57.30%)至少参与了1项社会活动,平均参加社会活动数量为1.00(0,2.00)项,平均参加社会活动种类为1.00(0,1.00)种,平均社会参与水平得分为1.00(0,3.00)分。存在认知障碍的有589人(17.48%),平均认知功能得分为25.00(23.00,27.00)分。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研究对象的社会参与情况与其性别、年龄、城乡、教育水平、自评健康状况、是否饮酒和认知障碍状况有关(P<0.05)。其中,在无认知障碍的研究对象中,参与社会活动的比例为59.44%,高于有认知障碍的研究对象中参与社会活动的比例(47.20%,χ2=29.764,P<0.001)。
2.2 老年人社会参与种类及数量与认知障碍的关系
在参与活动种类方面,有社会参与(χ2=19.764,P<0.001)、参与社交娱乐类(χ2=16.835,P<0.001)、志愿服务类(χ2=13.532,P<0.001)及数字媒体类(χ2=55.115,P<0.001)活动的研究对象,相比于没有社会参与、不参与上述种类活动者,其有认知障碍的研究对象所占的比例都更低。
在参与数量方面,老年人是否存在认知障碍与其参与活动数量(χ2=55.788,P<0.001)和参与活动种类数量(χ2=52.195,P<0.001)相关,其认知障碍发生风险与参与活动数量(r=-0.999,P<0.05)、参与活动种类数量(r=-0.999,P<0.05)呈负相关关系,即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数量和活动种类数量越多,参与的活动越丰富,其发生认知障碍的概率越低。见表1。

表1 老年人社会参与种类及数量与认知障碍的关系 n(%)
2.3 老年人社会参与水平与认知障碍的关系
本研究中老年人社会参与水平得分不符合正态分布,因此采用Mann-WhitneyU检验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无认知障碍者和有认知障碍者的社会参与总水平得分中位数分别为1.00 分和0分,平均秩次分别为1739.88和1428.74。U检验结果显示,两组人群的社会参与总水平得分有统计学差异(Z=-7.367,P<0.001),可认为老年人参与活动频率越高,社会参与水平越高,其发生认知障碍的可能性越低。此外,无认知障碍者在社交娱乐类活动(Z=-4.994,P<0.001)、志愿服务类活动(Z=-3.711,P<0.001)、数字媒体类活动(Z=-7.426,P<0.001)上的参与水平皆高于有认知障碍者,而在学习培训类活动及其他类活动上则无显著差异。见表2。

表2 老年人社会参与水平与认知障碍的关系
2.4 老年人社会参与和认知障碍关联的多因素分析
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并分别纳入不同控制变量模型,分别计算调整后OR值(Adjusted OR,AOR)。结果显示,在只包含自变量的模型1的基础上,依次引入了人口学特征(模型2)、健康状况(模型3)、健康行为(模型4)等控制变量后,有社会参与(AOR=0.699)、参与活动数量(AOR=0.799)、参与活动种类数量(AOR=0.742)、社会参与总水平(AOR=0.885)、社交娱乐类活动的参与水平(AOR=0.898)及数字媒体类活动的参与水平(AOR=0.705)与老年人认知障碍发生风险呈负相关。见表3。

表3 老年人社会参与和认知障碍关联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AOR(95%CI)
3 讨论
3.1 我国老年人总体社会参与水平较低
结果显示,我国老年人总体社会参与水平较低,参与的活动也不丰富。在所有研究对象中,近1个月从未参与过任何社会活动的人数占比接近一半(42.70%)。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数量较少,种类也不够丰富,参与≥3项活动或≥3种活动的老年人分别只占11.07%(373人)和3.80%(128人)。此外,本研究中平均社会参与水平得分为1.00(0,3.00)分,与33分的满分相比相差巨大,说明大部分人的社会参与水平都处于较低水平。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从“生理”到“自我实现”,由低到高划分为5个层次,人只有满足了低层次的需求之后,才会寻求高层次的满足[15]。因此,部分老年人社会参与水平低下可能是其在温饱、安全等问题上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所导致的。本研究中,居住在城市的老年人中参与社会活动(67.53%)的比例显著高于农村地区(50.28%),这可能也说明了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程度低的问题可能随着其经济水平的好转而得到解决。王慧英对我国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情况的研究中发现,相比于户籍老年人,流动老年人在文化娱乐、人际交往和社会公益活动上的参与水平更低,但在经济活动中参与水平更高[16],原因可能是流动老年人将精力更多地放在赚取金钱上,以满足自身及家庭的温饱等生理需求。当前,我国虽然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经济发展仍处于不平衡、不充分的阶段,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仍面临不少难题[17],这可能是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程度低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3.2 老年人更喜欢参与娱乐休闲类及数字媒体类活动
本研究发现,老年人对于参与社会活动的种类存在偏好,更喜欢参与娱乐休闲类和数字媒体类活动。在过去1个月曾参与过串门拜访朋友、打牌、跳舞、社团活动等社交娱乐类活动人数占总研究对象的49.61%,但参与学习类活动和其他类活动的人数则只分别占0.74%及2.08%,说明娱乐休闲活动更受老年人的喜爱。另外,本研究中参与数字媒体类活动的老人占比为13.12%,说明数字媒体类活动也正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老年人群体的关注。北京大学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项目组于2019年发布的《中国健康与养老报告》显示,从2011-2015年,我国老年人网络使用率正在不断升高。这可能是由于时间的推移,老年人的整体教育水平更高,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老年人接触数字媒体的机会也更多。此外,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分别于2011年及2022年发布的《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和《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在2010-2022年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互联网普及率由5.1%上升至44.1%,这也佐证了我国老年人线上社会参与的意愿越来越强烈。根据胡还甫于2021年的一项抽样调查,会使用网络的老年人的比例达到了60.85%,甚至有7.31%的老年人能非常熟练地使用网络[18]。尽管该研究是在我国某一线城市中进行的抽样调查,且样本量较小,可能高估了当前我国老年人整体线上社会参与情况,但可以确定的是,线上的社会参与方式,具有不受时空限制,可让人随时随地参加活动,且可以与远距离的人们保持联系的优势,因此在未来,老年人参与线上社会活动的水平可能会越来越高。
3.3 社会参与水平越高,老年人认知障碍发生风险越低
本研究的重点在于探讨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情况和认知障碍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老年人参与的社会活动数量越多、种类越丰富,其认知障碍发生风险越低。这说明,参与更多的社会活动是老年人发生认知障碍的保护因素。此外,老年人认知障碍的发生也与其参与活动的水平高低有关,较高频率参与社会活动有助于减缓老年人认知障碍的发生。原因可能是,老年人在参与社会活动时获得的认知刺激,能够激活和加强各种神经生物学通路,使老年人更好地补偿任何潜在的大脑变化,从而保持其认知功能在相对稳定的状态[19]。压力、焦虑等负面情绪在以往研究中也被认为是影响认知功能的因素[20],在参与和他人的交往中,老年人能够获得更多的物质和情感支持,产生积极的情绪状态,从而缓冲负面情绪对健康带来的不良影响[8]。此外,参与更多的社会活动还提供了扩大社会网络以及增加社会支持、获得资源的机会,可能通过影响其行为来影响认知功能[10]。因此,提升社会参与的水平,能够维持老年人的认知功能,降低老年人的认知障碍的发生风险。
3.4 不同种类的活动对老年人认知功能的保护作用大小不同
本研究显示,不同种类的社会活动对认知功能的影响不同,例如参与社交娱乐类及数字媒体类活动对老年人认知障碍发生的保护作用,相比于学习培训类及其他类活动更为明显。国内目前一些干预研究采用娱乐疗法对脑卒中患者进行干预,发现其认知功能有所改善,可能的原因是,在娱乐类活动中,老年人的负面情绪能得到缓解,记忆能力与思维能力也能得到充分锻炼[21]。参与数字媒体类活动能降低老年人认知障碍发生风险的原因可能是,电子产品的使用是一项复杂的任务,需要调动多个认知领域,而参与数字媒体类活动能够很好地锻炼多任务处理的能力,进而防止老年人认知功能受损[22]。另外,既往研究显示,老年人更多地使用互联网与较低的孤独感有关,老年人使用微信、电子邮件等联系方式作为面对面社交的补充,可以增进其与亲友等彼此间感情,从而避免社交隔离和潜在的孤独感,这也能够很好地维持其认知功能[23]。
在多因素分析中,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类活动与认知障碍间的关系不再显著,这一结果与现有的大部分研究发现不一致[24]。可能的原因是,既往研究的志愿服务类活动主要集中在主动向他人提供志愿者工作上[24],而本研究中志愿服务类活动则包含了照顾残疾人和病人。老年人在参与该类活动中,将感受到更多的辛苦与劳累,亲友的疾病、老去甚至是离世,也将为其带来更大的经济及情感负担,使其认知障碍发生风险升高。此外,虽然学习培训类活动在客观上能够使老年人获得认知刺激,保护其认知功能,但本研究并未发现参与这类活动对老年人认知功能存在正向影响的证据,可能的原因是本研究中参与学习培训类活动的人数较少,导致结果出现偏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