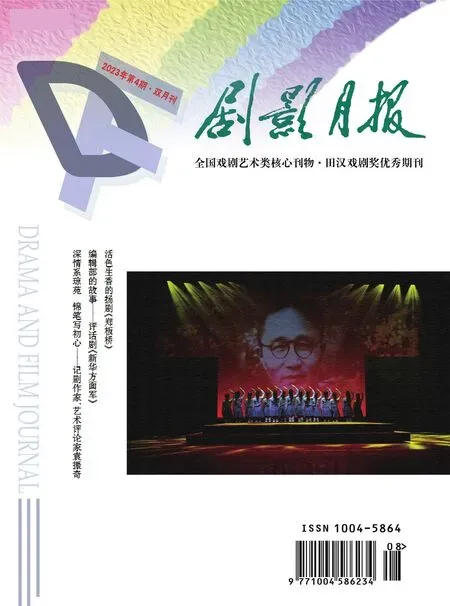王国维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美学比较研究
——从《〈红楼梦〉评论》与《诗学》出发
■王静
悲剧作为美学研究中重要的一种美学形态,一直被中西方的文艺理论家所讨论。王国维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在中西两方的美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通过比较他们的悲剧美学,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在悲剧的情节与功用方面的理论既有相似点,也有不同之处,不同的时代背景与文化土壤孕育出了不谋而合又各具千秋的悲剧理论。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第一次提出悲剧的定义,并且系统性地介绍了悲剧的组成。我国著名学者王国维则在《〈红楼梦〉评论》中第一次提出了属于中国的悲剧美学概念,借由《红楼梦》延展构建了一套悲剧理论体系。他们二者的悲剧理论在中西两方的美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观之《〈红楼梦〉评论》与《诗学》,我们可以明显发现中西两方学者在悲剧理论方面同源的思考与不同的考量。
一、王国维的悲剧理论及特征
王国维作为国内第一个系统性阐述悲剧理论的学者,他的悲剧美学受到了西方哲学极大的影响,尤其以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哲学为代表。但是王国维也将国学融进了西方美学之中,借《〈红楼梦〉评论》,率先定义了中国近代悲剧美学。
(一)人生之欲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的第一章中就提出“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这里的“欲”源于叔本华唯意志论中的“欲求”,但王国维在此中引入老庄哲学中对于生命的认识。当人的欲望无法被满足时,人就会感觉到痛苦;而当人没有欲望时,又会觉得厌倦,这也是痛苦的一种。因为欲望,人生就像钟摆一般往返于痛苦与厌倦之间,所以王国维认为悲剧的本源来自人的生活欲望,唯有在去除私欲的过程中看清荣辱、看淡生死,方能得到超脱。
(二)悲剧的三种
王国维受叔本华悲剧学说的影响,将悲剧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的,第二种是“由于盲目的命运者”,第三种是“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以上三种悲剧中,王国维认为第三种最佳,在剧中没有绝对坏人,也没有突如其来的变故,只是普通人身处其位,被迫造成的苦难与不幸。王国维之所以认为在我国古代悲剧中唯有《红楼梦》最能体现悲剧意识,也是因为其是第三种悲剧类型的代表。
(三)解脱说
与亚里士多德相似的是,王国维也认为悲剧有一定的社会功用——可以给人带来解脱。王国维将解脱分为两类:“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一种是冷观他人苦痛之后的悟世,一种是通观人生悲剧之后的自悟。一种是对生活本质的感悟,一种是自身的“放下”,前者比后者难百倍,也高百倍。王国维一直将伦理价值作为美学价值的重要支撑,曾说:“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悲剧的价值在于在人世中给予人们精神的解脱与觉醒,得到暂时的平和。
二、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及特征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了西方第一个完整的悲剧的定义:“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模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亚里士多德继承了他的老师柏拉图的观点,认为悲剧的基本属性是模仿,模仿的内容是某些对象的行动。表达行动的对象必然是一些拥有思想和性格特点的人物。因此,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有六个必要组成成分:情节、性格、语言、思想、戏景和唱段。
(一)情节中心说
在悲剧的六要素中,亚里士多德最强调的就是情节。在当时的悲剧中,角色大多选取神话、史诗中的现成人物,缺乏可创造性,所以剧作家往往会在情节上投入大量精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亚里士多德认为好的悲剧一定要情节复杂,而决定情节复杂程度的三大成分则是突转、发现和苦难。“突转”是指剧情突然向相反的方向转变——顺境转向逆境或者逆境转向顺境,“发现”是指主人公由不知到知的醒悟或顿悟,“苦难”是指主人公所遭受的毁灭性的痛苦。亚里士多德认为,同时发生的主人公的顿悟与情节的突转,是情节的精妙之所在。
(二)净化说
不同于柏拉图认为史诗和悲剧会挑起人的欲望、扰乱国家秩序,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可以净化人的心灵、疏导人内心的情绪,具有道德教化的作用。在观看悲剧的过程中,人们会产生怜悯和恐惧等令人激动的情绪,当这些情绪如同风暴一般扫过内心后,人们会获得发泄,并在发泄后获得内心的宁静、平和。亚里士多德将这如同病人得到治疗和净洗的过程称为“净化”。
(三)过失说
为了使悲剧让人产生怜悯和恐惧的感情,以达到净化的目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主人公应该因过失而遭难。一方面,他认为主人公的苦难不能完全是源于自己,因为自作自受的人不会令人同情;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主人公的苦难虽不源于自身罪恶或道德低劣,但需由于自己的某种过失,这样可以引起观众因小错引起大错的恐惧。因此,亚里士多德要求悲剧中的人物是立体且复杂的,纯粹的好人和坏人都不能构成悲剧。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极具有逻辑,同时也兼顾了道德原则。
三、王国维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情节论
(一)相同的追求苦痛与必然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的第三章提到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具有乐天精神,所以无论是戏曲还是小说都带有乐天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例如《牡丹亭》《长生殿》无不是在主人公历经艰难后,拥有大团圆式结局。然而王国维认为悲剧不能一味满足国人的阅读欲望补缺为圆,应该秉持悲剧的内核,反映真实生活。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也曾提出悲剧不应该表现人物从败逆之境转入顺达之境,不一味地追求“奖罚分明”,理应遵循悲剧自身的标准,取得悲剧应该达到的社会效果。
就王国维评判悲剧的标准而言,他认为能称得上纯粹的悲剧的只有《桃花扇》和《红楼梦》。这两部作品的悲剧意识相当浓厚,但是王国维认为还是《红楼梦》胜于前者,可被称为“悲剧中的悲剧”。他认为《桃花扇》相较《红楼梦》在情节逻辑上迂回不够合理、恰当,如主人公侯方域历经艰难后在白云庵地遇爱人李香君时,二人仅相逢一面,尚未来得及叙语,就被张道士点化,双双抛弃爱欲出家,这样的情节发展实在是过于突兀。这一看法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不谋而合,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中的“突转”与“发现”一定要符合情节的发展,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事件与事件之间一定要有前因后果的关系。
可以看出,针对悲剧情节的构成,王国维与亚里士多德都秉持相同的观点,悲剧从始至终必然贯彻其“苦痛”的特点,不追求所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时,在悲剧情节的发展过程中,一定要符合该有的逻辑,不可强行改变故事发展进程。
(二)普通人本能意志的结果与高贵者在命运使然下的犯错
在悲剧的起因和对象方面,王国维与亚里士多德所持的观点不尽相同,前者认为悲剧是普通人本能意志的结果,后者认为悲剧是高贵者在命运使然下的犯错。
王国维吸收了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关于悲剧成因的讨论:第一种悲剧为恶人肇事造成,第二种悲剧为命运的盲目不公造成,第三种悲剧由角色地位、立场不同而造成。王国维与叔本华一致认为第三种悲剧最为可取,因为这种悲剧是由于角色处于互相对立的状态,被迫对对方造成伤害,是人坚持本能意志的结果,无可抱怨也无不公平所言。在这方面,亚里士多德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完美悲剧的主人公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此类悲剧最能产生效果,尤其是惨痛的事件发生在近亲之间时,如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儿子企图杀死父亲。人物所犯的错误,并不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邪恶与罪恶,这些在命运使然下犯的错误,成了悲剧最能引起人怜悯的部分。
关于悲剧的对象,王国维认为其应该是普通人,让观众感到此种悲剧“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或可以加诸人”,因而更加有代入感。主人公既不是“恶毒愚蠢到极限”,也不是“极端高尚”的人,他们在道德上“平平无常”,符合大多数人的特点。同时,他们所遭受的苦痛不是罕见而例外的,而是随时可能降临在自己头上的,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悲剧模仿的对象必是表现比今天好的人,是高贵者,他们遭受了不该遭受的不幸,他们或许可以“不具备十分的美德,也不是十分的公正”,但是他们必须比今天的人更好,如俄狄浦斯、忒勒夫斯、苏俄斯忒斯,他们名声显赫,出自少数几个大家族。在亚里士多德心里,这样的人物构成的悲剧最符合悲剧意识与艺术的标准。
四、王国维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功用论
(一)相同的宣泄恐惧与悲悯
我们可以从《〈红楼梦〉评论》中看出王国维对艺术品的审美作用格外重视,他与亚里士多德在悲剧的社会功用方面的理论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王国维认为悲剧具有疏通内心、释放感情的作用。他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中提出:“欲如悲剧中之主人公,且演且歌以诉其胸中之苦痛者……夫人生中固无独语之事,而戏曲则以许独语故,故人生中久压抑之势力独于其中筐倾而箧倒之。”当现实中的人遭受苦痛,只能自己压抑着,无人可以听其倾诉,然而当这些苦痛再现于悲剧作品中,主人公代替观众说出了自己无可诉说的悲情,观众感同身受后,自身的情绪便能宣泄而出,得到缓解。当自身的感情得到释放后,心情便可归于平静。
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感情不可以强制地压制,应该通过宣泄的方式进行适当的控制和调节,悲剧则可以充当这个宣泄的渠道。通过宣泄之后达到内心宁静的过程,在西方美学范畴中被称为“净化”,是一种无害的快感。如何通过发泄情绪达到净化的目呢?王国维与亚里士多德都提到了两种感情——怜悯与恐惧。可以说悲剧的一切情节设计都要以激发观众的恐惧与怜悯为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恐惧是一种由不幸之事产生的痛苦与烦躁,怜悯是看见他人遭受不该遭受的痛苦,随后想到这种痛苦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而产生的感情。亚里士多德在给悲剧下定义时就曾明确提出:“悲剧的模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感情得到疏泄。”在《诗学》中讨论悲剧的情节设计时,亚里士多德花了极大的笔墨讲解作者应该追求什么,避免什么才能使悲剧最大限度地产生“净化”的效果。当然,悲剧引发恐惧和怜悯并不是在宣扬这种感情,而是为了使人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就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话:“昔雅里大德勒于《诗论》中,谓悲剧者,所以感发人之情绪,而高上之。殊如恐惧与悲悯之二者,为悲剧中固有之物,由此感发,而人之精神于焉洗涤。”王国维认为悲悯、恐惧的情绪被悲剧激发的过程也是内心得到陶冶和锤炼的过程。
(二)精神上的净化与伦理上的解脱
王国维在探讨悲剧的功用时,不仅吸收了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还受到了如叔本华、尼采等西方哲学家的一定影响,他结合老庄哲学在伦理上的思想自悟自创了一套关于悲剧的效用与价值的论述——解脱说。王国维将悲剧的效用和价值与悲剧的本源“人生之欲”结合起来,表示悲剧不仅能揭示人生的痛苦,更能启发观众解脱。他认为《红楼梦》作为“悲剧中的悲剧”揭示了生活的苦痛是由于追求自身意志造成的,想要获得解脱,唯有自己放下“欲望”,领悟人生真谛。
王国维认为解脱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宗教式的遁入空门例如出家,一种是对生活本质的通悟,而这二者都要求人们通观人生苦痛,悲剧的作用恰好可以在这里体现出来。王国维认为悲剧除了可以使人抒发情感获得内心的宁静以外,还能让人找到轻荣辱、淡名利,突破“小我”桎梏的方法。王国维的解脱说,是在伦理上阐释悲剧的效用,而解脱中想要摆脱的是除了“人伦忠孝”以外的全部“生活之欲”,既是佛家中的“空”,也是老庄哲学中的“无”。这些理论与王国维自身弃私忘欲、离世解脱的人生价值观息息相关。
而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并没有如同王国维一般否定人的欲望与被欲望牵动的情绪。他认为当欲望与情绪被悲剧引发出来后,只要将其适当地宣泄出去,获得长时间的宁静,悲剧就为社会起到了调节人们生理和心态的作用。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中,强调的更多的是疏导而不是压制和消灭,这是他与王国维的悲剧理论在悲剧的功用方面极大的不同。
五、结语
从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第一次提出悲剧的概念到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第一次系统阐述国人的悲剧美学,其间跨越了十几个世纪,二者的悲剧美学观既有异曲同工之处,也有不尽相同的观点。亚里士多德与王国维在悲剧的情节构合上都讲究悲剧意识,追求从始至终的苦难,并且强调故事发展的逻辑与合理性;在悲剧的社会功用上都认为悲剧有宣泄情绪、使心灵获得宁静的作用。但是在悲剧的对象和成因上,王国维认为悲剧是普通人处于不同的地位而被迫向对方造成的苦痛,是个人意志的结果,而亚里士多德偏向悲剧是高贵者在命运的戏弄下犯的错误。在悲剧的功用上,王国维的解脱说明显受老庄哲学和叔本华“唯意志论”的影响,相较净化说的疏解调节情绪,他认为应该直接通过悲剧消灭“人生之欲”,以取得长久的内心宁静。从现如今的美学观点看二者当时的悲剧理论,各有不全面之处,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土壤中对于悲剧的独特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