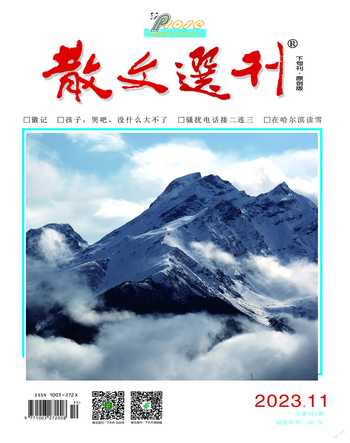把灶火
苏国钟

说起工作履历,我可谓“老干部”了。
从五岁始,我就“参加工作”了。
五岁时,我就得在大人的支使下,学着起火做饭,尤其是烧柴“把灶火”。
我们村家家户户用的柴火,大部分是从村后山捡来的“相思树”落叶,一条一条或一团一团的,看上去像晒干的面线一样,作为火引和主要燃料相当好用,一点就着。老家村子背靠几座连绵的小山。小山也是我们的“柴火库”。为了保证一周的柴火,我常常和母亲在周末的时候上山“拾草”。“拾草”是一个综合性的称谓,其实就是到山上捡树上掉下来的枯枝败叶,有时也会把一些树枝用镰刀砍下,摆放折叠好,用绳子捆起来挑回家。那时候家里太穷,一年到头买不了两双拖鞋,大伙儿穿的拖鞋清一色是人字拖鞋,常常是走着走着,上面的橡胶带就脱了或断了。这时,索性把拖鞋扔在草筐里,光着脚丫上山,久而久之,脚底磨出厚厚的一层皮,竟然不怕草丛中的小刺,在夏天烈日暴晒的山路上也能健步如飞。
把灶火时,首先搬一块竹凳坐在灶膛前,抓一把干草塞进灶孔里,再拣几根枯枝,有的粗,有的细,长一点的就用膝盖顶住折断,搁在干草和锅底之间。
“ 嚓”的一声,把点燃的火柴伸向干草。火“刺刺”地响着,越烧越旺,很快把细树枝点燃,同时烤热,慢慢引燃粗树枝。粗一点的树枝往往没那么容易一下子点燃,特别是像小孩子手臂一般粗的树枝,搞不好就会半途熄火,冒出一股黑烟,把小孩子熏成小黑包公。所以,在粗树枝没有完全烧开的情况下,还必须小心翼翼地用一把1米左右长的铁钩子或者铁钳子,在粗树枝和细树枝之间隔出间隙,有时候也需要在细树枝和枯草之间压出一定的空间,这样才能保证火不至于缺氧熄灭。
因为年龄尚小,难免因为操作不当而中途灭了火,这时候有几种补救措施:一个是用铁钩子把干草弄得蓬松一点,间隙更大一些,让空气流通起来,然后把嘴巴凑近灶膛口,用嘴巴对着火星吹气,吹一次不行,那就两次、三次,直到“噗”的一声,火苗子重新蹿起来。有时候是因为干草已经没了,树枝还没真正点燃,那就赶紧再抓一把送进灶膛里,用吹火星或点火柴的办法,重新燃火;再有的时候,树枝其实已经被烧红,只是还没蹿出火苗,只需要用铁钩子把树枝略挑起来,外面的空气一进去,瞬间就又自动燃烧了。
用多少树枝和多粗的树枝,用大火还是小火,跟做什么饭有着紧密的关系。
最常干的是烧开水,往往也就是接连用几把干草,配合一小把细细的枯枝就能够轻松搞定,如果烧的开水比较多,需要装满三四个热水瓶,那就多几把小枯枝才能搞定。起初,锅里的水风平浪静,烧了大概10 分钟,锅里四周开始冒着小气泡,这时,赶紧添一把柴火,水就沸腾起来了。
其次是煮地瓜汤,那就得先派出干草和细树枝,用大火把水烧开;再把切好的地瓜轻轻地倒进锅里,用相对粗一点的树枝,中火慢烧二三十分钟,地瓜就会熟了,起锅时香气四溢,入口时香甜润酥,吃后唇齿间依然留有余甘。
如果是做米饭、炖鸭汤、红烧肉,那就得更加小心掌握火候。就拿做米饭来说,当锅里面的水沸腾的声音传来的时候,就得把旺火调成温火,只让几根粗一点的树枝在锅底下保持中火状态,大约持续15 分钟左右,锅里面的蒸气会把锅盖有規律地轻轻顶起,约莫再过10 分钟,锅盖不再跳动,说明饭已经煮熟,得及时把火熄灭,不然就会烧焦,粘锅底。那个年代,地瓜就是惠安乡下的主食,大部分人家常年吃的都是纯地瓜汤,偶尔也会加少许米粒,那就算是改善生活了。记忆中,只有过年过节才有米饭和鸡鸭鱼肉。平时把灶火,有时候会把还没有去皮的小地瓜扔几个进去灶膛里,埋在树枝下面,一顿饭烧下来,地瓜也烤熟了,用铁钩子插出来或者用铁钳子夹出来,慢慢剥皮享用。
碰到“南风天”的时候,灶台旁边的树枝树叶会有不同程度的湿润,就连火柴盒也会略显湿润,火柴往往要划动很多下才能起火,有时候把火柴盒两边的纸擦烂了还起不了火。好不容易起了火,赶紧用手捂住这“希望之火”小心翼翼地送到灶里去点树叶,结果门口一阵微风吹来,“希望之火”又灭了!好不容易再次点燃了树叶,就得像呵护幼儿一样捧在手心里,不让它再次熄灭。
夏天“把灶火”相当“烤”验人,本来就非常燥热,在灶膛前“烤”上个把小时,豆大的汗珠像瀑布一样从前额、耳后根倾泻而下,“唰唰唰”地洒在地板和手中的树枝上,有时候滴在铁钩子上,还会“嗞嗞”作响。
饭煮熟了,赶紧一溜烟跑到后门通风处呼吸新鲜空气。这一顿饭把火下来,直熏得满身满脸烟灰,又加上衣衫破旧,活像从战场逃出来的士兵。
冬天“把灶火”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
柴门外寒风呼号,灶膛前温暖如春。后来长大之后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美国总统冬天的时候招待贵宾,一左一右坐在壁炉前谈事情的那股惬意,似曾相识,不禁抿嘴而笑,这不就是我童年的感觉吗?
不知道到了哪一年,小煤炉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家家户户都有一个高度几十厘米的小煤炉,蜂窝煤球七个孔的、九个孔的、十几个孔的,堆在家里面,垒成了一座小山。那时候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给煤炉起火、换煤球。换煤球的时候,要把煤炉上一锅开水先端下来。记忆中,常常不小心让开水洒到地上,溅到脚掌,疼得赶紧把拖鞋踢掉,满地乱跳;特别疼的时候,还要挤一点牙膏涂在伤痛处。换下的煤球灰,夹出来的时候往往还是原来的形状,可以把它拿去门外或门内掩盖鸡屎或鸭屎,用脚一踩,瞬间灰飞烟灭,然后再用扫把簸箕扫掉,几乎不留痕迹。
不知道到了哪一年,煤气灶兴起,小煤炉也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耳朵里面尽是“啪”“哧”的煤气灶起火的声音。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