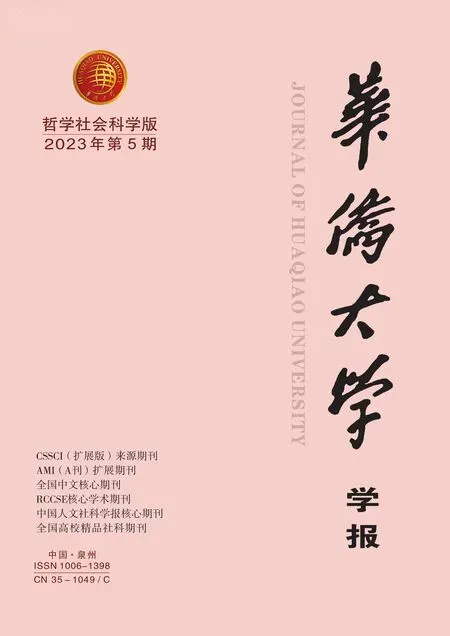程序正义独立价值的先天性及其认知神经基础
○王思敏 张 沛
在法哲学领域,程序正义研究的核心问题是阐明程序正义何以可能。有关这一问题的探讨,历史上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程序工具主义”(后文简称“工具主义”)和“程序本位主义”(后文简称“本位主义”)(1)陈瑞华:《论程序正义的自主性价值——程序正义对裁判结果的塑造作用》,《江淮论坛》2022年第1期,第13页。。“工具主义”不承认程序具有独立价值,认为衡量正义与否的唯一标准是结果正义的实现程度,程序本身只有作为手段和工具的作用。与之相反,“本位主义”认为程序除了具有工具价值外,还具有独立价值,而真正的正义不应该只是结果正义,还应包括程序本身的正义,甚至认为只要坚持公正的程序,就可以做出公正、合理的判决或决定。现今,尽管大多数学者都已经承认了程序正义独立价值的存在,但在程序正义独立价值如何存在这一问题上,“本位主义”始终没有给出一致且有力的证据。
有关程序正义独立价值的争论促使人们必须深入思考正义问题,也为司法改革和国家治理提供了一系列重要建议。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该争论依然造成了许多难题。在国内,司法界长期以来忽视了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形成了“重结果,轻程序”的传统,这一现象已经成为司法改革的重要阻碍;而国外情况则恰恰相反,由于罗尔斯的巨大影响力,以及“程序本位主义”在实践中较强的可操作性,重视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或者说“重程序,轻结果”已经成为西方世界的共识,但对程序的过度推崇却可能导致本该增进社会正义的程序成为破坏正义的诱因。例如,1994年轰动美国的辛普森案中,检察机关以程序不当为由否定了关键证据并宣布辛普森无罪,到导致大量民众对司法程序的公正性产生质疑。这一系列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在于,学界和司法界对程序正义独立价值的存在方式及其作用机制始终模糊不清。
有关程序正义独立价值存在方式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应该包括两个方面:(1)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是如何存在的?(2)这种独立价值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科学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一个长久以来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很难在原有的理论维度上得以解决。程序正义独立价值的争议长期悬而未决的原因之一在于:“本位主义”阵营无法提供足够坚实的事实证据,以致理论上的争辩无法在实践层面验证。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心理学家也开始研究程序正义,在“程序正义独立价值如何存在”这个问题上,对人类婴儿的研究发现:既使最终结果相同,婴儿也更愿意接受公平的程序。也就是说,程序正义不但具有独立价值,对程序正义的趋向还是人类的本能,相关的动物实验也佐证了该观点。另外,对不同年龄段儿童的研究还发现,尽管追求程序正义是一种本能,但这种本能会随着年龄和认知能力的增长逐步发展。在“独立价值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上,认知神经科学通过“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发现,程序正义的确具有为结果利益服务的工具职能,但程序正义同时也具有独立的职能,且人脑对两种职能的加工过程是分离的;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之所以认为程序正义具有独立价值,是因为即使没有物质利益的刺激,公平的程序本身也可以刺激主管奖励机制的脑区,即程序正义具备某种“内在价值”。
然而,来自认知科学的证明并非无懈可击,这些证明依然会面对来自对学科交叉这一方法和心理学内部的质疑。因此,未来的研究(1)仍需进一步发挥交叉学科的优势,共同研究人们评估程序正义独立价值的神经机制;(2)同时值得关注的是,程序正义不是一个单数名词,而是一个复数,因此需要在不同情境中对程序正义的标准进行细致划分,以最大化地利用程序正义实现社会的善治。
一 程序正义独立价值问题的争论
在程序正义何以存在的论证中,“工具主义”是以“经济人”假设作为逻辑起点,这种假设似乎是天然合理的,在现实生活中更符合人们的一般思维,而“本位主义”在承认程序的工具作用之外,还认为程序的作用不止于此。如此,论证“程序正义独立价值如何存在”这一问题的责任主要需由“本位主义”一方承担。
首先,对于程序正义的存在基础,“工具主义”和“本位主义”有着不同的看法。“工具主义”认为人们完全是以追求物质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经济活动的主体,此时程序正义只作为人们争取自己利益的工具而存在。正如边沁所说:“对于法的实体部分来说,惟一值得捍卫的对象或目的是社会最大多数成员的最大幸福……程序的有效性最终取决于实体法的有效性。”(2)Bentham,J..Principles of Judicial Procedure.1843.London,pp.6.,使用程序的目的在于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种论证似乎是自明的。但“本位主义”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该观点无法解释人们在某些情境中宁可牺牲部分利益,也要选择程序正义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不争馒头争口气”。“本位主义”对该现象的解释是:程序正义本身就具有值得追求的价值,且这种价值独立于物质利益,单纯用物质利益来解释人的选择会忽略人的复杂性。
为了对抗“工具主义”的“经济人”假设,“本位主义”需要为程序正义独立价值的存在寻找一种有同等论证效力的证据,并在某种自然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证明人类追求程序正义同追求物质利益一样,都是人的自然需要。对此,“本位主义”主要采用了以下两种论证策略。
“本位主义”的第一种论证策略认为程序正义具有某些独特的,结果正义无法实现的作用。比如迈克尔·贝勒斯(Michael D.Bayles)认为法律程序可以让当事双方充分参与审判过程,令其明白裁决是如何做出的,从而使双方更易接受裁决结果以化解矛盾,他将这种作用称为“过程价值”(process values)(3)迈克尔·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23页。。美国法学家罗伯特·萨默斯(Robert S.Summers)也持有相似观点,他认为人们对结果正义的判断在绝大多数时候是一种主观的感知,并没有客观的标准,而程序正义可以使当事人得到公平、人道的对待,并产生一种受尊重的感觉。同时充分且恰当的程序可以使当事人了解他们被如此对待的原因,可以提高当事人对审判过程和裁判者的认可度,从而促使当事人更愿接受审判结果(4)陈瑞华:《通过法律实现程序正义——萨默斯“程序价值”理论评析》,《北大法律评论》1998年第1期,第181—204页。。
但这种证据很容易被“工具主义”反驳。“工具主义”采用的是一种还原主义的路线,可以这样反驳:人们之所以选择尊重程序,是因为公正的程序从长期来看,是有利于个人利益的。这一论证是霍布斯式的,可以被称为“长期利益”或“间接利益”论证,也就是说程序正义之所以具备这些作用,是人们权衡“长期利益”和“间接利益”的结果。比如当事人选择接受判决,不是因为他认可了程序,而是他在衡量以后发现尊重程序可以带来社会的稳定,而不遵守程序可能会造成周围人对自己的敌意,在充分衡量长期和间接的利益后,他选择接受判决。
“本位主义”的第二种论证方式是证明程序正义具有某些不可被还原为物质利益的价值。耶鲁大学学者马修(Jerry L .Mashaw)采用“永远把人类——无论你亲自所为还是代表他人——当作目的,而绝不仅仅当作手段来对待”这一康德式的话语,认为人的权利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得到尊重,这是人的基本价值。比如人作为主体需要得到的尊重,不应为了结果正义而被剥夺。因此,人有权平等地参与关乎自己利益的审判过程,并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得到人道的对待,这种参与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且这种价值不同于结果带来的价值。基于此,马修认为程序正义中的“平等”“可预测性”“透明性”“理性”“参与”“隐私”是人的基本需要(5)陈瑞华:《程序正义的理论基础——评马修的“尊严价值理论”》,《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第145—153页。。然而,马修的论证诉诸于一般的人类直觉,这种论证方式带着直觉主义的基本弱点。“工具主义”可以反驳:这些所谓的需要没有真正的证据,无法证明所有人都赞同自己有这些需要,而在事实上,每个人对程序正义价值的判断也都不尽相同。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个世界存在着依靠丛林法则生存,从不顾及程序正义的人;或存在专钻程序正义的空子并以此谋生的人。
此外,在“本位主义”内部,也存在人们对程序正义的趋向是否具有“先天性”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此处仅在广义层面使用“先天性”这一概念,指人们天生就具有对程序正义的趋向;与之相对的观点则认为,对程序正义的趋向是依赖后天教育形成的。一些学者认为,程序正义的某些原则是先天(并非依赖后天教育)存在的,它们透过漫长的历史而镶嵌在人类的本性中,这些原则构成了程序正义的存在基础。罗尔斯认为,为了保证社会的正义和良序,人类通过“反思平衡”,可以自然建立一些普遍的、先天的和确定不移的社会观念。罗尔斯认为这些标准包括平等、自由等,是可以被人们普遍认可并共同遵循的。罗尔斯之所以认为基于某些先天的观念可以建立一套可确定的秩序,是在为程序正义寻找一个相对客观的基础。但这种看法却遭到了哈贝马斯的批评,哈贝马斯认为罗尔斯主张的自由、平等原则是基于其抽象的理论。他认为并没有什么先天的原则,人们之所以选择程序正义,是因为人类在漫长历史交往中逐步形成了一些普遍的规则,程序正义正是历史交往的产物。人们对程序正义的偏好,以及程序正义的原则都是在后天逐渐形成的,即所谓“通过对话来获得规范的有效性要求”(6)Jurgen Habermas.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MIT PRESS,1993,pp.103.。可以看出,哈贝马斯是用到一套类似“文化相对主义”的论证,实际上这一论证已经动摇了“本位主义”的基础。“工具主义”或可借此声明,既然程序正义没有先天性,那它可能只是人们为了满足某些需要而采用的普遍流行的某种产物,如此,程序正义自然也会随着需要的改变被历史抛弃。
可见,尽管“本位主义”采用了很多论证方式,但这些方式并不能算成功。一方面,各种论证都可以被还原为某种形式的“工具主义”;另一方面,其内部也在独立价值的来源问题上存在争议。然而,“本位主义”论证方式存在的问题不止于此,一个理论如果是有效的,不仅要在理论上证明其正确性,还要具备更强的现实解释力。也就是说,“本位主义”理论需要解释人们在现实中是如何使用程序正义来行事的,对此,“工具主义”表现的依然更加优异。在“工具主义”看来,我们选择尊重“程序正义”,是因为它可以带来现实利益,同时我们可以通过计算遵守或违反程序正义而得到的收益大小,来做出遵守或违反的决定。这种计算可以是长期的,也可以是短期的,这取决于个人对所处环境的判断。尽管“本位主义”可以提出很多例外现象,但是“工具主义”可以用更多的现实案例回应。比如他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平等不过是争取自身利益的手段,证据是人们总是在因不平等而遭受利益损失时,才会要求平等;一旦在不平等中获益,就很少以不平等为由而放弃利益。此外,对程序正义的要求完全可以成为换取实际物质利益的筹码,例如以程序不公平为理由,要求他人进行经济赔偿或拒绝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最后,对于无法明确看到利益回报,却依然选择程序正义的行为,“工具主义”依然可以合理地假设,这可能是出于某种未知的原因,而这种原因最终指向的是物质利益。比如,人们选择程序正义是为了彰显自己较好的合作资质,或者希望在更长期的时间线上得到对方的回馈。
可以看出,法哲学界的论证局面对“本位主义”非常不利。尽管如此,理论学家大都相信程序正义独立价值的存在,毕竟一个人人自利,只把程序作为利益工具的社会不是我们愿意接受的。综上,为了研究程序正义独立价值的存在方式,“本位主义”必须完成两个任务:(1)证明即使排除利益回报的可能,人们依然会趋向选择“程序正义”,同时为了排除这种趋向仅仅是后天形成的心理惯性,还必须证明该趋向具备一定的先天性,而并非完全由后天形成;(2)明确程序正义独立价值的作用机制,即如何不依赖于人们趋利避害的本能而发挥作用。
二 程序正义独立价值的存在及其先天性——来自发展心理学的证据
要证明程序正义独立价值的存在及其先天性,现实中显然不存在这样的条件,毕竟现实中的选择难免被各种因素所干扰,但发展心理学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方案。发展心理学主要致力于在新生儿到成年人的分阶段研究中,揭示人的先天因素和后天情境对其心理及行为倾向变化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发展心理学通过设计纵向实验,经过一定的时间跨度去采集人类某些行为倾向的变化,从而分析造成该变化的核心影响因素。例如,在婴幼儿到青少年的时间跨度上,对人类程序公平性的感知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发现:(1)在程序正义是工具还是本能需要的问题上,人类婴儿已经具备了识别不公平程序的能力,并且具有选择公平程序的趋向,即公平是一种本能需要,这样的观点也得到了动物实验的佐证,即选择公平是高等动物的共同趋向;(2)在程序正义到底是先天还是后天的问题上,实验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年龄更大的儿童逐渐具备了识别复杂程序的能力,对程序公平呈现出更明显的趋向。
(一)追逐程序正义是人的本能性需要:来自人类婴幼儿和动物实验的证据
婴幼儿实验是心理学中用于研究人类本能的重要方法,由于婴幼儿不具备复杂的逻辑思维能力,而且尚未接受系统的社会教育,其行为往往是出于本能的,因此可以用来识别人类先天具备或者早期发育中的行为趋向。也就是说,参与实验的婴幼儿年龄越小,得出的结论就越能反映人类的本能倾向。此外,在程序正义独立价值的研究中,心理学家认为,如果发现人类婴幼儿的选择是基于程序的公平与否,例如选择程序公平下产生的相对较小的收益,则可以说明程序正义具有独立的价值,即人类并非只是把程序作为获取更好结果的工具,而是先天性的对程序正义具有一定的趋向。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类婴幼儿先天具备识别程序公平与否的能力,同时可以对一些简单的程序不公平事件做出拒绝性的反应。当然,由于婴幼儿无法使用明确的语言表达其对程序公平喜欢或者讨厌的能力,心理学家一般通过观察婴幼儿对公平或不公平分配程序的注视时间以及后续行为,从内隐认知层面推断出他们对不公平分配程序的不满和对公平分配程序的喜爱(7)Xu Huanv.Children’s Mastery of the Concepts of Procedural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Reflected in a Distribution Activity.Advances in Psychology.2014,04(2),pp.239-251.。
Sloane等人发现即使是19个月的幼儿也具有公平分配资源的期望(8)Sloane,S.,Baillargeon,R.,&Premack,D.Do infants have a sense of fairness?Psychol.2012,23(2),pp.196-204.,具体而言,如果两个幼儿都完成了实验者布置的任务,他们就会期待得到同样的奖励,但如果他们中只有一个完成了任务,而另一个只是在玩耍,那他们就不会有这样的期待,说明此时的幼儿已经可以初步分辨出结果不公平的来源,即分配过程的不公平。此外,Surian 和 Margoni 发现20个月大的幼儿已然能辨别帮助程序中的一致和不一致。在实验中,研究人员向20个月大的幼儿展示了一个主角对另外两个接受者提供帮助的视频。一种情况下,主角不偏不倚地同时帮助这两个接受者;另一种情况下,主角有偏见地立即帮助其中一个接受者,而另一个接受者则等待较长时间后才得到帮助。尽管在这两种场景中,每个接受者最终都得到了帮助,但结果却发现,相比无偏见的帮助场景,幼儿对有偏见的帮助场景观看时间更长。如果把年龄扩大到三岁,则会有更加明显的实验结果,Baumard发现在一个简单的故事情境中,三岁的幼儿便可以根据每个人在任务里的贡献量来分配奖励(9)Baumard,Nicolas.Preschoolers Are Able to Take Merit into Account When Distributing Goods.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12,pp.492-498.。更重要的是,Kenward 和 Dahl发现,在资源分配游戏中,当三岁左右的幼儿不作为资源分配的受益者时,他们会更偏爱于与将资源在接受者之间等分(10)Kenward B.,Dahl,M.Preschoolers distribute scarce resources according to the moral valence of recipients' previous actions.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11,47(4),pp.1054-1064.。
心理学家通常会利用动物实验来探索人类更为原始的本能,而来自动物实验的结论也可佐证程序正义趋向的先天性。著名的动物心理学家Waal设计了这样一个实验,两只僧帽猴可以用鹅卵石向实验者交换食物。一开始,两只猴子得到的是同样的食物(黄瓜),此时,两只猴子交换食物的频率基本相同。随后,实验者改变了规则,给一只猴子更美味的葡萄,另一只仍然是黄瓜,这时被给予黄瓜的猴子便不愿再次交换食物,甚至表现出愤怒的情绪,将鹅卵石和黄瓜抛出笼子。倭黑猩猩被认为是同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物种之一,实验发现它们同样具有很强的公平意识,当一只倭黑猩猩被给予了好吃的食物后,它并不会马上吃掉食物,而是不断地给实验者和同伴打手势,直到实验者给予同伴和它一样食物时,它才愿意收下食物(11)Waal,F..The origins of fairness.New Scientist,2009,204(2734),pp.34-35.。甚至在非灵长类的动物中也发现了类似现象,灰鹦鹉在同伴获得更多花椰菜时表示抗议,狗在执行任务后如果没有得到与同伴一样的奖赏则会拒绝执行后续指令。这一系列的动物实验可以说明,追求公平在高等生物中是普遍存在的,并与平等、分享原则一起形成动物正义的行为簇(12)马克·贝科夫、杰茜卡·皮尔斯:《野兽正义:动物的道德生活》,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22年,第10页。。
上述婴幼儿实验和动物实验主要说明了以下两个问题,(1)“工具主义”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将程序正义作为获得利益的工具,这在事实层面上存在漏洞。因为即使在不需要考虑结果收益,或者在当事者们拥有一致结果的情况下,婴幼儿也会倾向于选择程序公平。同时,婴幼儿实验还排除了“工具主义”的“长期利益”假设,即人们放弃利益选择公平是为了得到长期利益。因为对婴幼儿来说,选择长期利益的认知能力尚未成熟。(2)上述实验结果证实了人类对正义的追求具有一定的先天性,因为无论是在程序还是结果上,婴幼儿都更偏爱公平的选项,这佐证了罗尔斯的假设。
(二)程序正义趋向性伴随人类认知发展逐步成熟
婴幼儿对程序正义存在先天的偏好,是否意味着哈贝马斯的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并非如此。哈贝马斯认为程序正义的标准是在人类的社会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在他看来,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开展交往活动,在交往过程中,人们会逐渐形成程序正义的原则,同时,他将促进交往顺利进行的认知能力,称为当事人的“交往资质”。心理学中将不同年龄段孩子作为当事者的实验,也可证实哈贝马斯的这一假设。不同年龄段的实验表明,人们使用程序正义的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认知能力的提高不断成熟,并逐渐发展出辨别复杂程序公平性的能力。人类对程序正义趋向的先天性并不是程序正义的充分条件,婴幼儿表现出的对程序公平性的趋向也并不能说明人类对程序正义的偏好完全是先天的,毕竟程序正义的实现包含着一系列的规则,而对于这些规则的理解需要一定的认知能力。
研究者发现5~8岁的儿童可以处理较为复杂的程序正义问题。Grocke 等人使用均分和没有均分的两种转盘,考察了5岁儿童对程序公平的认知水平,结果发现,有一半儿童会选择均分的转盘来分配多余的资源。同时,如果不均等的分配结果是由均分的转盘做出的,他们便会普遍接受这样的分配;相反,如果不均等的分配结果是由没有均分的转盘导致时,他们大多会拒绝这样的结果(13)Grocke,P.,Rossano,F.,Tomasello,M.Procedural justice in children:Preschoolers accept unequal resource distributions if the procedure provides equal opportunitie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2015,140,pp.197-210.。此外,研究者首先让一名儿童作为分配者给两名接受者分配物品,这个时候儿童一般会选择公平分配,但在分配结束后实验者多给出一个物品,这时他可以选择扔掉物品或是进行不公平的分配。结果发现,6~8岁的儿童宁愿扔掉物品也不愿进行不公平的分配,甚至当儿童自己是接受者之一时,也依然会选择扔掉物品(14)Shaw,A.,Olson,K.R.Children discard a resource to avoid inequity.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General,2012,141(2),pp.382-395.。
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能够发展出利用程序公平性进行其他判断的能力。Fry和Corfifld研究了10岁左右儿童如何对权威进行评判,发现儿童在对权威人物进行评判时,程序公平起着更重要的作用(15)Fry,P.S.,Corfifld,V.K.Children’s judgments of authority figures with respect to outcome and procedural fairness.The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1983,143(2),pp.241-250.。Fagan 和Tyler发现,当10~16岁儿童认为法律过于严酷或者执行者不能公平执法时,他们会降低对法律的合理性评价,并对法律报以嘲讽的态度(16)Fagan,J.,Tyler,T.R.Legal socialization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Social Justice Research.2005,18(3),pp.217-241.。此外,Murphy还发现青少年更愿意与公平执法的警察展开交往(17)Murphy,K.Does procedural justice matter to youth?Comparing adults’ and youths’ willingness to collaborate with police.Policing and Society.2015,25(1),pp.53-76.。
除了从上述不同实验中对比不同年龄段孩子对程序正义的判断,也有研究在同一实验中考察了儿童和青少年面对程序公平时的行为演变。Shaw 和Olson研究了5~8岁儿童如何使用公平程序或者不公平程序来分配奖品。结果表明,在所有年龄段的儿童中,选择公平程序的人数均多于选择不公平程序的人数,且7~8岁儿童使用公平程序的人数远多于5~6岁儿童。如果让儿童在扔掉物品和不公平程序之间进行选择,相比年龄小的儿童,年长儿童则更多选择宁愿扔掉奖品,也不选择不公平程序(18)Shaw,A.,Olson,K.R.Fairness as partiality aversion:The development of procedural justice.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2014,119,pp.40-53.。Damon利用4~8岁儿童在生活中遇到的两难情境来对比他们对公平的认知,结果发现,4~5岁儿童的只能把个头大小作为公平与否的标准;5~6岁儿童开始把公平和平等联系在一起;6~7岁儿童开始按照贡献来评价公平性;8岁儿童开始考虑到相对复杂的个人需要(19)Damon,W.Early conceptions of positive justice a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operations.Child Development.1975,46(2),pp.301-312.。Mills 和Grant的研究还发现,6~8岁的儿童开始质疑成年人的分配决定,他们能意识到成年人的选择可能是不公平的,从而开始选择用公平的程序来进行资源分配,而不是让成年人直接分配(20)Mills,C.M.,Grant,M.G.Biased decision-making:Developing an understanding of how positive and negative relationships may skew judgments.Developmental Science.2009,12(5),pp.784-797.。有关程序公平判断的发展过程,Damon提出了公平的认知发展阶段论模型,他认为儿童的公平推理水平与其数学和物理问题的推理水平高度相关,大多数儿童在这两个领域(公平领域和认知发展领域)的发展体现出紧密同步的特点(21)Damon,W.Early conceptions of positive justice a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operations.Child Development.1975,46(2),pp.301-312.。
综上,无论是婴幼儿还是青少年,他们都具有追求程序正义的自然倾向,即使这种倾向有可能带来物质利益的损失。更重要的是,自然倾向并不是追求程序公平的决定性原因,因为理解程序需要一系列复杂的理性加工,因此,人类追求程序正义的倾向虽然具有先天性但并非恒定的,而是会随着认知能力的成熟逐步发展。
三 认知神经的证据:程序正义独立价值发挥作用的认知神经基础
上述实验即便证明了程序公平具备一定的独立价值,但“工具主义”依然可以反驳:这并不能为解决现实问题带来更多的帮助。因为我们不明白其独立价值发挥作用的机制,因此即使它在理论上存在,在现实中依然是无意义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在于行为实验揭示的结果依然存在于现象层面,而现象背后的内在机制对我们来说仍旧是一个“黑箱”,因此要想真正地解决问题,就必须打开黑箱,对其内在机制进行探索。
如果承认一切意识现象都依赖于物理性的载体,那么人类加工程序公平和结果时的大脑活动,无疑能直接证明程序公平是否具有相对于结果的独立性。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技术是20世纪90年代产生的,利用高能磁场对人类大脑活动进行观测的技术,又被称为“科学的读心术”。具体而言,人体血液中含有氧合血红蛋白和脱氧血红蛋白,脱氧血红蛋白具有比氧合血红蛋白T2*短的特性,再者脱氧血红蛋白较强的顺磁性会破坏局部主磁场的均匀性,也使得局部脑组织的T2*缩短,这两种效应的叠加结果便是降低局部磁共振信号强度。当脑区活动增强时,该区域脱氧血红蛋白的相对含量降低,磁共振信号强度随之增强,如此便获得了相应脑区的激活图像。2000年以后,随着fMRI技术的广泛使用,科学家开始用其研究人脑加工程序公平事件的神经机制,结果发现,人们加工程序公平事件的脑区和加工结果公平的脑区不尽相同,两种公平的作用机制相互联系,却不相互隶属。进一步的实验则证明,人们选择程序公平是因为其本身就具有价值,而不是它能带来更高的物质价值。
(一)程序正义工具价值和独立价值的作用模式在神经层面的分离
Dulebohn在2009年首次使用fMRI技术探索了个体加工程序和结果的脑机制(22)Dulebohn,J.H.,Conlon,D.E.,Sarinopoulos,I.,Davison,R.B.,&McNamara,G..The biological bases of unfairness:Neuroimaging evidence for the distinctiveness of procedural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09,110(2),pp.140-151.。在实验中,两位参与者被要求同时完成一道数学试卷,成绩较好的一人会在随后的分钱实验中成为提议者(proposer),成绩较差的一人则作为回应者(responder),只能被动选择是否接受提议者的分配。然后,两位参与者将通过显示屏得知自己的试卷批改过程是否公平。例如,参与者通过显示屏得知自己的试卷中只有一道题被批改,且其刚好答错,而剩余题目都未参与计分,因此被安排为回应者角色,这种成绩评定过程便是程序不公平的。最后,研究者以评定过程显示屏和分配方案显示屏,分别作为反应大脑加工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的记录屏。脑成像的结果发现,在结果不公时,背外侧前额叶、前扣带皮层和前脑岛激活更强。这些脑区也经常出现在最后通牒任务的分配结果不公时,主要负责情绪加工。而当程序不公平时,腹外侧前额叶和颞上沟激活更强,这两个脑区则是参与执行控制和规则反思的脑区,反映了理性加工。这就可以合理地推论,人们对结果公平与否的判断更多基于一种直觉性的情绪反应,而对程序公平与否的判断则是逻辑思维这一高级认知活动的结果。既然人们对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的判断,在神经机制层面的表征并非不处于相似的脑区,那么二者依据的判断标准自然也不尽相同。
2014年,Feng汇总了20篇有关公平行为的神经基础研究,发现有两个不同的加工系统参与了公平行为的策略决定(23)Feng C.,Luo Y J.,Krueger F..Neural signatures of fairness-related normative decision making in the ultimatum game:A coordinate-based meta-analysis.Human brain mapping.2015,36(2),pp.591.:一个是快速的自动的直觉系统(intuitive system),包括前脑岛、杏仁核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这一系统可以快速识别和评估违反公平准则的行为;另一个是与认知控制有关的深思熟虑系统(deliberate system),包括背侧前扣带回、背外侧前额叶皮层、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和背内侧前额叶皮层,这一系统则会整合追求公平准则和获取自身利益之间的冲突,从而回应直觉系统的反应,并最终做出更为灵活的决策。也就是说,不公平的规则会被直觉系统直接识别出来,但是直觉系统并不负责选择接受或者拒绝这样的规则,最后的决策行为还需通过深思熟虑系统,对不公平规则引起的心理不适和可能的利益得失进行综合评估后作出。
这两个研究针对的都是程序正义发挥作用的机制,采用的两种方法都证明了人脑对程序公平的加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过程,有其专门负责的神经系统,而不是利益权衡的副产品。
(二)人类选择程序正义的内在神经机制
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在绝大多数时候是联系在一起的,很难单独去探索各自的作用,因此二者的功能总是纠缠不清。为了说明在无关利益的情况下,人们为什么还愿意选择公平的程序,心理学家设计了巧妙的实验,排除了结果的影响,并分离出了程序公平的作用。
首先,心理学家发现,不公平的程序激活了消极情绪,同时会引起认知冲突。一般认为,前脑岛的激活表征了个体的消极情绪状态,尤其是愤怒和厌恶情绪(大量研究发现前脑岛与疼痛、压力、饥饿、口渴、愤怒和反感等负性情绪状态有关)。2003年,Sanfey等人在《Science》上的一篇研究(24)Sanfey,Alan G,Rilling,et al.The Neural Basis of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in the Ultimatum Game.Science,2003.,证明了不公平的程序和前脑岛的关系。在实验中,2个参与者需要分配一笔固定数目的钱,其中1名参与者作为提议者向另外1个回应者提出如何分配这笔钱,回应者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提议者的分配方案。若接受,就按提议者的方案分配;若拒绝,则2人都得不到钱。按照“经济人”假设,回应者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应该接受任何提议,因为即便少得钱也比不得钱更好。如果提议者预测回应者会追求利益最大化,那么他应该选择分配尽可能少的钱给回应者,从而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然而,来自不同国家、采用不同分配金额和不同实验设计的行为学实验一致证实了:人们并非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相关的脑成像结果表明,回应者前脑岛的激活强度在收到他人不公平分配时显著大于其收到公平分配时,在其选择拒绝时显著大于选择接受时。此外,随着分配不公平程度的增加,回应者前脑岛的激活程度也随之增强,同时提高了其对不公平分配的拒绝率。这说明,回应者之所以放弃利益也要维护公平,是因为不公平行为本身就会让回应者产生了强烈的消极情绪,这种情绪甚至可以压倒获得利益的理性计算。Civai等人于2012年发表的研究扩展了这一结论,他们进一步发现,回应者不但在得到更少的钱时会激活前脑岛,在得到更多的钱时也会激活该脑区。也就是说,即使回应者得到了比提议者更多的钱,依然会产生厌恶情绪,这说明,人们厌恶不公平,不仅是因为遭受了利益的损失,还有对不公平(包括优势不公平和劣势不公平)本身的厌恶。
与之相反,公平的程序则会激活人脑的奖赏机制。人们喜欢物质利益,也喜欢公平的程序,在大多数时候,两种喜欢是联动的,因此我们很难识别人们对公平程序的喜爱是出于对程序本身的偏向,还是把其当作追求物质利益的工具。为此,Tabibnia在2008年设计了一个实验(25)Tabibnia G.,Satpute A B.,Lieberman M D..The Sunny Side of Fairness.Psychological Science.2008,19,pp.339-347.,实验者在实验中控制了总的收益量,也就是说,无论程序是否公平,实验参与者最终获得的收益量都是一样的。结果发现,相比面对不公平的程序,参与者在面对公平程序时,报告了更高的幸福感,而且公平程序激活了与奖赏有关的脑区,如腹内侧前额叶、腹侧纹状体和杏仁核。Feng(26)Feng C.,Luo Y J.,Krueger F..Neural signatures of fairness-related normative decision making in the ultimatum game:A coordinate-based meta-analysis.Human brain mapping.2015,36(2),pp.591.的一系列公平行为神经机制的研究也表明,当回应者面对提议者给出的公平提议时,双侧的腹内侧前额叶和后侧脑岛、左侧后扣带、楔前叶以及右侧颞下回有显著激活,这些脑区也都是与积极情绪相关。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偏爱公平是因为公平选项本身对于人们来说是一种奖励,进而激活了与奖赏有关的脑区。
事实上,心理学实验已经证明了“工具主义”的“经济人”假设存在严重问题,人们不但追求物质利益这一“外在利益”,还会追求程序正义所具有的“内在价值”,而且人类对程序正义“内在价值”的追求机制是一种生物本能。如此“本位主义”就获得了同“工具主义”同样效力的论证基础。
四 质疑和展望
2000年以来,用心理学解决哲学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方法,也取得了很多成果,甚至在欧美,“自然主义”或“唯物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显学”。有学者指出“就目下的情况而言,也没有什么别的不同体系性的本体论立场可与唯物论争锋。作为其结果,哲学与科学中的那些最具典型性的理论建树,都以一种或隐或显的方式受到唯物论所推出的诸种概念思想的制约。”(27)Moser,P.K.Contemporary Materialism-A Reader.Routledge Chapman &Hall,1995.。此外,学科交叉的方法在近年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比如,耶鲁大学开创性的“伪善”实验证明了道德伪善的存在,而“镜像神经元”的发现揭示了同情心的生理基础,这都证明了心理学和哲学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这并不代表心理学和哲学交叉研究的方法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可以说,这种方法取得的成果和它的争议一样多。下面将针对本研究可能引起的内部和外部争议,进一步探讨未来哲学和心理学交叉研究的可能方向。
(一)心理学论证的问题和有限性
本研究使用了学科交叉的方法来研究程序正义问题,但该方法本身就充满争议,其争议的原因不仅在于这种方法本身,还在于这类研究的不成熟。然而,随着近些年实验哲学取得的一系列成果,质疑的声音也在逐渐转化为建设的声音,即使是罗尔斯也在1995年就承认“必须以道德心理学去长久地支持一个合乎理性的正义之政治社会”,不过质疑依然需要被严肃对待。
第一种质疑是针对用心理学解决哲学问题这一方法本身的。心理学和哲学的交叉,或者说“实验哲学”从一诞生就饱受争议,支持者认为这是“一场哲学革命”,反对者则将其斥为“一个尴尬的概念”(28)费多益:《实验哲学:一个尴尬的概念》,《哲学分析》2020年第1期,第43—53页。。这里简单列举几种质疑:首先,心理学的论证是“描述性”的,也就是说心理学所提供的证据只是对事实的描述,无法为我们是否支持“本位主义”的观点提供辩护,即便“本位主义”被证明是正确的,却也是无用的;其次,这种方法预设了“基因决定论”或者“生物决定论”的观点,忽略了人类社会历史对人的塑造作用,而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一个具有主体意志的人会被消解掉,从而变成一个完全由物理规律支配的“哲学僵尸”(philosophical zombie);最后,人类复杂的行为和情感能否被还原为客观的生理现象,这一点是存疑的。比如,以往的心理学研究认为某些脑区的激活代表着人的奖赏机制被激活,但此时人可能根本没有感受到快乐。当然,对于这种方法的质疑远不止这些,而对这一质疑的回答超出了作者的能力范围。实际上,这个问题已被众多国内外学者深入探讨过(29)有关实验哲学的质疑,本文参考并借鉴了约翰·塞尔的《心灵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中列举的8种质疑和回应;以及徐英瑾在《唯物论者何以言规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63—200页)中列举的5种质疑和回应。对实验哲学的辩护,本文参考了徐向东在《理由与道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94—405页)中的“论一种适度的自然主义”一节的相关内容。。为了不偏离研究主题,本研究的目的只是在心理学的框架下,为程序正义独立价值提供某些事实性的证据。
第二种质疑存在于心理学内部,即目前的证据是否构成对“本位主义”的充分证明。首先,对婴幼儿的研究证据能否充分证明程序正义趋向的先天性,毕竟婴幼儿只有简单的行为指标可反应程序正义的趋向,而程序正义趋向的复杂性是随着人类逐渐成长并发展出来的。人类成长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这就不能排除程序正义是一个社会“教化”的结果。其次,即便程序正义的趋向具有先天性,那这种先天性能否在后天被充分表达?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虽然人类对程序正义的趋向具有先天性,但在人类的理性充分发展后,先天性的作用会逐渐让位于精密的理性计算。最后,认知科学和fMRI对程序正义的研究是否成熟到能够足以确定实验结果的正确性?毕竟除了脑岛,双侧的腹内侧前额叶、左侧后扣带、楔前叶以及右侧颞下回是否能作为表征奖赏机制的特异性脑区,在心理学内部还有争议。而且当前研究只能证明程序正义会产生“内在奖励”——但如何转化为外在的程序正义趋向并不清楚,也就是说证据链条并不完整。
上述质疑可以进行如下回应,首先,先天性只能说明人的一种本能趋向,并不否认后天的作用,这种先天性只是让程序正义的趋向在人类发展中成为一种更具优势的发展方向。其次,人的行为趋向确实是先天和后天共同作用的结果,至于二者所占的比例如何尚未可知。不过,研究发现人类婴幼儿时期的行为反映是一种更本能的行为倾向,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本能虽然会受到理性的制约,但也会成为人们行为的底色。这至少说明婴幼儿对程序正义的趋向绝对不会被后天教化完全取代。最后,目前的研究已经构成了行为和神经反映的互证。在行为上,人们会表现出对程序正义本身的趋向,在fMRI的测量下,可以发现伴随这些行为的是人脑“奖赏机制”的激活。然而当前的证据仅限于此,人脑的奖赏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程序正义在不同情境下的作用方式对这一系统的激活也将有所差异。
(二)未来发展方向
程序正义是一个古老又现代的问题,罗尔斯、哈贝马斯和哈耶克等也曾围绕这一问题开展过针锋相对的直接讨论,长期的争论证明了该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同时,程序正义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不能被无限制的争论下去,其内在作用机制的模糊,将导致实践过程中各种各样的自相矛盾,甚至会加重纠纷。然而,程序正义涉及哲学、法学和心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因此,未来对于程序正义问题的研究需要整合各学科的力量。
首先,需要完成研究框架的统一和研究问题的明确。尽管心理学界对程序正义的关注已有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也证明了程序正义在社会治理上的促进作用。然而遗憾的是,程序正义的作用机制、程序正义的内在标准这些关键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离真正掌握程序正义的规律还有很大的距离。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其中一个原因是,目前心理学的研究仍然缺乏统一的研究框架,导致目前的研究很分散,难以聚焦核心问题。此外,心理学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应用层面,由于没有合适的理论指导,心理学研究者无法设计出更为精细的实验,以明确程序正义更为基础的心理机制。上述两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哲学和心理学的深度合作。哲学家擅长提出问题,并通过逻辑推论筛选出合适的理论方案,但很难验证该方案的可靠性,而构建用于验证理论难题的可行性方案,正是心理学家所擅长的。
哲学和心理学的深度合作需要一套可以兼容的问题框架,尽管程序正义问题在哲学界和心理学界分别具有相对固定的研究框架,但是两套研究框架却存在较大差异,关注焦点也不尽相同,如此一来便很难合力而为。因此,为了便于开展共同研究,至少要明确以下几个问题:到底什么是程序正义?判断程序正义与否的标准是什么?程序正义的目的是什么?程序正义与一般意义上的平等或者结果正义有何异同?
其次,未来研究要尽快从“单数的质性研究”转入“复数的量化研究”。程序性正义是一个庞大的话题,即使是罗尔斯的观点,也曾被哈贝马斯指责是实质正义而非程序正义,而后来的学者也都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了各自对程序正义的定义。心理学有关程序正义的定义也是五花八门,这种定义的混乱给后续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阻碍。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很多研究希望把“程序正义”作为一个单数名词,并探索其发挥作用的机制,这种希望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因为哲学的学科特点就是寻找问题的共性。但是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人们对程序正义的定义是存在分歧的,而且程序正义在不同情境下的作用机制也不相同。比如同样是在程序公平中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有的人选择质疑程序的可靠性,有的人坦然接受了结果,这二者心理机制肯定是不一样的,需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者需要将“程序正义”视为一个问题的集合,而不再把其视为一个单数名词。在不同的情境中,针对不同的人,程序正义的作用机制都不是完全相同的,只能进行精确且具体的研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把研究陷入琐碎,而是在不同位面开展研究的同时,尽快找出问题的共性。目前心理学界热门的计算建模方法可以缩短这个进程。计算建模的方法可以将复杂的影响因素放在同一个心理模型中进行研究,并通过行为实验和定量分析筛选出比较核心的因素,以确定行为背后的最为核心的加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