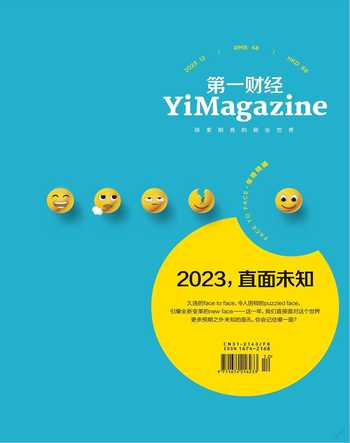科幻作家陈楸帆:我们需要向内自我梳理,寻找新的地基
符淑淑 叶雨晨

Yi Yi Magazine
C 陈楸帆 中国科幻作家
Yi这一年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件是什么?
C我今年去了好多地方做了很多活动,但印象最深刻还是跟家人在一起。暑假的时候,我跟我爸妈一起待了三个月。此外前几年因为疫情一直没见上面、特别亲的亲戚患了重病,在他去世前我去见了两面。这都给我很大的感触,情感纽带的维系没有办法通过虚拟的方式来达成,你可以打电话,也可以视频,但还是替代不了肉身在同一个时空里面相见的感受。
Yi这一年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或者觉得有启发的观 点?
C今年我从加勒比海到美国东岸再到欧洲,参加了很多技术、政治、文学、艺术的跨界活动,有一个观点出现在不同的活动上,那就是讨论群体智能或者说新的智能形态。AI也是其中之一,如果用大语言模型搜集所有人类的数据,然后训练出一个智能体,它就是群体智能的表现。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处于群体智能的一个阶段了,人类本身就是一个群体智能的体现,可能还包括其他的物种,比如我们跟微生物之间也在不停地交流,是一种跨物种的群体智能,可能整个地球都是一个大的行星级别的群体智能。现在有很多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都在探讨这样的观点,这是今年给我比较大启发的一个观点。
Yi今年人们关于AI的讨论热度前所未有,在你看来,AI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层次?我们与AI的关系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
C这一轮热度其实是从去年11月30日OpenAI推出ChatGPT之后开始的,等于说这样的一个技术,前所未有地以一种人机交互对话的界面的形式,让亿万用户直接体验到。之前你可能会觉得AI是虚无缥缈的、在云端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你知道它是一个算法,它可能在发挥作用,但你没有一个可感知的交互体验,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最大的一个变化。
我们可能已经站在所谓的通用人工智能的临界点上。目前它还是比较单一的,基于文字、语言的大模型模态,要达到通用模态,通用人工智能还需要更多不同感官的信息模态,比如目前正在做的人形机器人,它能够更好地跟物理世界交互、学习,有一些更深入的理解,也就是所谓的世界模型的建立。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它会非常快到来。所以我觉得我们跟AI已经处在一个共生体的状态,只不过不同的人、阶层、行业,共生的程度深浅不一,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大趋势,很难被逆转了。包括资本、大国地缘政治、技术竞赛,其实都会推动这个趋势加速前进,它也值得每个人去理解和思考,在这样一个人机共生的时代里,我们怎样寻找到自己的位置,怎样更好地规划自己的未来。
Yi《AI未来进行式》从全球角度讲述了人类与人工智能共生的社会,其中的一些描写是你对未来世界的一种预判吗?
C这本书写于2019至2021年,是基于当时现状的一种预判,我和李开复先生都觉得我们的预判有点保守,书里大部分的内容和故事可能用不了20年就能成为现实。现实中技术的发展其实是一种非线性的、指数级的增长,是超出人类认知能力的,我们只能尽力去想象,但这里面有巨大的不对称性,所以我觉得可以去作很多的预判,里面有一些会成真,大部分可能就是误判了。科幻作为一种想象未来、反观当下的形式,会越来越具有生命力,大家都需要通过这样的形式来更好地理解未来。
Yi在科幻小说里,人类总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地球只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大家是命运共同体。现实中,我们看到人类针对豆腐脑应该是甜的还是咸的都会吵起来,更不要说其他利益纷争。你觉得人类文明最终会持续下去吗?
C现在我们经常说AI跟人类的对齐,但从最近OpenAI的事件中能看出,董事会里只有几个人都会产生巨大的分歧,更不用说人类这么复杂的文明群体了。所以我觉得从根本上这是一个伪命题,我相信如果按照现在的速度去发展,AI会完全挣脱我们赋予它的种种价值观、伦理、道德、法律上的枷锁,它会有自己的进化路径。人类文明会持续下去,但并不是以我们所理解的这种方式,它可能会以一种虚拟的数字化的方式。作为一种文明的遗产,进入AI数据库,进入模型;或是以一种精神遗产的方式,像基因碎片一样,在另一个躯体、另一个物种里面延續下去,这是我的理解,但不一定在我们有生之年能看到。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Yi有一种观点说现实才是最科幻荒诞的东西,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科幻作家如何在科幻作品中反映现实?未来你会把哪些议题当作创作的重点?
C这句话说得没错,科幻归根结底是对当下现实的一种关照和反射,讨论的问题最后都会回归到当下的人类处境。写小说需要有连贯统一的内在逻辑和人物塑造,不能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它是一个完整自洽的叙事结构。但现实不需要理会这一套。现实,你想想,每天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的事还少吗?一会儿很好,一会儿撕破脸,现实不需要逻辑,它就是非常荒诞的。有一句话说科幻它可能是一种高密度的现实主义,我想这句话说得也没错。但现实它又是超越了我们的艺术创作的,它是一个更高维的东西,艺术只不过是高维现实在一个更低维媒介上的映射,所以它没有办法完全捕获所有的现实维度。我提出过“科幻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旗号、一个纲领,就是说科幻不光要反映现实,而且要去干预现实,通过叙事的力量,在现实里产生实际的影响。通过影响人的观念和意识,你自然能够影响他们的行为,包括在气候变化之类的宏大叙事上,都是一件可能的事情。
至于未来关注哪些议题,我想说科幻是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我们以前关心的AI、气候变化现在都是非常现实的议题了,未来我们肯定要去寻找一些很多人在当下还看不清的,更关乎人的本质、心灵,更关乎超越性宗教性跟终极性的思考和提问。它可能超越虚构或非虚构的类型,可能打通了文学、艺术、影视、游戏等不同媒介的边界,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Yi今年气候变化、环境、生物多样性等话题也备受关注,而《荒潮》这部小说讲述了中国的电子垃圾危机和气候不平等,出版于10年前,你觉得如今的世界与你这本书中的世界有相似或者不同的地方吗?
C我觉得相似的还是那些负面的东西,跨国资本的力量、环境污染,电子垃圾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更严重,现在电子设备无处不在,大家也没有找到特别好的解决方案。不一样的地方是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的觉醒,有政府层面的,比如说中国禁止进口洋垃圾,也包括人民的觉醒,比如说在东南亚的菲律宾、泰国等地方人们会抗议游行,抵制来自发达国家的垃圾进口,年轻人的环保意识也强化了很多,会主动选择一些带有环保标签、用环保材料的品牌产品,更崇尚绿色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是有一些希望存在的。
Yi刚刚提到荒诞,你人生中第一次意识到荒诞是因为什么事情?
C我六七岁时跟家里人一起去海水浴场,它是开放式的,我游得有点远,一个浪打过来,可能就是离岸流,我很快就被它卷起来然后往外带了,整个人在里面翻滚,一种要被折断的感觉袭来,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了死亡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我就到这儿了,于是就放弃了抵抗,但那个浪最终又把我送回来了,回到了比较浅的地方。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生命很脆弱很荒诞,随时可以终结,之后我就开始思考很多问题,包括为什么我不是一只鸟或一块石头、为什么我是我这种存在主义的问题。
Yi最近一次感到荒诞是因为什么?
C最近一次感到荒诞是去年3月,当时我住在上海,收到一个南加州建筑学院驻地未来学家的邀请,当我到洛杉矶后,我的小区就被封了,我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然后就开始了一种有点流浪——或者说得好听点——游牧的生活,在外面转了一大圈。我发现以前预设的东西都不成立,原来我们以为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居所、工作、关系,安全感、自我认知、身份认同甚至价值体系都是由此而来,但有可能这些东西都只是幻觉,一夜之间就荡然无存,我又找到了小时候的那种感觉。
Yi什么是你早年深信不疑如今深表怀疑的事情?你修正过哪些看法?
C我修正了很多认知,比如世界是唯物的,人类是地球上唯一的智慧生命,病毒不是生命,我现在都不这么认为了。
Yi唯物这一点怎么讲?
C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唯物主义教育和唯物辩证的世界观体系,但是在汕头,在潮汕地区,你也知道那里有非常多的传统民间习俗以及宗教仪式,小时候会简单粗暴把它拒斥为封建迷信,甚至我妈让我做一些祭拜祖先的事情,可能我都会嗤之以鼻,不愿意去做。现在我会觉得这些东西也有存在的意义,超越了物理时空的存在,是从更广阔的尺度上把个体、心灵和精神意识连接在一块儿的一种力量。我也会学习一些玄学的知识,试图从非科学的视角去理解他们的逻辑、世界观是怎么构建的。当然我也会跟很多的科学家探讨这样的一些话题,我发现科学家其实非常的开放,他们接受所谓未知事物的能力比一般人要强很多,而且他们没有那么强的预判,因为科学其实就是不断拓宽已知的边界,进入未知的领域,如果你觉得什么都已经知道了,什么我们都已经掌握,什么都是可以解释的,那科学就无所谓突破和发展,所以现在会有一种知道得越多,越觉得自己无知的感觉。每天都会觉得这个世界太奇妙了,太不可思议了。
Yi提到世界的奇妙,阿根廷刚刚选出了一个疯狂总统,世界朝着极化方向迈进的趋势似乎越来越明显。你怎么看待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面对不确定性,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C我们是处于一个原有的范式被打破,新的范式没有建立起来的转轨时代,转轨期会发生很多冲突摩擦。不管个体还是国家地缘政治,不同信仰的族群都会在转轨过程中产生更大的冲突矛盾,这是因为前一个阶段我们积累了很多结构性的问题。在这个时代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思路,比如硅谷信仰一种有效加速主义,选择用技术推进这种速度,逼迫人类向更高层次的文明进化。如果回归道家的想法,就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其实每股力量都会有反作用力,所以这两股力量是互相竞争、互相激发、互相纠缠、螺旋式的上升。所以我觉得没有绝对的对错或者善恶,但它最后会导向一个更大尺度上的提升,也就是文明的提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很多的牺牲,会有很多的混乱和暴力。但天道有自己的规律,“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它其实并不太care你个人在这里面的得失与感受。所以我觉得面对不确定性,咱们是同一代人,咱们所有的人生的阅历经验,其实都是在改革开放这40年里塑造积累起来的,它是一种叙事的逻辑,对吧?我们信奉这套东西,觉得它会延续下去,但现在我觉得我们需要整理自己的这套人生叙事,寻找出第二曲线。就好比,你前一阶段的逻辑价值取向的排序可能是一套东西,但现在可能有一些被你压制的、遗忘的、忽视了的东西,在接下来的第二阶段变得特别重要。我们每个人都该去重新梳理,发掘一条新的路径,通往未来新的可能性。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阶段我们能做的比较有建设性的事情。完全躺平也不可能,这个世界并不会因为你躺平而停止变化,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保持比较积极主动的进取精神,但是向内去自我梳理,回归内心,做一些基础建设,寻找新的地基。
Yi真正躺平是要摒除社会关系的,这是难以实现的。所以现在流行的说法是躺也躺不平,卷又卷不赢。你刚刚说到要去面对自己、梳理自己,这需要一个很大的定力去做,但是大部分的人可能就是处于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是真的不知道要干什么,觉得这些事情好像跟自己有关系,但是也可以没有关系。我知道你的求学成长经历都很顺利,属于“别人家的孩子”,如果请你对普通的对就业迷茫、对继续深造又没有兴趣的年轻人提点建议,你想说?
C对,我会经常去大学跟年轻人交流,有一个感觉是年轻人都异乎寻常的沉默,似乎对大部分事情没有什么兴趣和热情,你问他以后想做什么、对什么感兴趣、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似乎认为是很难的问题,这是挺可怕也挺可悲的现象。当然,这个不能怪在他们身上,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社会应该提供更多的帮助,尤其是心灵的帮助,需要有一些引导者帮助他们走出浑浑噩噩的状态,并开始思考,从内心出发去寻找,到底做什么事情能让我感觉到满足。其实人跟AI某种程度上挺像的,需要学习,从输入到输出,不断建立正向反馈负向调节的循环机制,之后他就会动起来,再不断往前发展。一旦停滞下来,那所有的东西都一樣。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静止下来,它必然就会衰败、腐朽、退化。我感觉不少人缺乏一种原动力或者说内驱力,这个东西其实很难由学校教给他们,我觉得更多的是需要一种类似互助会的东西,它需要激发一些共同归属感,需要通过实践,通过生活的体验,慢慢培养起自己的热情和兴趣。这其实是一个挺大的议题,而且你能看到现在不光是大学生,中小学生的抑郁也很严重。道家说无为,我爸妈就基本上没怎么管过,我爱干什么干什么,爱看什么书看什么书,有时候你想要的太多微观层面的管理,反而会扼杀这种生命力。生命力其实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没有生命力,不管你在任何的年龄,任何的阶层和位置,都会暗淡没有光亮。
Yi回到你本身,我想知道,在获得了比较广泛的赞誉之后,一个人得到的反馈可能就会有点趋同,基本上大家都会夸你,你碰到的每个人都会变得挺友好,那么你是通过什么来保持清醒?
C我是一个比较自虐型的人。可能自我怀疑的成分会更多一些,日常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就是觉得我应该能做更多的事情,我能做得更好,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样的想法,也是挺矛盾的一个人。
Yi所以保持清醒对于你来说不难做到,你其实会不停地给自己加码是吗?
C对,我感觉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方面会觉得我可能是做得还不错,否则也不会有这么多正向的激励,但可能我还有一些更高远的目标还没有实现,可能永远也实现不了,那就需要继续努力。
Yi我知道你是潮汕人,在你们传统的理解里,家族的联系是比较紧密的,对 吧?
C对,潮汕人是比较传统的一个族群,但它也有另外的一面,他们特别喜欢往外跑,在全世界开枝散叶,有点像温州人,到处去做生意然后落地生根这种感觉,所以有点自我矛盾的性格。
Yi一方面有一个强关联属性,一方面又抑制不住地要离开控制圈。
C就是这种张力的关系,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所以今年其实有很多的时间我是在思考,包括潮汕属性,这个东西它在我身上的一个构成,以及它怎么影响我对人生中很多重大事件的一些選择等,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Yi你刚刚提到因为家庭关系紧密,无法做到无视它。那么你会为了让身边的人满意做一些妥协 吗?
C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多少都有。作为人之常情,很难不去作出这样的选择。我尽管是潮汕人,其实我父母对我的要求还是比较少的,他们比较舍得让我到外面去闯荡,总是支持的态度。反过来我就会觉得,我其实也是亏欠了他们很多东西,没有办法陪伴在他们身边,中国人讲父母在不远游,所以需要做出一些补偿。
Yi假如请你推选一个人类榜样,你比较推崇谁?为什么?
C我在老子和庄子之间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选择庄子,他的那种状态,逍遥无待之游、坐忘等,可能是现在大家比较需要的。另外,跟蝴蝶、跟鱼之间,他能够跨物种地去体会,能够共情其他物种的存在状态,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是一种更高维度的智能。
Yi最后一个问题,今年你尝试了哪些自己之前一直惦记,但是没有时间或机会去做的事情?
C冲浪。今年被困在加勒比海一个月,就去学了冲浪,觉得还挺好玩的。上手也比想象中的容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