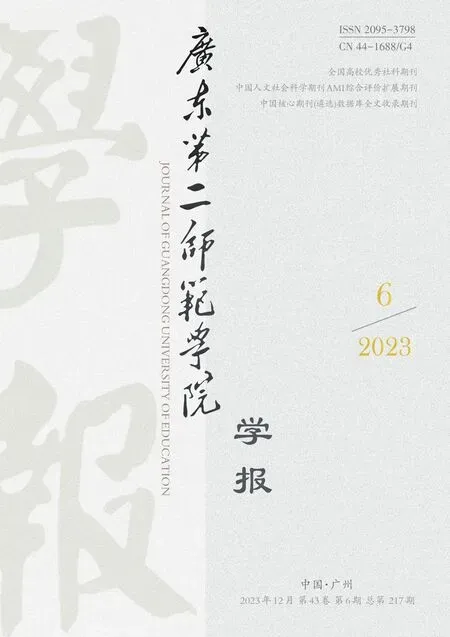学业权变自尊与初一学生抑郁的关系:自尊水平的调节作用
袁立新, 曾文秀, 古炜鑫, 黄伟霞, 吴妮妮*
(1.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教育学院, 广东 广州 510303;2.惠州市惠东县平山第五小学, 广东 惠州 516300)
一、问题提出
抑郁症是青少年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之一。 全国大样本的调查结果表明,我国青少年抑郁症检出率为24.6%,重度抑郁症检出率为7.4%[1]192。 抑郁症的早期发作会严重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导致注意力无法集中、思维能力下降、学习成绩降低和精神运动迟缓等[2],并增加非自杀性自伤和自杀的风险[3-4]。 青少年阶段抑郁症的发病率正处于急剧上升阶段[1]193,确定与青少年抑郁症发生有关的重要风险因素,对于制定青少年抑郁的预防和治疗方案非常重要。
已有研究表明,高权变自尊是抑郁的重要风险因素[5-7]。 权变自尊是指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或自尊取决于特定领域的成功或失败的程度[8-9]。 在某领域具有高权变自尊的个体,其自尊更多依赖于自己在该领域是否成功或达到自己的标准。 当他们获得成功或达到标准时,会导致自尊的增强;但当他们没有达到标准时,则会导致自尊的急剧下降,产生抑郁情绪。 例如,一项对12~15 岁学生样本的纵向研究发现,权变自尊可以预测抑郁症状的变化,具有高权变自尊的学生在6~8 个月后抑郁症状增加更多,表明权变自尊是青少年时期出现抑郁症状的一种重要的风险因素[5]。 使用领域权变自尊量表的研究发现,外部权变自尊(如他人认可、外表、竞争和学业)可以预测抑郁症状的增加[6,10]。 对某些特定领域权变自尊的研究也发现,友谊权变自尊[11-12]、学业权变自尊[2]、外表权变自尊[13]与抑郁情绪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这些研究表明,外部领域的权变自尊会导致个体的自我价值很容易因外部事件而波动,诱发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
自尊是指一个人对其价值的评价[14]。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自尊视为一个多维的结构,包含水平、稳定性和权变性等维度[15]。 自尊的不同维度,如自尊的水平与权变性可能交互影响个体的适应能力。 研究者认为,具有低水平且高权变性自尊的个体,因为个人的评价较低,并且把个人的价值高度依赖于权变领域的成功与否,会引发最多的适应问题。 具有高水平且低权变性的自尊是一种安全高自尊,这类人的自尊不依赖于成功,也不受到失败的威胁,因而适应性较好;而具有高水平但高权变性的自尊则是一种脆弱高自尊,这类人会经常怀疑自己的价值,需要不断的成功来支持和验证自己以防止自我价值的下降[16-17]。 因此,较之安全高自尊者,脆弱高自尊者在权变性领域经历积极和消极事件时,自尊是不稳定和脆弱的[8,18],因而更有可能出现心理问题(如抑郁)。 实证研究支持了这种权变自尊与自尊水平存在交互作用观点。 对大学生和初中生样本的研究表明,具有高自尊水平且低权变自尊者报告的抑郁水平最低,相反,具有低自尊水平且高权变自尊者报告有更高的抑郁倾向[19-20]。
但是,上述研究都是基于一维的权变自尊测量,即把自尊对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的权变视为相同的结构。 如Crocker 等的领域权变自尊量表里,每个维度(即一个领域的权变自尊)包括三类题目:“向上(Up)”的题目(积极结果事件会导致自尊的增加)、“向下(Down)”的题目(消极结果事件会导致自尊的降低)、“依赖(Depends)”的题目(自尊取决于结果而没有指定结果是积极或消极的)[9]。 有学者指出,这种向上、向下权变项目的混合可能掩盖了权变自尊与心理适应变量(如抑郁)的关系[21]。 目前有一些研究支持二维权变自尊的结构,发现基于积极事件与消极事件的权变自尊题目分属两个独立的维度(积极权变自尊与消极权变自尊)[21-23]。这些研究结果表明,积极权变自尊、消极权变自尊与抑郁的关系是不同甚至相反的[21,23]。 如,以高中生为样本的研究发现,即使控制自尊水平后,所有领域消极权变自尊仍能正向预测抑郁水平,且运动领域积极权变自尊负向预测抑郁水平[21]。 以大学生为样本的研究发现,研究所涉及的7 个领域的积极权变自尊都与抑郁显著负相关,而消极权变自尊与抑郁显著正相关;在控制自尊水平后,外表消极权变自尊和美德积极权变自尊仍然能显著预测抑郁[23]。 总的来说,积极权变自尊可能对心理健康是有益的,但消极权变自尊无疑是抑郁的风险因素。
综上所述,虽然前人在权变自尊与抑郁关系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基于二维权变自尊模型的研究仍较少,积极权变自尊、消极权变自尊与抑郁的关系,以及与自尊水平的交互影响仍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另外,在各种领域中,学业能力和表现在青少年学生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学业领域上经历的成功或失败会极大影响学生的自尊[2],研究学业权变自尊对青少年学生抑郁的影响,对青少年抑郁的预防和干预有着重要的意义。 因此,本研究拟基于二维(积极/消极)权变自尊模型,以方便取样为原则,选择初一学生为对象,考察学业权变自尊与抑郁的关系以及自尊水平的调节作用。 基于综述,本研究假设:1.积极学业权变自尊与抑郁显著负相关,消极学业权变自尊与抑郁显著正相关;2.在控制自尊水平后,积极学业权变自尊显著负向预测抑郁,消极学业权变自尊显著正向预测抑郁。 3.自尊水平可以调节积极/消极学业权变自尊与抑郁的关系。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本研究被试为来自广州市两所公立学校的263 名初一学生,其中男生144 人(54.75%),女生119 人(45.25%);年龄范围为11~14 岁,平均年龄为12.36±0.52 岁。 采用简单整群抽样法,在老师缺席的情况下,由经培训的心理学专业四年级学生作为主试,以班为单位组织问卷调查。 在调查前,征得参与学校和学生家长的同意,由学生本人自愿参与。
(二)测量工具
1.学业权变自尊量表
基于权变自尊的二维结构模型,参考有关学业领域的权变自尊量表[9,21,23],自编学业权变自尊量表以测量学生在学业领域的积极权变自尊与消极权变自尊。 量表共10 个题目,其中5 个基于积极事件题目测量积极学业权变自尊(如:当我期末考试取得好成绩时,我的自尊会增强)和5 个基于消极事件题目测量消极学业权变自尊(如:当我总是学不会时,我觉得我是没有价值的)。 量表采用5 点计分,从1(非常不符合)至5(非常符合),得分高表示自尊在学业领域的权变性高。
使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量表的二维结构模型(积极/消极学业权变自尊),各拟合指数为χ2/df=2.27, CFI=0.97,TLI=0.97,RMSEA =0.07,SRMR =0.03,均达到良好标准,说明模型对理论的拟合较好,量表具有结构效度。 在本研究中,积极学业权变自尊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9,消极学业权变自尊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2。
2.自尊量表(SES)
采用Rosenberg 编制的自尊量表中文版[24]测量个体的整体自尊水平。 该量表包含10 个条目,采用4 点计分,从1(很不符合)至4(非常符合)。 在对反向题进行反向计分后,总分越高,表示自尊水平越高。 该量表被广泛运用于我国青少年的自尊研究[25],具有较好的信效度[26]。 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0。
3.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
采用Radloff 编制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27]测量青少年的抑郁水平。 该量表评估学生在过去一周中经历20 种症状的频率,采用4 点计分,从0(偶尔或无)到3(多数时间或持续)。 在对反向题进行反向计分后,总分越高,表明抑郁水平越高。 该量表被广泛用于我国青少年抑郁的研究[28],具有较好的信效度[29-30]。 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0。
(三)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对三个量表共40 道题进行因子分析,结果得到特征值大于1 的因子8 个,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33.48%,低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三、结果
(一)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1 为各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 积极学业权变自尊与自尊水平显著正相关,与抑郁显著负相关;消极学业权变自尊与自尊水平显著负相关,与抑郁显著正相关;自尊水平与抑郁显著负相关。 结果支持假设1。
(二)学业权变自尊与抑郁的关系及自尊水平调节作用的检验
使用层次回归分析检验积极学业权变自尊和消极学业权变自尊对抑郁的预测以及自尊水平的调节作用。 前人的研究显示,青少年学生的自尊水平、学业权变自尊、抑郁水平等均存在性别差异[2],因此,本研究先将性别作为控制变量加以控制。 将全部变量转换为标准分,并生成积极学业权变自尊*自尊水平、消极学业权变自尊*自尊水平两个交互项。 第一步,将性别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方程;第二步,将自变量(积极学业权变自尊、消极学业权变自尊)和调节变量(自尊水平)纳入方程;第三步,将两个交互项(积极学业权变自尊*自尊水平、消极学业权变自尊*自尊水平)纳入方程。 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2。
表2 的第二步结果表明,在控制性别和自尊水平后,积极学业权变自尊可以负向预测抑郁(β=-0.11,t=-2.38,p<0.05),消极学业权变自尊可以正向预测抑郁(β=0.21,t=4.32,p<0.001),说明积极和消极学业权变自尊可单独影响抑郁。 结果支持假设2。 第三步结果表明,积极学业权变自尊与自尊水平的交互项不显著(β=0.05,t=1.28,p>0.05),说明自尊水平不能调节积极学业权变自尊与抑郁的关系;但消极学业权变自尊与自尊水平的交互项显著(β=-0.15,t=-4.11,p<0.001),说明自尊水平调节了消极学业权变自尊与抑郁的关系(如图1)。 结果部分支持了假设3。 简单斜率检验结果表明,当自尊水平高时(高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消极学业权变自尊对抑郁的预测不显著(β=0.03,t=0.41,p>0.05);但当自尊水平低时(低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消极学业权变自尊对抑郁有显著的正向预测(β=0.32,t=5.94,p<0.001)。

图1 自尊水平对消极学业权变自尊与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
四、讨论
(一)积极/消极学业权变自尊与抑郁的关系
本研究超越以往一维结构的权变自尊的研究,关注二维结构的权变自尊(积极/消极)与抑郁的关系。 研究结果发现,积极学业权变自尊与抑郁负相关,消极学业权变自尊与抑郁正相关,说明积极学业权变自尊较高的学生有更少的抑郁,而消极学业权变自尊较高的学生可能有更多的抑郁。 这与前人的结果一致[23]。 积极学业权变自尊高意味着对学业领域的积极事件(如取得好成绩、受到老师表扬等)较敏感,当他们在经历积极学业事件时自尊水平很容易增加,并产生积极的情绪。 而相反,具有较高的消极学业权变自尊的学生会对学业领域中的消极事件(如考试成绩不理想、被老师批评等)较敏感并表现出强烈的反应,自尊水平容易受消极事件的影响而降低,导致负面情绪。 临床研究也表明,关注负面刺激或沉浸消极情绪和消极生活事件的人,容易产生抑郁[31]。
本研究发现,即使在控制了自尊水平后,积极学业权变自尊、消极学业权变自尊与抑郁的关系依然显著。 这与Liu 和Huang 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 他们的研究表明,虽然在控制自尊水平后,消极外表权变自尊与积极美德权变自尊对抑郁仍有显著的预测,但积极学业权变自尊、消极学业权变自尊对抑郁的影响并不显著[23]。 这可能与研究对象不一样有关。 与大学生相比,初一学生的社会活动机会更少,更专注于学业,在学业上的竞争更激烈[7],学业是中学生最重要的任务,也是影响中学生自尊的最重要因素。 因此,学业权变自尊能单独影响抑郁,其影响甚至超过了自尊水平的作用。
这一结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理论上,该研究结果表明了区分积极和消极权变自尊的必要性,对于后续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实践上,启发教育者要关注学业成败和评价对学生的心理影响,鼓励学生以更大的热情追求学业的成功;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和面对学习过程中出现的消极事件,避免对学生的心理健康造成消极影响。
(二)自尊水平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考察自尊水平是否调节学业权变自尊与抑郁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自尊水平不能调节积极学业权变自尊与抑郁的关系,不管自尊水平高低,较高的积极学业权变自尊都有利于减缓初中生的抑郁程度;但自尊水平调节了消极学业权变自尊与抑郁的关系,当自尊水平高时,消极学业权变自尊与抑郁无关,但当自尊水平低时,较高的消极学业权变自尊会导致抑郁的恶化。 因为积极事件不会损害个体的自尊,所以不管自尊水平的高低,具有较高的积极学业权变自尊者都会有更强的追求成功的动机,更能享受学业的积极事件带来的积极情绪,有利于减少抑郁情绪。 而消极的学业事件会威胁个体的自尊,消极学业权变自尊高的个体对威胁自尊的信息或事件表现出强烈的反应,产生防御的动机。 他们在面对威胁自我价值的消极信息时会努力捍卫自我,这种防御行为会侵蚀他们的心理健康[17]。 不同自尊水平的个体在对消极事件的解释上存在差异[32]。 相对而言,自尊水平高的学生不容易受消极事件的影响,在失败时可能不会产生太多的消极情绪[33]。 而相反,低自尊水平的学生可能长期对自己有负面看法,特别是在重要和高度权变的领域这种负面看法更严重[34],容易导致更多的抑郁,进而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35]。 这一结果,一方面为自尊的内部结构之间存在交互作用提供了实证依据,揭示了自尊对个体心理健康影响复杂的机制,启示未来的研究者应关注自尊结构的多维性和复杂性(如自尊的水平高低和权变性);另一方面提示教育者在学校心理健康工作中要特别关注自尊水平较低学生群体的消极学业权变自尊,引导他们正确对待学业的消极事件,避免学业消极事件对自尊的影响。
(三)本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首先,本研究采用横断研究方法,探讨了积极/消极学业权变自尊与抑郁的关系及自尊水平的调节作用,但无法揭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今后的研究可采用纵向设计以便更好地考察积极/消极学业权变自尊对抑郁变化的影响。 其次,本研究只是探讨了学业领域权变自尊与抑郁的关系,但对初中生而言,其他领域(如外表,友谊等)可能也有重要影响[5,36],未来研究可以对这些领域权变自尊进行考察。 最后,本研究只是以初一学生为对象,未来可以扩大到整个青少年阶段的学生,以提高其代表性。
五、结论
(1)积极和消极学业权变自尊与抑郁的关系不同,表明了研究二维权变自尊模型的必要性。
(2)控制自尊水平后,积极和消极学业权变自尊可单独影响抑郁。
(3)自尊水平与学业权变自尊存在交互作用,具体表现为高自尊水平可以缓冲消极学业权变自尊对抑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