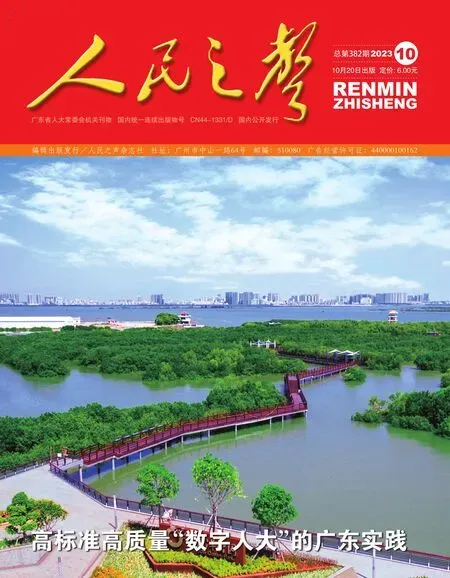教育立法见证改革和权利的成长
阿 计
8月下旬,学前教育法草案、学位法草案同时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此前的6月下旬,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亦已经历了初审。再往前追溯两年,教育法于2021年4月完成第三次修正,家庭教育促进法于同年10月正式出台,职业教育法于2022年4月大修告成。这一系列以“教育”为母题的立法和修法,昭示着近年来教育立法不断开拓的清晰轨迹,也构成了考察当下重点领域立法的鲜活样本。
正所谓“育才造士,为国之本”。教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使命,而教育立法,则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制度根基。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立法,在经历了建国初期的探索、先立后废的曲折后,于改革开放后才真正崛起。从历史的角度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直至本世纪初,是教育立法的第一个黄金期,初步形成了以教育法为核心,义务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教师法、学位条例等单行法为主干,以及大量法规、规章等构成的教育立法体系,终结了教育领域无法可依的困境。
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不断深化,教育立法也踏上了走向纵深的新征程。一方面,既有立法频频更新,陆续完成升级提质的改造。另一方面,新法创制多纬突破,不断书写补短创新的篇章。尤其是最近几年,这一立法势头更是驶入高歌猛进的快车道。从家庭教育促进法到学前教育法,或以法律干预转变了家庭教育的传统模式,或将法律触角延伸至国民教育的学前阶段,无不填补了空缺多年的教育立法短板。从爱国主义教育法到已列入立法规划的法治宣传教育法,更是以价值观培育为基点,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立法新路径。
立法,既是时代境况的映射,也是改革航船的动力。教育立法的变迁,始终伴随着肇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教育体制改革,担当着引领改革方向、破解改革难题、固化改革成果的重任。譬如,2015年连袂修改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确认了完善教育基本制度、下放设立高校审批权、改进高校评价模式等改革方案,进而拆除了教改进程中的诸多制度性障碍;2002年出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催动了多元化办学的改革步伐。2016年该法修改后,又进一步确立了民办教育分类管理的改革措施,进而破解了民办学校法人属性不清、财产归属不明等改革瓶颈;2022年大修的职业教育法,针对职业教育地位、职教学生就业等焦点问题作出一系列制度安排,进而打开了塑造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改革通途……诸如此类的立法、修法行动,不断重构着国家、政府、社会、市场与教育的内在关系,见证了教育改革的渐行渐深。
教育,既是事关国运的伟业,也是牵涉民生的大事。这就注定了教育立法必须融入公共性、民主性等灵魂。也正因此,捍卫教育公平、守护受教育权等立法追求,构成了教育立法的又一鲜明特质。譬如,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废除了“教育事业附加费”等旧制,并确立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免费、公益的义务教育理想由此真正得以实现,教育公平的阳光亦因此从城市普照至乡村;正在制订中的学前教育法,直面“入园难”“入园贵”学前教育小学化等社会焦虑,为满足“幼有所育”的民生期待提供了破局之策;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针对不断曝光、引发公愤的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2020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十一)、2021年修改的教育法等法律,已经构筑起全链条的追责机制。与此同时,更多践踏教育公平、侵犯受教育权的恶性行为,诸如招生循私舞弊、学位论文造假、非法授予学位等等,亦已纳入了教育立法的惩治视线……沿着“公平”和“权利”两大纬度前行的教育立法,不断在细节层面回应社会诉求、铸造制度正义,见证了教育立法日益走向“权利法”的历史变迁。
同时应当看到,教育立法的体系完善,乃至教育法典的最终编纂,仍需付出艰巨的努力。一方面,一些经年未改、滞后现实的教育立法,亟需启动修法工程。另一方面,现有教育法律体系仍存不少空白地带,诸如学校法、教育考试法、教育投入法、初等教育法、中等教育法、特殊教育法、终身教育法等重要的教育单行法,有待提上立法议程。此外,远程教育、跨国教育、人工智能教育等教育新模式的日益兴起,以及教育惩戒权、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校园欺凌等教育新议题的不断升温,亦在呼唤着立法的跟进。
正因此,最近几年教育立法提速快进的绚烂气象,标志着教育立法已迎来蓬勃生长的又一个春天。在此进程中,紧扣改革脉搏,高擎公平旗帜,坚守权利本位,仍应是教育立法不可偏废的价值追求。如此,我国教育大业才能进一步走向良法善治,并最终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