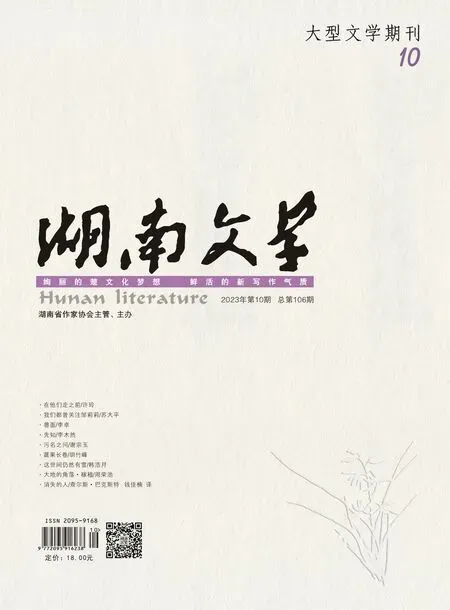三进焦溪
向午平
焦溪,不是村名,只是躲在湘西大山深处的一个小寨子。我没有去过几次,但她却偶尔会在心底萌动,撩拨着涨潮的心事。
第一次去焦溪,有点小,身体还未来得及长开,如早春的芽。我们几个小伙伴坐的是顺风车,一台手扶拖拉机从县城出发,在土路上扭来扭去地蹦跶了近一个小时,到罗依镇时我们的眉毛头发已满是灰白的尘土。站在河岸边,我很激动地东张西望。与那个藏在山沟沟里的家乡排茹相比,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很大的河,很大的船,半山腰上的小村子很幸福地望着浩浩荡荡的水,这就是焦溪。大与小,都是用家乡作的参照物。我那时候的视界很贫瘠,除了家乡的村子就是大得不得了的古丈县城。
去焦溪,可走陆路;那路只是羊肠小径,在山坡上顺了地势爬上去落下来,拐进去又弯出来,硬是把短短的行程极尽能事地拉出了长长的距离。走水路很近,渡过这条河,爬两里坡就可到了。于是,我们选择了水路,乘的是一条我眼中的大船,这船装上我们五个小伙伴都显得很空。两三个小伙伴跳进水里抓着船舷扑腾,摇出了一河的童趣,唯有我坐在船上吓得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然后,就是气喘吁吁地上坡,就是走进了一幢小木屋,就是见到了一个小伙伴的母亲,我很乖巧地叫了一声伯娘。伯娘很清脆地应了一声,就一路笑着风风火火地抓了一只大母鸡杀了,为我们做了一顿缺少油水的童年里最可口的晚餐。然后,就没有了然后,记忆就在这顿美味里戛然而止。但是,焦溪这个村庄的名字,那个叫伯娘的妇人,却是刻在了我小小的心里,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时不时地浮现出来,很温馨。
后来,我很多次乘船经过这条已改名为栖凤湖的河,就会不由自主地抬头望向半山腰,想起焦溪,想起伯娘。也想上去看看,又害怕时光的流逝会不经意间改变了记忆的温馨,最终不得不止住那份近乡情更怯的冲动。
在离第一次去焦溪三十四年后的一天,一群老人走了进来。我看到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妇人,一眼就认定她就是那个焦溪的伯娘。我说了我的名字,她愣了一下,很快就激动起来。她,还记得我,不是相貌,只是名字。后来,我去了济南挂职,又去了吉首工作,伯娘也偶尔给我打打电话;她说,寨子里通公路了,车子可以直接开到屋边;她说,寨子上搞开发了,好几座荒山都种满了黄桃和杨梅;她说,乡亲们养殖的热情高涨,鸡鸭蜜蜂都成堆成群了。她絮絮叨叨地说,我安安静静地听,电话的两头都一如既往地温馨,焦溪,也在这温馨中逐渐地丰满起来。
去年正月初四,我终于摁不住心中的渴望,约上原来的那几个小伙伴去了焦溪。天,下着小雨,我们开车从古丈县城上了高速再沿着罗凤公路行驶,二十分钟就到达了目的地。伯娘在院坝里乐呵呵地笑,我们几个则迫不及待地四处寻找当年的记忆,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一下子都变回了十几岁的孩子:那时候我是从这里爬上来的,那时候那蔸树好小,那时候这里是一条毛毛路,那时候……那时候的一切都从三十多年前的日子里伸出蓬蓬勃勃的藤蔓,挂满了今天的快乐。站在屋檐下,望着波来荡去的群山和山脚下蜿蜒而去的河水,想起从前坐车、乘船,弯七拐八的公路、羊肠式的小道,比起现在的高速公路和车子可以开到院门外的行程,简直就像做梦一样。那天,我没喝酒,却醉在了小院坝浓浓的情分里。
今年三月,我又跟着一帮作家去了焦溪。也是小雨,焦溪的村庄、焦溪的山水都在雨雾中朦胧。作家们把“走进美丽乡村采风活动”的横幅扯得呼啦啦作响,搅动着焦溪早春的梦,这梦里有幼小的桃树在路边绽放星星点点的桃花,更多的是花蕾在枝上随微风颤动,蓄力待开。那气势有点像它的主人鲁总,正在颤颤巍巍地酝酿着一场不为人知的喜悦。鲁总是焦溪人,漂过很多大城市,当过兵,开过宾馆,养过龙虾,卖过茶叶,跌跌撞撞很多年,最终还得回归到焦溪这片大山中来。鲁总说,山是有灵性的,它总会养活自己的孩子,我是焦溪人,焦溪不会抛弃我。于是,鲁总开始向大山要活法要出路。
鲁总是幸运的,焦溪是幸运的,县移民事务服务中心主任向前也正在为移民向大山要活法要出路。于是,双方携手,搭起公司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开荒种果,黄桃、樱桃、杨梅等相继在荒山里、在耕地上落地生根,发芽开花。
仲春的气温有些低,屋内火盆里的炭火却热乎乎地荡漾。作家们和几个村民代表座谈,时不时溅出一屋子的笑声。老支书说,以前山高路远,年轻人出去了就懒得回来,寨子都空了,就剩下几个老人在门前晒太阳;田荒了,地里尽是长长的芭茅草。现在好了,孩子们带着讲普通话的媳妇或女婿回来了;外地人远远地开了车来看花摘果,说不定今后还会有黄头发高鼻子的洋人过来看风景。一位老人说,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看到寨子里通公路,想不到还真实现了,以前那些肩挑背驮、爬坡翻坳的日子想起来实在是有些后怕。我说起三十多年前曾经来过焦溪,曾经在这里吃过一顿至今都难以忘记的美餐。老人沉默了一会,说,你那伯娘对你们真好,都舍得杀母鸡招待你们;那个年代,一家人难得有一只母鸡,你们吃了,你伯娘肯定要过上两三个月缺盐少油的日子。然后又笑着说,今天你们想吃什么?到我家去,鸡鸭鱼肉管够,免费接待一屋子的人愣了一下,又都禁不住大笑。我却笑不出来,心里酸酸的,又想起了伯娘。
雨停了,作家们走出屋外,在桃园中的机耕道上穿行。井然有序的梯土沿着山坡盘旋而上,桃树矗立,桃花绽放,淡红色与浅绿色相互渲染,盎然成趣;时不时有蕨茁壮而出,有的已舒叶展枝,有的还紧握着小小的拳头;偶尔也会有一株或几株甚至一小块深黄色的油菜花在风中摇曳,独自成景。山腰上的树林里隐约显现着星星点点的瓦楞,几柱炊烟婀娜其上,犬吠鸡鸣夹杂其间。公路在树丛与炊烟中时隐时现,偶尔有车辆鸣着喇叭向大山的更深处扬长而去。山脚下的栖凤湖像一块不规则的镜子闪亮亮地顺了山势铺张开来;湖中有小岛,或携手相握,或孤然沉默。远处便是如黛的青山,波浪般拥挤着层层叠叠地朝天边荡去。再远处,是蓝天是白云,是不知的远方。
山顶上建有一宽大的观景台,木质地板和栏杆很显大气,四角亭飞檐翘角古色古香,站立此处,山风拂面,四周的风景可以一下子揽进眼帘。同行的县文联副主席姚复科题亭名为“结义亭”,借桃园三结义之古意也映衬了亭在桃园中的实况,还留下了“水静桃园月,风动景外天”的对联。焦溪就这样完成了一幅新农村的画。
离开时,远远地看到那位伯娘正在小院里忙碌,由于走在一起的人太多,我犹豫着还是收回了已经迈出去的脚步,没敢再去打扰,生怕她又要热情地送这样送那样,忙个不停。想着等天气暖和一些,也该邀上那几个昔日的小伙伴再去那小院里闹腾了。突然间感觉这人生真是奇妙,有的人有的事遇到了经历了就如烟云般消散,再也不能想起;有的人和事就是那么一瞬间,便可定格一生,挥不掉也抺不去,就如这位伯娘,就如这个焦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