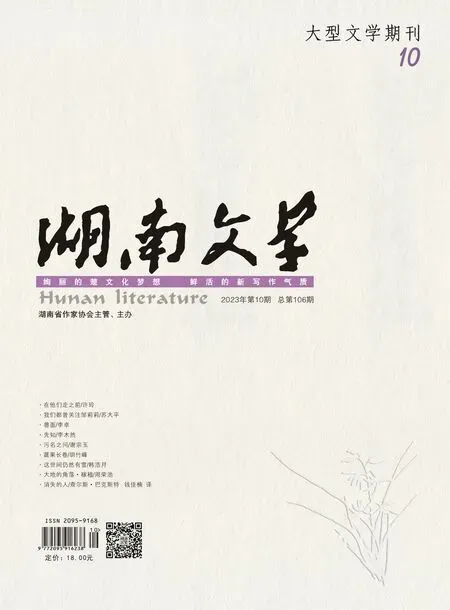这世间仍然有雪
韩浩月
一
今年夏天酷热,返乡后的假期中,白天多数时间待在家中,有一天两位老友相约出游,上午九点顶着白晃晃的阳光走出小区,来到路边时就已经汗流浃背,听了我对气温的抱怨,老友开玩笑说,要知道咱们这个地方,曾是六月飘雪之地,这才三十三度,算是挺凉快的啦。
与两位朋友在外面晃荡了一天,好几次晃神,脑海里总是出现大雪纷飞的场景,于是在返家途中,我说,咱们去看看那座墓吧,朋友没有说话,心领神会。时近黄昏,暑热渐消,朋友开着车穿城而过,向位于县城东外环方向的一块墓地驶去。
那是座著名的坟墓,名字叫孝妇冢,《汉书》《搜神记》中出现过它的名字,《史通》《太平御览》《淮南子》《说苑》等正史、野史杂记都有记载,白居易为它写过诗(东海杀孝妇,天旱逾年月。一酌酹其魂,通宵雨不歇。《效陶潜体诗十六首》节选),关汉卿拿它改编为戏剧《窦娥冤》,“六月飞雪”便源自于此,明清以来无数官员、诗人站在它的旁边唏嘘不已,为之挥毫……
对于这座墓,我并不陌生。我在县城工作的时候,单位距离这个墓地不过两三公里的路程,在办公室里偶尔走神,打开窗户遥望远处的栗子树林,心里就会想到,那附近埋葬着一个曾经轰动全国的女人。离开县城之后的二十多年,每年回乡去看望一位忘年交,这座墓旁边的小道是必经之路,每次经过,心里都会悸动一下,有诸多情绪瞬间涌现又快速消失,从未仔细去琢磨过那是什么情绪,但可以肯定的是,那里面藏着一种躲避的成分,是一种不到一定年龄无法去直面的东西。算下来,这么多年,真正去拜谒,只有过一次。
记忆中这座墓,一直很显眼,它一度很高大,原因是不断前来烧纸上香的人,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给它添坟,手捧,衣角兜,篮子装,导致它成为平原上一个村庄边最鲜明的标志符号。随着几年前县城外环路的使用,去这里变得很容易,反倒来的人越来越少了,虽然有硕大的旅游招牌就挂在路边电线杆上,但一天当中也不见有几个游客寻访,更是罕有当地人前来。这个时候,我也逐渐弄懂了自己每次路过但却不愿靠近的复杂而微妙的心理:一是觉得它太近、太真实了,缺少了外域人文景点的神秘与陌生所带来的吸引力;二是它的故事自小耳熟能详,只要是想想,都会有种沉重感与压迫感。
在外环路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等待几辆大卡车呼啸而过之后,朋友的车穿过环路,驶进了进村的小路。小路路况糟糕,轮胎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好在不到一两百米,就到了那座墓的附近。锁好车向北穿过一片庄稼地,一片小树林,看见一条被半人高榛莽所覆盖的隐约小径,小径的深处,便是那座墓了。脚踩在丛生的杂草身上,发出“唰唰”的声响,朋友说了好几句话,话音中带着叹息,“荒凉”是关键词。
实在是太荒凉了。虽然它一侧是外环快速路,一侧是良田,一侧是人间,但它仿佛被彻底遗忘了,但凡有人给铲掉路上的杂草铺上几块石板呢,也不至于如此。我没有穿长裤,草叶在小腿处制造着划痕,无数黑小的蚊虫蜂拥而上,离开之后,一定会是满腿包了,但这并没有影响我的心情,带着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前来时的那种略带不安的心情,靠近了墓碑的位置。
墓碑还在,一共三座,分别是康熙年间、光绪年间、新中国成立后竖的。康熙年间所立之碑,具体时间为康熙三十四年(1695),由按察佥事涂铨立撰写碑文,上书:“纯孝也而蒙不孝之株,无罪也而罹有罪之祸,致天悯奇冤,郡遭大旱”。光绪年间所立之碑,具体时间为光绪三十年(1904)所建,上书:“其孝至于上格天心,下慰舆情,使千百年后沾其德泽”……经历时间洗礼,个别碑文模糊了,但整体仍可辨认。
藤本植物攀缘缠绕在墓碑上,各种杂树、草木实在太密太厚了,导致居然找不见了墓地,幸好有墓碑的提醒,否则即便有游客前来,也无法发现。朋友轻声念着碑文,那是清朝一位县令撰写的,我看着、听着、理解着,这时身后一股淡淡的檀香味隐约传来,转身寻找,发现有三炷香已经没了大半,还剩下一小截在缓缓地燃烧着,我们三个人有些惊讶,看来不到一个小时前,有人来过,看来这座墓还没有被完全遗忘。
烧香总是有所求,朋友思索一下迟疑地问,前边那位烧香的朋友,来给孝妇上香,求的是什么呢?我想了几个词,但话到嘴边都觉得不合适,于是说道,可能是寻求一种安慰或者说告慰吧,曾经的故事,太苦了,若有内心也很苦的女性,前来烧一炷香,也算倾吐了心事。
二
据《汉书·于定国传》记载:东海有孝妇,年纪轻轻守了寡,年迈的婆婆怕拖累悉心照顾她的儿媳,不惜以自杀为方法,想促成儿媳改嫁,官府拘捕儿媳,使用酷刑逼迫她认罪,孝妇临刑前说“我若冤死,三年大旱”,孝妇死后果然大旱三年,百姓苦不堪言,当地有一位名字叫于定国的人,他的父亲于公在监狱任狱卒,于公建议新任太守前往孝妇冢祭奠,为其翻案,奠后顿时大雨倾盆,旱情也立刻解除。清代诗人屈复以《孝妇冢》为诗名,记录祭奠时的一幕:
大火烧空云欲沸,火云烈烈蒸天地。
孝妇冢前起清风,飞霜之色空中坠。
当时谁致死含冤,徒令人高驷马门。
荆棘参差石纵横,白日有光神有灵。
驱除旱魃求应许,北风飘拂东海雨。
我还是小孩子时,没什么娱乐,村庄或县城里有戏剧演出,便是大人孩子们的共同节日,因此山东吕剧版、山东梆子版、评书版《窦娥冤》,都曾入耳入脑,表演艺人的沉浸与投入,以及唱腔传递出来的惨烈、凄婉、悲怆情绪,无不让人惊心动魄。而在知道《窦娥冤》的故事原型,居然离自己如此之近时,本能的反应不是别的,而竟然是恐惧——我们年龄小的孩子,聆听这样的故事,如误入大雾当中有敬畏也有躲避的心理,再正常不过。
起初,孝妇的故事因为被与罕见的大旱年份联系在了一起,而有了感天动地的震撼感,而后,一些演绎又使得它变得更具传奇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搜神记》,在《搜神记》里,孝妇临刑前所说的话,变成了“青若有罪,愿杀,血当顺下;青若枉死血当逆流”,行刑后,果然血沿着挑起五色长幡的竹竿逆流至顶,又顺幡流下,且血的颜色呈青黄色。
有关孝妇被杀后流出的血的颜色,民间传说也有不同说法,比如我们当地人,就偏于相信孝妇临刑前说的话是“我如有罪,红血流下,如系冤杀,白血逆流”,孝妇被杀后白血成汪,因此附近有村庄被命名为“白血汪村”,后来可能是觉得不好听,被更名为“白溪汪村”。这样的记载与传说,让我少年时期一度产生困惑,觉得这个故事编得有些离奇,后来才想明白,人们纷纷往这个故事里“添油加醋”是融合并寄托了诸多对“对错、善恶”的价值判断使之更具道德审判标准。不管承认与否,孝妇的故事已经成为我故乡所有人共有的一份文化遗产,单就我而言,从沉重到释然,从不解到理解,从远离到走近,这名汉代的女性,曾在我复杂的心绪中,折射出故乡的另外一种样貌。
《搜神记》中的“青”是孝妇的名字,她的全名据称叫周青。然而,在清代县令所撰写的碑文中,第一段就说到,其实他也不知道孝妇的真实姓名。由于关汉卿的《窦娥冤》影响实在太大,周青的名字就逐渐被窦娥的名字所取代,后世的相关作品,也纷纷沿用《窦娥冤》的说法,强化了窦娥,淡化了周青,比如明代成化十五年(1479)朐山县令刘昭,在其所著《汉东海孝妇窦氏祠记》便如此记录:“孝妇东海人姓窦氏”,清代的《云台新志·程学恒云台诸山纪游》也写道:“此去二十里为窦娥坟,古芳可吊。”不过,作为老家人,我还是更愿意称呼她为周青。
我脑海里还储存着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到周青墓前的画面,当时它比普通的坟墓要大十倍之多,让人怀疑这不是坟墓,而是一道小山坡。墓中间有一条隐约的小道印痕,民间传说是周青死后被葬于早她而去的婆婆墓边,没多久,两座坟墓自动合在了一起——这个说法自然是虚构,但我相信在某个时期,定是有无数人前来拜谒,他们踩出了这条小道。
当时年轻,只记得这些画面,并无更深的感慨,现在想来,死去丈夫的周青,如果改嫁,想必也不会冤死,在汉代,改嫁并非多难的事情,其中很著名的改嫁故事,包括卓文君在丈夫死去之后嫁给了司马相如,蔡文姬先后嫁给卫仲道、匈奴贵族左贤王、董祀,当时再嫁或改嫁者最多可达五至六次,如《汉书·陈平传》曾记载,阳武户牖富人张负孙女先后结婚六次。在这一状况下,周青孝顺婆婆固然感人,但婆婆为儿媳的未来着想,不惜牺牲掉自己的性命,这份性情也非常值得尊重,在封建社会,两名女性的守望相助,让人看到了女性群体身上的一抹光辉。
三
除了周青之外,我的故乡还有一位著名的女性,因为美国学者史景迁《王氏之死》的书写,而被现代人更为广泛地知道,可惜她没有像周青那样留下全名,只被后人记得了一个“王氏”的称谓。《王氏之死》的写作,大量借鉴使用了县令冯可参的《郯城县志》、县令黄六鸿的《福惠全书》及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这三本书的内容,虽然据传钱钟书在访问耶鲁时,私下称史景迁为“失败的小说家”,但后来仍有不少学者认为,《王氏之死》是一本微观历史写作的优秀读本。
《王氏之死》的故事大致是这样的:王氏在一个冬夜与人私奔,被情人抛弃后无奈返家,丈夫得知后趁其熟睡时把她掐死,欲嫁祸给邻居,失败后将王氏抛尸于雪路,次日假装妻子失踪报官,审理案件的县令从状子以及其他细节方面发现了纰漏,比较轻松地就把这个康熙年间版本的《消失的她》的案子给破了。
史景迁在《王氏之死》中大量引用了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内容,而这部短篇小说集,以正视真实的人性、宣扬自由奔放的生活与情感、同情小人物的命运而著称,因此出现在《王氏之死》中的王氏,是与周青完全不一样的女性形象,甚至可以说是部分走向了周青的反面,如果说周青可以立“贞节牌坊”的话,那么王氏则因为犯了封建社会的“大不韪”而成为众矢之的,周青的死惊天动地,而王氏之死却像一只被碾死的蚂蚁那样,如此轻飘悲凉……
虽然周青与王氏,在她们所处的不同时代得到了不同的评价,但她们的共同点也有许多:她们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女性,她们的命运以及生命本身,都属于“被宣判者”,在被“宣判”之前,她们没有自己的发声权利与渠道,而在被“宣判”后,一切定义与评价,全由旁人评说,她们失去了自己鲜活的生命,也失去了自我价值的实现,无论从小处还是大处说,无论她们死后得到的是荣誉还是羞辱,都改变不了她们人生的悲剧底色。
《王氏之死》的中文翻译,虽然被指并不出色,但还是有网友整理出了一些句子,让我心怀怅惘,比如:“在世上,现在是冬天,但这里很温暖。冬天,绿色的湖水上,莲花盛开,花香飘向风中的她,有人试着去采,但当船接近时,莲花就漂走了。”“她看到冬天的山上开满了花,房间亮得耀眼,一条白色的石头路通向大门,红色的花瓣散落在白石上,一枝开花的树枝伸入窗户。”从这些句子当中,能够清晰感受到史景迁在通篇充满苦难的书写里,仍然传递出一份浪漫,这份浪漫局限于局部,描写的都是细小琐碎的事物,但正因为如此,当下的读者才能感受到,个体生命的美好,不容被粗暴地剥夺。
曾有朋友误认为,《王氏之死》写到的王氏是周青,是窦娥,想要解释清楚,确实要花点时间,因为过去我也曾将她们混为一谈。其实这也无妨,从民间传说、典籍记载、国外书写等多个层面来看,把她们放在历史长河中,她们其实就是同一个人,或者说是一个性别的代表人物。在明白这点之后,再说到我故乡这两位有名的女性人物时,总是有千言万语堵在心口,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四
周青做过梦吗?她应该是没有做过梦的。一个年轻的寡妇在失去丈夫之后,她的生活也便失去了颜色,她要谨言,要素衣,要躲躲闪闪,即便在夜里,她也不敢做梦,美丽从此与她无关,她变得无比脆弱,来自外界的任何一点打击,都有可能让她身败名裂。于是她掌握了一门反击的技巧或者说武器——孝。守在夫家,孝顺婆婆,相依为命,于是她可以出门了,腰杆可以挺直了,她身上有了一层无形的盔甲,她成了生活的勇士,如果不是心怀愧疚的婆婆用死亡的方式想要给儿媳一个自由,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她们都将是十里八乡赞扬的佳话。
周青的婆婆不知道,她的死,间接地杀掉了两个人。周青没有选择的自由,同样,她的婆婆也没有,她们只能活在人们的期待里、赞颂中,维持着和睦的关系,满足着人们对于“童话”的需求,她们谁都不能亲手打碎“童话”,否则,恼羞成怒的人,便会选择其中之一,将罪责强加于她们身上。知道周青的冤屈很难吗?不,只是那时候掌管人命的人,觉得杀死周青更能让大众感受到背叛所带来的惩罚力量。周青什么错都没有,所以只有“六月雪”“血倒流”这样极具张力的描述,才能映衬出她的冤屈。我故乡曾经有不少女性,在生活里遭遇误解或不公的时候,也会说一句“我比窦娥还冤”。
王氏做过梦吗?相信她是做过梦的。一个不会做梦的人,不会爱上一个不值得爱的人,不会逃跑,不会在黑暗的道路上寻找每一个发光的亮点拼命地朝它奔去。她的梦里有鲜花、青草、蝴蝶、清风、风筝……在她死亡的那个瞬间,她的梦黯淡了下来,她的丈夫不是掐死了她,而是掐死了她的梦一个普通人未经审判让另一个普通人的生命消失了,这是一种狰狞,也是一种坍塌。当她的尸体被抛弃于雪路当中时,她的梦又开始了,她的灵魂会在空中看着她的身体,那是一朵枯萎后在雪中又逐渐盛开的花,大雪可以暂时掩盖罪恶,但掩盖不了梦境……
周青与王氏,死时都还是年轻的女子,是父母的女儿,是村庄里的风景,可在悲剧发生之后,有关她们的一切都消失了,她们的形象如浮雕一般凸显了出来,在浮雕的背后,一切都是如此灰暗与模糊这两座浮雕被推到了一个无形的舞台之上,诬告者、审判者、行刑者、围观者,与这两座浮雕一起构成了一个戏剧场景。是的,她们成为了一场戏的主角,成为千百年来人们不断咀嚼的一个悲情故事而本来,她们的命运是平淡过完一生,不留任何一个字的记载。时至今日,人们难道也能忘了她们各自故事的戏剧性,而仅仅把她们当成普普通通的人吗?不可能了。
我在故乡小城的一所房子中,断断续续地敲下与周青与王氏有关的这些文字,窗外的光线忽明忽暗地折射到电脑屏幕上。脚下的这片土地,因为埋葬着冤屈之骨而显得有些沉重。几十年了,这个地方没有大旱过,也未曾出现大涝,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谈起周青与王氏,都有点惆怅感,仿佛距离她们并不遥远。
等待春花烂漫的时候吧,从田野里采一束花带到“孝妇冢”旁,送给周青(或者说窦娥)、王氏,告诉她们:这世间仍然有雪,但已经不再有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