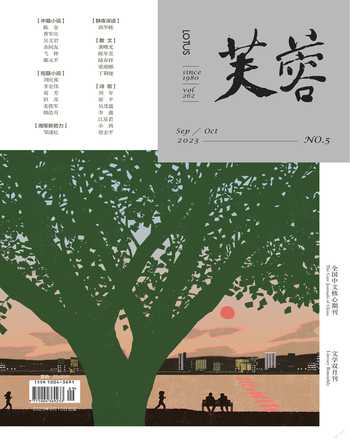追风
但及,浙江桐乡人,现居嘉兴。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已在《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作家》《上海文学》《花城》《作家》《钟山》《大家》《山花》《江南》《清明》等刊物发表作品三百余万字。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选载,并入选多种年度选本。著有长篇小说《款款而来》,小说集《七月的河》《藿香》《雪宝顶》,散文集《那么远,那么近》《心在千山外》等。
1
灯一盏盏亮了,照明小巷的幽闭处。
透光的月亮出来了,高悬在树丛的一角。饭店里很闹,窗子里折射出一堆人,在干杯、说笑。收费的老头背个小包,在汽车丛里晃荡。足浴房门口有霓虹一抖一抖,像蝴蝶在起舞。广场台阶上坐着几个人,伸着长腿在聊天。
我的车夹着凉风在疾驶,“云上人家,云上人家。”我嘴里轻声念着。
后轮气不足,开起来有些涩。一天下来,腰酸手胀,不过我还是吹着口哨。送餐途中,我经常会吹,哨声飘荡在电驴子四周。为了赶时间,我抄了小道,从中学边上插入一条小弄。我已经看到云上人家了,别墅区,在一个围墙里,里面的花草树木探着头。
一幢幢别墅骄傲地屹立在夜色里,延伸过去是树林,林子后面便是秀湖。我能隐约看到秀湖反射出来的一道道白光。抵达林子时,才发现没有路了。我迷路了,只好折回来。在一个泥坡上掉头,或许太急了,车子竟斜了。努力用脚去撑,车还是倒了。
电驴子横在夜色朦胧的小道上。
折腾了好一会,才返回正道。进小区,签字,登记,然后朝着2幢开去。灯光下,依稀看到2这个字样。院子里花草幽暗,叶片里夹杂着光亮。把车停好,从箱里提出打包的食物。是一盒牛排饭。用手机照亮眼前,光线拉开路,把我挪到一道木门前。院内花卉密实,能看到一朵朵肥硕的花。
按了院子外的门铃。门开了,探出一张贴着面膜的脸来。“怎么这么晚?”伴着拖鞋的声音,出现一个中年妇女,卷发,家居便服。我递过餐盒,香水味也到了。我看不清对方,面膜有些恐怖。“对不起,有点晃出来。”
“都是油,怎么搞的?”
“不好意思,是我的问题,向你道歉。”
“都成这样了,道个歉能解决?”她像提着一个烫手的东西。
“真是对不起,刚才……”我没说车子摔倒一事,觉得说不出口。
“我要投诉。没有责任心,没有道德,没有……”
一股脑儿经受对方语言轰炸后,我还是对她弯腰,鞠了一躬。狗趴在窗口后面,黑色的眼珠闪着让人胆怯的光。是条大狗,我有些怕,那东西好似随时会冲出来。
院子安静又恬适。临别前,我还不自觉地张望了一眼,记住了一把撑着的太阳伞,还有伞下的桌椅。它們像剪影一样好看。
还没送出下一单,小康的电话就来了。那人年纪轻轻就大腹便便,此刻,我能想象小康把腿架在茶几上的情形。“又被投诉了,扣五十块。要长记性,五十块你要跑多少单?”小康的口气就像家长,其实他比我还小。小康三十岁也不到。
我感到委屈,对刚才面膜后面的那张脸有了恨意。
臭女人,坏女人。这女人真投诉了,我紧咬嘴唇,电驴子开得更快了。
2
他背手,踱步。我们列队站在他面前。
每天早上,小康都要给我们训话。他把昨天我的事说了,扣钱,就是扣钱。顾客一投诉我们就倒霉。“我们的配送平台叫追风,追风就是比风还要快。配送小哥比的是精益求精,一个字——快。”他字正腔圆,铿锵有力。
早训后,我们像鸟一样四处散开,各自待命,等待订单上门。这会儿,魏珍应该到医院了。她脚崴了,肿得像馒头。她不让我陪,害怕我调休扣钱。我想象她一瘸一拐走进CT室的情形。我没跟她说昨天的事,这样的事我从不说,没必要。她在恒心公司做保洁,从一个台阶上跳下来,结果脚扭了。我希望她骨头没事。骨头有事要打石膏,麻烦就大了,我心里这样祈求着。
到良库取货时,朝订单瞄了一眼。云上人家2幢。怎么又撞到了?这回她点的是炸鸡与薯条。我的心开始不规则地跳动。
阳光在树缝里游荡,钻来钻去,我在树荫下穿梭。白天的别墅区与夜晚不一样,可以说比夜晚更高档,大理石、小桥流水及整齐的花圃都滋养着我的眼。电驴子在2幢前停下。她在,旁边还有个花工在修剪枝条,地上放着工具和肥料。来到院前,她就看到了我。“又是你,怎么又是你?”她问。
我不吭声,把餐盒从箱里取出,心里还憋着气。
“对不起,昨天态度不好。跟老公刚吵完了一架。”
那人向我道歉,这是我没想到的。小木门敞开着。里面点缀着好多花卉,有月季,有牡丹,还有垂挂下来的蔷薇花,鲜艳的花朵在阳光下很灿烂。我不作声,放下就想就走。“扣钱了吧?如果扣了的话,我补你。”她把手叉在腰间,额上闪着汗珠。她长得不算漂亮,偏胖,但看上去匀称。
“不用。”我冷冷地说。
花工瞄了我一眼,继续剪着。大剪子发出咔嚓声。“那么,喝瓶饮料吧。”她把边上一瓶没打开的饮料递我,是柠檬红茶。“不能收客户的东西,我们有规定。”说完我骑上了车。
回头望过去,花朵缠绕在她的四周,她看上去有一种富态。我颠簸着车一直往前。这时手机倒是响成一团,我出小区,在转弯处停下。“还好,只是伤筋。配了红花油,我下午就去上班。”魏珍这样说。
“明天再去吧。”
“为什么要明天?”这把我给问住了。她就是这样一个人。
搁了电话后,我就汇入了大街的人流中。我的衣服是黄的,头盔是黄的,连送餐的箱子也是黄的。黄是代表色。我心里在说,好啊好,魏珍总算没事,我怕她伤骨头。现在没问题了,包袱也卸下了。我甚至没有去想刚才那女人的事,平安最重要。
晚上回家已经九点多,每晚都差不多。老远,就看到我们屋里亮着的灯光,很无力,但很温馨。我知道魏珍已经把菜放在桌上,凉拌猪耳什么的,饭也在电饭煲上热着。我会喝下一杯荞麦酒,嗑几颗花生。这是每天必备的。
路灯下,一群孩子在小广场玩足球。义庄以前住的人少,这几年多了,房价也涨了。当年我就是考虑这里房租便宜才来的。这里是嘉兴城北,紧临墓地,当地人忌讳。此刻,球在地上滚来滚去,有时还飞到空中。我看到丁当和丁冬都在,他们叫着喊着,像一股风一样奔来奔去。在路灯下停了一会,抽完一根烟,我吼了一声:“丁当丁冬回家!”
这一喊,队伍里的两个小鬼就停下了脚步。
他们悻悻然,很不情愿地跟在我车后,朝着家的方向走来。
3
每天总有許多的事。
车轮架着我,在城市里东奔西走,托着一份份快餐和点心,再一一送进别人的嘴里。我是送货员,是厨房与大胃的传递者。
时间总是匆忙。晨起,做早餐,哄孩子吃饭,然后电驴子架起三个人:丁当、丁冬和我自己。我开得快,像是与时间在赛跑。电驴子只能带一个小孩,我的后面紧紧抱着的是两个。我穿小路,在曲折的弄堂与小道上争分夺秒。两个小子又不得安宁,常常吵闹,做小动作,抠身子。有一回丁当还掉了下去,摔地上,打滚,额上起了个包。
送完孩子,我就到平台新城站。我们在蓬莱路。七点钟准时集合,穿戴好,每人一车一箱子,在一个停车场边上听小康训话。完了,便高呼口号,我们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一天紧张的工作便拉开了帷幕。天天如此,只是下雨时,这训话改在了走廊。一长条,像送葬的队伍。
秋天到了,雨水就喧哗不已,这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雨披穿在身上,一身紧绷,像裹了个不透气的套子。下雨容易出事,有时候人会被甩出去,王小刚就摔过,脚上开了个口子,血流了不少。红红的,与雨水混在一起,分不清彼此。每次下雨,我都提醒自己,小心小心再小心,你有家有老婆有孩子,你的命比天还要大。
越是下雨,单子就越多。雨在催,订单也在催,那些嗷嗷待哺的人更是催个不停。台风“烟花”来的时候,狂风夹暴雨,吹得水都要飞起来。树被折得弯过来,形成一个大的弧度。广告牌从空中飞落,砸在地上,发出很大的轰鸣声。小区里的横幅被吹碎,布条子在雨中疯狂拍自己。那天中午,一会儿工夫,竟有二十五单,乖乖,我被这个数字吓住了。
什么是追风?这便是追风。
我就像是一条鱼,在雨帘里穿梭。到后来,也忘了时间,忘了里程,中间还回蓬莱路换了个电瓶。雨像在浇,风吹得睁不开眼,白花花一片,看不清路,也看不清自己的车龙头。什么也看不见,我只是一味地向前,向前,像一台连轴转的机器。自己不知道跑了多少小区,多少写字楼。鞋湿透了,倒出来都是水,还带着我的体温。头发贴在额上,后背也是水,不知是汗还是雨。回到家,我煮了老姜茶,外加红糖。喝了两大碗,喝完后还吐了。魏珍说,你啊你,还当自己是小年轻啊。她有心疼,也有抱怨。
好在我的同事都平安,过后大家都笑嘻嘻的,没当回事。
只有苗长水心悸,他从没见过台风,这威力令他发怵。他说,妈呀,怎么会是这样呢?像在瀑布里,一点不假,就在大瀑布里面。
4
我喜欢城西。城西树多、河多,还有一个新挖出来的秀湖。
秀湖很灵动,闲下来的时候我就在湖边转。看看那些透蓝的湖水、丰茂的水草,有时还会有小。那些精灵脖子上有花羽毛,在芦苇丛里穿来穿去,有时是一群,有时是单独一只,轻轻划动水面,可爱极了。
坐在长椅上,吹着湖上的风,抬头就能望见云上人家。我不时会想到那个时而发威、时而温柔的女人。花园给我留下了印记,那些密实的花朵在夜里和白天绽放,鲜艳,茂密,与周边浑然天成。富人的世界离我很远,我很难想象他们的生活。有一点我不明白,她为何常点快餐?像她这样的人不应该这样,家里应该有用人,帮她弄好饭菜。或许她会开一瓶红酒,与闺密一起坐在吧台,或者在露天桌椅上优雅地进餐,就像电影里经常出现的画面。不过,我也不想搞懂这些,说到底这与我何干呢?我只是被扣了五十块钱,有些心疼。那别墅离我遥远得很。
事情常常这样,你想什么就会来什么。那天傍晚,手机嘀嗒作响,平台上的单子一张张飞来,我一看又有云上人家2幢。街上,轿车挤成一团,像小脚女人一样挪动着。相反,我的电驴子仿佛有神助,在里面穿梭,来去自如。晚霞散着,一堆堆,呈带状,绵延在西边高楼和树丛的上方。晚风也来了,从银行大楼侧面吹来,带着夜晚降临的那份无奈。
当气派的花园别墅出现时,显得很宁静,余晖正挂在墙角上,光还斑驳地反射到玻璃上。太阳伞收了,直立着,一动不动。藤蔓把进院的小木门包裹成一个拱门,我按响门铃。铃在里面响。我不停地摁,就是没人出来。
提起餐盒,找出上面的电话号码。电话没人接。我气恼,心想又轮上这人了。
推开木门,进入院子,一根蔷薇花枝挡在眼前。来到屋前,我把脸贴在玻璃窗上。“喂,有人吗?快餐到了。”声音带着不耐烦,还惊飞了一只停在花丛里的蝴蝶。
有影子,我不能确定,把眼睛更紧地贴住凉凉的玻璃面。现在我看清了,一个人在地上像蛇一样盘着,在扭动和挣扎。我以为看错了,努力睁大,把目光拉直。是的,是一个人,家居服上有抽象的图案。有情况,我开始敲打玻璃窗,又去推面前那道门。
门锁着,推不动。屋里的人扭得更厉害了。
应该有后门,我下意识地想。我心急火燎绕到屋后,后门真有,门虚掩着。猛一推,发出很大的声响,还有一股反弹力让门颤抖不止。我冲了进去。在客厅的中央,在一块沙发地毯的旁边,我见到那个人。就是她,我认识的那个女人。
女人蜷缩在地,眼闭着,在喘气。“怎么啦?你怎么啦?”
把餐盒扔一边。我蹲下来,摇动她身子。
“……难……难受。”声音轻得像蚊子叫。
危险!眼前这张脸在扭动,变得难看又夸张。
“有人吗?家里有人吗?”我高声地喊。站起来,环顾四周,希望屋子里出现其他人。没有人回应我。我奔向厨房和卧室,里面空空荡荡。只听到狗叫,声音发闷,像是从隔壁某个地方传来。
女人还在挣扎,在地上,好似在滚动,不久又停了。
我六神无主。不过很快,我掏出了手机,拨打120。快,越快越好,我这样对自己说。“有人出事了,你们快点,在云上人家!新城街道云上人家2幢!”我一直记得这个地址,忘不了这个地址。
搁下手机,四周寂静一片,狗的叫声突然停了。霞光透过西窗落在地上,在地毯上织成一道光柱,但我依然觉得这环境尖锐。屋里阴森森的,像被什么沉重的东西压住了,望出去连那个漂亮的院子也容颜尽失。女人一动不动时,我害怕极了。我怕她这会兒就死去。手机一直在叮咚地响,那是订单的推送,我仿佛没听见,更无心去看。我不时蹲下,又不时站起,额上都是汗。
“坚持一下,快了,快了,救护车快到了。”时间真的过得很慢很慢。
直到救护车长长的笛声从院外传来,我那紧绷的神经才松弛下来。
5
她就坐在我对面。
我像是屁股上长了疮,浑身不舒服。她恢复了健康,看起来白里透红,头发也盘了起来。乌黑的头发像上过一层漆。边上坐的是她男人,高个,清瘦,戴眼镜。她说他有个家具厂,做红木家具。
“我心脏不好,那天情况很严重。幸亏你来了。”她说。
她给我递茶,边上围了一堆的水果。她男人拿出烟来。我平时会抽几根,但现在则慌乱地摇头,我说不抽,抽不来。抽得里面乌烟瘴气,这像话吗?
“你救了我。是你。”
她这样说,我就不好意思。这是巧合,或者也是天意,我说不清。那天我乱成一团,感到这环境的压抑。现在环顾这屋内,竟是另外一番呈现:华丽的窗帘,气派的水晶吊灯,红木桌椅闪闪发光,还有两个跟人一样高的精致大花瓶……一切仿佛都醒过来了,生机勃勃了。
“真是瞎了眼,我还骂过他呢。”她朝男人看了看,男人也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
她把头又转向我:“你不会一直记着吧?”
我摇了摇头。我的确忘得差不多了。
音响里放着轻音乐,乐声像在掏耳朵一样,轻轻地拂撩着。茶叶挺好,枚枚翠芽,绿得沁人,它们在玻璃杯里荡漾开来,一根根往下沉。我拿起,抿了一口,茶水带点甜味。
她取出一个信封。信封放在中间的茶几上,她中指发力,一点点往我这边移。
我看到信封里露出的人民币边角,那是很厚的一沓。“有点俗气,可我想不出更好的方法。我只是想说谢谢。”她把它推到我面前,停下。
我把它推了回去:“这不行,不行。”
我只是打了个电话。我想都没想,推得坚决又迅速。
“医生说了,幸亏送得及时,我老公也是这样认为的。”她又把信封推了回来,再度来到我面前。
“其实,这没什么。”我的声音有些发抖。
是不是要收?要不要?我在持续斗争。我觉得拉不下这张脸,我心虚,好像收了自己就不道德了。我又推了回去。这回推得较慢,信封与茶几面像在来回地摩擦。
“哎,你……真是一个好青年。”她的脸变红了,这样总结道。
男人的目光里有赞许,像在回应她的说法。
我在盘算,如果她再把钱推过来,我就收下。我内心是有这渴望的。我希望她再推,望着她,期待着,可这双手不动了。男人来电话了。他说了声对不起,移步到院子里。玻璃后面能看清院子里的人影和花影。
“我这个人年纪不大,却是一身的毛病。每天吃的药你都猜不出来。我要吃十几种药。就当补药一样在吃。不瞒你说,我还在吃抗抑郁的药,这种药吃了会发胖,你看我胖不胖?”
这让我惊愕。当着我这个外人,她会说这样隐私的话。我浑身燥热。
“我常常这样,一个人守着这个大屋子。你看这房子,够好吧。你说我过得幸福也对,你说我过得凄惨也行。”
6
“傻瓜一个。”魏珍一下子定性了。
我告诉了她前后经过,告诉了她我没有拿钱。“哪有你这样的人呢?你救了人家,人家感激你,偏偏装清高,装得像富人。你好好看看我们这个家,冰箱是房东的,桌子是房东的,连我们睡的这张床也是房东的。”
老婆说的是真话。事实上,从别墅里出来我就后悔了。我可以理直气壮地拿,但我这人脸皮薄,拉不下来。这一来二去,就错失了。现在魏珍一骂,我更觉得丢脸。“好了,不要说了好不好?”我喉咙竟响了起来。
“做错了事还喉咙老大,真要被你气死。”魏珍把正在洗刷的铝锅摔得砰砰响。后来,还把床上的被子抱走,看来今晚她要睡沙发了。沙发上堆了衣服,她胡乱地挪到凳子上。
“老爸,妈妈怎么啦?”丁当悄悄地问。
“老爸犯错误了,弄丢钱啦。”我哭笑不得地说。
“丢了多少?”
“不知道,可能很多。”
“噢。”小孩子在做作业。灯下的光萦绕在两人之间,丁当与丁冬在悄悄地耳语。
我很后悔跟魏珍说。我没忍住,其中还有夸耀的成分。这次夸耀完全得不偿失,魏珍有一个星期没与我说话,就像个陌生人。她走路一瘸一拐,有时还用个木棍当拐杖。她对小孩的脾气也不好。
“听见了吗?别磨叽了,上学要迟到了。”好像整个世界都欠了她一样。
这以后,我经常收到那女人的电话。她的电话让我期待,也让我不安。她问我好吗,生活如何,如果需要她会帮助我,等等。我总告诉她一切都好,每天忙忙碌碌,但挺充实。我就是这样说的,一半是真,一半也是客套。
“好青年。你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有志气的一个。”
她这样评价我。我听了飘飘然,但过一会又觉得不可能。我只是个打工仔,哪里谈得上有志气呢,我觉得她这话有些离谱。
她偶尔还点餐,像以前一样。她点牛排、熏鱼、虾、沙拉,等等。有一回,我终于忍不住了:“多吃快餐不好,我每天在送,但我知道不好。”这是真心话。与以往不同,那天她穿了套运动装,灰黑色的,还配了双白色运动鞋。我说完就后悔了,她比我懂得多,我何必这样说呢?
“你说得对,我开始锻炼了。我要改变我现在的生活,不能再这样了。一直在吃药吃药,我要运动了。”她把手伸到空中,来回比画着,像要抓住什么。
“你是好青年。我是说你给我带来了不一样的感觉。你是那样单纯、善良,对生活充满了热爱。我用一个词语概括,就是阳光。”
我抓起了头皮。从来没人给我戴过如此的高帽子。我既觉得她可爱,也觉得她荒谬。“不是的,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否认她的话。
“从你那天不收这个钱开始,我就这样认定了。像你这样的人太少了,你从事着辛苦的工作,可你开朗、大度。”
她的话像炸弹,一颗颗地在我面前爆炸。我活到现在三十六年,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我。我惊愕、好奇、哑然,觉得眼前这人有点不真实,更像是我臆想出来的。
“小弟,路上骑车注意安全。”
在电话里她常常会这样关照。开口闭口都是小弟,好像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她让我叫她姐,我开不了这个口。“我会的,我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我这样回答她。
“对啊,你有老婆小孩。你的安全不光是你的,也是你们全家的。”她的口气仿佛变成了小康。小康有时候就这样跟我们讲大道理,但她的大道理比小康动听,至少我听得进。
7
中秋前一天,苗长水在ICU里昏迷了。
我和大伙在ICU大门外朝里张望,其实什么也看不见,只能看到桌子和一道白色的布帘。不知道里面的人是生是死,人人都有一种自危。他是闯红灯才出的车祸,为了赶时间,为了他那份追风平台上的业绩。
苗长水比我大两岁。有时我们把电驴子停下,靠着树干聊天。他很搞笑,常常说一些风趣幽默的话。老婆跟别人跑了,他单身一人。他说他比我好,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口袋里还有把口琴,拿出来横在嘴里,吹出一些曲子来。那些个小调就呜呜地在街边游荡。
从医院出来,回到追风新城站。站里很乱,墙上贴着各种制度,以及每个人的健康证和大头像。小康的头像最大,他是站长。电脑前两名小伙正忙着。小康在看报表,我与几个工友走近,他吓了一跳。我们把医院的情况说了,说在催费,扬言再不缴费,就不抢救了。大家都担心苗长水,苗长水可能连命都不保。
“不是我不想管,这事真不好办。他没有交社保,没有工伤保险。”小康放下报表说。
“怎么可能?我们不是每个人都缴了吗?”我站在他面前,声音有些异样。
“跟苗长水谈过,可他就是这样。他不想掏这个钱,他说他安全得很,可偏偏出了事。”
“规定里有,每人必须参加保险的。”
“话是这样说,但人家苗长水不肯,我有什么办法。”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总要有一个办法。”
“我都是按规定在办事。”
“你说一声,平台到底管不管?”
“他没保险,又闯红灯,要负全责的。”小康把平台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放屁!”想到苗长水会死,忍不住,我竟骂人了。我激动得很,与平时那个文绉绉的我完全不同,脸也涨得绯红。
“你说什么?”
我又拍了一记桌子:“都是你,一天到晚催我们快快快。他闯红灯,有一半也是你推过去的。”
“放肆!”小康一下子变脸,瞪着我。“简直是狂妄。”他的脸色从来没这么难看过。
这一夜我没睡好。一直记得小康那蔑视的目光,我有点后悔,觉得自己冲动了,但说出去的话等于泼出去的水。我再也收不回来了。我告诉自己没事,一切都会好的,苗长水也会好的。我这样宽慰自己。
天亮后,丁当与丁冬很兴奋。中秋节到了,学校放假,他们两人一直在床上闹腾。魏珍在电饭煲里烧了粥,早去上班了,桌上放着咸菜和煮鸡蛋。一只苍蝇在头顶嗡嗡地飞,阳光降临,屋子里射进了一道红光。
刚骑上电驴子,就收到平台发来的短信。短信说,我已被除名,从今天起不用上班。收到这短信时,我一阵恍惚,没想到小康的报复来得那么快。墓地边延伸出大片的林地,有一群鸟在枝头吵闹,嘈杂又响亮。我觉得它们在嘲笑我。
赶到蓬莱路时,大伙儿已各自散去。我故意晚点过去,避免与同事尴尬相遇。
站里,只有杨海峰一人,他懒洋洋地守在电脑前。隔壁充电间里,电瓶的指示灯像幽灵一样在闪光。海峰朝我点头,神情尴尬。我去推小康辦公室那扇死寂的门,那门一动也不动。
“出去了。”海峰冷冷地说。
“苗长水怎么样了?”我又问。
“不知道。”对方冷漠地说。
风沿着高楼的过道扑过来,我一脸茫然。现在我的手机一片寂静,平时这个时候嘀嗒声不断,繁忙一片。手机里工号479的那个人已被他们清除,479号再也回不到工作状态。看边上的杂货铺、理发店,还有送水工进进出出,我觉得无比陌生。我还穿着我的工作服,电驴子上还装着黄色图案的箱子。
我没有把这情况告知魏珍。她会埋怨,会嫌我多管闲事,把一个好好的饭碗给丢了。我四处转悠,没有送货的电驴子像是脱了缰一般。踱进一片树林,躺在草地上胡思乱想。那会儿手机却响了,一看,竟然是她。“小弟,在忙吗?”我告知她不忙。我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
“告诉你个事,我要工作了。中秋以后,到我一个小姐妹的花店。”
“真的?你真要这样做了?”
“是时候了。我不能这样了,再这样下去身体要垮了。”
我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只是沉默着。
“今天中秋节,我把一盒月饼放在了花店。你呢,顺便去拐一趟,离你们平台新城站不远。去参观一下那家店,顺便也把月饼拿了。”
“这,这不好吧。”我觉得很意外。
“去看看那家花店吧,布置得挺洋气。店的名称叫花仙子,中山西路153号。记住,别忘了月饼啊。”
“这个好像……好像……”我支吾着。
“我能跨出这一步有你的功劳,记得要去拿啊。祝你们全家中秋快乐!”
她去工作了,我却把工作丢了。我在犹豫要不要把失业的事告诉她,她却把电话搁了。
事实上我到现在也叫不出她的名字,送餐单上留的都是应女士。我不好意思问她的名字。不过这没关系,收到祝福已经让我激动。居然给我节日礼物,想到这我就浑身发热。
8
回义庄,已过九点。故意拖这么晚,我装出很忙的样子。
月亮静静地爬上树梢,月色浓密,地上仿佛罩了一层银色的膜。我轻轻推开家门,两个小子看到月饼,顿时欢呼起来。礼盒包装得精致,外面礼袋,里面有铁盒。丁当和丁冬趴在桌上,艰难而又认真地拆着封皮。一打开,两双小手就抢夺起来,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塞进嘴里。
“哇,好吃。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丁当说。
丁冬在嚼,根本没时间顾上说话。两个人狼吞虎咽。
“哪来这么好的月饼?”魏珍拿起礼盒。“香港双黄白莲蓉月饼。”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念。
于是我说了实情。
“又是那个女人。好啊,你还在跟那个女人交往,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你说。”她的脸色变了,开始夺孩子们手里的月饼。
她把月饼一一夺下。“你这是干什么?”
“问你!”她吼了一声,然后就把孩子们吃过的月饼和铁盒里的月饼往垃圾桶里扔。丁冬叫了起来,丁当还要去夺,但来不及了。垃圾桶里都是脏物,有泔水,有吃剩的饭菜。一家人看着这些月饼被脏水吞没。丁冬哭了,丁当则瞪着一双愤怒的眼睛。
强忍怒气,我一声不吭,来到室外。今天烦恼事太多了,我不想与魏珍再来一场争吵。
夜深了,义庄更静了,凉风从墓地那边吹来。月亮好像在与云层捉迷藏,时不时地躲起来。大地一会儿亮开,一会儿又变得模糊。我有些伤感,换了以前我会摔东西,骂人,但今天没有。想到苗长水,我那颗急躁的心稍稍缓和一些。没人告知我他的情况,我只能在心里默默为他祈祷。
地里偶尔有长长的蝉声,它们躲在草丛里,和着风声发出尖锐的吱吱声。月亮大而圆,默默地注视着大地。
喜欢这片月光,柔柔的,我想这会儿的月亮也照在云上人家。就这样我抬起头,仰望起天来。云在盘旋,在快速地移动,一会儿聚,一会儿散。我睁大眼,仿佛真的在云上看到了她。是的,她就在上面,在看着我。此刻,云密了,甚至把月亮给吞了。云包围了月,月躲在了云的深处。
花仙子店的情形又浮现了。各种颜色的插花融合在一起,造型各异,姿态万千。一进店,我就看到了那盒月饼,很显眼,放在柜台的一角。看到它的一刹那,我内心升腾起一股暖流,这真是幸福的滋味。
尽管我没吃上一口,但仿佛尝到了月饼的甜香。月亮又出來了,云被月照得透明,像松散的花絮。对着那片幽暗之地,我轻轻地叫了一声:“姐。”
就这样,我一会儿想想苗长水,一会儿想想那个遥远的姐。
月色如绸,空气清冽,我听着自己击打地面沉重的脚步声,一下,又一下,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