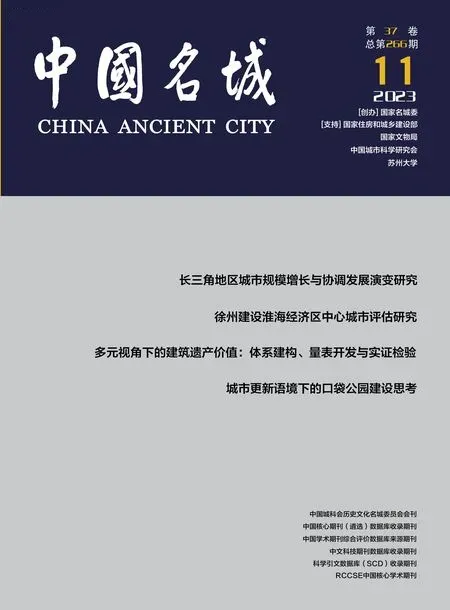重庆地名时空分布特征及变迁机制研究
——以渝中半岛为例
杜春兰,王一婷
引言
地名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史的记录与见证,包含了大量的典故、习俗及地域特色,记载了民族迁移、环境改变等人类历史发展轨迹,是传承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自2007年联合国正式确定地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名文化遗产逐渐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中国较早地认识到地名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1977年成立中国地名委员会,2004年成立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并随之启动“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兴起了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热潮。实施地名保护对于提升地方文化显现度,进而推动城乡文化建设和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这需要基于对地名空间分布、历史变迁,以及地名文化内在机制识别等的大量基础研究。
1 研究基础
1.1 研究现状
以往,学者基于地名在文化遗产、社会记忆、城市形象等方面的重要价值[1-3],通过揭示其空间分布特征规律[4-6],于政策制定层面[7-8]、规划设计层面[9]提出相关对策及策略,以此来应对地名文化所面临的问题及困境[10],已经形成丰富的研究成果。同时,伴随着学科交叉,新技术手段为定量研究提供了助力,例如语义分析软件应用方面,陈萍等对重庆地名词汇特点进行了论析[11]。运用GIS对地名数据可视化处理来建立信息图谱[12],分析空间分布特征、演进规律[13-15]等方面,王彬等最早将GIS应用于广东地名景观分析,之后此类的研究逐渐增多,凌欢等运用核密度分析法对泉州市古街巷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成因进行研究,林琳等运用GIS核密度估计法对广东江门的聚落地名进行空间分布及成因探析,但这类研究主要以静态地名景观研究为主,地名景观时空演变研究较少。
对重庆地名文化遗产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周文德在《重庆市政区地名通名再探》《沱与坨地名文化差异》中结合重庆自然地理情况对地名进行分析[16-17];杨宇振的《历史与空间:晚清重庆城及其转变》探讨了晚清到民国不同阶段的重庆城景象[18];蓝勇的《重庆历史地图集》《重庆古旧地图研究》整理汇编了从秦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古地图及影像资料,展现了重庆市的历史演变[19-20];周勇主编的《重庆通史》记载了从公元前200万年到公元1952年重庆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21];等等。就既有研究成果而言,从历史变迁视角对重庆地名的空间格局演化展开探索,运用GIS手段分析地名时空分布并深入剖析其变迁机制,能为服务重庆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提供重要理论支撑及实践指导的成果仍有欠缺。
1.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重庆地名作为地方知识体系的传承,充分体现了自然地理环境及不同文化影响下的地域特征。渝中半岛作为重庆母城,其地名浓缩了“山城”“江城”的自然精华,记载了其历史演变的痕迹,积淀了巴渝文化、移民文化、抗战文化等厚重的人文底蕴,展现了重庆母城独有的文化记忆,是中国地名的典型案例。2017年《重庆市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施方案》的出台,为重庆地名文化相关研究指明了方向。但伴随着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消失地名的数量在近十年内急速增长,据2019年统计数据显示,消失地名已达1 168条[22]。
为此,通过对《巴县志》[23]、《重庆历史地图集》[24]和《新中国出土墓志·重庆卷》[25]等文献资料的收集,筛选出4个具有代表性的时期的渝中半岛地图,分别是明清时期(1891年)、民国时期(1920年)、抗战时期(1942年)以及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地图。这4个时期的地图内容详实且能较好反映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中,明清时期的《重庆府治全图》对当时重庆城几乎所有的道路、城门和重要的庙宇、府衙、会馆都做了精细的描绘,是研究古代重庆城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26]。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过渡期和转型期,城市地名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见证了城市的发展与变迁,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对探索不同时期空间格局具有重大意义[27]。抗战时期,党政军机关以及工厂、商业、学校纷纷搬迁,由此涌现了大量包含国民政府西迁和抗战记忆的地名。新中国成立后,市人民政府对部分重庆地名进行了变更。
对以上4个代表性时期的渝中半岛地名信息进行梳理、甄别,建立了基础数据库,运用归纳统计法、类比分析法等对地名特征等进行分析。同时,将收集到的地名点位落入1∶50 000渝中区地图(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通过GIS核密度空间分析法,对渝中半岛地名时空分布特征、历史变迁进行总结,对其动力机制进行深度剖析,以此服务重庆地名文化遗产的认知体系建立和保护实践。
2 渝中半岛地名类型及特征
2.1 地名类型体系
梳理4个代表性时期的地名数据,其中明清时期496条,民国时期247条,抗战时期409条,新中国成立后410条,去除重复地名数据,共计820条。根据相关规范中对地名类别采用的“面分类法”“线分类法”,划分为“自然地理类”“人文地理类”,并参考《四川省重庆市市中区地名录》中的分类标准[28],将渝中半岛的地名划分为两大类:自然景观型和人文景观型,其中自然景观型包括以地形地貌、水文以及动植物命名的区域,人文景观型包括以行政区划、建构筑物、历史文化、生产活动、愿望愿景、姓氏宗族、宗教、数字、人物、神话传说、图腾文化等11种方式命名的区域。
根据对地名的初步分析可以发现,在前人的分类方法中,行政区划类(如县、村等)在地名总数中占比最大,达到了32.68%,但这一类型地名划分对于研究地名特征规律并没有特殊的参考价值。再者,传统地名的来源常常具有多元化特征,有时会出现2种,甚至3种以上类型复合命名的情况,例如“凤凰台”既有建构筑物属性,又有图腾文化属性,而前人的分类标准无法规避地名类型交叉重叠的情况。此外,前人的分类方式中部分分类对景观视角下重庆地名特征研究意义不大,如数字、人物、神话传说、图腾文化等。总之,前人的分类方法无法完全涵盖重庆地名的类别情况。
因此,为规避重复划分和对地名特征没有影响的要素,本研究结合前人分类方法提出新的分类标准,并对重庆地名进行进一步梳理和归纳,将地名一级分类划分为自然景观型、人文景观型和自然人文复合型(表1)。其中,自然景观型地名的二级分类是地形地貌类、水文类以及动植物类,人文景观型地名二级分类是建筑工程类、经济活动类、历史文化类、姓氏宗族类和宗教文化类,自然人文复合型地名既包含自然属性又包含人文属性。新的分类标准补足了既有分类标准中的缺漏,使分类体系更加完整、合理。
2.2 地名特征
从统计数据来看,虽然历经多年城市化建设对原始自然环境的改变,重庆独特的地形地貌特征仍然十分明显。以自然景观特征命名的地名占总数的17.31%,在其下属3个分类中,地形地貌类占比达到8.66%,约占自然景观型地名的50%。比较典型的有:山、岩、石、坪、坝、坡、坎、塝等;另外,作为著名的山水之城,以江、川、溪、沱、沟、湾等命名的地名体现了渝中半岛明显的水文特征,这类地名占总数的5.49%,占自然景观型地名的31.69%。以地形地貌和水文命名的地名约占到自然景观型地名的82%,体现了重庆显著的山水相融的自然山水格局特征。动植物类地名命名虽然占比较小(3.17%),但也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例如“鹅颈项”“黄葛街”等。
人文景观型地名是在人类生产、生活及社会活动等作用下产生的。人文景观型地名占到总数的76.59%,占比较大。在其下属的5个小类中,建筑工程类占比最大,在地名总量中占比达到31.22%,是命名的主要依据。其次为历史文化类,历史文化类地名中抗战时期、民国时期出现较多,如“捍卫路”“解放路”“胜利路”“民生路”“民权路”等,记录了当时城市的发展与变迁。经济活动类和宗教文化类地名分别占总数的10.61%和9.51%,这两类地名大多来源于明清时期,反映了当时重庆古城经济繁荣、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在人文景观型地名中,姓氏宗族类地名占比最少,约占总数的5.49%,其明显受到重庆3次移民浪潮的影响,诸如“戴家巷”“竹家街”“朱十字”等地名,均是以当时聚居于此的宗族姓氏命名的。
按照新的分类标准,有6.09%的重庆地名属于自然人文复合型地名,虽然其占比较小,但是能看出特殊的命名方式。根据其不同的自然属性和人文属性,可以将这一类地名继续细分为:建筑工程+水文、建筑工程+动植物、历史文化+地形地貌、历史文化+水文、姓氏宗族+地形地貌、姓氏宗族+水文、宗族文化+地形地貌7类。在自然人文复合型地名中,姓氏宗族+地形地貌类地名占比最大(2.20%),典型代表有马家岩、蔡家塆、黄家垭口等。
3 时空分布与变迁机制
3.1 自然景观型地名的时空分布
将所有具有自然属性(自然景观型+自然人文复合型)的地名依据3类地名点位分4个时期落入渝中区地图,运用GIS进行核密度计算,并通过叠合进行空间分析,从而获得渝中半岛自然景观型地名从明清到新中国成立后4个时期的空间格局,以及时序变迁情况(图1)。

图1 各时期自然景观型地名核密度分布
从整体分布变迁情况来看,自然景观型地名随时间变化并不大,但在民国时期出现数量减少的情况。除1920年地图本身记载数据较少外,自然景观型地名在明清至民国这段时间内存在部分消亡情况,如“篼子背”“坳坡岩”等地名都在这段时间内消失了。这可能是由于这段时期的城市建设使得渝中半岛自然要素减少,导致反映自然地理特征的自然景观型地名也随之消失。
而在空间分布上可以更直观地看出,自然景观型地名的分布与重庆山水格局密不可分。表征坝、坡、岩、坎、岭、岗、山、塆等地形地貌类的地名集中分布在渝中半岛地形地貌特征较为突出处。如明清时期的地形地貌类分布图较好地呈现出渝中半岛山脉,即佛图关—鹅岭—大梁子一脉。表征沟、池、水、溪等水文类地名分布特征明显,大多分布在渝中半岛北部和南部沿江地区,主要集中在水量稳定处以及长江、嘉陵江沿岸。动植物类地名集中分布在渝中半岛南部,与现有绿地密集区域大体位置一致。
渝中半岛独特的自然地理特征决定了自然景观型地名的时空分布格局。从地形地貌特征来看,渝中半岛位于四川盆地东侧平行岭谷地带,同时被两江切割,形成了典型的低山-丘陵谷地-江河地貌单元,因此地形地貌类地名多集中于自西向东横穿渝中半岛的山脉沿线以及两江峡谷区域。从水文及气候特征来看,重庆水系发达,且属亚热带气候,降水较多,水量丰足,有利于动植物的生长,因此渝中半岛水文类及动植物类地名也较为丰富。在自然要素丰富的区位,人们更倾向于以自然景观命名。自然景观型地名是渝中半岛人对地理环境直观认识的产物,是对自然环境适应性选择的结果。
3.2 人文景观型地名的时空分布
渝中半岛作为重庆母城,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本文选取的4个时期分别具有其代表性的历史文化背景,如明清时期反映了重庆古城的巴渝文化;民国时期反映了民主与科学的文化;抗战时期反映了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的抗战文化、红岩精神等。
将全部具有人文属性(人文景观型+自然人文复合型)的地名依据5类地名点位分4个时期落入渝中区地图,运用GIS进行核密度计算,并通过叠合进行空间分析,从而获得渝中半岛人文景观型地名从明清到新中国成立后4个时期的空间格局,以及时序变迁情况(图2)。

图2 各时期人文景观型地名核密度分布
从整体分布变迁情况来看,人文景观型地名在近70年的时间跨度上总体呈现出先增多再减少的趋势,但在历史更迭中还是保留并延续了明清时期的历史文脉。从明清时期到抗战时期,人文景观型地名总体呈现出由城市中心向外扩张,且密集程度继续加深的趋势。可以看出,这一段时期内,由于多种新兴文化的出现和融入,此类地名也在逐步增多。比如:明清时期渝中半岛有诸多以古城墙、宗教文化等命名的地名;而到了民国时期,受“三民主义”“新文化运动”等影响,出现了“民族路”“民权路”“民生路”等地名;抗战时期,“和平路”“精忠路”以及“五四路”等地名出现;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胜利路”“解放东路”“解放西路”“新华路”等地名。这些受特定时期文化影响的地名在历史的更迭中不断变化。在新中国成立后,受到重庆地名更改①的影响,不少蕴含历史文化的地名被更替,人文景观型地名整体呈现减少趋势。
空间分布特征方面,明清时期的人文景观型地名分布范围与重庆古城范围基本一致,而在民国时期出现了整体东移的情况,此后,人文景观型地名在此基础上向外扩散。二级分类方面,建筑工程类地名分布与城市区域发展情况相吻合,集中在城市建成区,包括渝中半岛中部以及地势平缓的两岸;经济活动类地名主要集中在两江沿岸码头处,并在城内呈现出集中分布的情况,与经济贸易中心分布有关;历史文化类地名在明清时期分布较广且密度较大,沿交通线延展,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文化类地名逐渐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地名保护的困境;姓氏宗族类地名呈集聚性分布,且与建筑工程类地名集中处基本重合,集中分布在渝中半岛东部和中部,这一类地名数量在抗战期间大幅增加,可能与战时重庆作为陪都涌入了大量人口有关;宗教文化类地名在空间分布上变化不大,集中分布渝中半岛中部,并呈现一定程度的集聚。
相较于自然景观型地名,文化景观型地名时空分布较为稳定,前期主要集中在渝中半岛中部、重庆古城范围内;中后期随着建筑工程、经济活动的外溢与姓氏宗族的外迁,文化景观型地名也整体由渝中半岛中部向四周扩散,但同交通线、宗教寺院、人口分布等分布高度契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中心向外扩张的进程。
3.3 变迁机制及其原因
将各时期地名数量分类统计后发现(表2),明清以来,渝中半岛地名由人文景观型地名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且总体呈现增长趋势;自然景观型地名在占比上总体有较大幅度减少;复合型地名占比相对平稳,4个时期占比均维持在7%左右。
在人文景观型地名中,建筑工程类地名在近70年间上涨了约4%,其中在抗战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后这段时间上涨了3%,反映了渝中半岛在此期间建筑工程量增多,城市化建设迎来飞速发展。经济活动类地名在明清至抗战时期迎来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在之后大幅下降,反映出抗战之前重庆较好的经济发展,以及抗日战争对重庆经济的影响。历史文化类地名在5类人文景观型地名中增长幅度最大,且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说明各时期的历史文化及事件均在历史文化类地名上得到较好的呈现。姓氏宗族类和宗教文化类在占比上随时间均呈下降趋势,且宗教文化类下降趋势明显(约10%),可能是宗教活动在人们生活中的比重减小所致。自然景观型地名中,地形地貌类及水文类地名虽然存在波动,但总体占比较稳定,反映出渝中半岛的自然山水特征并未发生较大改变。值得一提的是,动植物类地名随时间下降幅度较大(约5%),是自然景观型地名占比总体下降的主要原因。

时期 明清时期(1891 年) 民国时期(1920 年) 抗战时期(1942 年) 新中国成立后(1959 年)地名类别 数量(个) 比例(%) 数量(个) 比例(%) 数量(个) 比例(%) 数量(个) 比例(%)地形地貌 44 8.87 22 8.91自然26 6.36 30 7.32 13.91动植物 34 6.85 18 7.29 20 4.89 9 2.20 19.35 21.06 17.36水文 18 3.63 12 4.86 25 6.11 18 4.39建筑工程+水文 9 1.81 2 0.81 3 0.73 3 0.73建筑工程+动植物 5 1.01 0 0.00 1 0.25 2 0.49历史文化+地形地貌 3 0.60 3 1.21 2 0.49 6 1.46历史文化+水文 4 0.81 1 0.40 3 0.73 1 0.24姓氏宗族+地形地貌 4 0.81 2 0.81 4 0.98 13 3.17姓氏宗族+水文 3 0.60 4 1.62 7 1.71 2 0.49宗教文化+地形地貌 6 1.21 3 1.21 7 1.71 4 0.98自然+人文6.85 6.06 6.60 7.56建筑工程 117 23.59 55 22.27 101 24.70 112 27.32人文经济活动 47 9.48 25 10.12 58 14.18 45 10.98历史文化 81 16.33 50 20.24 91 22.25 118 28.78姓氏宗族 35 7.06 16 6.48 23 5.62 19 4.63宗教文化 86 17.34 34 13.77 38 9.29 28 6.82 73.80 72.88 76.04 78.53
变迁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物理环境的稳定是地名存在的重要基础。城市建设或其他因素引起的自然环境改变,或建筑、街道等载体消失,会导致地名随之消失。这一点从各个时期的自然景观型地名和宗教文化类地名的整体下降趋势中可以看出,如明清时期的宗教文化类地名“文庙”得名于曾位于临江门一带的宗教建筑,但随着文庙的消失,地名也随之消失。大阳沟曾是嘉陵江边一条小溪的支流,大阳沟上建有会仙桥。但在20世纪末期,大阳沟所在区域建起大都会广场,2010年在会仙楼原址上,修建重庆环球金融中心,之后大阳沟被改为暗沟,“大阳沟”和“会仙桥”地名也被取代。与之相反,建筑工程类地名呈明显增长趋势,是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建筑增多所致。
其二,思想意识的转变对于地名更迭起到决定性作用。宗教文化类地名在近70年间占比逐渐减少,明清时期占总体的17.34%,民国时期占13.77%,新中国成立后仅占6.82%。其背后除了物理环境等因素带来的影响,显然与思想解放和宗教在人们生活中比重减小有直接联系。
其三,经济的发展对于地名更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在经济加速发展时期,经济活动类地名也在增多,而在国民经济发展停滞时期,这类地名也在减少。同时,经济形式的改变也会导致地名的消失,例如,民国时期的地名“栖流所”因收留流浪人群而得名,后来随着经济发展,不再需要此场所,地名也随之消失;又如“打铁巷”本因区域内有打铁产业而得名,但随着时代变迁,作坊逐渐被工厂取代,匠人被迫离开,地名也随之消失。
其四,地名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城市演变的缩影、历史兴衰的见证。历史因地名而延续,地名借历史而长存。例如,抗战时期历史文化类地名增长数量最多,新中国成立后,以历史文化命名的地名占比达到顶峰,为28.78%。历史事件的发生是此类地名数量增长的主要原因,如为了纪念1939年5月4日日军对重庆进行的无差别大轰炸,重庆市政府将日军投下第一枚炸弹的道路命名为“五四路”。文化是环境的产物,环境是文化的载体和媒介[29],渝中半岛的地名文化与文化环境、人文活动具有高度的关联性。
4 结语
通过对渝中半岛地名的分类梳理,发现重庆地名具有较突出的地域特征,充分展现了重庆的自然山水、历史文化以及人文底蕴。对其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地名存在空间差异性和时代差异性。进一步分析其变迁机制可以得到:自然景观型地名往往受地形地貌、水文特征、动植物资源等自然地理要素影响,并且随着城市建设的逐渐推进数量减少;而人文景观型地名往往受到物理环境、思想意识、政策、经济水平以及历史事件等影响,呈现或增加或减少的变化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在4个时期的变迁中,民国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除建筑工程类、历史文化类、经济活动类以及水文类地名仍呈现增加趋势外,其他类型的地名均有下降。其中,宗教文化类、地形地貌类以及动植物类地名减少明显。而这恰好反映出目前重庆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困境:快速城镇化下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地域特征的老地名不断消亡。
面对该困境,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应该从自然地理、历史文化和风土民俗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深挖渝中半岛具自然及人文特征的地名价值,加强空间环境与历史地名联动性保护,进而与时俱进、结合现代科技,以普通民众更易于接受的方式加以宣传与呈现。
本文以渝中半岛为例,探讨了明清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地名变迁特征、空间分布格局,剖析了变迁机制及其原因,但在时间跨度、覆盖广度、研究深度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希望能在后续研究中得以补充和完善。
说明:本文是在重庆市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项目成果基础上完成的,感谢毛华松老师、陶陶老师在项目过程中的悉心指导,同时感谢项目组成员华思佳、白婕妤的前期协作。
注释:
① 1950 年6 月5 日,重庆市第一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提出《请更改各公共场所及街道名称案》。该议案对部分公共场所、街道地名进行了更改,对重庆的政治、经济、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